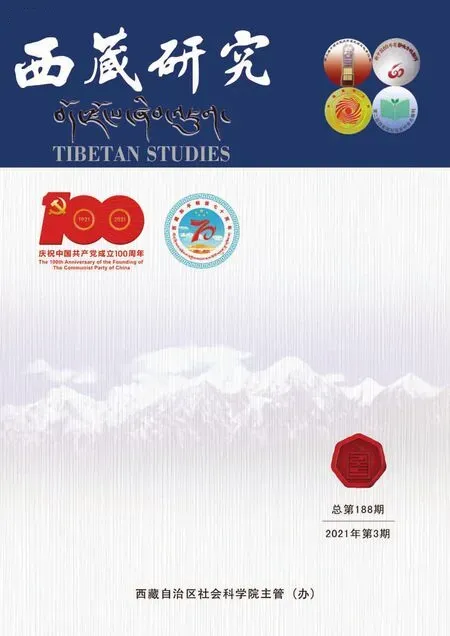论和平解放前后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的影响问题
王小彬 柳欢
(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北京100089;2.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协议第一条即规定要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但是十四世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否认和平解放时期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存在的历史事实,指责中国政府提出“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是无的放矢,甚至连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也以西藏没有帝国主义势力为由,拒绝人民解放军入藏。1949年11月,噶厦致信毛泽东,信中说西藏是“宗教发达兴旺的美妙地方,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力,从未丧权于外国,请不要让(共产党)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1]。一系列矛盾言论的存在使得我们完全有必要厘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用“帝国主义”的表述,和平解放前西藏到底有没有帝国主义势力,有哪些基本事实;如果有,谁是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帝国主义是否包括印度、尼泊尔;哪些事件标志着帝国主义势力被驱逐出西藏。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帝国主义”话语
驱逐“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目标,是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一面旗帜。“帝国主义”表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
19世纪末西方主要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发展蜕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这一鲜明变化,希法亭、卢森堡、考茨基等人对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发展形成了古典帝国主义理论(1)以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一书为标志,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开始形成。其后,希法亭、卢森堡、考茨基、布哈林等人围绕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度阐述。然而,早期的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家霍布森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以及与之相伴的资本过剩”、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等理论观点存在明显缺陷或不足。。然而,相关论述虽具有指导意义但仍存不足。在批判继承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列宁结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实践,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等内容进行了科学阐释,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在列宁领导下,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强制地向东方各民族移植的外国帝国主义,无条件地阻止了他们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剥夺了他们达到欧美已经达到的水平的可能性,……外国的压迫始终妨碍着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应当是推翻外国的压迫。”[2]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近代以来中国的帝国主义问题,深刻意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是造成中国社会沉重灾难的重要冲击力量。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李大钊于1919年在其《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即指出日本所宣称的“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3]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中李大钊再次指出:“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决讲不出公道话来”[4]。通过一系列深度思考和理论阐述,中国共产党科学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并于中共二大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写入党的最高纲领。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帝国主义问题有着深刻把握,其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立场观点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民族群众所进行的“反帝”斗争具有重要引导作用。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在很多著述中都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阐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5]《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6]631-633。通过系列阐述,毛泽东细致剖析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从而更加明确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近代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同时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方针、策略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引。
作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解放前后西藏地区的帝国主义问题成为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考量。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势力依然留在西藏,不仅没有实现如其他省市一样的彻底清除,反而变本加厉地试图阻挠和干预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内部事务,甚至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帝国主义势力相关方面及其影响仍然存在于西藏地方。在此情况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是符合国家整体安全战略和西藏地方利益的势在必行之举。中国共产党从帝国主义理论及革命经验出发,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将矛头直指英美。英美等国渗透到中国西藏事务中,阻挠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解放进程,同时西藏地方的亲帝反动分裂分子以及在藏享有实际特权并曾作为英帝国主义势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印度和尼泊尔两国同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构成了这一时期西藏帝国主义势力的相关方面。
二、和平解放前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及其相关方面
对于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及其相关方面,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经验以及国内、国际统战需要,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应对策略。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人民解放军坚决打击和揭露的主要对象,也是反帝宣传的重点。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走狗”,但出于国内统战需要,他们仍然是可以争取、改造的对象,只要改弦更张,站在爱国的立场上,则既往不咎。印度、尼泊尔是外国在藏特权的实际享有者,但同新中国一样也是深受帝国主义危害的国家,新中国出于争取远东以及全世界和平、团结等现实因素的考虑,总体上对他们采取朋友间的友好态度。同时,坚持坚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和策略,既团结又斗争,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办法解决争端。在涉及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其他问题都好解决。对于他们的在藏权益,中共认为“印度与中国在西藏的商业贸易关系完全可以保持”[7]172,当然,这种商贸关系要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本节尝试就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和相关方面及其各自在藏利益以及中共对他们采取的不同态度和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英美帝国主义势力
在世界殖民浪潮中,中国西藏地方同祖国命运一样进入了西方殖民视野。葡萄牙等西方国家自17世纪起就以传教、通商为名进入中国西藏。在侵略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帝国主义列强中,以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为甚。
1.英国
进入18世纪,英国将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喜马拉雅诸山国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后就将侵略目标转向了中国西藏。通过武力入侵、欺诈勒索等方式攫取了大量侵略权益,严重侵害中国西藏主权,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西藏和平解放进程。
(1)侵害中国西藏主权
英国在中国西藏通过不平等条约于通商、邮电、驻兵等方面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这些特权成为近代英国在华特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
1888年,英国以中国西藏军队越过藏哲(锡金)边界、西藏地方在隆吐山(2)隆吐山为中国领土,后为英印政府所占据。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获得派员入藏的权利,名为探路,实为侵略,这一举动遭到中国西藏地方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中国西藏地方在隆吐山设卡作为拦截。设卡为由悍然侵入中国领土,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遭到中国守军的有力抵抗。然而,清政府及驻藏大臣升泰等一味软弱求和的消极态度助长了英军的嚣张气焰。英国侵略者长驱直入,相继抢占中国西藏地区的日纳、隆吐、则利拉等地。1890年升泰与英印政府总督兰斯顿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藏哲边界,确定哲孟雄(锡金)为英国的保护国,条约中还规定有关通商等问题容后再议。有关问题的谈判结果最终于1893年达成,双方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条约规定开辟亚东为通商场所,英国派员常驻亚东处理商务事宜。凡英国商民在西藏境内与中国商民发生的商务纠纷要由中国驻边官员和英国派驻锡金办事官员面商办理。印茶可以进藏贸易,同时规定五年内不入藏贸易,五年后入藏纳税不得超过中国茶叶进入英国纳税之数。在藏贸易的英印商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得到充分保护。通过上述条约,英国开始获得在藏通商特权。
然而,英国仍不满足侵略所得,企图扩大在藏特权,英军在麦克唐纳、荣赫鹏率领下于1903年冬再次侵略中国西藏,1904年8月3日占领拉萨。在此过程中,英国不顾西藏主权属中国所有的历史事实,阴谋同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沟通,暴露了其试图甩开清政府控制中国西藏的野心。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逼迫下,双方拟订《拉萨条约》,驻藏大臣有泰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主要内容有:承认锡金与西藏的边界;在西藏开放江孜、噶大克及亚东为商埠,以便于双方商民的往来贸易;不得抽税;英国派官员监管各商埠;西藏赔偿英政府750万卢比,分75年偿清,后改为250万卢比,3年付清;英国在下司马的春丕谷驻兵至赔款交清为止;没有英国同意,西藏不得向其他任何外国转让租借土地,不许任何外国派员或代理人进入西藏,道路、电线、矿产等均不许外国享用等。同时,在附约中设专条规定英国政府驻江孜的商务委员在必要时可以前往拉萨与驻藏大臣和西藏官员讨论商务问题,这充分暴露了英国长期以来阴谋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野心,即英国政府企图通过在拉萨派驻代表,以便同西藏地方直接沟通,避开西藏事务交涉过程中中国政府的主导地位。这一尝试自19世纪末即已开始,某种程度上在《拉萨条约》签订过程中实现了其罪恶企图。英国帝国主义势力侵略干涉中国西藏事务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直接更加露骨的阶段。
由于《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加上俄国的干涉,英印政府并未将条约送至伦敦换文,英国政府也未敢公开承认。作为条约一部分的英印总督的声明,包括关于要求西藏地方赔款的数额调整变化,甚至连噶厦也未参与其中,只是由远在印度的英印殖民地方政府单方面操作完成。英国著名的“西藏通”查尔斯·贝尔以及英国历史学家兰姆在他们的著述中都认为这个条约是有争议的。查尔斯·贝尔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中国政府不同意,该条约(指《拉萨条约》,译注)尚未形成定稿,原因是中国政府不承认在西藏享有宗主权。与中国必要的谈判将在远征军返回英国地盘后再进行。”(3)原文:The Convention was not final.for the assent of China,whose suzerainty over Tibet we had recognized,was not gained.The necessary negotiations with that Power had to be undertaken after the return of the Expedition to British territory.[8]兰姆也认为“它(指《拉萨条约》,译注)的有效性无疑是值得商榷的、有争议的。”(4)原文:When he mentioned Lhasa Treaty he wrote:its validity was certainly open to question.[9]在此基础上,中英双方继续谈判,1904年12月,清政府派唐绍仪赴印商谈改约事宜。1906年4月27日,双方于北京签订《北京条约》,共六款,以《拉萨条约》为附约,承认其全部条款,“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政治”“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10]。围绕具体通商事宜,双方又于1908年签订《修订印藏通商章程》。条约规定,英军撤退后,印度边界到江孜一路英国所建的11处旅社由中国原价赎回,但其中一半要以公平价格租与印度;中国将电线接修至江孜后英国可以酌量将由印度边界至江孜的电线移售给中国;中国在各商埠筹办巡警后,英国应将商务委员的卫队裁撤。同时,英国获得了如下侵略权益:可以在各商埠内租地建筑房栈;英国商务委员有会审权以及来拉萨同西藏地方官员的直接交涉权;英印人民在各商埠享有治外法权;还有收发电报、邮政权等。通过这两项不平等条约中国损失了大量权益,但在名义上保全了西藏对外事务上由中央主持交涉的主权。
与此同时,英帝国主义势力还阴谋玩弄文字游戏,炮制中国在西藏只享有宗主权(5)“宗主权”指封建社会中君主对其诸侯行使的支配权力,后扩大到国与国之间,指使他国从属于自己,从而干涉其内政外交的权力。与“主权”不同,“宗主权”关系中的被干涉方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在近代英国帝国主义势力侵略干涉中国西藏的过程中,通过玩弄“主权”“宗主权”的文字游戏,企图否定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的论调。关于主权还是宗主权的争论一直贯穿于20世纪初以来的中英涉藏外交谈判以及中外学者学术交锋的过程之中。1905年,在印度会谈时,唐绍仪对此据理力争,声明中国对西藏享有完全主权,不是宗主权。1906年北京会谈时,中国代表再次坚持这一立场,最终在《北京条约》中既没有提宗主权,也没有提主权。然而,对英国人来讲,似乎代表着中国放弃了主权的提法,助长了英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野心。1907年,英国、俄国在彼得堡签订《英俄协定》,这是一个完全背着中国签订的协议,在国际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篡改成宗主权,为西藏地方反动分裂活动埋下了伏笔。
(2)损害中国领土完整
英国除晚清时期通过划定藏哲边界蚕食中国领土外,还于1913年西姆拉会议期间同中国西藏地方代表私下制定“麦克马洪线”,企图将大块中国领土划予印度,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完整。
附有“麦克马洪线”的《西姆拉条约》未能获得中方正式签字,因为“麦克马洪线”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不仅中方未予承认,“麦克马洪线”在初期也未获得英国理直气壮的认可,自1914年西姆拉会议以来英国政府长期未敢公布。1929年,英属印度外交政治部副秘书长艾奇逊主编的《艾奇逊条约集》一书谈到有关西藏和西姆拉会议的内容时只字未提“麦克马洪线”。由于英国未能满足帮助西藏摆脱中央政府实现“自治”的要求,“麦克马洪线”也未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认可。从1914年“西姆拉会议”到1947年印度独立期间的33年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一直有效地管辖着“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藏南地区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才又逐渐蚕食中国藏南土地,这引起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抗议。南京国民政府及西藏地方“外交局”(6)西藏地方政府于1942年非法成立的“外交”机构,西藏和平解放后并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围绕“麦克马洪线”问题同英国政府进行了大量交涉,终因印度独立、英国帝国主义势力退出印度次大陆,未能获得实质进展。
英国政府殖民时期虽未能根据“麦克马洪线”实现对中国藏南领土的完全非法占据,但其存在为印度独立后中印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严重隐患,并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
(3)干扰中国西藏和平解放进程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英帝国主义势力已退出南亚次大陆的政治舞台,其在藏特权为印度所继承。然而,英国仍不愿完全放弃其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着西藏和平解放进程。英国对中国和平解放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拒绝向西藏地方和谈代表发放入港签证。对于西藏解放事业,中央制定了和平解放的战略方针,尝试采用北平等地的解放模式尽最大可能减少藏族群众在解放过程中的生命财产损失,以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方式解决解放问题。围绕谈判地点形成在两军前线谈判、在印谈判、在港谈判、在京谈判等几种方案,为宣示中国在藏主权,同时避免第三方势力插手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最终决定西藏地方代表必须赴京谈判。西藏地方政府以滞留印度的“亲善使团”代表夏格巴等人为赴京谈判代表,着手双方谈判事宜。然而该代表团最终未能成行,究其原因:其一,西藏地方仍存侥幸心理,试图拖延时间以争取英美等国更多支援。其二,在离印赴港签证问题上受到英国和印度的阻挠。印度政府试图插手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因而希望双方代表在印谈判。英国势力退出印度次大陆后,其在中国西藏、尼泊尔等地区相关事务的处理上往往以印度政府态度为行动指南,因而在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问题上同印度亦步亦趋。与此同时,英国在二战后虽于全球范围内采取战略收缩态势,然而对于中国香港仍不愿放手,故不愿因任何因素将时为其殖民地的香港牵涉在内。在一系列复杂因素影响下,英国在西藏地方代表入港签证问题上屡加阻挠。另一方面,一些英国人在藏帮助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阻挠西藏和平解放进程。西藏和平解放前后,英国人理查森(又译为理查逊、黎吉生)、福克斯、福特等仍留居西藏,为西藏地方顽固对抗中央出谋划策。印度独立后,英国驻拉萨代表理查森转而成为印度代表,继续服务于英国留下的在藏侵略特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帝国主义及其相关方面的恐慌,1949年7月,英国人理查森煽动西藏地方政府制造第二次“驱汉事件”,试图割裂民族关系。理查森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11]32。此外,英国人福克斯、福特受雇为西藏地方政府工作。福克斯建议西藏地方军队在解放军进藏的路口、关卡架上大炮阻击解放军,无线电报务员特务福特在昌都从事特务活动,为西藏地方政府提供无线电等军事、情报服务。
2.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头号帝国主义强国,随着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美国的侵略触角加快向亚洲等地区渗透。与此同时,随着铁幕的拉开,美苏冷战格局形成,阻挠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美国在试图支持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同时,西藏也逐渐成为其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
早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就已尝试插手中国西藏事务。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拉萨途中,美国驻华使节柔克义曾同其接触,然而由于英国的反对态度,美国的相关活动长期未获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又以入藏探测公路为由派托尔斯泰等人赴藏,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后经西藏地方政府请求为其提供无线电设备。总体而言,这一历史阶段,美国虽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一定接触,但活动范围有限。美国对中国西藏的重视程度随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节节胜利而不断提高。解放战争后期,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美国出于冷战背景对抗中国共产党的考量逐渐转变了其对藏政策。1949年1月,美国驻印度大使提议:“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当准备把西藏当作独立之邦来看待”[12]。1949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的露丝·坎培发表评论:“一旦共产党在中国获得胜利,美国不应当继续认为西藏是在中国当局权力范围之内”[13]。据此,美国政府加强了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联系,1949年8月,美国广播电视总台托马斯父子入藏联络,在返回美国后,托马斯父子于美国机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要求美国:“提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指导西藏人的游击战争”(7)参见劳威尔·托马斯:《从西藏回来》,载《纽约时报》1949年10月17日,转引自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在人民解放军兵临金沙江、十四世达赖移驻亚东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及情报部门不断鼓动达赖出逃国外,并允诺为其提供支持。1951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后,美国仍没有放弃鼓动西藏地方拒绝承认协议有效性及鼓动十四世达赖出逃的努力,始终未放弃插手西藏事务,不断与当才活佛、嘉乐顿珠等在境外活动的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交流并提供支持。1956年,中国康藏地区叛乱的爆发使美国的干涉再次活跃。美国加大了对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的支持力度,在塞班岛及美国本土的科罗拉多等地训练西藏情报人员,训练完成后空投回西藏进行情报搜集等破坏活动。1959年,十四世达赖出逃过程中,美国再次提供服务以方便相关人员叛逃。
3.在藏帝国主义势力矛头直指英美的原因
1949年9月,新华社发表社论: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出西藏。1950年8月,中国政务院(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给毛泽东主席的请示报告中,就关于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交流西藏事务再次指出:“我拟于本星期三会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我们很愿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退出西藏”[7]172。可见,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中央政府的“反帝”目标非常明确,将在藏帝国主义势力的矛头直指英美。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新华社的表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方面,英帝国主义势力对包括西藏在内的近代中国造成了沉重灾难,大量攫取在华特权,与此同时还阴谋侵占中国领土,鼓动中国内部分裂,干扰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在解放西藏过程中将美国作为国内“反帝”的头号目标既是对美国干涉西藏事务的合理反应,同时也与当时国际冷战格局及国内解放战争的整体形势息息相关。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地结束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代替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反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14]1245“因此,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14]1358。
由此可见,将英美作为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反帝”对象,是中共中央在对西藏地方及国际国内整体形势综合考量基础上作出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激起了入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的革命斗志,推动了西藏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
(二)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
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及开展反帝斗争的过程中,极其重视帝国主义追随者这一敌对力量,直斥其为“走狗”“反动派”。
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民主革命经验对西藏地方帝国主义势力及其相关方面进行了正确分析,客观认识到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的存在。在有关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的表述中将其称为“反动派”“侵略分子”。目前可见对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的首次清晰描述是1952年西藏“伪人民会议”事件期间毛泽东的指示文件,文件指出:“追究主谋分子,是完全必要和完全适当的。……惟所谓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应即是指鲁康娃(8)时为西藏地方政府两“司曹”之一,在十四世达赖避居亚东期间被任命为“司曹”。“司曹”,又称代理司伦,为旧西藏地方政府官职,地位在噶伦之上。190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留居内地期间首设伦钦(司伦)一职,由夏扎、雪康、强钦(强基、羌勤、锵清)同时担任。夏扎、强钦于1919年前后相继去世后,伦钦一职仅剩雪康一人。后又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侄子朗顿为司伦,1939年朗顿被动离职后,司伦一职暂停设置。1950年底十四世达赖出走亚东时任命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人为司曹(代理司伦),1952年二人被撤职后,司曹一职废止。、洛桑扎西(9)同鲁康娃。、索康(10)指索康·旺钦格勒,为西藏地方索康家族重要成员,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等反动集团的首要分子,亦即过去达扎反动派的重要分子”[15]69。与此同时,这一历史时期,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不仅包括两“司曹”、索康等国内反动力量,部分反动分裂分子在逃至国外后依靠美、印等国的支持继续顽固抵抗,形成了国内国外反动分裂分子内外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联动的总体趋势。
然而,与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坚决反击不同,在对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的处理上大体服从当时西藏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即未放弃对该类人员的争取,始终将其作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如对鼓励策动“伪人民会议”事件的两司曹在将其撤职后仍网开一面,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同十四世达赖谈话时曾提道:“两个司曹现在怎样?在筹委会中能不能将他们放进去,或者将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安排一个位置。开会时他们愿来,我们欢迎,不愿来就算了。总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15]115。对于敌视和平解放的噶伦索康,仍对其开展统战工作,为其在办学筹备委员会等统战组织中安排职务。对滞留国外的十四世达赖的兄弟也欢迎其回国。毛泽东在1955年3月9日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提道:“昨天我和达赖喇嘛谈话时,达赖说他的哥哥在外国不回来怎么办?我说:你不害怕,你回来了,就是对的。他害怕,不回来也可以,他不害怕了,回来也好”[15]121。
(三)印度、尼泊尔
1.印度
(1)从英印政府到印度政府——帝国主义在藏殖民特权的攫取与承续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多次武装侵略中国西藏,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殖民特权。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时,英驻藏代表处摇身变为印度驻藏代表处,前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仍任代表。1947年,黎吉生给噶厦提供备忘录,想要继续让印度继承和保持英国的权益。西藏地方政府认为,印度都已经摆脱了英国的控制,西藏也应该从英国享有的特权下解放出来,于是西藏地方政府要求修改以前晚清时期同英印政府签订的条约,与印度建立新的关系。1947年10月16日,西藏地方政府曾致函联合国,还写信给尼赫鲁,要求归还英印时期侵占的包括大吉岭和锡金在内的西藏领土,印度不予理睬。1948年1月,黎吉生威胁噶厦“印度获得了连同(英国所订有关)印度的条约及其一切权利,只是为了友好,才请西藏回答遵守问题,如果不回答,……将使印度感到不快,会对西藏本身带来危害。”(11)参见《噶厦原外交局档案》,转引自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干涉侵略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西藏当局不顾印度威胁,复文“印度方面应将印藏边境毫无质疑地属于西藏的领土(土地、村落、百姓)归还西藏,……如果归还领土,西藏再将就过去条约之事进行商谈。”(12)参见《噶厦原外交局档案》,转引自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干涉侵略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黎吉生直接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印度继承了(英王)陛下政府对西藏的权利和义务,并将继续恪守存在的各项条约直到双方均愿达成新的协议为止。……如果西藏不遵守英藏条约及印度继承权益的话,印度西藏间现有一切交通来往即将断绝。”(13)参见《噶厦原外交局档案》,转引自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干涉侵略西藏地方斗争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西藏地方当局只能暂时将此事搁置。国民党走后,西藏又提出修约。印度政府派驻锡金代表达亚尔(H.Dayal)又哄骗西藏方面,说共产党很危险,不是谈修约的时机,如果共产党进攻,印度将向西藏提供援助。于是印度全面继承了英国在藏权益和对藏政策。根据条约内容,印度从英国方面继承的特权主要有:英国在亚东和江孜派遣武装卫队的权利;英国建立的十二处驿站;在江孜、亚东、噶大克派驻商务代表;在亚东下司马占有一块租借地;英印商人享有治外法权,等等。
(2)印度政府在藏侵略权益的扩大化与政治干涉
印度独立后,继续扩大在中国西藏的侵略权益,不仅企图保持从英国继承的在藏特权,还罔顾事实通过武力手段侵占中国国土,同时加强对中国西藏地区内部事务的政治干涉。
印度将不丹、尼泊尔和锡金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后,目标直指“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全部中国领土。截至1949年底,印度在靠近“麦克马洪线”东端的瓦弄设立了一个哨所,在达旺地区推进到德让宗。此后一年内印度又增设了二十个哨所[16]。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入昌都,这时印度开始向前推进,企图通过对东北边境特区进行实际控制来造成“既成事实”。“印度政府不想让达旺(Tawang)落入中国人的手中,否则将给中国人在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留下立足之地。因此就在昌都战役之际,印度迅速将印度边防管理处的黑廷(Khating)少校派往达旺,从拉萨指派的负责管理达旺的西藏喇嘛手中夺取了控制权。1951年2月9日,印度国旗首次飘扬在达旺的上空;截至1951年8月,整个达旺地区都处于印度政府的控制之下。”[17]
在推进军事侵略的同时,印度还积极干涉和插手中国西藏事务。1951年4月27日,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到达北京。凯墨和土丹旦达转道印度途中曾于新德里拜见印度总理尼赫鲁,转交了十四世达赖给尼赫鲁的信件,请求印度总理对西藏地方与中央的谈判“给予指导”。尼赫鲁分析了当时谈判的形势,告诉西藏地方代表,估计中共会提出以下三条:一是要西藏回到中国大家庭,不承认这一条没法谈判,国际地图也早已标明西藏属于中国,所以必须承认。二是西藏外交要由中国统一管理,不承认这一条也没法谈,因此也得承认。三是解放军要进驻西藏,承认了这一条,西藏今后就会有很多困难,我们印度同西藏毗邻,对我们也很危险,所以不能同意。他授意西藏代表“要运用巧妙的办法”同中国周旋[11]39。与此同时,印度允许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夏格巴、嘉乐顿珠等在其领土范围内活动。这一历史时期,印度对其支持力度的变化大体以1954年为界。在此之前,印度基于发展同新中国友好关系以及尽可能在与中国政府关于印度在藏特权的谈判中占据优势等方面的考量,对夏格巴等人的在印活动采取限制态度。中印协定签订后,印度所期望的以放弃在藏特权以及承认中国在西藏主权来换取中国政府对其侵略占领中国“藏南”领土采取默认态度的幻想破灭。在此情况下,印度政府转变策略,开始加强同夏格巴等人的交流合作,并为其提供经费等多种支持。1959年拉萨叛乱爆发后,更是收留十四世达赖等西藏叛逃人员,将其作为同中国交流的筹码。
(3)对印度是“友好国家”还是“帝国主义”的策略考量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由于保有从英帝国主义者手中继承的大量殖民特权,印度成为中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的重要相关方面。
印度虽然于1947年获得了独立和自治,但仍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仍然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存在。在成立共和国后,亦未能根据新的共和国的性质,制定出自己独具特色的安全战略,并善待一些较小的友邻国家,而是心安理得地继承英帝国主义势力在南亚的特权和地位,还不时表现出对外扩张的欲望,以至于当时一家上海出版的杂志批评尼赫鲁“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徒,是破坏人民解放运动进展的恶棍,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14)参见《尼赫鲁与英美帝国主义》,载《世界知识》,1949年9月16日,转引自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毛泽东也认为“印度绝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羁绊之下 ”[18]。由此可见,虽然印度不是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国家,但对于印度的帝国主义色彩,中国方面是有充分认识的。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于1949年12月30日宣布承认新中国,是较早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过,印度政府实际的想法是想借此换取新中国对其在藏特权的承认。1950年11月1日,印度驻华大使馆在给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阐明了自己的关切:“印度政府一再明确表示,他们在西藏并没有丝毫政治野心或领土野心,并不会在西藏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寻求任何新的利益或特殊地位。同时,他们已经指出,依照惯例和所签订的协定,在有着密切的文化和商贸关系的邻国之间自然存在着某些权益。这些睦邻关系已经通过印度政府向拉萨派驻全权代表、向江孜和亚东派驻商务代表以及在通往江孜的商路沿线设置邮电所和电报局而体现出来。……印度政府所关心的是,上述这些有益于印度和西藏双方的机构和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至于因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而受到损害,应当继续维持下去”(15)参见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西藏问题与法律准则》,瑞士:日内瓦1959年版,第133—135页,转引自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1—672页。。由此可见,印度政府不寻求“新的特权地位”,但关心的是从英国那里继承的在藏特权,还暗示中国政府承认《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对新中国的外交想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与新中国谋求友好关系,发展自己的大国地位;二是继续保留印度在藏特权。这两个看似有点矛盾的外交思想,实际上正是尼赫鲁大国外交思想的体现。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奉行不结盟政策,也就是不和苏联、美国任何一方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就是要印度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形成以印度为核心的第三种力量。尼赫鲁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让印度成为亚洲的大国,同中国谋求友好关系符合其成为亚洲大国的需要,能壮大自身力量。另一方面,在与中国交好的同时,印度希望继续保留在西藏的特权,以确保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支配地位。印度政府积极承认新中国,就是希望新中国能心存“感激”,继而承认其在藏特权。然而在承认新中国时,印度又有所保留。在关于中国在西藏享有“主权”还是“宗主权”的问题上,不顾中国在西藏享有主权的客观事实,根据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采取摇摆态度,玩弄两面手法。
之所以未将印度列为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源于中国人民对印度民族受压迫命运的深切同情。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6]474。在《论联合政府》中再次强调:“我们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19]其次,对中国政府来说,不直接将矛头指向印度,是我们的一个外交策略。明面上说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就是不想把印度推向我们的对立面。中国政府认为印度作为同样受过压迫的国家,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一面,是能够联合的对象。1951年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为印度国庆举行的招待会的祝词中说:“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7]292;最后,印度历史上与中国西藏在宗教文化、商贸关系等方面有密切联系,且很多特权是在清末民初中央力弱的情况下签订条约导致的,我们希望通过谈判建立新的友好关系,不能像对待帝国主义那样一下子直接废除以前的不平等条约。由此,中国政府没有将“反帝”矛头指向印度,但我们必须承认,印度从英帝国主义势力手中继承的在藏特权使其成为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帝国主义势力的相关方面。
2.尼泊尔
尼泊尔与印度不同。一方面,尼泊尔在历史上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存在;另一方面,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尼泊尔也未免除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命运,1815年廓尔喀(今尼泊尔)被迫同殖民者签订《塞哥里条约》,大量特权为英国所占有,尼外交受英属东印度公司监督。1846年,亲英的忠格·巴哈杜尔·拉纳发动政变,夺得尼泊尔军政大权和世袭首相职位,国王的大权旁落。拉纳家族的独裁统治使尼泊尔不再具有同中国的“藩属”关系,实际上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但相比于印度的完全殖民地地位,尼泊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独立性。
在英国的煽动下,1855年廓尔喀(今尼泊尔)进犯西藏,清政府陷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泥潭,无力顾及,西藏地方战败。1856年西藏地方代表与尼泊尔签订《西藏廓尔喀条约》。根据条约,尼泊尔在西藏有以下特权:西藏每年将向尼泊尔赔偿一万尼币;尼泊尔商民可在藏自由经营,不纳税收;在拉萨派驻代表;在日喀则、江孜等地派官驻兵[20]。据此,尼泊尔开始成为在藏特权的享有者。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尼泊尔的在藏特权已为新中国政府所注意,同时,中国政府还认识到尼泊尔政府受印度政府深刻牵制的现实状况。在此情况下,尼泊尔完全不具有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地位,而是同印度一样成为西藏帝国主义势力的相关方面。
三、驱逐帝国主义及消除其势力影响的历史事实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中国政府为解决西藏的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积极努力,在收回外交权、取消外国在藏殖民特权以及清除在藏反动分裂势力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
(一)收回外交权
1941年,以达扎摄政为首的亲英反动分裂分子把持了西藏的政教大权;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政府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其目的就是要把国民政府驻藏代表机构同英国、尼泊尔等国代表机构一样列为“外国”代表机关,以示西藏是一个“独立国”。西藏和平解放后,这个非法的“外交局”依然在活动。如果不收回外交权力,肯定会影响与印度的谈判,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收回外交权,统一对外权势在必行。收回外交权力也采取慎重稳进的态度。首先,对西藏“外交局”,先“原封不动”。1951年底,外交部派杨公素到达拉萨筹备外事处,进行外事准备工作,但在随后的一年内,“外事处除了自卫、开荒种菜、闭门学习外,无外事可做”。其次,设立外事帮办,再逐渐停止“外交局”的活动。1952年6月8日,周恩来致电张经武:“我方外事处可先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下,设一外事帮办,作为我代表处理外事问题的助手,即行定名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外事帮办,以杨公素担任之,事前应与阿沛商量,并通知达赖,然后公开宣布,公开对外。并按照‘十七条协议’第十四条规定,将西藏地区涉外事宜逐步收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问题,目前仍然采取原封不动的方针,但应逐渐停止其活动。”[21]再次,“架空”非法的“外交局”,其人员的一切对外活动应事先与外事帮办取得联系,并须取得中央代表同意。印方的一切交涉活动必须事先与外事帮办联系,并取得中央代表之同意[22]。最后,争取合署办公,将原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的人员吸纳进外事帮办办公室,转化为国家外事工作人员。中央在统一对外的过程中,一直积极争取噶厦的支持,1952年9月底,张经武邀请全体噶伦就中央统一对外问题进行座谈。同年11月6日,全体噶伦、基巧堪布、译仓(秘书处)、四大仲译、孜康两孜本等齐集张经武代表处,书面答复,同意执行中央统一对外的协议,赞同原“外交局”人员加入外事帮办办公室。1952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正式成立,杨公素为西藏外事帮办,柳霞为副帮办,原西藏地方“外交局”人员与外事帮办办公室合署办公。这标志着“十七条协议”中规定的“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的目标得以实现,也为中外之间通过谈判解决涉藏问题创造了条件。
(二)取消西藏地方的外国殖民特权
尽管中国政府一开始就声明了坚决废除印度在藏特权,但是因为有些情形未明,没有立即进行解决,印度政府依然企图享有在藏特权。根据1908年的《修订印藏通商章程》规定,英印政府得以在中国西藏亚东、江孜等通商地域驻卫兵,但对卫兵人数进行了限制,亚东不超过25人,江孜不超过50人。到1952年,亚东实际驻有卫兵30名,江孜80名,后来又不断增加,此外还雇用了不少当地人员。江孜建有大规模的营房、仓库,储存了大量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这些都是英国侵略西藏时留下的特权。但在1952年冬,印度政府竟然提出要派兵前来亚东、江孜换防,表明要继续享有这种特权。中国政府回复,武装卫队涉及中国独立和主权完整的问题,欢迎撤走,至于换防则不同意。至于由驻锡金甘托克的政治代表前往西藏视察其驻亚东和江孜的商务代表处驿站这个问题,中国政府认为可以同意来,但只是临时措施,不能作为惯例。经过几次交涉,印度发现想要继续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已经不可能。于是尼赫鲁接受潘尼迦的建议,“大方地放弃所有无法得到的东西,而坚持更带根本性且不必一定有条约作依据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23]。随后,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印谈判正式开始。谈判过程中,双方达成默契,对边界问题不谈。中方的策略是,谈判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不成熟的问题包括“麦克马洪线”等边界问题等条件成熟后再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影响解决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在新的基础上确立印度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正常关系。印度则认为不能提边界问题,以免中国利用这个机会翻旧账,以此回避中印之间实际存在的边界问题[24]。
印度在谈判中想尽可能保留在藏特权,1954年1月2日、4日的前两次会谈,印度代表团团长赖嘉文多次强调在西藏的特权是继承英国的,有条约或者习惯形成,不是不平等。这次他列举了印度在西藏的邮电、驿站等多项特殊权益,同时还意图增设贸易中心,对先前的特权予以扩大。印度方面漫天要价,实则虚弱,许多特权要求印度代表团自己也不清楚,无法加以辩护,是完全凭着印度商人及地方官员的要求提出的[25]218。中方代表团团长章汉夫说:“这是一本糊涂账。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哪些商埠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承认……但是,只要不损害我领土主权的,我们可以承认。至于双方来往,必须搞个手续,边民来往也要有正常手续。这样,就必须搞一个中印协定。”[26]
了解印度的意图后,章汉夫在第四次会谈上做了针对性的发言。对印方提出的商务代理、卫队、邮政、电报、驿站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会谈明确表示,凡属特权的必须取消,但按照需要可以保留某些不损害中国主权的传统习惯。最终,中印之间通过12次全体会议的谈判和若干次小组的交换意见后,于1954年4月29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又称《中印协定》),同时进行了换文。协议规定:中国在印度的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印度则在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中国政府同意指定亚东、江孜、帕里为贸易市场,印度政府同意指定噶伦堡、西里古里、加尔各答为贸易市场;规定了朝圣事宜、双方商人来往国境事宜;规定时间内撤走武装卫队;驿站逐步移交中国政府等。至此,印度在中国西藏享有的特权完全被取消,中印之间也建立了新的友好关系。
按照《中印协定》,1954年12月10日开始,中国政府与印度政府的代表就印度在拉萨经营邮政、电报、电话及其设备,还有12个驿站的设备等移交问题进行商谈。1955年3月3日完成全部的清点和估价,双方同意所有驿站的价格为316828印度卢比(折合人民币16.5万余元),中国政府于3月31日将全部款项付清,自4月1日起,上述企业、驿站及其设备全部归中国政府所有。在江孜洪水灾害中,印度驻江孜的武装“卫队”和各类机构人员除11人被救出外,其余200余名官兵、家属都在洪水中丧生,被救生还者不久撤离西藏。驻亚东的65名武装“卫队”人员于1954年10月3日全部撤离。按照协定,1957年6月,印度政府将其在中国西藏亚东地皮交还给中国政府。至此,印度在西藏的特权被完全取消(16)摘自2017年12月10日,在北京阴法唐同志寓所的采访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尼泊尔仍想继续享有其借助英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力量所侵占的在西藏的特权。直到1952年,噶厦“外交局”每年还按旧例给尼泊尔送一万卢比的贡金,被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发觉后予以制止。尼泊尔方面还几次试探中央政府对其在藏特权的态度。与此同时,由于印度对尼泊尔有特殊影响,尼泊尔外交关系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度的控制。中印谈判的完成为中尼两国通过谈判建立新的友好平等关系创造了条件。经过两年的谈判,1956年9月20日,《中尼协定》签订,尼泊尔在西藏近百年的特权也被废除。1957年3月21日,尼泊尔驻江孜的最后3名“卫队”人员撤离,同时其驻拉萨、日喀则的6名武装“卫队”人员也撤离出境,其驻江孜商务代表处于1959年1月撤离江孜。中尼两国的友好平等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使得尼泊尔与西藏长达千里的国界能够处于友好和平状态,从而巩固了我国西南部分边防[25]224。
(三)清除西藏地方的反动分裂势力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在藏反动分裂势力不仅包括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而且包括福特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在藏公民。其中,福特等人在昌都战役期间即被抓获清除。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分子虽顽固对抗中央,但中央及入藏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以发展壮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线,从未放弃对相关力量的争取,并取得一定成效。整个西藏解放时期,除夏格巴(17)指夏格巴·旺秋德丹,时为西藏地方政府四品孜本。曾任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派为同中央接谈代表,滞留印度,从事分裂活动。、当才活佛(18)指当才·土登诺,塔尔寺活佛。和平解放前受中央委托入藏劝和,入藏后暴露反动立场,后长期滞留国外从事分裂活动。及嘉乐顿珠(19)解放后长期滞留国外从事分裂活动。等少部分反动分裂分子叛逃至国外,绝大多数仍留藏活动。至1956年康藏地区叛乱爆发,反动分裂分子伺机而动,开始进入活跃期,不断制造袭击解放军等反动事件,给中央及入藏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的工作带来极大挑战。1959年3月,叛乱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发布《在西藏平叛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其中指出:“西藏噶厦政府已经撕毁协议,叛变祖国,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局势迫使我们提前同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分子进行决战,进行一次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平息叛乱的战争”[27]203。在平息叛乱的同时,中央仍秉持宽大为怀的统战政策,“对捕获的叛乱大小头子,除个别罪大恶极、非判处死刑不足以平民愤者外,一般仍判处劳改”[27]205。“对于俘虏和其他放下武器的敌人,一律不许报复杀害”[27]206。至1962年3月,西藏全区平息叛乱结束,除部分人员逃至境外继续从事分裂活动,西藏境内反动分裂分子基本肃清,帝国主义势力通过境内人士干涉中国西藏地方事务的历史自此结束。
四、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西藏地区的持续影响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在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及入藏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下,虽实现了取消西藏地方外国特权、清除西藏地方反动分裂势力等胜利,然而,帝国主义对华以及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影响仍继续存在并延续至今。其一,美、印等国继续支持叛逃至国外的西藏反动分裂分子;其二,西方国家延续其霸权思想,在国际舞台以西藏“人权”作为阻挠中国崛起的手段;其三,由英国帝国主义势力非法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对当代中印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一)继续支持境外西藏反动分裂分子
1959年西藏平叛开始后,部分反动分裂分子冥顽不化逃至国外同阿乐群则(20)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伪人民会议”组织者。等早期外逃人员联合继续从事反动分裂活动。为在中印领土争端等问题上争得谈判筹码,印度成为西藏反动分裂分子开展对抗的大本营,先后在穆索里、达兰萨拉为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提供工作场所。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失败后,印度公然撕毁同中国达成的包含“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大了对西藏分裂分子的支持力度。同时,十四世达赖的出逃使美国国务院、中情局实现了其长期追求的目标。在美国支持下,西藏反动分裂分子于尼泊尔木斯塘建立起偷袭西藏的前沿基地。仅1963年6月,囤聚木斯塘的反动分裂分子打死解放军干部数人,抢走牛羊上千只。在中美关系改善后,中情局停止对木斯塘反动分裂分子的经费支持,印度接管了之前由中情局资助的很多工作,直到1974年该基地撤销。此外,美国等国家罔顾历史事实,多次邀请西藏反动分裂分子头目作为其政府的座上宾,公然为西藏反动分裂分子张目,持续为境外反动分裂分子的反中国行径提供各种支持。
(二)在国际舞台打西藏“人权”牌
1959年西藏上层叛乱全面爆发后,平叛民改工作同时进行,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获得了千百年来旧西藏从未拥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西藏历史翻开崭新一页。然而,美国等国不顾新中国在西藏实现的巨大人权成就,悍然将“西藏人权问题”这一伪命题推向国际。20世纪70年代前后中美关系缓和,这一问题被暂时搁置。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人权外交的开展,中美关系热度的回落,“西藏人权问题”再次为美国所利用。1987年12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修正案》,对中国西藏人权横加指责,随后其他西方国家议会也纷纷效仿,通过指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的议案。2003年5月8日,美国国会的一份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总统报告无端干涉中国内政,敦促中国政府尊重藏族的人权和自由。2020年12月27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2021年综合拨款法案及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法案”,再次对西藏人权状况进行歪曲抹黑和无端指责。由此可见,美国等国无视自身殖民侵略他国的历史及在种族屠杀、歧视等方面糟糕的历史记录和人权状况,以“西藏人权问题”这一伪命题作为打压中国的手段,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虚伪、傲慢和双重标准。
(三)“麦克马洪线”的困局
1914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外交人员麦克马洪阴谋炮制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企图将数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藏领土非法占据,并将这一殖民遗产留给印度。印度独立后,依据“麦克马洪线”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最终占据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全部中国领土。此外,根据“麦克马洪线”,在中印边界中段、西段也形成了领土争端。这些争端成为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数十年来中印边界冲突的原因,深深影响着中印良好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五、余论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环,也是对中国对藏主权地位的明确昭示。和平解放的实现成为西藏历史性变革的崭新起点,为西藏各族人民解放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达赖集团及其支持者不顾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忽视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赢得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局面,在国际上炮制中国共产党“侵略”西藏、在西藏进行“种族灭绝”等荒谬论调。这一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国内外反华势力试图以所谓“西藏问题”干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梦的实现;另一方面,对西藏和平解放相关历史问题的阐释不足也为敌对势力的错误言论留下了滋生空间。有基于此,加强对西藏和平解放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国内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西藏研究的重要方向。
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有关问题目前在两个重要方面尚存在认识不足。其一,对于和平解放前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问题存在认识模糊,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构成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合理性基础。然而,十四世达赖及其支持者围绕西藏是否有帝国主义势力等问题同国内研究者长期抵牾,关于谁是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哪些事件标志着帝国主义势力被驱逐出西藏等相关问题国内研究者也未能充分理清。本文的研究工作希望能够对此问题进行一定解答。其二,对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时间及其标志国内外研究者也存在争议。对于该问题的正确认识事关能否对整个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全部工作形成正确认识。目前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一)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二)1951年和平协议签订十四世达赖返回拉萨后,西藏地方政府经过复杂的程序讨论后,最终决定承认协议,并以十四世达赖的名义致信毛泽东。西藏地方政府对和平协议的确认使得部分研究者以此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实现的标志;(三)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印、中尼西藏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外国在藏特权的取消以及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这一和平解放目标的实现。(四)也有学者以1959年拉萨上层叛乱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开展的平叛民改工作的完成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实现的标志。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时间及其标志构成了西藏和平解放研究亟待解决的模糊性问题之一,我们把问题与思考提出来,求教于诸方家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