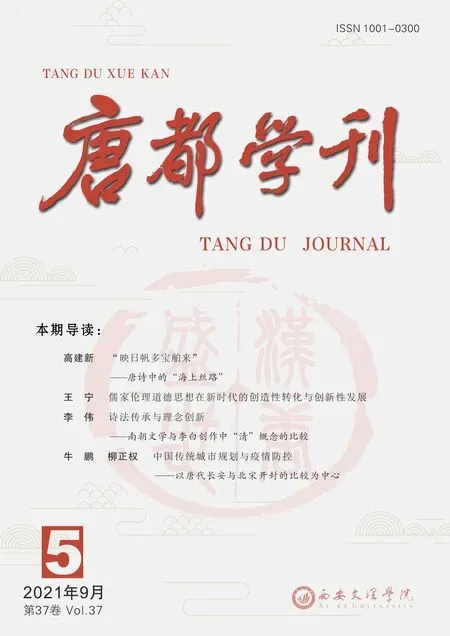诗法传承与理念创新
——南朝文学与李白创作中“清”概念的比较
李 伟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14)
李白创作的审美艺术风格是“清新明快”,这已成为学者共识。同时他也以“清”来评价和规范其他作品,因此对“清”的认识理解便构成了李白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如此推崇具有“清”的风格的诗作且身体力行,绝非凭空产生而应该是渊源有自的。通过对其诗文的考察总结,李白的这种创作倾向和南朝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那么以李白诗文中体现的“清”的概念为中心,与南朝文学及文论中有关“清”的认识进行比较,作一番文学史的溯源,便显得很有必要[注]从中国古典文论的角度,深入对“清”的概念进行深入阐释的论文,可参见蒋寅先生的《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之《清:诗美学的核心范畴——诗美学的一个考察》,中华书局2003年版。。
一、李白诗学思想之辨析及其与南朝文学之关系
在正题开始之前,需要澄清李白诗学思想中“清”的问题,尤其是他创作与理论主张的矛盾。首先是关于“清”的概念使用问题。本文中的“清”是指运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的概念术语,当然对其哲学学术思想上的认识也有涉及,至于其他内容和用法则溢出我们的讨论范围。另外,李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树存在着相悖离的倾向,这里我们要去伪存真,以李白的创作为基础,兼顾其理论主张,发掘其真正的文学思想,还李白所认识的“清”的概念以本来面目。
按照文学史的一般规律,作家的创作是对其理论的实践,理论则是创作经验的提炼和升华,理论和创作应该保持高度一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却出现了一些特例即创作与理论相悖离,李白就是其中的代表。那么这就必须辨清原由,做出取舍,寻找李白真实的文学思想,为进一步的讨论打下基础[注]关于文学史上文论与文学思想的问题,可参见罗宗强先生《李杜论略》中的相关论述,而其研究成果则以《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为代表。他对“文学思想”问题的开拓成为这方面最早将理论付诸研究实践的学者。参见拙文《李白〈古风〉其一再探讨》,收入《中国诗学》第1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就现存的资料来看,李白的文学理论认识大都散见于其创作的诗辞文赋中,缺乏系统的总结。首先,李白的《古风》其一历来受到文学史家和诗论家的重视,被认为是李白文学思想的纲领性认识,这其中表现出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复古意识,而且对《诗经》以后的文学发展史的认识有诸多偏颇之处。李白把“雅、颂”视为正声,自此衰落后,文学再未达到此高度,“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在李白看来,不仅以“哀怨”为特征的《离骚》等“楚辞”文学很难企及“正声”传统,而且自汉代以降文学就处于大倒退中,毫无可取之处。“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李白认为,扬雄、司马相如的汉大赋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股颓波浊流,对以后的文学发展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建安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更是不足称道,这样说来,李白几乎把《诗经》以来的文学史一笔抹杀了,《楚辞》、汉大赋、魏晋五言诗等在我国文学发展中的贡献被全盘否定。其次,与《古风》其一的认识相表里,李白对诗歌形式的看法也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载:“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这里李白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学观定位于“将复古道”之路上,在诗歌形式上极为推崇四言,而把五言和七言诗视为“声调俳优”之作加以贬抑,因此这真可算是《古风》其一观点的注脚。
但是把李白其他关于诗歌的认识和以上复古思想加以对照,我们就会发现李白的理论认识本身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而且焦点就集中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认识上。一方面,他强调“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另一方面却在一些诗歌中称赞魏晋南北朝的诗人。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游敬亭寄崔侍御》:“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去数百年,风期宛如昨”;《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遐谢朓》:“独酌板桥浦,古人谁可征?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由此可见李白对谢朓推崇备至,同时《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说明他对江淹和鲍照的评价也是颇高的。所以在李白的许多短小评论中,六朝文学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不仅在理论评价中有这样的矛盾,李白在其创作实践和理论认识上更显扞格难通。据《本事诗》的记载,李白把四言诗作为诗歌中表现“兴寄深微”的最佳形式,但是现存李白的诗作中只有两首四言诗《上崔相百忧草》《雪谗诗赠友人》,而且写的质木无文,并不成功。李白写的最好的诗歌还是乐府歌行体诗,大部分是五言和七言诗。同时在创作中模仿六朝诗歌的作品也很多,象他就特别欣赏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那一浑然天成的佳句。《赠从弟南平太守之谣》云:“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送舍弟》:“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鲍照的诗歌也是李白经常学习的对象,《行路难》其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用意亦与鲍照《拟行路难》十八“莫言草木委霜雪,会应苏息遇阳春”近似,其对南朝乐府的“吴声”“西曲”也有深入学习。
通过以上分析,李白的复古理想只是他文学理论的极少部分,在他对六朝文学的大多数评论以及创作实践中,称许和学习占据了主流的倾向。关于李白文学思想中的复古意识,应该是有其产生原因的,那就是他把政治代替文学,对文学的评论其实表达的是心目中的政治理想[注]关于李白《古风》其一文学思想的内涵,可参见拙文《李白〈古风〉其一再探讨》,收入《中国诗学》第14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像这样的情况,文学史上不乏其例。而且一个诗人文学理论思想的形成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政治因素是其中之一。李白在盛唐气象的激荡下始终洋溢着文人特有的积极用世精神,《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云:“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所以这种宏大的政治理想也会不自觉地渗透到李白的文学理解中,使得他的文学理论被夸张和歪曲而与其真正的文学实践相背离,很多评论也失之偏颇。罗宗强先生早在《李杜论略》曾指出:“事实上创作实践才是他的文学思想的更为直接、更为真实的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学主张也是一样,它不仅反映在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里,而且更充分、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在当时的创作倾向里,只根据当时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去判断当时的文学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全面而广泛地分析当时的创作倾向。”[1]受到这种认识的启发,李白的创作实践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对六朝文学的认识决非“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句可以代替,李白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经验与六朝文学特别是南朝文学密切相连。
至于具体分析李白的创作与南朝文学的关系,可以有很多途径,“清”的艺术风格便是其中之一。李白经常以“清”和带“清”的词语来表述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如在《古风》其一中强调“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把“清真”作为最高的审美追求。《上安州裴长史书》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李白在此以己文对诸人之文,激赏自己“清雄奔放”的艺术风格,而且评论他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推崇自己之意不言自明。同时他也以“清”极力称赞别人的佳作,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泽畔吟序》:“崔公忠愤义烈,形于清辞。恸哭泽畔,哀形翰墨。犹《风》《雅》之什,闻之者无罪,主之者作镜。”不仅李白对此有自觉意识,后人的研究亦多重视此处,稍后于李白的杜甫称赞白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论李白曰:“宏拔清厉,乃其诗歌也。”明代诗论家李东阳曰:“太白天才绝出,真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种评价与李白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翻阅李白的作品,他以“清”评价魏晋六朝特别是南朝文学甚多。如《王右军》:“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送储邕之武昌》:“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也是来自南朝时人对谢灵运清新自然诗风评价的启发。因此除王羲之是东晋人外,其余诸人都是南朝文学的代表诗人。因此南朝文学成为李白文学思想中“清”的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
二、南朝文学视阈中“清”的思想文化内涵
自从曹丕《典论·论文》中“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至”开始,以“清”来评论文学创作成为一时风气,到南朝时期尤为炽烈,这与魏晋时期由清谈发展而来的玄学思想密切相连。
“清”是南朝文学评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大到文化形态的判定,小到具体诗人及作品风格的评价,从创作实践到文学理论,无不如此。要解决“清”这一概念所代表的内容,必须了解当时使用针对的对象、含义、倾向和思想背景。根据对南朝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的统计,《文心雕龙》中使用“清”评价文学有30次,《诗品》中也出现了15次之多。而且《诗品》的宗旨是评价历代五言诗人优劣,将112位诗人分为三等,以“清”而论的人数,上品11人中有3人,中品39人中有5人,下品72人中有5人,因此以上中品出现的比率为高,这些诗人代表了各个时代的最高成就(在其《诗品序》中还出现两次)。这时“清”大多是与其他词语连用,如“清绮”“清铄”“清切”“清省”“清英”“清和”“清峻”“清畅”“清雅”“清巧”等。由此可见,“清”在南朝时期的文学生活中被广泛应用,是当时重要的评价标准。除使用数量多之外,受到此风熏染的诗人都是一时之选,在诗坛上具有重要地位。如《颜氏家训·文章》评何逊诗:“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2];《诗品》评沈约诗:“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3]310;《梁书·吴均传》评吴均诗:“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诗品》评范云诗:“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3]310;《中说·天地》中唐初李百药评自己的学诗心得:“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4],特意指出沈约“刚柔清浊”的“四声八病”说。另外有的诗人虽未明确有这方面的记载如谢朓,但是他属于“永明体”的代表,与沈约过从甚密,而且其诗与何逊作品相似,故而他的艺术风格属“清”的范畴之列。
当时以“清”评价文学,大多含有称赞颂扬的意味,属于褒义词。如《文心雕龙》中具有“清”的风格的作家包括贾谊、张衡、曹丕、嵇康、张华、潘岳、陆云等,并在文学的发展中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明诗篇》中,将张衡的“清典可味”和“古诗十九首”并提,而“古诗”本身也具“清音独远”的特征[注]参见《诗品》。,因此崇“清”之意甚明;论嵇康时:“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强调正始诗歌唯“清峻”的嵇诗和“遥深”的阮籍最佳;《时序篇》以“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总结西晋一代文学,论东晋文学时单独拈出简文帝的“渊乎清峻”加以赞扬,可见具有“清”的特征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被屡次褒扬。当时的“潘陆优劣之争”也可见出南朝时人对“清”的风格的推崇。对于西晋最著名的两位诗人潘岳和陆机,《世说新语·文学》载:“孙兴公曰:‘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5]327。《诗品》记载谢混的论述:“潘诗烂若锦绣,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通过比较,时人大多认为潘岳的成就更高。而潘岳之文“藻清艳”[注]参见《文选·籍田赋》注引臧荣绪《晋书》。“清绮绝世”[注]参见《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晋阳秋》。,可见潘美于陆的重要原因就是其文具有“清”的风格。当然此时也有极少的不同意见,《颜氏家训·文章》载:“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者,恨其每痛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其实颜之推和刘孝绰欣赏典正雅润的文风,以雍容为特色,何逊的诗歌当然不合他们的审美趣味,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代表当时文学发展方向的是以沈约为主的“永明”体诗人,而他们及萧绎对何逊诗是称赞和喜爱的。同时在《文心雕龙》总结创作经验的篇目中也屡次推崇“清”的要求。如《养气》:“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风骨》:“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能准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定势》:“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声律》:“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章句》:“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才略》中举了许多具有“清”的特色的作家事例,包括“议惬而赋清”的贾谊、“洋洋清绮”的曹丕、“奕奕清畅”的张华、“循理而清通”的温峤等。因此“清”所代表的文学特色是南朝大多数诗人具有的,也为时人所欣赏,反映了文学发展的方向。难怪魏徵总结南朝文学时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文华者宜于咏歌”[注]参见《隋书·文学传序》。,希望能吸收南朝的“清音”优长以促进未来健康文学样式的形成。
“清”在南朝时多指明确简约之意,《世说新语·文学》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5]264。褚、孙在此区分了南北学术的不同特点,孙安国指出了南方所重的“清通简要”,这种文化的特长与上文的分析不谋而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清”的含义。当时还有关于南北文化分野的讨论,如《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的一段话,他指出“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北史·儒林传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支氏之意说南人的学术是以小见大,正与《北史》的“约简”相合。所以“清通简要”之“清”亦是约简之意。通过考察,文学中的用法亦如斯。《文心雕龙·诔碑》:“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此“清”即是“该而要”的简约。《奏启》:“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清”在这里指“文而不侈”,即有文采但不繁杂淫靡,还是简约之意。《熔裁》:“士衡才优,而缀刺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以“繁”“清”相对,则此“清”指“繁”的反面,即简约。其他的例子还有不少,如《颂赞》:“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章表》:“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书记》:“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会其才,炳蔚以文其响”。与陆机相比,潘岳的“清”指其文写的清新流畅、简约自然,最擅长的是哀诔之文,这种文体以该要雅泽为特色,语言精练。由此可见,南朝时人所说之“清”是指简约明确。
在明确了“清”的含义之后,还需对其使用对象有一认识。任何术语在使用时,都有较为集中的对象,当然这种使用受到时代思维的局限。通过整理归纳,这时“清”的使用对象集中在下列一些方面:语言词汇,如《世说新语·文学》载:“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颜氏家训·文章》:“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隋书·经籍志》:“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曼藻,思极闺房之内”[注]魏徵等著《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2卷。;《文心雕龙·章句》:“句之清英,字不妄也”[6]570;《颂赞》:“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6]158;《诗品》评班婕妤:“《团扇》短章,词旨清捷”;评戴逵:“安道诗虽嫩弱,有清上之句”,虽是评价前人,但反映的是钟嵘的认识。音韵格律,如《文心雕龙·声律》:“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中说·天地》记载李百药的诗学渊源:“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诗品序》:“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流通,口吻调利,斯为足矣”[3]112-113;《诗品》评“古诗十九首”:“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文心雕龙·才略》:“《乐府》清越”,指的是《乐府》歌诗音韵流畅、悦耳动听。一种艺术风格,包括文体和诗人,如《文心雕龙·宗经》:“风清而不杂”;《定势》:“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诏策》:“晋世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铭箴》:“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其例甚多,兹不赘述。
因此“清”所修饰的对象大多是文学的细节问题,这与当时处于文学觉醒期相一致,很多本质问题刚开始讨论。“永明体”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这标志着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对音韵格律有了自觉意识,而且其主要倡导者沈约曾提出“三易说”,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注]参见《颜氏家训·文章》。,这都是为文的基础和细节,并没有很深的道理,但在此时提出已属难能可贵。钟嵘《诗品》中的“自然英旨”说的确很好,但他在具体操作时也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前有反对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的不良倾向,这与沈约的“易见事、易识字”一致,要求创作时用典不宜过多,以免影响清晰流畅的文风;后有关注文学的音韵格律,要求“清浊通流,口吻调利”,与沈氏“易读诵”相仿。而这些要求与“清”所标示的文学特征类似,它指语言简约精练、音韵和谐流畅,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达到谢朓提出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注]参见《南史·王筠传》。。此外,“清”在这时已是构成文学作品本质性的重要标准,《文心雕龙·明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虽然刘勰强调四言诗为“正体”,但其衰落在南朝已是不争的事实,联系钟嵘《诗品序》的“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那么此时真正代表文学本质特征的是五言诗,《定势》:“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也把“清”作为这几种美文学体裁的特征,可见这已是共识。
通过以上分析,南朝时期对“清”所代表的文学意义已经有初步认识,成为时人普遍欣赏的艺术风格,也是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审美特征。尽管对它的运用和认识只是文学作品的语言、韵律和艺术风格之一种,但是从其受关注的热烈程度,我们明显可以断定“清”所凝聚的思想内涵反映了南朝向隋唐文学演进的趋势和文学本质特征的发展方向。
三、李白诗学思想中“清”的内涵创新
就文学自身发展规律而言,南朝的成就要远远领先于北朝,因此唐代文学必然是站在南朝文学的基础上来寻求进一步的突破,初唐时期沿袭南朝末期宫体诗风的状况就是明证,当然这其中也会孕育变革和发展。“清”的演变轨迹与此文学背景息息相关,当盛唐文学和李白诗歌达到中国诗歌史的顶峰时,“清”所代表的内涵就有了质的飞跃,这其中以李白的认识最为深刻。
《唐音癸签·法微(一)》曰:“诗最可贵者清。然有格清、有调清,有思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储、韦之属是也。若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俗。王、杨之流丽,沈、宋之丰蔚,高、岑之悲壮,李、杜之雄大,其才不可概以清言,其格与调与思,则无不清者。魏文帝《典论》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其论七子诗与文章,未尝不并重清云。”[7]这里把“清”作为盛唐诗歌的主导艺术风范,可谓灼见。不论是王孟之清新自然,还是高岑之慷慨悲壮,抑或是李杜之雄浑博大,虽然在细微处有具体的不同,但都可以“清”来总结当时最核心的文学风格。作为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李白诗歌中的“清”要高出众人之上,“格清”“才清”“调清”“思清”是就文学的才气、韵律、思想、格调等具体问题而言,可李白是“其才不可概以清言,其格与调与思,则无不清者”,说明其诗表现的“清”也有上述的风格,但同时又超越了那些具体范畴而有了不可言说却实实在在的境界感,是自然而然、无心自通形成的。
李白对“清”的风格的推崇,在理论中有所表述,但更多地是通过其创作实践呈现出来。在《古风》其一中梳理了《诗经》以来的文学变迁,提出要想改变日益衰颓的文学风气,必须“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把“清真”作为由以往文学实践得出的审美理想加以肯定,指导当时的创作。同时把“清”的内涵上升到“自然”的高度,作为最高的美学风范,《古风》三十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8]133可以说本诗为其一的“清真”做了很好的展开和注释,那就是诗歌要写的天真自然,像西施的美貌那样,出自本色;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虚伪地模拟他人,矫揉造作,是可笑而不足取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仅再次申明主张,而且暗含了自己的思想渊源。南朝时鲍照赞美谢灵运曰:“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李白的认识就由此而出,在创作中也对谢诗很推崇,因此这时的李白把“清”的风格与“自然”的审美理想联系起来。
首先,李白诗中表现的“清”与南朝时的认识有继承,如语言、用典、韵律和思想感情的表达等,都有淋漓尽致地呈现。李白诗歌中出现最多的典故是《庄子》的“大鹏”意象和“功成不受赏”的鲁仲连。《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8]312还有一篇《大鹏赋》,李白始终把《庄子》中自由自在的“大鹏”视为自己的精神象征,在运用此典时丝毫不隐瞒自己的雄心壮志,写的清楚明白,使用得贴切恰当,把自己的精神追求形象地展现出来,而且在临死时也以“大鹏”的衰落自比。鲁仲连的典故出现的也很多,《古风》其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8]101。鲁仲连“却秦振英声”“意轻千金赠”,李白将之视为自己的“同调”以表达“澹荡”的人生哲学,可谓深得古人用心。用语不多、恰如其分地表现思想,从用典就可看出李白诗中的“清”的特色。
其次,在语言和韵律上,李白的诗歌高度凝练纯净,看似口语般通俗易懂,却是回味无穷,这是根据“清水出芙蓉”的要求提炼出的诗化语言,读来珠圆玉润,音韵和谐流畅。“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十字将个人的心灵愁绪清晰形象地呈现出来;同为写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不仅形象,而且音韵宛转,有回环往复的流动感,这让读者在欣赏时不禁心有所动。而且李白的诗之所以流传甚广,其原因就是语言明白如话,韵律流畅,读来朗朗上口,如《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些诗歌没有生僻的字词,意思简明易懂,正反映了“清”所指的语言音韵特点。而且李白创作最多的是乐府诗,吸收了南朝“吴声”“西曲”的艺术特色,语言清丽明快,情感真挚朴实,有极强的韵律感,如《子夜吴歌》《采莲曲》《长干行》《清平调》等,胡适《白话文学史》说:“他是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的,所以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自然”。由此可见,李白诗歌的“清”与南朝文学存在着不少的联系。
再次,李白是一位极富理想色彩的诗人,追求天真、自由、傲岸的人格风骨,从来没有要刻意隐藏自己的思想情感,反而时刻以充满青春式的激情敞开自我的心扉,书写属于自己的豪情壮志,所以李白诗歌情感完全是爆发式的,犹如滔滔江水,倾泻不尽,仿佛只有这样才是他最佳的情感表达方式。因此他的诗情像排山倒海的激流涌动无尽的生命力,给读者一个完全坦诚、清晰的“李白”形象。如《蜀道难》的荡气回肠、《将进酒》的激情澎湃、《行路难》的坚定执着等,这些最有代表性的诗作无不洋溢着李白式的情感涌流,这种明确的情感表达也是“清”的内容之一。
最为重要的是,李白把“自然”这一最高的审美理想充实到“清”的内涵中,从而做到了钟嵘试图想做而未达到的境界,这就全面超越了南朝的诗学理解,将“清”这一极具内涵意蕴的概念提高到了崭新的美学境界,当然这主要体现于李白的诗歌创作上。既有“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道家式的超凡脱俗,还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儒家式的积极进取;不仅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宛转低回,还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满怀,抑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岸独立,李白的诗歌总是如胸臆般自然流出,抒写的就是他那飘逸潇洒的丰神和不可遏抑的生命强力,每首能激起欣赏者共鸣的好诗都是李白真正的心声,表达的都是他的真性情,丝毫没有刻意的雕琢,也没有欲说还休般的矫揉造作。读李白的诗,欣赏到的是畅快淋漓的情感渲泄和精神激越,他完全把自己的所知、所想、所感清楚无遗地呈现在世人眼前,难怪任华论其诗:“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所以当“自然”与“清”联系起来时,“清”的意义就具有理想境界的价值,真是有“斯人清唱何人和”的喟叹,此种涵泳不尽的诗情是最自然的声音,恐怕后人再难以企及,所以明代王世贞说李白的诗“以自然为宗”,“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赵翼说:“工丽中别有一种英爽之气,溢出行墨之外”,此即自然之气。李白“清雄奔放”之“清”与南朝认识的最大不同正在“自然”涵义的引入,这是最高的审美理想境界。
对“清”在文学中的认识是随着不断创作来丰富和发展的,任何文学现象都要经历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就“清”来说,南朝的认识尚浅,反映的是文学创作的细节问题,而且“清”大多与别的词连用,意涵指向尚不确定,说明这是一个认识相对较低的层次阶段。但毕竟时人已对“清”的风格日益取得认同,折射出未来文学思想的发展方向。顺着南朝开辟的道路,李白通过创作将“清”的认识带到了非常深入的境地,既包含了对南朝认识成果诸如语言、音韵的继承,更有用“自然”的审美理想[注]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参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日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来提升其价值意义的巨大创新,这正是文学发展的辩证过程;同时体现了对李白诗学思想的理解是要在文学史的纵向进程中来完成,他的成就是以南朝文学为基础的,我们从对“清”的比较中可以深刻感受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