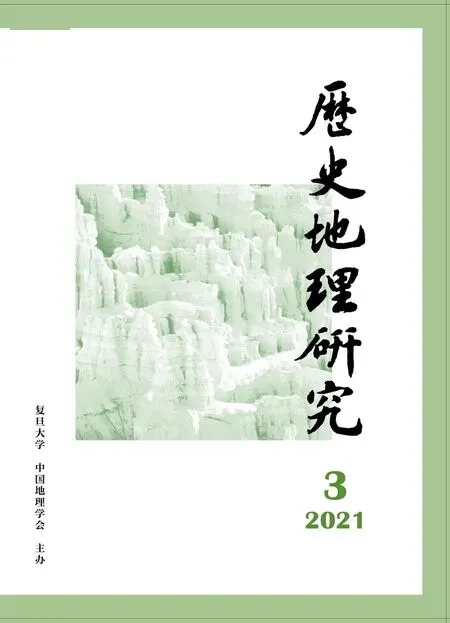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
辛德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历史地理学,在中国是一门既有悠久历史渊源又完全基于西方现代学科理念而发展起来的学科。所谓“悠久历史渊源”,是指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随着这一学科在中国的普遍发展以及对相关学科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譬如所谓环境史等),回顾这一学科在中国创立和发展的过程,既是对学科创建者的纪念,也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在前辈学者奠定的学术基础上做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研究。
关于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这一问题,从目前所见相关论述来看,学术界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这主要涉及如何看待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性质的问题。
众所周知,很久以来,颇有一些学者,把禹贡学会的成立和《禹贡》半月刊的创办,看作中国业已建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标志,至少当时业已开启了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这一派学者特别强调,《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名称“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直译为中文便是“中国历史地理”,而这种情况清楚表明新式历史地理学已在中国正式诞生。
核诸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到,当时不仅是《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刊名,一些大学地理系的教材在讲述地理学的构成时也都引入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然而,若是循名责实,审视《禹贡》半月刊上刊载的学术论文,审视禹贡学会成员和20世纪30年代其他中国学者的所有研究论著,就可以看到,当时并没有实现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西方新式历史地理学的转变。
这些论著,大多还是局限在传统沿革地理的范畴之内,甚至根本没有人明确提出过从事新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张。当年禹贡学会所规划的研究内容,只是编制历史地名词典、绘制历史地图等,因而并不能简单地用其英文译名来判断实际的研究内容。如同禹贡学会的骨干成员侯仁之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在以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这个名词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1)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页。
据侯仁之先生介绍,在禹贡学会活动的20世纪30年代,欧美世界真正的“现代历史地理学”,也就是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也还刚刚兴起不久。(2)侯仁之:《历史地理学概述》,《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第44—49页。须知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之作,亦即英国学者达比主编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在禹贡学会建立两年之后的1936年才出版。因而,即使当时确实想要全面采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的学科理念和方法,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了解到欧美历史地理学的实际进展状况,也就很容易理解,由于当时中国学术在整体上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滞后程度,以及沿革地理在中国的深厚传统所造成的惯性,以禹贡学会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所做的研究在总体上未能逸出于沿革地理的范畴之外,这本来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按照侯仁之先生的看法,这种基于西方现代学科理念生成的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应该是在1949年以后才形成于世并逐渐发展壮大的。(3)侯仁之:《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第7—16页。对此,史念海先生也持相同看法。(4)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河山集·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55页。下文即以此认识为基础,以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三位开山大师为核心,概括叙述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创立过程及其初期发展状况。
一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建过程中,侯仁之先生的贡献,无疑具有转折性意义。1946年秋,侯仁之先生赴英国利物浦大学,亲炙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夏,侯仁之先生以《北平历史地理》一文,获取博士学位。后其随即回国,在燕京大学任教,之后随燕京大学转入北京大学。
不管是对侯仁之先生个人,还是对中国学术界,这都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一段值得庆幸的经历。侯仁之先生这段经历,意味着中国学人得以直接学习和接受了国际上最前沿的历史地理学学术理论和学术方法,并迅速将其引入中国。
1950年7月,侯仁之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的文章,针对这一年春季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历史系选修课程“中国沿革地理”对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看法。(5)侯仁之:《“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第3—6页。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先生以其在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中所做过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为基础,以首都北京的历史城市地理问题为例证,既有崭新的学术视角和深厚的研究力度,又有具体、典型的切入点,清楚阐述了西方新型历史地理学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的联系和区别,从而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
首先,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侯仁之先生在主张把大学历史系中列为选修课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更名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同时,还明确提出,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不能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是要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都应包括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内。
在研究方法方面,侯仁之先生认为,新型的历史地理学既然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就自然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相比,在着眼点上,这种新型历史地理学首先需要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历史资料。与之相应的具体方法,主要是要优先考虑“复原”所研究对象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存在的面貌,即“使今日的地理情况还它原来的面目”。这种认识方法的要义,在于从现今存在的地理面貌出发,上溯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样态,而这可以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和一项基本方法。
至于更为具体的研究途径或者解决问题的手段,侯仁之先生特别强调研究者需要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两个方面通过必要的训练以获取相应的能力。由于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属性,使得大多数历史地理的状况无法直接观察,所能利用的主要材料“是从历史上得来的”,所以研究者必须接受历史学的训练,以“藉助地图和文字”来进行各项复原工作。当然,侯仁之先生更加强调的是现代地理学的基本观念和研究方法,强调历史地理学者理应具备良好的地理学基础。他认为,相对于新型历史地理学所面临的研究问题来说,学者们若是“没有现代地理学的训练,是很难胜任的”。
后来,侯仁之先生又陆续撰写一批阐释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文章,主要有《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历史地理学概述》《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文物考古工作》《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等,对相关问题做更为深入、也更为系统的阐述。这些论述,也是目前中国学者对历史地理学科基本理论、方法做出的最为全面系统、也最为深入的论述。在论述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创立过程这一问题时,《“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这篇文章尤为重要。该文虽然论述相当简单,但却清楚阐述了新型“历史地理学”区别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理论与方法。后来的相关理论论述,尽管更加周详,但在本质上并没有能够超出于这篇文章之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侯仁之先生这篇文章推动教育管理部门改变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的名称,对在各个大学开设这门课程的教师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人们普遍能够用新的眼光来看待相关研究——这就是侯仁之先生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这篇文章中所讲的“必须是从根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上把这门课程彻底地改造过来”。学术的发展并没有违逆侯仁之先生的期望,这门学科的整体面貌,随之很快发生变化。
除了理论论述之外,侯仁之先生更身体力行。他在20世纪50—60年代,对北京的城市起源与演变、西北沙漠变迁以及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等问题作出了具有典范意义的重要研究,对这门学科在现代学科理论指导下全面、深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评价侯仁之先生的具体研究对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影响时,有必要强调野外考察方法的运用问题。重视并积极采用野外考察的方法,这在今天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界早已蔚然成风,被所有历史地理学者习以为常。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初,包括侯仁之先生本人在内的所有的学者都还隔膜在外。当时,侯仁之先生率先强调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要积极开展野外实地考察,而不能再仅仅拘泥于史书的文字记载。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他在沙漠变迁研究中对野外实地考察方法的运用,还具有强烈的典范性意义。这种典范性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侯仁之先生特别强调,野外考察方法的利用,“不仅涉及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与资料的来源,而且关系到历史地理的发展方向与前途”。具体来说,“如果我们坚持旧的做法,那就只有埋头书案,只是从书本子上找材料、下功夫,这样就必然要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极大的限制”。通过自己在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布和沙漠和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研究实践,侯仁之先生意识到,在这些沙地中间“竟然埋藏着那么丰富、那么众多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从细小的遗址遗物一直到巨大的古城废墟,为探讨历史时期沙漠的变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6)侯仁之:《走上沙漠考察的道路》,《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46页。。简而言之,侯仁之先生认为这种野外实地考察的方法大大拓展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而这正是他所提倡的新型历史地理学区别于传统沿革地理的重要内容,即是否从事野外实地考察并非仅仅是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同时也同学者们选取的研究对象紧密相关。采用了野外实地考察的方法,同时也就丰富和拓展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第二,侯仁之先生从事野外实地考察伊始,就特别注重相关领域人员的专业性和多学科的协同性。在探索宁夏河东沙区、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侯仁之先生开展了一系列实地考察。这些考察工作,通常都要组织第四纪地质地貌学者和考古学者协同作业,再加上侯仁之先生本人的历史地理学特长,就能使上述三个学科的学者各自发挥所长,很好地发现并深入认识相关现象,进而融合上述三大学科解析的内容,科学认识相关历史地理现象,阐明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和原因。
这与前述第一点一样,同样具体而又深切地体现了新型历史地理学的现代科学特性。我认为,只有清楚认明到这一特性,才能真正做好历史地理学的野外考察工作。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有很多学者一向对此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很多历史地理学的考察远远没有能够达到侯仁之先生当年的水平。在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历程的时候,这种情况是足以引人深思的。
二
就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而言,地理学可以说是一门区域的科学。而地理学的区域特征决定了历史地理学也同样具有浓重的区域色彩,甚至可以说,区域特征与区域差异的发展变化乃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就像中国的历史学者同样应该并且也可以研究外国史一样,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当然应该而且可以研究外国的历史地理问题。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来说,迄今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和首要问题,却基本上都是中国这一地域范围之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问题。这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客观事实,自有合理的因缘。
基于这样的客观缘由,20世纪5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在中国倡导的历史地理学,其实际构成内容,首先也应当是中国疆域范围之内的各项历史地理问题;实际上,侯仁之先生大声疾呼的“历史地理学”正是这样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概括地说,中国这一区域之内的历史地理问题,也就是所谓“中国历史地理”的内容,所涉及的时段很长,变化很多;所涵盖的地域很广,差异也很大。这种局面,给全面建起这一学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在当时能够直面这一挑战并取得相应成效的学者,首推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建设所付出的努力,主要体现于《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这部大学授课讲义。这部讲义涵盖的地域范围,都以中国的疆域为限,而这正直接呼应了侯仁之先生把“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改变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倡议。
据史念海先生自己公开的表述,这部讲义在1953年时就已形成雏形,当时包括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这三大部分。(7)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跟随史念海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时,在先生家中看到的大约为20世纪50年代油印的讲义,另外还包括历史气候变迁的内容。(8)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言(第3—4页)里曾经谈到,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感到不应摒弃自然地理的变化于中国历史地理之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史念海先生在前述关于历史气候变迁的讲义里,全面爬梳相关原始记载,对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的冷暖变迁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得出了系统性的认识。史念海先生这一研究,不仅要比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相关成果早很多(9)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98页。,而且很多结论还同竺可桢先生后来的研究明显不同。至今,这份讲义对深入认识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仍有重要价值。
由于史念海先生治学严谨,精益求精,这部讲义稿直到1991年底才正式修改出版(10)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草成之时起,内部油印本即散布很广(1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第4页。,很多院校的相关专业也曾采用为教材,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2)按:武汉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前辈学者石泉先生就亲口向笔者讲过史念海先生这部讲义在当年的流行情况,它在历史地理学界之内,应该是尽人皆知的。。其更为实质性的意义,在于这部讲义丰富、系统的内容,正很好地构建起侯仁之先生所期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形态。可以说,史念海先生这部讲义已经搭建起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框架,因而完全可以把它视作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在中国全面建立的一项重要标志。
史念海先生之所以能够在侯仁之先生倡导新型现代化的历史地理学科之后短短十年左右时间就做出这么大的成就,与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开始认真思考并积极尝试如何超逸于传统沿革地理的范围具有很大关系。(13)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所谓水到渠成,良有以也。
除了这部讲义之外,体现史念海先生对创建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学科所做贡献的另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是他在1963年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河山集》,即“《河山集》初集”。这部论文集中最多的内容,是专题阐述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重大基本问题。这些论文,大多都是从叙述自然环境基础入手,分析中国经济地理的大格局。其所论述的问题,较诸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显示出一派全新的气象。其中个别与这种大区域地理格局稍微有些区别的文章,如《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一文,也是首先着眼于自然环境对早期“聚落”这一地理现象的制约和影响。其眼光和方法,不仅与传统的沿革地理迥然不同,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超前性;甚至在今天考古学者对古代聚落遗址的研究中,仍具有很强的典范性意义。总之,《河山集》初集同《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的历史经济地理部分正相辅相成,即《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是概述基本地理状况,这些专题论文则是深入地展开具体的论证。
回顾20世纪50—60年代的实际研究状况,如果说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整体面貌已经基本形成了的话,那么史念海先生的上述研究无疑在这当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和核心的地位。因而,史念海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当之无愧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如上所述,侯仁之先生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关键的转折性作用;此外,谭其骧先生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文将会谈到。这些前辈学者们努力的方向和重点各有不同,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成果规模宏大而又具备完整的体系,因而他对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是远超于其他学者之上的。在这一点上,其重要性是独一无二的。
正因为史念海先生在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最多,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所以,教育部便在1983年指定由史念海先生来撰写“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14)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第2页。。这一情况,可以很好地说明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三
学术往往是在继承中创新的,现代学术中新的学科理论、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几乎每一个方面的创新都要有所因承。从这一意义上讲,一个新兴学科的形成和朝向新方向的深度发展,自然需要很好地继承其脱胎而出的传统学术。
在中国,对于具有悠久沿革地理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来说,只有在充分、有效地继承沿革地理传统的基础上,才能使新式的历史地理学切实建立起来并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而事在人为,并不是谁都能够具备相应的条件来承担这样的使命。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创建的过程中,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学者,当首推谭其骧先生。
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的主体内容,是历代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谭其骧先生治学,在方法上偏好考据,其辨析史料史事,目光敏锐,思维邃密,在沿革地理研究方面,素有显著成就。譬如《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刚先生书》《〈两汉州制考〉跋》《新莽职方考》《西汉地理杂考》诸文,其精深程度皆不让清朝乾嘉诸老。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的考据方法,于舆地沿革之中运用甚广,成效也殊为显著。但所谓考据的实质,是辨明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是史事发生和存在的客观状况,这应该是所有历史研究所必需的基础工作。
清代乾嘉考据之学开山鼻祖阎若璩所著《四书释地》,本来专为考释《四书》地理问题而发,孰知竟因释地而及人,再因释人而及物,复因释物而广至释训诂、释典制,书乃一续、二续、三续,越写问题越多,越写篇幅越大,而去古史舆地则愈来逾远。这一情况形象地说明,如清朝四库馆臣在该书提要中所说,古史舆地考据研究的本质,“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15)《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四书释地”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5—306页。。也就是说,一项好的沿革地理考据,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地理要素本身,牵连到什么,就要能够处理什么问题。反过来看,在这样的沿革地理考证过程中也能不断发现其他相关的历史问题,解决相关的历史问题。
这样的内在本质,决定了研究者需要读书既多且精,这样才能具备“旁参互证,多所贯通”的能力,才能发前人所未发,解决重大疑难问题,推动学术向纵深发展。对于绝大多数历史学者来说,这都是一项难以应对的挑战;学术水平的高低,也于此看出分晓。谭其骧先生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之外,还深度参与曹操、蔡文姬等历史问题的讨论,就是因为他具备了阎若璩般的文史研究综合素质。而正是他这样的学术功力,为历史地理学的全面建立和持久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
谭其骧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所做的最重要工作,是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部图集的编绘,动议始于1954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完成大部分工作,而在1975年出版了内部发行本。这部图集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历朝历代疆域政区的基本状况。这样的内容,当然属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但对于新型的历史地理学来说,疆域政区的沿革变迁,同样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大力研究。
附带说明,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中,每幅图后都附有近三千字的“图说”。这些文字说明,简明地表述了谭其骧先生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状况的总体认识;同时,这也是一项重要的疆域政区研究成果。这些“图说”,对更好地利用这部图集,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历代政区沿革研究更为重要的价值,是为历史地理学科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古代文献对各项地理要素及其相关因素的记载,实际上大部分是以政区建置或其他一些类似的地名作为载述其事的地理坐标,所以,要想精准深切地从事各项历史地理研究,首先就必须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历代疆域政区的基本面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如前所述,谭其骧先生通贯深邃的文史研究素养,保证他足以承负这一使命,为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而像他这样的素养,在中国学术界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部质量精良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和出版,若是没有谭其骧先生主持,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尽管这部图集的出版印行已经迟至20世纪70年代,但在中国初创历史地理学的十几年内,图集的编绘业已全面启动、全面展开,这本身就是创立和建设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工作。若是考虑到这部图集出版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全面大发展,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在世界上的辉煌地位,就更容易理解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创立历史地理学科和推动历史地理学科发展这一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反映历代疆域政区的盈缩迁改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要河流的河道、湖泊水域和海岸线的变迁。例如黄河河道、鄱阳湖与洞庭湖的水域、苏北海岸与渤海湾海岸,等等,像这样一些重大的水道和水域的变化,都有比较具体的体现。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逸沿革地理的范畴,进入新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譬如海河水道错综复杂的变迁过程,更直接触及河北平原上诸多历史地理要素。(16)谭其骧:《长水集》上册《自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历史地图集》还直接体现了诸多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要成果,而这些内容对建立历史地理学的贡献也更为直接。
与上述对黄河河道变迁状况的直接研究着眼点有所不同的是,谭其骧先生还对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患与中游地区土地利用形式的关系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17)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长水集》下册,第1—38页。尽管该文的具体结论,或有可商之处(18)辛德勇:《由元光河决与所谓王景治河重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旧史舆地文编》,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2—75页。,但是谭其骧先生的基本着眼点,不仅在当时极富现代性的学术眼光,而且即使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明的前沿性质。谭其骧先生本人也“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19)谭其骧:《长水集》上册《自序》,第10页。。
从方法论角度讲,这项研究更大的意义,是直接开启了中国古代植被变迁的大规模研究。谭其骧先生在这项研究中指出,黄河中游或以农业为主,或以牧业为主,这两种不同的土地利用形式,直接导致当地水土流失的增多或是减少。而水土流失的加重,自然更容易造成下游河道的决溢以至改徙。后来,以史念海先生为代表、以黄土高原区域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植被变迁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普遍开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可若是追本溯源,则不能不归功于谭其骧先生的首倡。这也是谭其骧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和发展所发挥的一项重要创建作用。
上面简单陈述了侯仁之、史念海、谭其骧三位前辈学者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创立和早期发展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陈桥驿、石泉、黄盛璋等诸位先生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立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当然,文中讲述的只是笔者个人的一些直观看法,难免偏颇而欠周详,诚恳地期望同道学人予以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