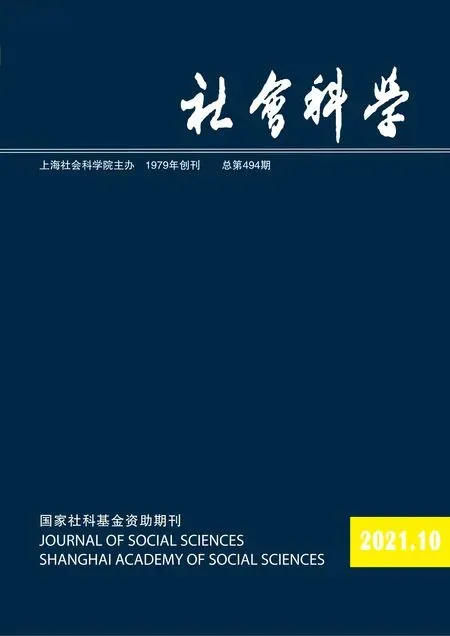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论争研究
王文佳 汪伟民
独立至今,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论争主要围绕三派外交思想展开——极端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及和平主义。(1)参见Kanti Bajpai, “Indian Strategic Culture”, in Michael R. Chambers(ed.), South Asia in 2020: Future Strategic Balances and Alliances, Carlisle Barracks, PA: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02, pp.245-304; Steven A. Hoffman, “Perceptions and China Policy in India”, in Francine Frankel, Harry Harding(eds.),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39-49; Zhang GuiHong, “The Rise of China: India’s Perception and Responses”, South Asian Survey, Vol.13, No.1, 2006, p.95; Swaran Singh, “India-China Relations: Perception, Problems, Potential”, South Asian Survey, Vol.15, No.1,2008, pp.84-86; Jonathan Holslag, “Progress, Perceptions and Peace in the Sino-Indian Relationship”, East Asia, Vol.26, 2008, pp.48-49; Jabin T. Jacob, “Friend, Foe or Competitor? Mapping the Indian Discourse on China”, in Happymon Jacob(ed.), Does India Think Strategically? India’s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Manohar, 2014, pp.229-272。各个流派均包含迥然不同的外交哲学和地缘政治考量。近年来,随着印度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日渐加深,印度正逐渐放弃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对华实用主义思想,转而推行具有主动进攻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对华策略。这种对华策略的急剧转变一方面有其外交思想根源,另一方面也受到国际体系转型和印度国内政治变化双重压力的驱动,同时美国的强力介入和战略诱惑也起到巨大的催化作用,这大大增强了印度对华策略的冒险性和机会主义色彩。本文立足于对印度政治和外交精英的公开讲话文本的解读和分析,从印度对华策略论争的角度厘清印度战略界人士对华策略的外交思想基础、具体流派,对华策略的变迁及其动力以及各派的具体对华策略,同时归纳总结目前中国战略界不同流派的观点,通过对比分析试图找到化解中印对抗与冲突的有效路径。
一、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的外交思想基础
印度战略界三大流派的对华策略各有其外交哲学思想基础和地缘政治内涵,其代表人物遍布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媒体等多个领域,深刻影响着印度领导层的对华决策。
(一)极端民族主义
印度的极端民族主义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兴起,主要由“激进尼赫鲁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新民族主义者”及“超现实主义者”(2)Ian Hall, Modi and the Reinvention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43-44.组成,其思想根植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一个由宪法规定为世俗主义的国家中,极端民族主义者显然超越了抽象和理想化的世俗宪法框架,使宗教深刻影响其外交思想。(3)C. Ram-Prasad, “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India”, in K. R. Dark(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2010, p.140.它将印度视为世界一流大国,但暂时被不公平地忽视了,特别是在地区事务中更是如此,因而其倾向任何可能实现印度大国地位的政策。(4)C. Ram-Prasad, “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India”, in K. R. Dark(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2010, p.160.极端民族主义者特别强调身份认同在获得强国地位中的突出作用,认为它能够团结人民、一致对外,尤其能够凝聚军队力量、提升军人战斗意志。在国际事务中,极端民族主义者持一种类似“霍布斯结构”的世界观,认为国家都是自私逐利的,国际竞争是零和博弈,修昔底德式的弱肉强食观念对其战略思想影响十分明显。因此,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在国际关系中往往体现为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5)Ankit Pandan, “Hindu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4/hindu-nationalism-and-foreign-policy/, 2014-04-04.即通过限制敌人权力的扩大来维护自身的安全。
具有浓厚印度教色彩和遵循考底利耶“曼荼罗”地缘政治考量的极端民族主义外交思想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化”,即在文明上只有一个“印度性”,但在政治上可以存在更大的多样性,(6)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10.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促进南亚经济一体化,并巩固印度地区霸主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异教”为信仰的巴基斯坦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眼中最大的障碍,他们进而对支持巴基斯坦、利用巴基斯坦平衡印度的大国产生仇视心理。印度指控巴基斯坦资助克什米尔武装分子制造分裂及扶植恐怖势力袭击印度,而印度的暴力手段是合乎道义的自卫反击。由此可看出,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使用武力,但往往会为其寻找合法化的辩护理由。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战略关切也左右着印度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主张印度崛起首先依靠“自力更生”,但又主张在有明显政治和经济收益的情况下参与战略伙伴关系。
对华极端民族主义者目前广泛分布于印度决策层、退休军官、前政府官员、智库、防务专家和学者之中。决策层以印度部长秘书级机密组织——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为核心,其中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7)这两位高官也被视为极端民族主义者中的“现实主义-民族主义者”代表,见下文。及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等是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提倡更加公开地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联盟,以增加新德里与北京的谈判筹码;在边界问题上主张将恢复明确的实际控制线作为谈判的第一步,将两国关系正常化与边界问题挂钩,并为寻求解决方案注入更强的紧迫感。鹰派退休军官、前政府官员、防务专家及学者主要通过从事外交政策和战略事务研究的智库和主流新闻媒体的社论发声。(8)如前海军参谋长阿伦·普拉卡什(Arun Prakash)在《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s)等报刊发表多篇社论;前安达曼-尼科巴司令部总司令、前印军战略部队司令部总司令、海军中将维杰·尚卡尔(Vijay Shankar)现为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PCS, The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高级研究员;前中央司令部总司令、陆军中将维杰·库马尔·阿鲁瓦利亚(Vijay Kumar Ahluwalia)现为地面战争研究中心(CLAWS, 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负责人;前中央司令部参谋长、中将高塔姆·班纳吉(Gautam Banerjee)现为维维卡南达国际基金会 (VIF, 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兼编辑;陆军准将阿伦·萨加尔(Arun Sahgal)曾效力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国防部,现为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高级研究员;前印度海军指挥官阿比吉特·辛格(Abhijit Singh)现为观察家基金会(ORF, The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员等。他们是印度战略界最为激进的反华势力,具有较大影响力。鹰派前政府官员包括前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副国家安全顾问、VIF副主席萨帝什·钱德拉(Satish Chandra),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秘书、资深外交官、现VIF负责人阿尔温德·古普塔(Arvind Gupta),资深外交官和前驻缅甸、墨西哥大使拉吉夫·巴蒂亚(Rajiv Bhatia),前驻日本大使、现德里政策集团(DPG,Delhi Policy Group)负责人克里尚·辛格(Hemant Krishan Singh)等。鹰派安全及外交战略家包括印度总理政策顾问团成员、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政策研究中心(CPR,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成员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印度战略事务委员会(Council for Strategic Affairs)主席阿迪蒂纳吉(A. Adityanjee),《印度防务观察》(Indian Defence Review)编辑巴拉特·维尔马(Bharat Verma),防务专家优素福·翁哈瓦拉(Yusuf T. Unjhawala)等。鹰派学者包括印度经济学家、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桑吉夫·桑亚尔(Sanjeev Sanyal),印度著名学者、战略家和记者拉贾·莫汉(Raja C. Mohan),印度第一届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成员、著名进攻现实主义学者巴拉特·卡纳德 (Bharat Karnad),美国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教授、ORF项目负责人哈什·潘特(Harsh V. Pant)等。他们往往受中国“背叛”的愤恨情绪和将其视为“他者”的世界观驱使,秉持中国必须归还从印度“夺走的每一寸土地”的“复仇”立场,利用印度公众普遍对1962年冲突和对中国的无知,在印度国内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些人中不乏印度教右翼势力,他们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不了解印度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内政,但这不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因为其世界观是基于印度教文明的独特地位。这一派的主体是受中印边境战争影响较大的官员和军人,他们对中国和印度的内政外交有较深的理解,并能向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建议,正是他们将中国视为印度无法忽视的威胁。
极端民族主义者中持较为现实观点的战略家也被称为“现实主义-民族主义者”,(9)Hemant Krishan Singh, Arun Sahgal, “India’s Foreign Policy: Agenda 2020”, Delhi Policy Group, https://www.delhipolicygroup.org/uploads_dpg/publication_file/indias-foreign-policy-agenda-2020-1239.pdf, 2020-01-29.现任外交部长苏杰生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与曾扬言准备好为夺回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中国控制区阿克赛钦(Aksai Chin)而流血的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不同,“现实主义-民族主义者”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印度第一”,主张利用全球矛盾创造的机会促进国家利益,并毫不犹豫地根据自身利益调整立场。他们拒绝贸然挑起对印度不利的国际事端,而是追求联合美国、应对中国、深耕欧洲、安抚俄罗斯、发挥日本作用、吸引邻国、扩大邻里关系和支持者(10)S. Jaishankar, 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 India: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20.,其思想实质上是企图利用全球力量打压中国,实现印度崛起。
(二)实用主义
印度实用主义外交思想源于对先前占主导地位的尼赫鲁“理想主义”和“道德性”的摒弃,转而注重权力和物质利益,为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赢得了世界大国的尊重和赞赏。实用主义者未必不是印度教徒,但更多地将印度教视为一种“多元现实”,是一种文化现象。(11)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4.在占总人口80%的印度教徒中存在着不同的教派和种姓团体,他们之间除了相互反感外,鲜有共同之处。他们认为国家间是竞争对手,而非敌人,国际社会的良好运行有赖于国家行为体对彼此权利的认可。实用主义者将“不结盟”策略看作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基本来源,因为它确保了印度继续有能力不受大国或国家集团的限制,从而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作出决定,同时保证了印度与所有大国保持平衡和良好的关系,不向任何大国倾斜。(12)M. S. Rajan, “Pragmatism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South Asian Survey, Vol.1, No.1,1994, p.88.但这种“不结盟”观允许印度在其主权和国家尊严受到威胁时接受外部军事援助,将协调一致视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因而看重通过国际制度扩大影响力。
美国波士顿大学印裔国际关系学副教授曼贾里·查特吉·米勒(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等认为,印度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是一种“过程实用主义”(procedural pragmatism),即不断吸纳所有在特定背景下和政治上有利于实现既定目标的政策,是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不断更新,也是政治宗教民族主义与先前制度化外交思想的结合;(13)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 Kate Sullivan De Estrada, “Pragmatism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How Ideas Constrain Modi”,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3, No.1, 2017, pp.28-34.在外交事务中采取价值主张与价值创造两个策略相结合的方法,即向他国索取、拒绝让步的同时又在双方间整合共同利益,从而缓解僵局,达成自身目的。(14)Amrita Narlikar,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India’s Rise to Power”,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8, No.5, 2007, p.992.
目前对华实用主义者以三位前瓦杰帕伊政府的高官为代表:前外交秘书、前国家安全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萨仁山(Shyam Saran),前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3年)重要促成者希夫尚卡尔·梅农 (Shivshankar Menon) 和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尼鲁帕玛·拉奥(Nirupama Rao)。他们对中国十分了解,掌握专业的中国知识,是瓦杰帕伊政府中国问题决策团队的核心。其他著名人士还有前外交秘书、前驻华大使顾凯杰(Vijay Gokhale),前政府内阁秘书处副秘书长、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贾雅德瓦·拉纳德 (Jayadeva Ranade),前驻华领事、资深外交官基山·拉纳(Kishan S. Rana),IDSA所长、资深外交官齐湛(Sujan R. Chinoy), IDSA战略专家格普利特·库拉纳(Gurpreet S. Khurana)等。由印度外交部资助建立的德里中国研究所(ICS,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Delhi)是这一团体中具有代表性的智库,其中甚至不乏和平主义者。其他代表性的实用主义学者,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斯瓦米纳坦·艾亚尔(Swaminathan Aiyar),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拉杰什·拉贾格帕兰 (Rajesh Rajagopalan) ,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著名汉学家、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Bali Ram Deepak), 历史学家、战略家佐拉瓦·辛格(Zorawar Singh)等。
对华实用主义者承认但不过分渲染“中国威胁”。他们认为,虽然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讨论证明了中国的叙事力量,但中国目前不具备称霸亚洲的优势,未来的亚洲和世界将是多极的秩序,(15)Shyam Saran, “Is a China-Centric World Order Inevitable?”, Inaugural Lecture, https://www.icsin.org/ckfinder/userfiles/files/Shyam%20Saran’s%20lecture.pdf, 2017-07-20; Shivshankar Menon, “China & Asia’s Changing Geopolitics”, ICS Analysis, No.35, https://www.icsin.org/uploads/2020/01/17/dac7b3c1b02f1158a2dbd34e60f1e3b5.pdf, 2020-01-17.因此“中国威胁”被夸大了。同时,实用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崛起确实导致了亚太地区政治和安全的不稳定,使得印度追求自身利益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16)Shivshankar Menon, “China, the World and India”, China Report, Vol.52, No.2, 2016, p.133.印度必须设法确保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良好行为”。他们认为,边界问题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双方都不将解决边界矛盾作为优先事项,而是作为两国关系的杠杆继续存在;尽管两国不断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但都不准备从根本上改变边界现状。狄伯杰指出,当前地区平衡明显倾向中国,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动力降低,只有经济增长和应对国内外挑战的能力才会使印度在边界线问题上获得中国的理解。(17)Bali Ram Deepak, “India’s Myopic China Policy Needs to Change”, Sunday Guardian, https://www.sundayguardianlive.com/opinion/indias-myopic-china-policy-needs-change, 2020-07-11.但实用主义者并不排除以暴力解决争端,诉诸武力与否取决于国家间期望使用暴力的程度。(18)[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4页。
(三)和平主义
印度的和平主义外交思想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性”与国家利益的融合,(19)Andrew Kennedy, “Nehru’s Foreign Policy: Realism and Idealism Conjoined”, in David M. Malone, C. Raja Mohan and Srinath Raghavan(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01.是自由国际主义与强国思想的融合。(20)Stephen P. Cohen, India: Emerging Powe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38.印度的和平主义者主要包括尼赫鲁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传统的反西方左翼人士等,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思想曾在印度独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独立初期演绎为一种理想主义,塑造着其外交政策。尼赫鲁曾表示,今天的理想主义就是明天的现实主义,(21)Shri Yashwant Sinha, “India’s Foreign Policy: Success, Failure and Vision in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9285/Indias+Foreign+Policy, 2002-11-18.因为和平无法建立在仇恨之上。(22)转引自Krishnan Srinivasan, “Values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Neutralism, Isolationism and Multi-engagement”, in Krishnan Srinivasan, James Mayall and Sanjay Pulipaka(eds.), Values in Foreign Policy: Investigating Ideals and Interests, London: Rowan & Littlefield, 2019, p.136。但后来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普遍认为这导致了印度外交的失败。(23)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 Kate Sullivan De Estrada, “Pragmatism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How Ideas Constrain Modi”,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3, No.1, 2017, p.27.实际上,和平主义与实用主义并不完全冲突,他们同样怀着“做有声有色的大国”梦,同样强调“不结盟”策略,同样重视国际制度的作用,但和平主义者对强权政治持批评态度,呼吁通过集体安全安排和强有力的国际机构超越强权政治。和平主义者,尤其是左翼人士对美国持怀疑态度,批评其正在利用印度以确保“离岸平衡手”的地位。(24)Siddharth Varadarajan, “Eastern Promise, Western Fears”, The Hindu,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columns/siddharth-varadarajan/Eastern-promise-western-fears/article14931411.ece, 2011-01-25.苏米特·甘谷利(Sumit Ganguly)指出,尽管这一想法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淡化,但印度政治文化中仍存在着一种反美情绪。(25)Sumit Ganguly, M. Chris Mason, An Unnatural Partnership? The Future of US-Ind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Carlisle Barracks, PA: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 Press, 2019, p.26-27.
和平主义者坚信印度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将产生兼具高贵品格和战略能力的领导人,能够为世界带来秩序,(26)Stephen P. Cohen, India: Emerging Powe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38.因此主张印度采取主动。他们十分赞赏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中国的边界谈判策略,希望印度能够效仿苏联一举解决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和平主义者先天的道德优越感也决定了和平主义者是软实力的推崇者,他们批评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拥有的是一种虚假的“阳刚之气”,由于缺乏综合国力的支持正在失去可信度。他们认为,印度外交的真正力量在于其独特的“例外主义”,它根植于印度的文明、文化、思想、精神、音乐、电影、艺术、多元民主等,世界期待印度成为道德领导。(27)Krishnan Srinivasan, “Values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Neutralism, Isolationism and Multi-engagement”, in Krishnan Srinivasan, James Mayall and Sanjay Pulipaka(eds.), Values in Foreign Policy: Investigating Ideals and Interests, London: Rowan & Littlefield, 2019, pp.149-150.因此,和平主义者珍视其外交政策中长久以来形成的宝贵价值观,包括“不结盟”“非暴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认为所有从帝国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国家都应被平等对待。
印度战略界的对华和平主义者包括前辛格政府新闻发言人、前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前印度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IDSA高级研究员桑贾亚·巴鲁(Sanjaya Baru),新德里内政部前高级官员、前警察局长苏布拉曼尼亚(K. S. Subramanian),政治家、专栏作家苏廷德拉·库尔卡尼 (Sudheendra Kulkarni) ,经济学家、著名媒体人尚卡尔·贾 (Prem Shankar Jha) ,ICS副主任郑嘉宾(Jabin T. Jacob)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中印关系研究专家坎蒂·巴杰帕伊(Kanti Bajpai)等;还包括一些对中国有较深了解的外交官,如前驻华大使任嘉德(C. V. Ranganathan),前驻土耳其、乌兹别克大使,资深外交官巴德拉库马尔(M. K. Bhadrakumar)等;也包括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实业家,如印度最大集团公司塔塔集团董事长拉丹·塔塔(Ratan Tata)等。
对华和平主义者反对将崛起的中国视为威胁,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利益攸关者,(28)M. K. Bhadrakumar, “Who Stands to Gain from War Hysteria?”, The Hindu, https://www.thehindu.com/opinion/lead/Who-stands-to-gain-from-war-hysteria/article16882577.ece, 2009-09-20.“亚洲世纪”的关键问题将是中印两个大国能否以有助于促进地区及全球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方式来管理它们的关系。(29)Jabin T. Jacob, “India’s China Policy: Time to Overcome Political Drift”,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4/07/PB120601_India_China_Policy.pdf, 2012.在边界问题上,和平主义者大体认同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的历史观,(30)参见[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认为印度错失了避免战争、同中国和平划定边界的宝贵机会。(31)Sudheendra Kulkarni, “LAC Has Little Meaning. Can India-China Reimagine Contours of a New Boundary of Assured Control?”, The Indian Express,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india-china-stand-off-line-of-actual-control-galwan-valley-sudheendra-kulkarni-6465585/, 2020-06-19.他们批评极端民族主义者无法摆脱1962年的阴影,将恶意动机归咎于中国,并利用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框架掩盖偏见和无知。他们认为,印度政府在边境不断建立常规军事力量是未跳出传统思维定势的体现,破坏了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前景。2020年6月15日发生在拉达克东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恶劣事件使和平主义者认识到,解决重大问题需要妥协和让步,印度应该摒弃尼赫鲁“自以为是的不妥协”,主动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32)K. S. Subramanian, “Galwan Valley Clash: Where Do India and China Go from Here?”, NewsClick, https://www.newsclick.in/galwan-valley-clash-where-india-china-go-here, 2020-07-17.
上述三派思想虽观点迥异,但都承认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是一个天生的亚洲和世界领袖,认为印度在这两个层面都全面落后,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落后。基于这种看法,三派战略界人士都认同,国家经济发展是决定印度和中国权力差的关键,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看待和改变这种权力差。此外,他们也都承认第三方,尤其是美国和巴基斯坦是影响中印关系的外部核心变量。
二、近年来(33)关于印度战略界对华认知何时发生变化有不同说法:一说是2010年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同时金砖五国发生分裂,导致印度战略心理失衡,转而改变对华认知;二说是2016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定位越来越高,将印度视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并试图与其结成准联盟关系,这种外部因素刺激了印度战略界的对华认知。本文不进行严格的时间划定,使用“近年来”指代。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的变迁及其动力
长期以来,印度战略界三派对华策略总是处于激烈的论争之中,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总有一种主流的对华策略主导着其对华政策。1962年以前,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根植于“印中亲如兄弟”的和平主义思想为主。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导致两国关系戏剧性崩溃。战败导致印度战略界产生了以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为首的“激进尼赫鲁主义者”,他们对中国充满仇恨、怀疑和畏惧,诱导印度人民将中国看作“热衷战争、险恶的非道德”国家,“不值得欣赏,只能用更强的武力加以限制”。(34)[美]苏米特·甘古利主编:《印度外交政策分析:回顾与展望》,高尚涛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94-95页。1988年中印外交取得突破,为两国在不解决边界争端的情况下重建关系铺平了道路。两国均认识到,国家的稳定发展是以和平周边为前提的,这反映了中印战略界强调实用主义和更广泛的优先事项的转变。近年来,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动、印度民族主义的强势崛起以及不断发酵的“中国威胁论”,印度战略界对华主流策略再次发生重大变迁,极端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对华指导思想。
(一)从实用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
印度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并取得成功以来,政治精英希望对内通过扩大贸易和投资提升政治影响力、对外确立西至波斯湾东至马六甲海峡海域主导地位的愿望催生了对华实用主义战略思想。(35)Mohan Malik, “China-India Relations in the Post-Soviet Era: The Continuing Rivalr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42, 1995, p.321.这一派战略界人士尽管未能彻底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但认识到新世界秩序是由经济主导的,因此能从国家利益的首要性及其可实现性出发,务实地看待印度同中国的关系, 几任前高级领导人如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及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等均持这种观点。曼莫汉·辛格执政时曾表示,中印应避免由过时的均势思维驱动的分化政策和行动,而应努力在从安全到贸易和投资等一系列问题上建立一个更有意义和更具包容性的合作框架。(36)“Manmohan Calls for a Trilateral Framework on Economic Front”, The Indian Express, http://archive.indianexpress.com/news/manmohan-calls-for-a-trilateral-framework-on-economic-front/21645/, 2007-01-24.根据1999年至2007年印度议会最大的十个政党发布的官方文件,印度的国大党、人民党、共产党等主要政党均赞成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扩大两国经济合作,并批准了政府为双边贸易便利化所采取的措施;同时也有政党主张在边界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但表示愿意就划界问题进行建设性谈判。(37)“All Parties for Purposeful Relations with China”, Financial Express, https://www.financialexpress.com/archive/all-parties-for-purposeful-relations-with-china/114760/, 2004-09-08.
这一时期,实用主义接触策略也广泛存在于智库和学术界,对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渴望使他们珍视与中国的和平关系,同时保留了对两国关系的犹疑。(38)Jonathan Holslag, “Progress, Perceptions and Peace in the Sino-Indian Relationship”, East Asia, Vol.26, 2008, p.52.实用主义者提倡“平衡+接触”,遵循务实的原则,一方面明确中国为印度带来了挑战,主张对中国未来权力投射进行预期型防御,但反对对“中国威胁”进行不必要的渲染;另一方面重视双边关系中事关印度利害的经济因素,倡导中印在经济、环境和文化等问题上展开合作,认为两个亚洲大国的合作将加强它们与唯一超级大国谈判的立场。(39)Mohan Malik, “Eyeing the Dragon: India’s China Debate”,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https://apcss.org/Publications/SAS/ChinaDebate/ChinaDebate_Malik.pdf, 2003, p.5.如印度极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戴辛格(Giri Deshingkar)坚信,两国不断增长的经济文化联系将巩固互信(40)Mohan Malik, “China-India Relations in the Post-Soviet Era: The Continuing Rivalr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42, 1995, p.322.;拉贾·莫汉认为,印度需要一个既不愚蠢浪漫也不愚蠢鹰派的政策;(41)Raja C. Mohan, “The Middle Path”, The Indian Express,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the-middle-path/522993/0, 2009-09-30.CPR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尼米·库里安(Nimmi Kurian)指出,中国利用贸易刺激转移对其加强权力企图的注意力,因此新德里需要采取平衡的政策,将竞争和合作结合起来。(42)Nimmi Kurian, Emerging China and India’s Policy Options, Delhi: Lances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6.由于政治精英和战略界自上而下的带动,中印关系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了明显的提升。
近年来,印度战略界主张调整对华策略的呼声越来越高。鹰派前外交秘书坎瓦尔·西巴尔(Kanwal Sibal)在2013年李克强出访印度后撰文称,我们对中国的让步没有换来任何回报,在边界和跨界河流、核供应国集团和安理会成员国地位、中国在印度邻国的破坏性政策等问题上一无所获。印度需要一个连贯的政治战略,以纠正与崛起中国的关系中日益严重的不平衡。(43)Kanwal Sibal, “India’s China Syndrome”, India Today, https://www.indiatoday.in/opinion/kanwal-sibal/story/indias-china-syndrome-kanwal-sibal-india-today-164639-2013-05-28, 2013-05-28.2014年右翼党派成员莫迪当选印度总理显然给鹰派人士以更大的“希望”,他们声称印度应采取一种更加“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44)Kanwal Sibal, “Our Foreign Policy Needs Adjustment”, India Today, https://www.indiatoday.in/opinion/kanwal-sibal/story/narendra-modi-india-foreign-policy-siachen-pakistan-china-191715-2014-05-06, 2014-05-06.根据布鲁斯金学会(印度)研究员德鲁瓦·贾伊尚卡尔(Dhruva Jaishankar)2018年对127名印度战略界人士的调查,其中超过半数的人员将中国看作印度最大的外部威胁,三分之二的人员将美国看作印度最重要的全球伙伴,近半数的人员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印度应加强与美国的合作。(45)Dhruva Jaishankar, “Survey of India’s Strategic Community”, Impact Series of Brookings India,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9/03/Survey-of-India’s-Strategic-Community.pdf, 2019.
这种变迁表明极端民族主义正在代替实用主义成为印度战略界的主流思想,具体体现在“传统战略家”与“新一代具有前瞻性和远见的战略家”(46)B. Raman, “The Jugular Reality: India’ Strategic Debate”,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https://www.c3sindia.org/archives/the-jugular-reality-indias-strategic-debate/, 2012-06-06.之间的分歧。印度传统战略家和新一代战略家都强调中国军事激进主义和军队现代化的影响,重视能使北京不断推进权力投射议程的经济影响力。两代战略家都提倡加强印度对华能力,如发展基础设施、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和提高外交水平等。与前者不同,新一代战略家认为,印度不仅应采取传统手段对抗中国,还应与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培育战略一致性。坎瓦尔·西巴尔称,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摒弃对结盟的“过敏”,摆脱仍然困扰我们的“不结盟”弊病,摒弃左翼、第三世界的言论,不允许“战略自主”的概念限制更具决定性的外交政策选择。(47)Kanwal Sibal, “Our Foreign Policy Needs Adjustment”, India Today, https://www.indiatoday.in/opinion/kanwal-sibal/story/narendra-modi-india-foreign-policy-siachen-pakistan-china-191715-2014-05-06, 2014-05-06.
两代战略家的分歧还表现在巴基斯坦和中国谁才是印度最大威胁的问题上。传统战略家认为中印没有历史的结构性敌意,中国的要求仅限于对藏南地区的领土主张,而不是企图增加印度国内安全问题而导致印度分裂;而巴基斯坦则代表着一种对立的国家理念,其造成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决定了它是印度最重要的邻国。新一代战略家认为,崛起的中国更加危险,如何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应对中国才是印度对华策略论争的核心议题。他们称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关注超过了其应有的程度,随着事态发展到一定阶段,印度“自信”可以打败巴基斯坦,因此主张政府将更多资源转移至对抗和遏制中国上来。
中美战略竞争格局形成以来,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论争越来越集中于印度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和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选择这两个问题。极端民族主义在印度日趋成为主流思想,这导致某些持实用主义观点的政府高官有时不得不依赖极端民族主义的话语作为内部和外部的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巩固其影响力。此外,中印共同崛起的事实使和平主义者仍有潜力成为印度战略界具有一定说服力的一个群体。总体来说,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极端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及和平主义思想在印度外交决策界以及政策舆论方面仍然保持着各自不同程度的影响力。
(二)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变迁的动力
首先,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印度基于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主动应对。国际格局的动态变化体现在权力分布的转移中,由此左右着其他大小国家面对权力转移时所采取的战略,(48)G. John Ikenberry,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1, No.1,2016, p.16.印度认为其正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冷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格局受到美国相对衰落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冲击。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和技术等领域对中国展开打压。中美之争通常被置于霸权国与崛起国间权力转移的框架下审视,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指出,崛起国所在区域通常被认为发生了全球霸权国与地区崛起国之间的区域权力转移。(49)G. John Ikenberry,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1, No.1,2016, p.9;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Character, and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Orfeo Fioretos(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i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59-75.霸权国在全球和地区主导的等级秩序是一元的,即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均以霸权国为首。崛起国首先挑战的往往是地区的经济秩序,这样在地区就形成了双重等级秩序——以霸权国为首的安全秩序和以崛起国为首的经济秩序,这促使地区国家的战略随着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50)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the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86.实力较强的国家倾向制衡,较弱的小国会利用对冲等策略来避免大国竞争带来的损失,当实力低于某个门槛时,该国将别无选择,只能“迁就”。(51)Jack S. Levy, “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John A. Vasquez, Colin Elman(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pp.139-140; Hsin-Hsien Wang, Shinn-Shyr Wang and Wei-Feng Tzeng,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How Lesser Powers Respond to Competing Great Power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sue & Studies: 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on China, Taiwan, and East Asian Affairs, Vol.56, No.2, 2020, p.2.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实力较强且与中国是邻国,与霸权国美国产生了明显的利益趋同——霸权国应对的是对国际体系的威胁,地区大国则对其邻近区域的权力失衡作出反应。这种潜在的动态三角格局大大提升了印度的战略重要性,使其成为地区的“轴心”。基于这一事实,美国加强对印度的拉拢,将其视为“天然伙伴”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棋手,并提供了实质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催化了印度战略界对华的大国野心。同时,俄罗斯继续与印度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这进一步增加了印度的战略资本。
其次,伴随着印度国内政治强人出没、人民党强势崛起和国大党衰落,印度民族主义势力急剧上升。由右翼组织“国民志愿团”(RSS)把控的人民党获得了印度联邦和地方议会的绝对优势,对内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成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52)王世达:《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2期。对外重申尼赫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的理想,致力于将印度建设成为“领导型大国”。印度前任总理瓦杰帕伊亦为“国民志愿团”成员,但由于其政治技巧和议会席位不足,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较小。这些“障碍”在莫迪政府时期被消除。2019年选举中,印度人民党夺得下院303个席位,莫迪成为1971年英迪拉·甘地以来首位连续赢得多数席位的印度领导人,强势开启了“莫迪2.0”时代。莫迪为进一步巩固议会的支持,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话语,他曾在一次受访中申明:“我相信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时,我的‘印度教特性’将是一笔财富。”(53)Girish Kuber, “My Hindutva Face Will Be an Asset in Foreign Affairs”, The Indian Express,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politics/my-hindutva-face-will-be-an-asset-in-foreign-affairs/, 2014-04-23.
此外,中国的快速崛起令印度产生了强烈的战略挫折感和威胁感。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庞大的对外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并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苏杰生直言,世界或许会感谢中国的腾飞,但印度却不得不应对一个强大近邻的影响。(54)参见Subrahmanyam Jaishankar, 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 India: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20。随着中国不断加强印度洋军事力量投射、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印度的“自危感”不断上升,并逐渐转化为一种战略愤怒,认为1988年以来采取的正统对华策略已经失效,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和理性谈判是徒劳的。坎蒂·巴杰帕伊认为正是这种愤怒感驱使着印度战略界对华认知的转变。(55)Kanti Bajpai, “Modi’s China Policy and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Pacific Affairs, Vol.91, No.2, 2018, p.246.
三、印度战略界各派对华具体策略论争
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对重要文本的解读,对极端民族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基于其外交思想和各自的“中国观”所提出的具体的对华策略进行归纳和比较分析。各派的重要代表主要通过公开讲话、或经印度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智库和主流新闻媒体发表观点,(56)前者如隶属国防部的IDSA,由三军各自设立的智库——CLAWS、海事基金会(NMF,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和空军研究中心(CAPS, Centre for Air Power Studies),由外交部资助建立的ICS,其他著名智库如ORF、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ICRIER,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金奈中国研究所(C3S,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梵门阁(Gateway House: Indian Council on Global Relations)、印度联合军种研究所(USI, The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for India)、VIF、DPG、CPR、IPCS等。Syama Prasad Mookerjee博士研究基金会(SPMRF,Dr. Syama Prasad Mookerjee Research Foundation)是印度教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的突出代表,主张在边界争端和对华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后者如《印度快报》、《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等。其中一些观点已经被印度现政府践行,在短期内仍将继续是印度政府的主要对华政策内容。
(一)极端民族主义对华策略
极端民族主义者最突出的特点是大肆宣扬中国正在对印度施加“胁迫性压力”,中国是印度的“长期威胁”,并由此主张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的对抗和遏制策略。在边界问题上,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侵占印度领土。中国在边境线上不断加强军事防御和基础设施建设,非法跨越实控线进入印度境内,破坏印度的军事基础设施,最终可能像1962年那样“给印度上一课”。(57)P. Stobdan, “Is China Desperate to Teach India Another Less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34, No.1,2010, pp.14-17; Brahma Chellaney, “Last lesson of 1962: Don’t Be Caught Off-guard Again”, Times of India,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home/sunday-times/all-that-matters/Lasting-lesson-of-1962-dont-be-caught-off-guard-again/articleshow/11583174.cms, 2012-01-22.中印边界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是中国刻意为之,因为中国始终将领土争端作为向印度施压的“杠杆”,通过挑起边境紧张局势、小规模冲突和提出领土主张迫使印度反应式地寻求军事解决办法,进而使印度增加国防开支,掣肘经济发展。(58)Xerxes Adrianwalla, “The Spectre of China”, Gateway House, https://www.gatewayhouse.in/spectre-china/, 2012-07-12.
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印、中美关系近三十年来的“现状”。中国以超越并取代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为目标,谋求印太海域的霸权,企图将巨大的经济利益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同时不断加强印太海域的军事存在,使地区国家不得不屈服于其霸权。中国不希望印度崛起,先是支持巴基斯坦为印度制造“两条战线”的军事威胁,试图将印度束缚于南亚一隅。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他们认为中国逐渐“入侵”南亚,(59)Arun Prakash, “How to Play Against China: India Will Need to Bring Order and Alacrity to Crisis Management”, The Indian Express,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india-china-border-stand-off-line-of-actual-control-galwan-valley-6474725, 2020-06-25.用其绝对的大国力量迫使印度“绥靖”,进而代替印度成为南亚次大陆的主导力量,(60)S. Kalyanaraman, “The China-India-US Triangl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and a New Cold War”, IDSA Comment, https://idsa.in/idsacomments/the-china-india-us-triangle-kalyanraman-210920, 2020-09-21.因此与中国的任何妥协只会加剧其优势,进一步削弱印度的地区和全球地位。
印度在中美之间的选择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热衷的议题。极端民族主义者鼓吹中美之间正在爆发“新冷战”,而印度已深陷其中。面对强大对手的“高压胁迫”,印度必须遵循战略一致、而非战术便利(61)“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s Speech at the 4th Ramnath Goenka Lectur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2038/External_Affairs_Ministers_speech_at_the_4th_Ramnath_Goenka_Lecture_2019, 2019.的原则建立伙伴关系,并做好付出相应代价的准备,因为在这场大国竞争中没有“搭便车”的空间。(62)Hemant Krishan Singh, Arun Sahgal, “India’s Foreign Policy: Agenda 2020”, Delhi Policy Group, https://www.delhipolicygroup.org/uploads_dpg/publication_file/indias-foreign-policy-agenda-2020-1239.pdf, 2020-01-29.他们基于其“复仇”和“中国威胁论”的核心思想,认为应采取以下对华策略:
第一,提高印度综合国力,增强对华内部硬制衡能力。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印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两国关系不平衡的根源,他们深谙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权力来自经济实力。桑吉夫·桑亚尔指出,印度应采取短期和长期措施对抗中国,前者包括加强边境线的军事防御和武器系统的投资,后者包括利用人口优势与中国展开工业经济竞争。(63)Sanjeev Sanyal, “Rising China: Implications for India”, Gateway House, https://www.gatewayhouse.in/chinas-rise-its-implications-india/, 2010-07-30.印度战略界尤其密切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进程及其部署,认为印度必须加大国防支出,某种程度上印度正在与中国展开军备竞赛。在对待使用武力的态度上,极端民族主义者继承英迪拉·甘地的强硬立场,在军事战略上鼓吹从拒止型威慑转向惩罚型威慑。(64)Anit Mukherjee, Yogesh Joshi, “From Denial to Punishment: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Changes in India’s Military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sian Security, Vol.15, No.1,2018, pp.25-43.印度人民党联邦院议员苏布拉马尼亚·斯瓦米(Subramaniam Swamy)称政府在边界问题上持续与中国谈判会使后者视为“投降”,若中国军队确实“入侵”了印度领土,则无需与“侵略者”继续谈判。(65)Pritesh Kamath, “Subramanian Swamy Asks Govt to Call Off Negotiation If China Thinks India Will Capitulate”, Republicworld, https://www.republicworld.com/india-news/politics/subramanian-swamy-asks-govt-to-call-off-negotiation-if-china-thinks-in.html, 2020-09-05.反华代表人物布拉马·切拉尼扬言,若印度政府更早允许军队在边境冲突中采取积极的武装反制措施,中国的领土收益将更加有限。(66)Brahma Chellaney, “On China, India Is Making a Mistake”, Hindustan Times,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columns/on-china-india-is-making-a-mistake/story-QPxd0o3RJKhgzghOm7mX1I.html, 2020-09-18.
第二,突破传统“不结盟”策略,与美国结成联盟。阿伦·普拉卡什指出,在现实政治的世界里,利益压倒一切,印度必须放弃“不结盟”的陈词滥调,在可能的地方找到朋友。(67)Arun Prakash, “Beware the Rhyme of History”, The Indian Express,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beware-the-rhyme-of-history-british-prime-minister-neville-chamberlain-munich-conference-german-annexation-adolf-hitler-china-world-war-4582702/, 2017-03-24.拉贾·莫汉称,与美国及世界上其他民主大国结成联盟以遏制中国崛起将为印度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开辟一系列新的可能性。(68)Raja C. Mohan, “Global Coalition of Democracies, Amid China’s Assertion, Could Open a Range of New Possibilities”, The Indian Express,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us-india-democracy-china-cold-war-global-economy-6526409/, 2020-07-28.防务专家优素福·翁哈瓦拉指出,诸多证据显示,印度实际上已经与美国“结盟”,不仅体现在界定两国关系的形容词中——“天然盟友”“不可或缺的盟友”“定义21世纪伙伴关系”等,也体现在两国近二十年来迅速发展的防务关系中。他认为印度与美国结盟不会破坏战略自主性,相反,印度将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21世纪的联盟与20世纪的联盟不同,美国希望合作伙伴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但要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合作,包括武器销售、军事技术转让、外交支持、情报共享、联合军事演习和后勤保障等,这一点很适合印度。利用大国竞争,并与能让新德里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权力保持一致是正确的。(69)Yusuf T. Unjhawala, “Why India Should Align with the U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https://www.orfonline.org/contributors/yusuf-t-unjhawala/, 2020-05-16.
第三,发挥战略自主性,构建“志同道合”国家的“统一战线”。首先,利用民主价值观,构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反华同盟。克里尚·辛格和阿伦·萨加尔强调四个主要海洋民主国家美、日、印、澳的合作在印太海域的重要作用。(70)Hemant Krishan Singh, Arun Sahgal, “Strategic Balance in the Indo-Pacific: A Role for Maritime Democracies”, Delhi Policy Group, https://www.delhipolicygroup.org/uploads_dpg/publication_file/strategic-balance-in-the-indo-pacific-a-role-for-maritime-democracies-1121.pdf, 2018-12-03, p.11; Rajiv Bhatia, “Quad, China and the Indo-Pacific Churn”, Gateway House, https://www.gatewayhouse.in/quad-china-indo-pacific/, 2020-06-18.在此基础上,有分析人士提出将所有对中国行为表示担忧的国家,尤其是东盟各国吸纳进来,将该组织升级为“印太条约组织”,即亚洲版北约。(71)Mansheetal Singh, Megha Gupta, “Covid-19: China’s Adventurism with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9 Dashline, https://www.9dashline.com/article/covid-19-chinas-adventurism-with-taiwan-and-the-south-china-sea, 2020-05-28.巴拉特·卡纳德则认为,中美不太可能发生实际的敌对行动,因为双方有太多的利益纠缠,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激烈竞争。他提出印度应利用地区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担忧和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联手俄罗斯构建“金砖四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并在亚洲构建新“四国”组织(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72)Bharat Karnad, Staggering Forward. Narendra Modi and India’s Global Ambition, India: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8, pp.174-222.分别将中国和美国排除在外。在卡纳德看来,印度必须成为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中第三股力量的领袖,团结世界上不愿被迫在大国博弈中遭受利益损失的国家,成为世界权力的平衡器。
(二)实用主义对华策略
实用主义者总体上认同中印之间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一方面,两国关系由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地缘政治竞争所塑造,中印横跨在亚洲同一个地缘政治空间,利益在这里交汇,双方都努力将权力押注于同一地区,即南亚、东南亚、中亚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另一方面,实用主义者也看到了中印两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如气候变化谈判等,两国在改善现有国际秩序、保证海上交通线安全畅通方面有共同利益,两国建立起了处理边界问题、跨境河流、贸易逆差等问题的机制。在这一层面,实用主义者认为中印关系至关重要,必须得由它们自己来处理, 避免其他国家利用两国竞争来达到自身目的。(73)Shyam Saran, “What Does China’s Global Economic Strategy Mean for Asia, India and the World?”, ICS Analysis, No.35, https://www.icsin.org/uploads/2015/10/09/677d627ad1f9ba3cd77c0bbdd5389f98.pdf, 2020-06-12.
就中美战略竞争而言,实用主义者认为这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但两国在贸易、技术等领域的争夺不会自动转化为印度的明显优势,除非它建立起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框架。(74)Sujan R. Chinoy, “US-China Rivalry: A Strategic Moment for India?”, ICS Occasional Paper, No.49, https://www.icsin.org/uploads/2020/06/12/71885e5dd79ac44e71d6427bba86a461.pdf, 2020-06-12.美国试图通过印度与中国对抗,或使印度与美国及其盟友在海陆联手抵消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这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灾难性的。(75)Bali Ram Deepak, “China’s Global Rebalancing: Will It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in Bali Ram Deepak(ed.), China’s Global Rebalancing and the New Silk Road, Singapore: Springer, 2018, p.10.因此,印度有理由继续深化与美国的合作,与作为邻国的中国和睦相处,同时在复杂的亚太局势中选择其他合作伙伴。实用主义者坚持两国合作与竞争的本质关系,认为与中国接触应采取下列策略:
第一,加强中印战略对话,建立双边关系发展新框架。首先,双方应就核心关切和敏感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如梅农、齐湛等认同体系和单元层面的诸多因素导致中印趋于对抗,但这些因素不会导致对抗不可避免,中印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决定了双边关系的发展轨迹。中印真正需要的是战略对话,了解双方的核心关切,防止误判。(76)Shivshankar Menon, “Some Thoughts on India, China and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China Report, Vol.53, No.2, 2017, pp.188-213;Sujan R. Chinoy, “Introduction”, in Sujan R. Chinoy, Jagannath P. Panda(eds.), Asia Between Multipolarism and Multipolarity, Manohar Parrikar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2020, pp.xlviii-l.其次,利用中国的资源促进印度的发展,而不是对“中国威胁”采取反应式策略。如格普利特·库拉纳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孕育了印度的地缘经济机遇,“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可能并不明智。(77)Gurpreet S. Khurana, “India as a Challeng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ia Policy, Vol.26, No.2, 2019, p.27.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衰退,印度应成为区域及全球贸易和投资链的一环,佐拉瓦·辛格、拉维·布塔林加姆(Ravi Bhoothalingam)等人士反对印度政府盲目追随美国对中国打“经济牌”,妄图与中国脱钩。(78)Zorawar Daulet Singh, “On the Economy, Don’t Disengage with China”, Hindustan Times, https://m.hindustantimes.com/analysis/on-the-economy-don-t-disengage-with-china/story-Er5AOSLoDjS7bqTcB3ffEI.html, 2020-07-27; Ravi Bhoothalingam, “What Future for Indi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CS Occasional Paper, No.53, https://www.icsin.org/uploads/2020/07/28/332a9 eadaaacde00d3326e29c64f1b28.pdf, 2020-07-28.
第二,同时保持与中美的接触,并保证印度处在与中美的双边关系好于后两者彼此间关系的位置,且印美关系好于印中关系。《星期日卫报》(TheSundayGuardian)编辑总监玛德哈夫·达斯·纳拉帕(Madhav Das Nalapat)教授在同梵门阁创始人曼吉特·克里帕拉尼(Manjeet Kripalani)讨论时指出,印度分别与美国和中国保持良好的防务关系和贸易关系,是新德里同时拥有与华盛顿和北京良好关系的前提。(79)“Modi, XI Take Charge”, Gateway House, https://www.gatewayhouse.in/modi-xi-take-charge/, 2018-04-26.IDSA东亚研究员贾甘纳特·潘达 (Jagannath P. Panda)等认为,新德里应采取一种非对抗的、有分寸的方式来应对流动的国际事务——根据国家利益和关切来指导行动,而不是向一方倾斜。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印度应考虑战略和经济两方面关切,借助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来实现其遏制中国的目的,监测中国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力求代替中国成为高端IT产品的制造中心,参与美国“蓝点网络”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印度也为美国提供了平衡亚洲的有力杠杆。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印度则应继续培育与中国的区域伙伴关系,因为印度与中国的区域愿景——推动以亚洲为中心的秩序——相一致,印度也应继续与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展开合作。(80)Jagannath P. Panda, Mrittika Guha Sarkar, “India’s Capital Cusp in US-China Tensions. It’s National Interest First”, The Journal of Indian and Asian Studies, Vol.1, No.1,2020. pp.11-13.
第三,通过灵活机动地部署外交资产应对中国挑战。(81)Parsa Venkateshwar Rao Jr, “Nirupama Rao on How India Should Deal with an Insecure China”, National Herald, https://www.nationalheraldindia.com/india/nirupama-rao-on-how-india-should-deal-with-an-insecure-china, 2020-05-27首先,这涉及印度同周边邻国的关系。萨仁山、库里安及布塔林加姆等认为,印度必须遵循“邻里优先”的策略,扩大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成为次大陆经济增长的引擎,恢复对邻国的承诺,防止中国进一步压缩印度的战略空间。(82)Shyam Saran, “Is a China-Centric World Order Inevitable?”, Inaugural Lecture, https://www.icsin.org/ckfinder/userfiles/files/Shyam%20Saran’s%20lecture.pdf, 2017-07-20; Gautam Mukhopadhaya, Nimmi Kurian, “India Must Take the Lead in South Asia”, Hindustan Times,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analysis/india-must-take-the-lead-in-south-asia-analysis/story-pr5Pp9DIWAHdXI8T154UBM.html, 2020-08-25.其次,印度应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多极化发展,抵制中国试图主导亚洲的企图。在这一点上,实用主义者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具有相似的构想,即提倡印度在美、日、印、澳“四国联盟”(Quad)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将其建设成安全磋商与合作的平台以对抗中国,(83)Shyam Saran,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an Uncertain World”, 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 https://www.cprindia.org/policy-challenge/7852/foreign-policy-and-national-security, 2019-06-04.但最终目的是推动亚洲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关联、权力关系多样化的地区,因此实用主义者尤其重视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和亚投行等的作用。他们认为,疫情过后的亚洲更需要团结起来,实行新的多边主义,而印度应抓住这一机遇成为独立的一极。(84)Sujan R. Chinoy, “US-China Rivalry: A Strategic Moment for India?”, ICS Occasional Paper, No.49, https://www.icsin.org/uploads/2020/06/12/71885e5dd79ac44e71d6427bba86a461.pdf, 2020-06-12.
(三)和平主义对华策略
和平主义者对中国不抱固有的怀疑态度,相信两国和平崛起的前景,认为目前中印关系的紧张是两个崛起邻国“自然”竞争的结果。(85)Sanjaya Baru, “Bilateral Trade and Global Economy: An Indian Perspective”, in Kanti Bajpai, Huang Jing and Kishore Mahbubani(eds.), China-India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2016, p.59.针对两国间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平主义者认为这是印度缺乏全球竞争力的表现,需要在国内解决。桑贾亚·巴鲁批判莫迪的“自力更生”政策片面聚焦中国,忽略了真正使印度脆弱的因素不是贸易依赖,而是人力资本不足。(86)Sanjaya Baru, “It’s Not Trade Dependence that Makes India Vulnerable but Inadequacy of Its Human Capital”, The Indian Express,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post-coronavirus-world-pm-modi-economic-relief-package-nirmala-sitaraman-pms-woods-fms-trees-6408584/, 2020-05-14.针对印度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选择问题,和平主义者认为莫迪政府转向美国扰乱了中印关系。中国曾就阻止印度加入美国阵营作出努力,但未取得任何结果。(87)Prem Shankar Jha, “China-India Relations under Modi: Playing with Fire”, China Report, Vol.53, No.2, 2017, p.163.目前,中国已经被美国及其盟友包围,它希望深化其周边安全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反西方的左翼人士则认为,印度的舆论正在被西方话语钳制,印度沉浸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虚假自豪感中,全然忘记了中印共同的帝国主义侵略历史。印度同美国不可能有共同的事业,印度需要识破帝国主义的阴谋,拒绝成为棋子。(88)Abdul Rahman, “India Should Not be a Pawn in US Imperialist Efforts Against China”, People Dispatch,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0/07/05/india-should-not-be-a-pawn-in-us-imperialist-efforts-against-china/, 2020-07-05.因此,和平主义者认为印度应采取下列对华策略:
第一,弥合矛盾,寻找和平共处之路。和平主义者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在规模、经济和军事资源以及政治影响力均超过印度的国家,印度除了与其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目标,这必须被视为一个理性的、甚至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弥合两国矛盾,首先需要建立信任。一国的战略思维不应以对另一国的敌意为出发点,而应基于对该国的充分认识和研究以及世界秩序的结构性现实,为此印度必须摆脱对西方叙事的依赖,发展属于印度的对华专业知识和观点,印度政府应加大对中国研究的投资。其次,调整与美国的关系。郑嘉宾指出,尽管印度和美国有着共同的政治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已成为双边关系和印度全球政治战略的重要方面,但新德里绝不能夸大“美国牌”,印度的对华政策必须考虑到北京对来自美国的战略遏制的担忧。具体而言,印度必须谨慎参与涉及美国和中国邻国的多边军事伙伴关系。(89)Jabin T. Jacob, “India’s China Policy: Time to Overcome Political Drift”,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4/07/PB120601_India_Chin, 2012.再者,合作建设和平的周边区域。边界问题是两国拥有和平周边地区的根本障碍,尚卡尔·贾认为应将边界争端暂时搁置,其未来的解决需要双方作出相应妥协,现阶段两国应加强政治和经济关系,缓和边境地区局势。(90)Prem Shankar Jha, “China-India Relations under Modi: Playing with Fire”, China Report, Vol.53, No.2, 2017, p.171.最后,两国应对彼此的利益保持尊重。任嘉德认为,印度不应将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视为威胁,只要它是和平的,印度有责任确保其拥有航行自由。(91)“Increase of Chinese Presence in the Indian Ocean Is Not a Threat to India : C3S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C.V. Ranganathan IFS (Retd.)”,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https://www.c3sindia.org/defence-security/c3s-interview-on-indian-pm-narendra-modi-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s-informal-summit-at-indian-pm-narendra-modi-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s-informal-summit-at- mahabalipuram/, 2019-10-10.
第二,发展更为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构建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和平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是实用的,他们将经济合作视为两国重要的连接器,认为它具有改变中印关系游戏规则的潜力。如坎蒂·巴杰帕伊认为,中印应继续深化经济合作,以有效弥合“高政治”领域的分歧;(92)Kanti Bajpai, Huang Jing and Kishore Mahbubani, “Conclusion: Ways Forward for China-India Cooperation”, in Kanti Bajpai, Huang Jing and Kishore Mahbubani(eds.), China-India Rel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London: Routledge, 2016, p.211.郑嘉宾认为,两国经济关系必须从单纯的贸易扩大到包括投资、金融服务自由流动在内的经济合作层面,提高两国在其他领域冲突的代价;(93)Jabin T. Jacob, “India’s China Policy: Time to Overcome Political Drift”,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4/07/PB120601_India_Chin, 2012.任嘉德则强调改善两国的文化关系,包括促进更多的人员交流,改善历史遗留因素的心理投射。(94)“Increase of Chinese Presence in the Indian Ocean Is Not a Threat to India : C3S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C.V. Ranganathan IFS (Retd.)”,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https://www.c3sindia.org/defence-security/c3s-interview-on-indian-pm-narendra-modi-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s-informal-summit-at-indian-pm-narendra-modi-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s-informal-summit-at- mahabalipuram/, 2019-10-10.在全球层面,和平主义者认为两国必须合作建立一个支持各自增长雄心的国际秩序,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正外部效应。如果这两个亚洲邻国能够将自己的崛起转化为其他国家的新机遇,解决彼此在这一进程中的分歧,那么它们各自的增长和双边合作将带来全球利益。
四、中国战略界的回应
近年来,针对印度战略界对华的各种声音和中印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国战略界也产生了相应的印度观,它们是在传统认知基础上的演变和发展。传统上,中印之间存在相互认知的错位,即中国战略界并未像印度视中国为世界大国那样把印度也视为同等大国,这导致了安全认知的不对称。即使在印方把中国视为主要安全威胁的时候,中国也没有把印度当作主要的防御对象,因为中国的战略重点从来都没有定位在西南方向。(95)随新民:《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75、184页。如果说印度被中国感知为威胁的话,那也是前者多边或结盟关系的副产品。在地区层面上,约翰·加弗(John Garver)指出了中国对印度的核心看法:印度是一个企图统治整个南亚-印度洋地区及其所有国家的有霸权抱负的国家。(96)John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18.随着印度不断显露出发展潜力和权势野心,北京现在越来越关注印度通过外交举措和军事建设来争取大国地位。(97)Yuan Jingdong, “The Dragon and the Elephant: Chinese-Indi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0, No.3, 2007, p.133.目前中国战略界对印认知观点可大致分为三派:传统友谊派、矛盾不可调和派以及平行崛起派。
(一)传统友谊派
传统友谊派基于中印同为世界级古老文明、拥有被殖民的共同命运、都是当前具有独立意志大国的认识,秉持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主张两国以和平、稳定、繁荣为根本目标,不让边界分歧扰乱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传统友谊派对待印度颇为同情,因此总体上是宽容的。他们认为印度频频对华示强的根源既寓于历史的创伤和相对实力弱小造成的自卑感,是印度社会面对强者出现的自然反应,(98)《张晟、龙兴春:为何印度反华情绪强烈,中国却没有反印?》,环球网,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3zLRjG2mLOV,2020-08-05。也是莫迪政府迫切的内政需要,是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表现。对于印度在边界上不时表现出来的战略投机行为,传统友谊派提倡“小惩大诫”,对待印度应“立足和、不怕拖、不怕打”,(99)《大变局之下,中印如何打破边界僵局?》,《新京报》2020年9月29日。但不能影响中印友好关系的大局,更不能将其继续推向西方阵营。郑永年指出,尽管中国在国力上远胜印度,但仍必须将其提高到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高度,加强对印度的学习和研究,进行多轨道对话,增进两国关系,防止印度与他国结成对中国不利的联盟。(100)郑永年:《不要把印度推向美国的怀抱》,全球化智库(CCG,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http://www.ccg.org.cn/archives/58252,2020-08-04。
同时,传统友谊派普遍认同,印度的地位和外交战略绝不允许新德里成为美国坚定不移的追随者。(101)Mao Jikang, Li Mingjiang, “Between Engagement and Counter-Jedging: China’s India Strategy”, Maritime Affair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of India, Vol.15, No.2, 2019, p.9.有学者认为,“印度不可能轻易成为任何大国的盟友,中国人了解印度文化,看到了与中国价值观的相似之处,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成为西方的工具”。(102)Shaun Randol, “How to Approach the Elephant: Chinese Perceptions of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entury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34, No.4, 2008, p.218.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平衡行为是“一厢情愿”,印度从来不听美国的话。作为洲级国家和古老文明,印度和中国都不会让任何人把它们当作工具,它们有自己的议程,印度与中国有着同样的目标,即在未来成为多极世界的一极。(103)Shaun Randol, “How to Approach the Elephant: Chinese Perceptions of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entury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34, No.4, 2008, p.218.陈定定和龙兴春等从收益的角度分析,认为印度不太可能倒向美国,甚至一定程度倒向美国对中国影响也不会太大,因为印度目前的实力还无法支撑其对美国作出实际承诺。(104)Dingding Chen, “Why China Doesn’t See India as a Threat”,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2/why-china-doesnt-see-india-as-a-threat/, 2015-02-02;《大变局之下,中印如何打破边界僵局?》,《新京报》2020年9月29日。
由此,传统友谊派认为,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底气,适当争取印度,但也不应采取“以美划线”的立场,印度成为美国的盟友,也并不意味着其必然是中国的敌人。(105)《对话林民旺:中印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吗?》,人大重阳网,http://www.rdcy.org/index/index/news_cont/id/682776.html,2020-09-30。对于印度的战略野心和战略投机,中国必须在保证两国关系基本面健康的前提下给予有力反击,最终目标是将印度置于对华有利的位置上,同时保持战略理性,不至于简单地认为中印能够成为盟友。
(二)中印矛盾不可调和派
矛盾不可调和派认为,抗衡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的既定战略。印度目前充斥着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对华友好氛围荡然无存,破坏了中印关系中既有的诸多共识。它正在从狭隘的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中印关系,拒绝与中国共同崛起,试图强迫中国承认印度的大国地位以及退出其南亚势力范围,并利用中美战略竞争的利好外部环境“反华”和“遏华”。尤其是洞朗对峙以来,印度的自信行为促使中国战略界重新评估其战略能力和决心,改变了对印度在地区秩序中地位相对较低和静态的看法——印度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中国在亚洲的最大威胁,中印关系是仅次于中美关系的重要双边关系。文富德指出:“我们对印度崛起不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否则将会如印度人所提醒的那样,‘自食苦果’。这应该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世人的重要忠告。”(106)文富德:《理性分析“不可思议的印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9期。
在边界问题上,矛盾不可调和派认为印度仍在采取“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将中国的克制当作理所当然,并企图迫使中国接受印度的领土主张。印度在东西两段边界线上拒不让步,不懂交换,想要利用有利的国际局势迫使中方完全按照印方意志解决边界问题。有学者表示:“印度方面在麦克马洪线争议地区的灵活性对于公正、可接受并最终解决这一长期问题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印度会采取灵活的态度,因此我认为边境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107)Shaun Randol, “How to Approach the Elephant: Chinese Perceptions of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entury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34, No.4, 2008, p.216.
矛盾不可调和派认为,印度已经超越传统“不结盟”策略,正在配合美国走上一条军事上遏制中国、经济上“去中国化”的道路,充当着反华急先锋。美国正在拉拢印度,而且印度出于某些原因喜欢被拉拢作为平衡中国的力量,在军售防卫、“印太战略”、经贸投资等方面加速向美国靠拢。美国现在似乎对中国的发展歇斯底里,因此把印度作为一种工具来减少这种焦虑。对印度来说,这是其作为新兴力量令人满意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可以加强其在中美印关系中的议价能力。太和智库指出,印美关系走近几无悬念,虽然莫迪本人不喜欢美国,但并不影响其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之机最大限度挖掘印度的战略价值。国防战略和安全专家更注重美印防务合作的实质内容,如国防工业合作、军售以及信息和情报共享,这很可能导致印度陷入无法拒绝的制度化合作框架中。(108)Yun Sun, “China’s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India”, War on the Rocks,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3/chinas-strategic-assessment-of-india/, 2020-03-25.
总体来说,矛盾不可调和派认为中印较量将是反复持续的,就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8期研究报告中指出的,尽管中印国家战略的完全协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两国在亚洲机器系统中的飞速运转犹如两枚齿轮,齿轮与齿轮在接触的过程中会摩擦出“不和谐”的火花,但却造就了稳定的“动态啮合”状态,同时也推动亚洲机器的运转。(109)蓝建学:《新时期的中印关系: 现状、趋势及对策》,CIIS研究报告第8期,http://images.china.cn/gyw/zhongyinguxi.pdf,2015年3月。中国只可在中美大国博弈中给予印度适当的位置,直到中国国力超越美国,并将印度远远甩在身后,新德里才会接受中国的战略胜利,两国的竞争才会出现下降趋势。
(三)平行崛起派
平行崛起派认为现存的体系中有足够的空间供中印两个大国共同崛起、共同发展、互相依赖。中国和印度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重要非西方参与力量,两者力量的变化能够推动体系均衡性质的改变。有学者指出,中印崛起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的逻辑是相同的,引起的美国的反应也是类似的,但两国均不追求破坏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平衡,因为它们都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可以说中印都能接受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中被认可为全球大国。同时,由于两者均不是当前体系的创立者和主导者,所以不存在中国担心印度成长为挑战国际体系之国家的问题,只要印度不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并不会对印度的行为持异议。因此,不论是对国际体系,还是对双边关系而言,中印的崛起都不是零和博弈。(110)Zhao Gancheng, “The Rise of Chindia and Its Impact on World Syste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https://www.iddri.org/sites/default/files/Evenements_materiel/20070707_Zhao_riseofchindia.pdf, 2007-07-07, pp.4-11; Shaun Randol, “How to Approach the Elephant: Chinese Perceptions of Ind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entury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34, No.4, 2008, p.222; 赵干城:《中印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潜质与衍生》,《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 荣鹰:《“莫迪主义”与中印关系的未来》,《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另有学者则认为,虽然目前两国关系已陷入结构性发展瓶颈,到了非重构而难以重启的地步,但突破这种困境的唯一路径是两国建立起“分行于相邻车道的车际关系”,并在前进途中交流互动,互伸援手。(111)胡仕胜、王珏:《印度对华示强外交的行为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7期。
针对美印关系快速发展,平行崛起派认为目前的外部环境确实有利于印度。有学者指出,印度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处境较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战略深度合作。但印度崛起最大的问题是发展问题,这不能仅靠地缘政治投机解决,或靠别人扶持帮助。(112)荣鹰:《“莫迪主义”与中印关系的未来》,《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这一派战略人士因此强调对印度的警惕和阻止印度与其他国家结成反华同盟,但同时认为印度是可以争取的合作伙伴。另有学者认为:“印度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大可能具有助力中国的正面意义,但中国仍需要从大局出发制定促进稳定的策略,同时也需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印度应该被视为潜在的合作伙伴,中国应致力于促进和塑造与印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亦有必要应对印度将中国视作主要对手而来的各种消极现象,全力遏制将中印关系导向对抗的趋势。”(113)赵干城:《中国周边战略中的印度因素》,《国际展望》2014年第2期。
平行崛起派认为印度赶超中国的策略短期内无法实现,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挫败其野心。目前中美战略竞争是中印关系走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若能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印度的战略空间就会减少,进而同时依赖中美。同时,俄罗斯也可发挥中间调停的作用,适度调节中印竞争的力度和方向。在此背景下,中国可在适当的情况下同意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总体来说,三派战略人士正确地指出了中印关系的问题,但重点强调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由此而走上敌视印度的道路。他们能够超越地缘政治竞争的局限,站在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层面审视各自的发展战略,坚信中印对外部良好发展环境的要求是共同的、中印友好的实利是真实的(114)郁龙余:《“龙象共和”是否可能——论中印关系现实困境及发展前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9期。,这些因素决定了两国最终将走上正确的相处轨道。
结 论
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论争将继续激烈进行,极端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及和平主义的对垒反映了印度战略界对华认知既有非理性的激进色彩,也有基于经济理性的现实倾向和基于非暴力原则的理想主义。从目前印度主要战略智库和主流新闻媒体的公开文本来看,极端民族主义正在占据论争的上风,在数量和激进程度上都超过实用主义及和平主义。中印爆发边境冲突进一步为极端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养料”和发挥空间,实用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虽然不在少数,但很容易被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淹没。尽管如此,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和平主义和实用主义均曾是印度战略界的主流思想,并在成功实现印度的独立和经济腾飞中发挥了作用。因此,印度战略界的主流外交思想及其对华策略是处在动态变化中的,当前主导思潮的策略实施遭遇困境后,战略界将不得不作出调整。
推动实用主义向极端民族主义演变的三个因素——国际格局变迁、民族主义上升及“中国威胁论”上升——若发生变化,将促成新一轮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其强度和方式将会有所不同。中美趋向高强度广范围的竞争符合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大国矛盾打压中国、谋求私利的企图,这也将推动中国战略界越来越趋向“矛盾不可调和”的思想,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反之,中美竞争趋向缓和时,印度对美国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战略思考就将向实用主义回归。此外,印度执政党树立理性的政治目标和治国理念,推动印度自身战略定位革新,将有效减少国内民粹主义及“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从而推动战略界对华策略向实用主义转变,此时中国战略界也将转向传统友谊派和平行崛起派,这有利于两国建立良性的竞争关系。和平主义思想的实现主要依赖中美力量对比和中印绝对实力差的扩大,只有当印度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已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取得胜利、印度无力再与中国抗衡时,其国内战略界才会转向与中国建立深度的伙伴关系,甚至依附中国。
中印战略界对彼此形成的三派外交思想具有互相牵引的动能,构成潜在战略互动,即一国对他国决策过程和意图进行识别,并基于此形成己方的战略思想。中印战略界相互作用可形成三种战略互动模式:“威慑”“接触”和“绥靖”。“威慑”模式适用于双方均认为对方具有高度侵略性的情况,假设成功遏制另一方扩张即可迫使其和平化。双方获得安全的方式是通过威胁要对另一方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来实现。(115)Robert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31, No.2, 1979, p.292.印度战略界以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引发“威慑”模式,推动印度内部硬制衡力量和外部联盟及伙伴关系的建设,导致中国战略界相应地作出政策反应,包括将印度视为中国在亚洲的最大威胁,警惕其大国野心和美印联盟,双方均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基础设施建设以相互威慑。这是一种持续敌对和危险的战略互动模式。中国战略界对政策的合理运用将有助于两国“接触”和“绥靖”模式的启动。“接触”模式根据一国计划投入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力资源的程度可分为追随、“接触+遏制”和积极遏制,具体到中印战略界则可归为“接触+遏制”模式。平行崛起派支持印度崛起,但主张通过稳定中美关系来限制印度的战略空间,这对印度实用主义思想极具吸引力,它重视中印战略对话和经济合作的同时也主张印度保持与其他大国和国际多边机构的关系以平衡中国。在这种模式之下,两国对彼此的意图存有一定信任,能够给予彼此相应的发展空间,是一种较为理性的互动模式,是两国当前最有可能实现的状态。“绥靖”模式指的是在互惠的基础上、以符合现状政策的方法来处理国家间关系。这种模式需要传统友谊派和和平主义者共同努力,中国传统友谊派以保证中印友好关系大局为底线,对印度持宽厚态度,为印度战略界的和平主义者提供论据,有利于提升其在国内的话语权。此外,两派人士都支持加强对彼此的研究和学习,推动多轨道对话,这也有利于两国关系健康面的扩大。因此,“绥靖”模式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战略互动方式,是两国应最终达成的目标。
第三方因素,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对外策略也会对印度战略界的对华策略产生深刻影响。当前,美印关系的核心目标是制衡中国,可以预测,中美关系的走向将直接决定美国对印政策,因此,美国作为强力介入的第三方国家将是中印关系的长期影响因子。美国的介入方式包括以共同民主价值观和地区利益趋同作为前提,以经济援助和防务合作为具体策略,并辅以地区联盟体系的构建。两国基本达成了“准盟友”关系,这一方面催化了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情绪,使其不断鼓吹向美国靠拢;另一方面也促使实用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发出警告和反对的呼声,从而在印度战略界引起论争,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同时,美国战略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士认为印度是亚洲的不稳定因素,其实现美国“期望”的程度受制于诸多结构性因素,(116)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高级研究员、南亚项目负责人萨米尔·拉瓦尼(Sameer Lalwani)指出了四个结构性限制因素:印度的经济和军事能力有限,印度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与美国不同的优先事项,核武器限制了印度对威胁的看法以及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促使它进行对冲而不是追随美国。参见Sameer Lalwani, Heather Byrne, “Great Expectations: Asking Too Much of the US-Ind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2, No.3, 2019, p.50。因此主张与印度构建务实和弹性的双边关系,这种策略也必然推动印度战略界实用主义的再次兴起。
俄罗斯作为印度的传统军事合作伙伴,一直起着平衡美印关系的作用,尽管俄罗斯退居印度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但印度对其产生的“路径依赖”将继续发挥惯性。此外,上合组织、中俄印三方会谈机制等也为俄罗斯调解中印关系提供了平台。因此,俄罗斯作为中印间一个重要的第三方大国,其对华和对印策略左右着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2020年10月22日,在俄罗斯智库“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普京对中俄关系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两国理论上建立联盟的可能性,他表示中、俄、德三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并未提及印度这一名副其实的南亚大国,(117)“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64261, 2020-10-22.间接体现了普京对印度向美国倾斜的不满。同时与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关系冷淡不能不使印度战略界进行严肃的地缘政治思考,进而推动其趋于理性,为极端民族主义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