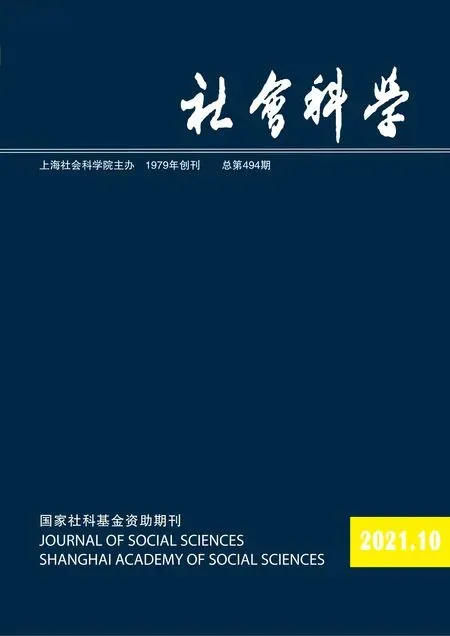冷战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一项理论评析
尹继武
国际政治心理学是运用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国际政治、外交决策问题的一门交叉性学科。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政治心理学、对外政策分析学者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开始领导人人格的精神分析,此后的研究聚焦领导人的人格、认知与情感等基本命题,进而应用于外交决策、国际冲突、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等诸多议题领域。(1)关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及其代表性著述,参见张清敏:《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基本评估》,《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期。二战以后,受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影响,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主流逐步走向认知偏差研究,当今以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代表的认知研究流派成为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广受学术界认可的主流路径。(2)[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6年版。从理论与方法来源来看,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受到心理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的影响,早期定性案例分析成为主流,冷战结束后,随着定量与实验研究在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普及,当下的方法选择越来越走向混合方法。此外,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受国际政治事件的主导,较多的研究问题均与美国或相关大国当下最为关注的国际政治问题相关,比如,冷战时期美苏的核威慑问题、大国战争、冷战后的恐怖主义问题等。
基于此,经典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聚焦领导人的人格与认知等传统心理学变量,以外交决策作为核心命题,契合美国外交及美苏核威慑等冷战时期的战略环境,探讨领导人政治心理的国际政治影响。随着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巨大变化,以及政治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新,当前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已出现了系列的理论进展,体现为经典命题的深化、研究议题的扩散、微观战略心理命题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演进和不同地区经验的重视等。(3)欧美学界关于国际政治心理学最新研究进展的综述,参见Joshua D. Kertzer, Dustin Tingley,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Paradigm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2018, pp.319-339。因此,本文基于冷战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路径和脉络的辨析,对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研究进行一项比较分析,提炼当前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前沿以及方法特色,也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探索性思考。
一、领导人政治心理学:人格、认知与情感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传统与主流分析对象是国家领导人,相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均将分析单元聚焦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和国家而言,微观理论一直呼吁有必要将领导人带回到国际政治研究中。(4)Daniel L. Byman, Kenneth M. Paullack, “Let’s Now Praise Great Me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4, 2001, pp.107-146.二战结束后,随着欧美国际关系学界逐步开展领导人的政治心理学研究,早期的经典研究已形成了三个流派,即人格分析流派聚焦领导人的人格特质与结构的分析,或使用精神分析,或运用定量文本内容分析;(5)Jerrold M. Post,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ill Clint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二战后领导人政治心理学的认知偏差研究,成为国际政治心理学早期研究的主流范式,杰维斯是认知流派的主要代表,也是最具开创性的集大成者。(6)杰维斯的个人学术历程回顾,参见Thierry Balzacq, Robert Jervis, “Logics of Mind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 Journey with Robert Jerv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4, 2004, pp.559-582; Nicholas Wheeler, “Interview with Robert Jerv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8, No.4, 2014, pp.479-504; Robert Jervis, “Polit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2018, pp.1-19。这体现为他关于错误知觉的经典研究,以及外交信号投射的开创性研究。(7)[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6年版;[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在领导人情感与情绪的早期研究中,较多学者认为情绪是理性的一种损害因素,无助于领导人外交决策中的正确判断、认知与决策。随着冷战后国际格局以及战略对抗的重大变化,国际政治心理学关于领导人政治心理的研究,在承继传统的人格、认知与情感分析的基础上,在这三个领域都有较为系统的前沿探索。
(一)领导人的人格分析
自乔治夫妇关于威尔逊总统的人格精神分析之后,似乎奠定了这一传统的经典研究方法标准。(8)[美]亚历山大·乔治、朱丽叶·乔治:《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张清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从理论来源来看,精神分析学说引入后并未成为领导人政治心理分析的主流。国际舞台上领导人的数量增长不多,研究对象数量以及不可接触性等,促使领导人人格分析并未成为国际政治心理学尤其是冷战后研究的前沿与主流。尽管如此,政治领导人研究仍有所推进,体现为冷战期间,在理论探讨上,格林斯坦(Fred I. Greenstein)从行为体必需和行为必需等角度论证领导人及其人格特质是否重要,(9)Fred I. Greenste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Problems of Evidence, Inference, and Conceptu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关于领导人人格分析的相关方法,尤其定量的内容文本分析技术,开始在赫尔曼(Margaret G. Herrman)等学者的推动下得以系统化运用。(10)Margaret G. Herrman, Thomas W. Milburn (eds.), A 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冷战结束后,在较为极端的冷战核威慑的巨大结构压力消解后,领导人个性因素的作用其实得到了提升,相关研究进展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的扩散。经典的领导人人格分析,主要聚焦的领导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总统,有单个案例的人格分析,也有系统性的总统性格类型学分析;(11)[美]詹姆斯·巴伯:《总统的性格》,赵广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另一类则是其他一些国家有着较为独特个性,对相关国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国家领导人或民族领袖,经典研究对印度甘地、德国希特勒的性格与人格探析较多。(12)[美]埃里克·埃里克森:《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吕文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美]沃尔特·兰格:《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程洪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冷战结束后,领导人人格的研究对象,聚焦美国及相关国家最新的国家领导人,比如克林顿、奥巴马、特朗普、拜登等成为重点人物,尤其是特朗普的独特人格特质引发了关于美国总统人格分析的热潮。相关研究聚焦他的超级自恋性格特质,以及不羁善变的核心特质等维度,进而分析其人格特质对于团队决策、官僚文化以及对外政策的影响。(13)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当然,其他一些较为重要的国家领导人,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总理默克尔、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等也受到较多关注。(14)比如,关于安倍晋三的人格特质分析,参见张勇:《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外交评论》2017年第6期。在全球政治走向民粹主义的同时,强人政治受到国际政治研究的重新关注。另外,由于冷战后恐怖主义的兴起,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关于本-拉登等主要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领导人的人格特质分析,也成为当下领导人人格分析的重要对象之一。(15)Jerrold M. Post, Narcissism and Politics: Dreams of Gl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Jerrold M. Post, The Mind of Terrorist: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From the IRA to Al-Qaed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7.
第二,研究方法的多元。早期关于领导人人格特质的分析,主要运用精神分析学说以及相关定性分析框架,偏向从已有领导人的言行中提炼出相关的性格特点。随着人格心理学的方法,以及政治心理学关于领导人人格分析方法的创新,一些定量的分析方法受到推广并得到使用。一方面,以赫尔曼等为代表的早期学者,结合政治情境,提炼出领导人人格特质分析的相关维度,比如权力、控制感、信任感、群体偏见等,将社会层面的人格特质结构进行了政治特质转换,进而基于相关的全球领导人数据库建设,提炼出人格特质分析的“远距离文本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受到政治心理学界的普遍认可。(16)Margaret Hermann, “Assessing the Personalities of Members of the Soviet Politburo”,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6, No.3, 1980, pp.332-352; Margaret Hermann,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 A Trait Analysis”, https://socialscience.net/docs/LTA.pdf.近期,美国心理学家运用精神分析的深层心理和动机剖析,提炼出特朗普的核心和主要性格特点,即超级自恋,(17)Dan P.McAdams, The Strange Case of Donald J. Trump: A Psychological Recko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但主流的领导人人格特质测试仍运用文本内容分析,或采用专家测试方法。比如,美国心理学家关于特朗普、拜登等人的人格特质的文本内容测试受到广泛关注,即通过系统搜集美国主流媒体关于特朗普、希拉里和拜登的报道,进行精神诊断的编码测试,从而得出相关领导人的核心人格特质得分,结合相关政策、言行进行行为预期。(18)Aubrey Immelman, “The Leadership Style of U. 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orking Paper, No.1, January, 2017, https://digitalcommons.csbsju.edu/psychology_pubs/107/; Anne Marie Griebie, Aubrey Immelman, “The Political Personality of 2020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Joe Biden”, Working Paper, No.1, August, 2020, https://digitalcommons.csbsju.edu/psychology_pubs/130/.尹继武等人通过美国问题专家的系统化问卷测试,也提炼出特朗普的五个人格特质维度,并指出不羁善变是最为核心的特质,而拜登的最大性格特点是对于环境压力的敏感性和脆弱性。(19)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李宏洲、尹继武:《拜登的人格特质及决策特点》,《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2期。
第三,研究主题的变化。传统领导人人格分析集中于“是什么”的描述性层面,即所研究的领导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大的性格特质是什么?更进一步,国际政治分析中必须揭示相关领导人性格特质发挥作用的条件与机制,比如,领导人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对于外交事务的兴趣程度、是否存在可以重塑环境的条件等。冷战后的领导人人格研究进展,一方面,在传统的人格稳定性基础上,有研究侧重于领导人人格的变化性,即在什么情况下,领导人的人格特质会发生变化,尤其是产生负面的决策、政治后果。这些条件包括时间变化、权力位置的拥有等,对于领导人的时间观、权力主导性、决策的理性等均产生重要影响。(20)Juliet Kaapbo, “New Directions for Leader Personality Research: Breaking Bad i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2, 2021, pp.423-441.另一方面,领导人的人格特质在于差异性,因此,在传统的五大人格等经典人格维度的基础上,当前有研究聚焦在战略决策情境中,领导人人格特质的差异性及其国际战略后果,比如,领导人的“自我控制”(Self-monitoring)信念的差异,会产生不同领导人对于外部声誉压力的追求与敏感性差异。(21)Keren Yarhi-Milo, 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二)领导人的认知分析
以杰维斯为代表的认知学派,重点探究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领导人的认知局限及其偏差,并讨论了其可能的形成机制与来源。所以,国际政治认知偏差研究重点考察领导人在认知能力、信息有限、压力决策、时间紧迫等诸多内外因素限制下可能产生的错误知觉,如杰维斯所总结的“统一性知觉”、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愿望思维、认知失调等。(22)[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6年版;Robert Jervis, How Statesmen Think: The Psycholog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杰维斯深受认知革命的影响,侧重探讨认知偏差形成的认知机制,即已有认知结构形成的信念与预期,会让领导人形成思维定势、认知结构,从而领导人看到的就是所预期看到的,领导人的认知受到自身的信念与预期的影响,体现出强化既有认知、忽视新信息合理性的认知相符特性。后续的讨论,很多聚焦杰维斯所总结的认知偏差在美苏冷战起源、战争历史类比等重大决策中的作用。(23)Deborah W. Larson,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第一,新的认知偏差及其来源。冷战结束后,随着认知革命在心理学的深入,杰维斯早期的认知偏差类型及其形成机制探究,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知识创新以及解释新事实的需要。因此,新时期认知偏差研究的进展体现为在有限理性的限定下,探究领导人认知偏差的新类型及其外交决策与国际政治后果。这些认知偏差类型,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借鉴行为经济学的重要行为心理学成果、以前景理论为代表的相关认知心理学最新成果,在国际危机、战争决策等国际政治研究中受到重视。前景理论的相关决策心理,比如损失规避、冒险心理、禀赋效应等,在领导人决策中也体现得较为明显,相关研究聚焦美国对德国希特勒的战争决策变化、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等案例。(24)Rose Mcdermott,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Michigan, 1998; 林民旺:《选择战争——基于损失规避的战争决策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在此基础上,人类决策的两种系统,即理性系统和直觉系统,也得到关注,在多元启发决策理论中有较好的应用。(25)韩召颖、赵倩:《国际危机中的领导人决策行为分析——基于多元启发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4期。此外,受中国战略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启发,相关研究探讨中国在处理争端、解决双边关系矛盾中出现的一种新型错误知觉类型——单边默契,这是一种基于各自不同理解和预期的错误知觉,即一种虚幻的默契。(26)尹继武:《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尹继武:《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一项理论性探讨》,《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1期。这种错误知觉在中国处理边界问题与相关国际争端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第二,认知偏差的理性功能。杰维斯确立了国际政治认知偏差分析的基本范式之后,关于错误知觉的战略功能便以其负面的效应为主,即领导人的错误知觉会使两个原本没有战争意图的国家因错误知觉而走向战争的结局。这也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安全困境现象。从研究逻辑来看,认知偏差的负面战略决策后果是主流。从经验现象来看,领导人的错误知觉更多产生了错误的战略判断与决策,从而引发非本意的冲突。但是,仍有部分学者关注认知偏差所可能具有的理性功能,从而形成认知偏差的适应性功能的分析视角。比如,在特定条件与问题领域,错误知觉与国际合作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如果行为体彼此忽视对方的非合作信号、意愿,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美丽的”错误知觉而形成的合作。(27)Eric Grynaviski, “Necessary Illusions: Misperception, Cooperation, and 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Security Studies, Vol.19, No.3, 2010, pp.376-406.如果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关于战争、博弈等“积极的幻觉”,很可能会对领导人的战争中止、合作形成等意愿产生促进作用。(28)Dominic D. P. Johnson, Overconfidence and War: The Havoc and Glory of Positive Illus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如果领导人在特定问题上形成了虚假的单边默契,至少在短期内,将会激发领导人达成短期合作的愿望,从而促进双边关系的进展,将争议问题搁置一边。(29)尹继武:《单边默契、权力非对称与中印边界战争的起源》,《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尹继武:《“单边默契”与中美战略合作的演进》,《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尹继武:《中国南海安全战略思维:内涵、演变与建构》,《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4期。综上所述,关于认知偏差的战略理性功能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成为领导人认知分析理论进展的重要内容,相关案例也多见于安全与战略决策领域。
(三)领导人的情感分析
领导人情感分析的第一阶段,强调领导人的理性与决策会受到自身情绪与情感的错误干扰,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与决策。这也是受到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理性人假定以及情感与情绪无益于理性的观点的影响。因此,在早期关于情感与情绪的讨论中,更多将领导人自身的情感作为有限理性的一种来源,或者是“受驱动的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的背后原因和机制。(30)Irving L. Janis, Leon Mann,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勒博(Richard Ned Lebow)在关于国际危机的经典研究中(31)[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赵景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总结出领导人自身的情感、政治需求以及愿望对错误知觉的形成有重要驱动作用。比如,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尼赫鲁对中国战略决心的低估也是受此影响,他自身的民族主义情感、政治需求和文化荣耀感等都是重要的推动要素。
第一,作为战略工具的情感。领导人的情感与情绪,对于他的政治需求与判断会产生扭曲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情绪与情感是需求产生的内在驱动力,需求与偏好是可变化和可塑造的。这种研究路径仍将领导人的情绪与情感看作一种干扰与非理性要素,而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界,越来越强调领导人或国家的情感与情绪实际上能够发挥理性的战略功能,因此,情绪与情感的理性战略研究成为新近领导人政治情感分析的主流。
在理性主义的逻辑下,外交的目标在于投射印象、传递意图,改变对方的政策和行为,因此,领导人和国家会综合运用各种外交工具与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32)[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相比,情感外交手段是一种通过领导人和国家的情感表演,从而传递相关战略信息与目标,这些战略信息包括战略决心、敏感性、战略意图等重要的国家间博弈信息。理性选择理论则强调,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国家难以确定彼此的信息、意图和偏好,这是因为理性国家的战略欺骗产生信息不对称。(33)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s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3, 1995, pp.379-414.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即使国家面对信息对称的情境,仍会产生错误知觉;另一方面,国家需要通过情感的表演来表达相关的战略信息,从而博弈双方形成在特定议题上的战略敏感性、原则底线共识。郝拓德(Todd H. Hall)的研究遵循此种理性主义的逻辑,强调在特定议题上,领导人和国家会通过愤怒情感、内疚情感、同情情感的表演,通过情感外交塑造情感的共同氛围,从而形成在特定战略议题上的信息认识与偏好互动。(34)Todd H. Hall, Emotional Diplomacy: Official Emotions in International Stag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遵循理性主义的路径,相关研究突出国家可能对于民族主义情感的利用,以此作为国家处理外交争端的一种谈判工具。与此相反,也有相关学者持情感本体论世界观,认为特定的民族主义与社会认同情感,是相关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民众构建“我们是谁”这种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要素。(35)Jessica Chen Weiss, 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eter H.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第二,作为理性必要的情感。上述将领导人或社会的情感作为一种外交策略与工具,仍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体现。基于情感的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国际政治心理学界逐步接受了情感对于理性的重要重构作用这一观点。西方哲学的传统将情感与情绪看作理性的对立面,即使情感外交的理性策略路径也是基于一种工具理性。然而,情感与情绪作为人类基本的心理体验,与人的理性能力和价值密不可分。这种认识的突破主要来源于国际顶尖的情感神经科学家的实验及其观察。(36)[美]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殷云露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以达马西奥(Antonio G. Damasio)为代表的神经科学家,在系列的临床观察中发现,如果一个病人由于生理病变,从而丧失了相关的情绪与情感能力,那么,这是一种符合“理想类型”的“理性人”的自然实验场景。然而,在系列的历史和当下的医学观察中,他发现,如果病人丧失了情绪与情感能力,那么,他的理性决策能力受到极大的伤害,简单的日常决策则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成本效应分析,而社会规范与伦理的遵循也会受到影响。基于此,情感神经科学家提出了重构情感与情绪的理性基础的命题。这为国际政治和外交决策中重新思考情感的理性价值带来了基础性的理论支持。
受此影响,关于领导人情感与情绪的理性本质分析,成为近年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界有关情感研究的前沿。(37)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4, 2004, pp.691-706.受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相关研究的启发,比如镜像神经元的发现,重新揭示了人际信任、共情中面对面交流机制的重要性,相关学者探究了面对面外交对于领导人建立初步信任感、发出昂贵成本的信号(比如签订约束双方的协定)的重要性。面对面外交是领导人之间意图领会、建立信任的重要渠道,而情感的神经科学研究为此提供了微观的心理学机制。(38)Todd Hall, Keren Yarhi-Milo, “The Personal Touch: Leaders’ Impressions, Costly Signaling, and Assessments of Sincerit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3, 2012, pp.560-573; Marcus Holmes, Face-to-Face Diplomacy: Social Neuro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另外,建立在情感的进化理性基础上,也可以重新探讨一些传统的情感类型对于人际、国际关系的重要适应性功能,比如恐惧对于国家生存是重要的(39)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 No.3, 2008, pp.451-471.,恐惧作为一种负面情感,虽然会对领导人的理性决策产生负面作用,但对于领导人及国家的生存却发挥着重要的理性适用性价值,而信任也有重要的适应性价值,它是国际合作、领导人之间友谊建设的重要渠道。(40)Earl Gammon, “Affective Neuroscience,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2, No.2, 2012, pp.189-219; Jacek Kugler, Paul J. Zak, “Trus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Neuro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teven A. Yetiv, Patrick James (eds.), Advancing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83-114.
二、战略互动的政治心理学:微观命题的深化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应用集中于国际安全和外交决策等高级政治领域,所以,传统上领导人的政治心理学大多为外交决策与国际冲突研究。冷战结束后,关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研究兴起,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也转移到新的议题分析中,包括新近的大国战略竞争、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除了外交决策之外,政治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更多聚焦战略互动,比如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过程,包括信息传递、意图辨析、偏好塑造、承诺策略、声誉逻辑等环节。(41)David A. Lake, Robert Powell(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基于此,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心理学,在战略互动研究领域的外交信号、战略心理等命题上,深入推进理论与经验研究。(42)Emilie M. Hafner-Burton, Stephan Haggard, David A. Lake and David G. Victor, “The Behavioral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1, No.S1, 2017, pp.s1-s31.
第一,外交信号的理论研究。(43)Robert Trager, “The Diplomacy of War and Pea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2016, pp.205-228; Christer Jonsson, “Diplomacy,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ing”, in Paul Sharp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Diplomacy, New York: Sage, 2016, pp.79-91.外交是国家间利益谈判与问题解决的过程,除了外交制度、文化等宏观研究之外,外交信号的传递逻辑成为政治心理学与外交研究结合的重点方向之一。自杰维斯具有开创性的理性主义研究之后,外交信号的理论研究遵循两种基本的路径,即理性主义和社会心理路径。
在费伦(James D. Fearon)的系统性推进之后,理性主义的外交信号研究开始成为外交信号传递可信性的核心解释逻辑。(44)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 No.1, 1997, pp.68-90.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外交信号的可信性在于其所承载的代价或者成本的展现,这种成本必须具有不可逆性,或者体现为如果违反则会带来较大的代价,这种代价表现在物质层次,在政治情境中更体现为政治代价。成本信号或昂贵信号,成为理性主义者观察外交信号可信的重要基础,其成本来源于两种方式:其一是自我约束的“自缚手脚”,其二是不断投入的沉没成本。在经验分析中,观众成本往往成为领导人确立外交信号可信的成本方式之一,尤其在民主政治国家。(45)Kai Quek, “Four Costly Signaling Mechanis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15, No.2, 2021, pp.537-549.依据杰维斯的分析逻辑,但凡国家或领导人作出的声明或行动,都是国家的外交信号,其可信来源于是否真实反映了行为体所传递的能力、意图等属性,因此,更为符合行为体标志(Index)的外交言行更具可信性,比如领导人自身的个性特征、国家的重大战略投入、私密场合的信息等,都成为可信性更高的信号。(46)[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与理性主义的逻辑相反,社会心理学路径关于外交信号可信的分析逻辑,着重强调一些非昂贵成本的信号表达方式、信号载体等,也能达到增强可信性的目的。这些非昂贵成本的信号确立方式有很多,典型的如面对面外交、内部协调与协商、隐蔽行动等。比如,面对面外交在传统的外交方式中并不受到重视,因为其具有欺骗性、秘密性等特点,这导致面对面外交更容易被看作是一种廉价外交方式。然而,郝拓德等学者的研究表明,面对面外交实际上能够确立领导人之间的初步情感联系和信任,正是这些信任情感使得领导人对于彼此的意图,尤其是合作意图,有着较为确定的把握,从而能够从各自的合作利益出发,签订具有较高代价的合作协议。(47)Todd Hall, Keren Yarhi-Milo, “The Personal Touch: Leaders’ Impressions, Costly Signaling, and Assessments of Sincerit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3, 2012, pp.560-573; Marcus Holmes, Face-to-Face Diplomacy: Social Neuro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在中国关于合作信号的表达中,有研究也提出,中国对美的合作信号,由于内在昂贵成本等并不突出,有较多的话语与外部声明的信号,但是,中国的话语以及中美之间关于合作意图的私下协商,也具有相应的成本与代价,因为也面临着较大的内部不同声音的压力。(48)Brandon K. Yoder, Kurt Taylor Gaubatz and Rachel A. Schutte, “Political Groups, Coordination Costs and Credible Communication in the Shadow of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4, No.3, 2019, pp.507-536.此外,秘密行动虽然是国家实施的特定战略行为,具有不可公开性,因此,理论上更多将其看作一种内部的干涉或者战略信息的表达,但其也能够传递可信的外交信号,因为它具有军事行动的代价。(49)Keren Yarhi-Milo, Austin Carson, “Covert Communication: The Intelligibility and Credibility of Signaling in Secret”, Security Studies, Vol.26, No.1, 2017, pp.124-156.
第二,战略心理的微观研究。如前文所述,虽然谢林在早期就对战略互动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理论论述,他从博弈论的简单数理逻辑出发,讨论了冷战期间大国核威慑等战略互动的行为逻辑。(50)[美]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王水雄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版。但将政治心理学应用于战略互动的微观细致逻辑,从而切入不同的战略心理命题,比如战略决心、声誉、信任、承诺、意图、偏好、风险决策等,则是近些年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特点。这些微观层次战略心理命题的理论研究,深化了当下战略研究的心理学微观视角,同时也与理性主义的战略互动研究有着较好的契合,因为战略互动的主流研究路径实际上是上述命题依据博弈论等形式模型的理性主义研究。
战略决心成为近些年国际政治心理学的重点理论研究命题。相关研究重点提炼了领导人判断、观察与知觉对手决心的基本理论依据,比如理性主义的成本代价论、声誉论的过去行为论、基于实力基础的物质主义论等。也有研究从决心声明的解读入手,系统性批判传统的行为论、声誉论等存在的不足,从而提炼了一种领导人观察对手的决心声明是否可信的理论依据,重要的一点在于对手是否有着坚决贯彻执行决心的相关外交行动能力,这种能力既有客观的国家军事与战略能力,也包括能否克服国内否决者的压力等。(51)Roseanne W. McManus, Statements of Resolve: Achieving Coercive Cred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也有相关研究探究了决心的认知偏差所造成的冲突效应,这种低估冲突决心的认知偏差,与传统的错误知觉理论以及理性主义冲突起源论均有所不同,而且如果把战略决心看作自变量,那么,战略决心是动态演变的,受到外部环境和领导人自身人格特质的影响。(52)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
自默瑟(Jonathan Mercer)开创性探究了声誉形成的悖论之后,关于战略与安全研究中的声誉逻辑讨论,已形成了诸多理论流派,比如过去行为论、行为体的执行能力论等。(53)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在声誉的形成逻辑中,乐观主义者坚持认为,从行为塑造开始,增强声誉兑现的能力及其执行决心,都可以保持较好的声誉记录。但悲观主义者则认为,领导人或国家追求盟友的声誉很多可能是徒劳的,只会增加国家间冲突。关于声誉形成的动力与来源问题,不同学者的看法存在差异,比如,唐世平坚持结构主义解释,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本质,造成国家间关于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从而国家间声誉的形成和维系是艰难的。(54)Shiping Tang,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14, No.1, 2005, pp.34-62.微观论者则关注领导人的内在特质差异,比如,不同领导人对于“自我控制”信念的程度不同,从而造成不同领导人对于外部声誉的敏感性差异。(55)Keren Yarhi-Milo, 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此外,声誉对于国际合作也有促进作用,国家会依据不同的观察视角与线索,评估对方是否具有相关国际合作的声誉记录,从而影响国际合作中关于对方意图确定性的判断,这在国际经济合作中较为明显。(56)Michael Tomz,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overeign Debt across Three Centu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上述战略心理的专题化研究不断深入,实际上反映了国际政治心理学的重要特点,即理论聚焦点在于决心、声誉的可信性及其机制,分野在于理性主义的成本代价论以及社会心理学的认知或情感捷径论。具体到承诺可信问题上,领导人或行为体对于彼此的战略决心以及声誉的判断,是基于对手的决心、威慑等积极或消极信号承诺是否可信。进一步而言,防御性现实主义着重强调战略再保证(Reassurance),这对于彼此意图可信的确立是十分重要的,化解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成为战略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核心机制,背后的不同理论假定及其逻辑存在差异。(57)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林民旺、刘丰、尹继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尹继武:《国际安全困境的缓解逻辑——一项理论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期。
第三,战略文化的特质研究。战略文化作为一国特定的战略思维及其策略方式的集合,既与相关领导人的人格与认知风格相关,同时也结合了国家的战略决策实践分析。战略文化的传统研究聚焦美苏等大国的战略竞争议题,分析苏联领导人的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以及大国关于攻防的战略思维及其手段选择,进一步形成了关于进攻性还是防御性战略文化的争辩。(58)Jack L.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1977,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ports/2005/R2154.pdf.近些年,关于中国战略文化与思维的实证研究,体现了国际政治心理学介入战略的宏观思维层面的努力,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外交及其文化、政治经验的适用性。
冷战期间,关于中国战略文化及其与武力使用关系的讨论,成为西方中国外交研究及其政治心理路径的核心问题,大多数路径持中国进攻性战略文化的分析,而中国文化路径学者提炼出较为独特的文明型国家形态,以及中国外交中关于面子、等级秩序、天下秩序等世界观想象。(59)Chih-yu Shih, The Spirit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Lucian W. Py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冷战结束后,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进入更为实证化的阶段,并形成了进攻性与防御性战略思维的争辩。一方面,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在《文化现实主义》中系统论证了中国“未雨绸缪”式的战略思维,从中国古代的兵法典籍以及战略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倾向于进攻性的现实主义战略文化。(60)[加] 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朱中博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与此相对,王元纲在汲取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同样基于明代等相关的战略实践分析认为,中国在权力对比、实力对比中的优势与劣势位置,实际上决定了中国是否采取武力等进攻性战略手段,这是一种实力地位决定的战略思维。(61)Yuan-kang Wang, Harmonious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另一方面,关于中国防御性战略文化的研究也得到较多支持,典型如冯惠云等人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操作码分析,较为系统地描绘了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世界观,在基于国家领导人的文本内容分析基础上,提出即使中国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等,都体现出较为强烈的防御性战略文化特质。(62)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后续冯惠云等人还对中国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操作码进行了系统性文本内容剖析,指出中国领导人战略文化的防御性特质。(63)Feng Huiyun, “Is China a Revisionist Pow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2, No.3, 2009, pp.313-334.
为了超越上述关于防御性还是进攻性战略思维的传统争辩,有研究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领土边界争端问题上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处理相关领土等主权争端的“搁置”思维,这实际上是一种为了解决问题,在无法形成真正共识的情况下,追求单边默契与共识的特定战略思维——单边默契战略思维。(64)尹继武:《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尹继武:《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一项理论性探讨》,《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1期。这在中国处理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中美建交关于台湾问题的处理、中国南海议题处理、中日建交关于争议的处理等问题上表现明显,而且单边默契有理性的和习惯的两种基本类型,能够短期内促进国家间合作,解决分歧,但长期会激化矛盾产生冲突。(65)尹继武:《单边默契、权力非对称与中印边界战争的起源》,《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尹继武:《“单边默契”与中美战略合作的演进》,《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尹继武:《中国南海安全战略思维:内涵、演变与建构》,《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4期。战略思维的提炼与问题解决、决策风格以及文化习惯等特质相关,对于理解特定国家的战略决策以及国际冲突等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也是政治心理学应用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体现。
在理解中国的战略思维方面,也有将分析单位聚焦特定的领导人,比如分析中国不同代际领导人的人格特点,辨析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在外交事务兴趣、信息开放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辨析其对待国际社会的不同态度。(66)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进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认知风格、类比思维等也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使得中国对外关系中领导人的决策、认知风格具有较强的文化特性。(67)张清敏:《隐喻、问题表征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2期;张清敏、潘丽君:《类比、认知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另一方面,在宏观思维层面,文化特质成为理解中国国家形式、对外关系决策方式、中国国际关系及其秩序观的基础,基于心理人类学的视角,中国的国际关系观有着自身的文化理性,区别于西方的国家理性特质,比如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形式、集体主义式理性以及天下秩序观等。(68)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中国台湾)南天书局2010年版。
三、冷战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进展的特性
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其研究进展体现为领导人人格、认知和情感三个层次,同时在战略研究领域有着较为重要的应用。从理论和方法特点来看,相比于冷战时期的经典研究,在研究单元、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文化特性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特性。
第一,研究单元的更新。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开创了领导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单元,同时也结合了冷战时期最为重要的核威慑、大国战略决策、国际危机等议题。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单元,仍然聚焦最为传统的领导人政治心理,在人格、认知和情感三个层次继续推进理论问题和知识创新,并结合最新的领导人案例,同时体现了三个重要特点:其一,领导人的心理重要性得到加强。与经典时期聚焦宏观的人格、认知和情感要素不同,当前关于领导人的政治心理学,聚焦结合了理性主义的分析单元,比如领导人的偏好、信息、风险意识、决策方式、意图理解等更为微观的命题,这在最近的《国际组织》(IO)专刊的主题中体现得较为明显。(69)Emilie M. Hafner-Burton, Stephan Haggard, David A. Lake and David G. Victor, “The Behavioral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1, No.S1, 2017, pp.s1-s31.其二,战略互动与决策的命题是集中议题。这也与理性主义关于战略互动的研究命题相结合,理性国家关于私有信息的相互传递及其解读,成为理性战略博弈的基本预设。与此形成理论逻辑争辩,政治心理学探究在这一理性国家预设以及战略信息理性传递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非决定性,而相关案例聚焦传统的大国战略竞争以及新时期中美等大国关系。(70)尹继武:《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其三,外交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外交及其沟通心理学,成为当下国际政治心理学聚焦的中观和微观层次,既与领导人的人格、认知与情感要素相关,同时也结合了外交信号的表达及其可信性分析。外交信号、外交谈判等议题彰显了国际政治心理学脱离传统的外交决策、国家间关系分析,走向外交行为的实质性分析。(71)Dan Hart, Asaf Siniver, “The Meaning of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Vol.26, No.2, 2021, pp.159-183; 熊炜:《外交谈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二,研究议题的时代特性。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始终与当下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相关。传统国际政治心理学主要聚焦大国外交决策、国际冲突等议题,随着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迁,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议题的时代特性表现明显。比如,结合最新的国际社会现象,相关热点研究议题不断成为政治心理学介入的分析对象。比如,冷战后不断出现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国际战争与干预等,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地区战略热点等,都成为重要的分析议题,随着大国权力转移的加速,中美在战略竞争过程中的意图信号等议题也受到关注。(72)近期基于大国战略竞争的意图、决心信号的解读研究,参见Kyle Haynes, Brandon Yoder, “Offsetting Uncertainty: Reassurance with Two-Side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4, No.1, 2020, pp.38-51; 尹继武:《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外交评论》2020年第5期。
第三,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特性。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研究方法较多体现了传统特性,比如外交史案例、领导人案例等。在领导人人格特质分析中,赫尔曼等学者也系统开展了文本内容分析。在主流的认知学派研究中,关于错误知觉及其对于领导人外交决策的影响,仍采用定性判断及案例分析方式。(73)Alexander L. George,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Chaim D. Kaufmann, “Out of the Lab and into the Archives: A Method for Testing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8, No.4, 1994, pp.557-586.冷战结束后,研究方法的多元与混合是一种重要趋势,尤其在领导人心理变量的测试以及心理因素如何产生影响的因果关系判断中,定量的回归分析、实验研究、文本内容分析等是重要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技术。尤其在领导人的人格特质、政策偏好等内隐变量的测试与度量过程中,相关的人格心理学、偏好测定的技术与方法不可或缺,比如,在特朗普等领导人的政治心理研究中运用较为广泛的操作码,在测试领导人的认知风格与人格特征时,成为政治心理学广泛运用的方法。进而,由于领导人的不可接触性,相关领导人政治心理及其作用逻辑的推论,要么来自历史经验的案例观察,要么来自大学生的室内实验归纳,因此,实验方法在提炼领导人的行为心理与决策偏好及其规律时运用较为广泛。(74)Rose Mcdermott,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 No.1, 2002, pp.31-61.总之,当前的国际政治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已走向多元与混合方法阶段,在前沿性的研究中往往包括了传统的案例分析以及新近的定量与实验等技术方法。(75)最新出版的著作都综合使用了多元方法,参见Keren Yarhi-Milo, Who Fights for Reputation: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第四,政治心理的文化特性受到关注。(76)当前欧美国际政治心理学界关于文化差异的讨论并非主流,但在中国学者以及全球国际关系和对外关系研究中,文化差异对于政治心理的丰富作用的研究较多,参见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and Jack S. Lev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经典研究,案例经验与文化特性大多为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领导人的案例以及外交决策案例,主要是美国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决策,体现了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特性。由于人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文化性,所以,经典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与命题,实际上具有较高程度的普适性。领导人的人格特质分析维度与技术、认知偏差的基本类型,以及情感的基本类型及其战略效用等,具有跨文化规律性。然而,随着全球国际关系概念及其学科构建的倡导,以及中国外交经验和政治心理要素的融入,政治心理的文化特性及其在外交与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
这种文化特性体现为两个层次:其一在理论假定层面,文化要素的纳入,改变了基于西方经验与文化中心主义的有限理性假定。(77)尚会鹏:《人、文明体与国家间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有限理性的来源,传统上并不包括文化差异的要素。然而,心理文化特性的纳入,彰显了文化理性、习惯理性的特质,从而使得理性的逻辑具有文化情境。在此假定之下,不同国家领导人的行为逻辑未必遵循统一的经济理性及有限理性逻辑,而是具有相应的跨文化差异。其二在经验层面,国家的领导人及其对外政策、行为,体现出相应的文化差异性。比如,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西方理性国家的行为逻辑在于“成本-效用”分析,而有限理性强调目标的理性和程序的有限理性,在文化理性的假定下,非西方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行为逻辑,实际上并非以“成本-效用”作为行为逻辑,而可能是其他的文化特质要素,比如面子、情感表演、自我投射、政治需求以及关系平衡等。(78)Chiung-Chiu Huang, Chih-yu Shih, Harmonious Intervention: China’s Quest for Rel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这些文化理性逻辑与传统的经济人有限理性逻辑有着较为一致之处,也有差异之处。总之,非西方经验的纳入,使得领导人、国家政治心理的类型及其政治作用逻辑更为丰富,在现实中也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理性限定。
结 语
综上所述,国际政治心理学在经历冷战时期的经典与传统研究阶段之后,理论与经验研究进一步进入学科的成熟发展阶段,这直接表现为研究议题的细致与深化,从探究政治心理要素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定性判断,到进一步提炼影响机制与作用条件。在领导人的人格、认知与情感研究路径中,探究新的案例、政治心理类型以及作用机制。同时,在研究议题上也结合了传统的安全与战略研究,以及新时期出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关系现象等。综合而言,随着学科研究的细化以及中观和微观研究的深入,诸如在领导人政治心理学初创时期具有奠基性的作品及学者难以出现,更多是相关议题细化、理论研究深入的微观实证研究。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特性,即探究研究者通常所见的国际事实背后的政治心理规律及其逻辑,研究事实只是表层,而且理论概念及其方法具有较强的跨学科特性和内隐变量特性。这种微观的政治心理逻辑分析,对于充实与弥补国际关系研究的宏观层次与不可接触性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理解国际政治中人性的必需。(79)Robert Powell, “Research Bets and Behavioral I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1, No.S1, 2017, pp.s265-s277.当然,基于与现实经验问题的密切联系,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关于领导人的政治心理探究,是外交工作的基础性环节,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同时,对于外交决策心理、战略互动心理以及国际冲突心理基础的讨论,对于提高决策质量、增强战略能力、化解国际冲突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知识启发。
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中,非西方的政治心理变量以及相关案例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中国外交中的领导人政治心理学以及战略心理分析,成为未来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议题、理论创新以及政策分析的重要方向之一。(80)国际政治心理学学科发展综述以及中国研究的方向,参见尹继武、王海媚:《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尹继武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4期;游国龙、刘曦:《21世纪以来心理文化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进展与问题——游国龙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