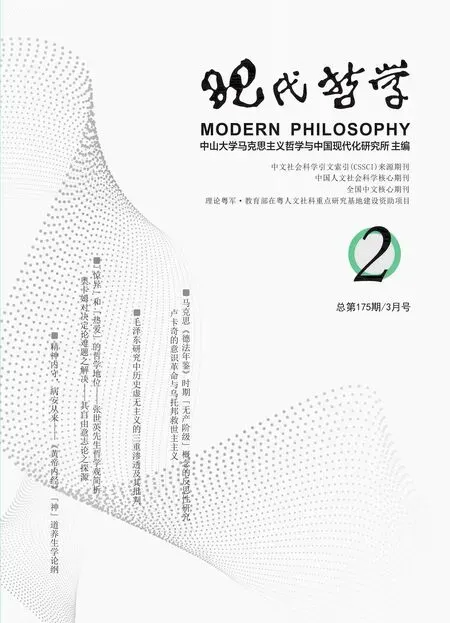从邻人到第三方政治
——论列维纳斯的“伦理-正义”的同构性与困境
林华敏
列维纳斯的思想常被冠以“伦理”之名,其伦理的核心努力也多被解读为对我与他人的“面对面”之原初关系经验的考察。这样的原初关系是前意识和存在之外的,是超越和形而上的。这导致列维纳斯的思想往往看起来是一种暧昧的、不可见的、晦涩的哲学(玄学)。但不论是对列维纳斯的“伦理”化,还是“暧昧”化的解读都可能是有失偏颇的,没有反映列维纳斯思想的全貌。在超越的、形而上的伦理关系之外,可见的、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维度也是他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列维纳斯在其许多文本中考察和描述了一种“面对面”伦理经验。这种经验的核心是:他人的绝对他者性对“我”的触发以及“我”的回应关系。这是一种亲密性关系。在这种亲密性中,列维纳斯指出了我与他人之间非对称的责任、爱、好客、人质、替代、无私等伦理内涵。在列维纳斯的语境中,这是一种超越、形而上的关系。因为在他那里,不论是“他人”,还是“面容”,其核心指向都不是看到的“对象”,而是那超越于“对象化”背后的绝对他性及其伦理意义的显现。当他描述这种关系时,更多地指向人与人在前意识、前存在的伦理境地。因此,这种关系更多地停留在“纯粹”“超越”与“神圣”的意义上,作为一种绝对的形而上的伦理/宗教关系,一种原初裸露的经验和绝对的关系。列维纳斯也意识到这种原初的“面对面”关系总是“成问题的”:非对称的伦理关系“它不能摒除正义,因为我与他人的关系不是一种与单个人的关系。总是有第三方,第四方,因为事实上我们在一个复数的社会中,在与他人之根本关系上,正义是不可摒除的,是叠加其中的”(1)E. Levinas, Is it Righteous to Be? Interviews with Emmanuel Levinas, ed. by Jill Robb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4. “Le Tiers, the third”有译为“第三者、第三人、第三方”等。本文统一译为“第三方”。。
因此,对列维纳斯思想的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面对面伦理”层面。可以说,在列维纳斯那里,第三方与正义问题从一开始就内在于面对面关系之中,是伦理的重要补充、调校和上升。这是列维纳斯思想关键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有许多问题需要梳理和澄清:面对面与第三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否先出现“我”和他人的关系,之后才出现第三方,才有我和第三方的关系,才有正义问题?第三方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并且调校着“面对面”关系?如何既爱邻人又爱所有人?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嵌在列维纳斯思想的基本结构中,是理解列维纳斯思想的关键。本文将尝试梳理从亲密关系到第三方、正义的内在逻辑,凸显正义问题在列维纳斯思想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与伦理的高度同构性,最后指出列维纳斯的政治理论存在的不足与面临的批评。
一、他人与“第三方”——亲密性与正义的同构性
我们往往认为在列维纳斯那里,“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伦理关系是原初关系,它具有优先性,并将对列维纳斯解读的重心放在我和他人的“面对面”伦理关系。然而,这个“重心”并没有完全呈现列维纳斯基本的思想图景。事实上,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异于存在,或本质之外》《正义与否?》等文本中都清晰表明在原初的伦理关系之外,他对第三方与正义关系更为深切的关注。这种关注显示了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向“政治”层面的一个内在伸展:从不可见到可见,从前意识到意识,从异于存在到存在,从言说到所说,从无端到秩序,从历时性到顺时性,从“面对面双方”关系到“多方”的关系,从爱到正义,进入到哲学、理性、国家、秩序等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延伸。这个阶段的思想主题,用列维纳斯的话说,“在话题之中和所说之中变为可见”(2)[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伍晓明译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78页。注:本文引文主要参照中译本,个别表述结合法文与英文版进行了文字调整。。它不仅揭示了列维纳斯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维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列维纳斯的思想从“暧昧”走向“明晰”。从这些文本中,我们看到列维纳斯在“面对面”伦理和第三方正义这两个议题上的重要论述和转换,以及对二者重叠关系的论述:一方面,他明确肯定面对面的伦理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正义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对这种关系提出“质疑”,指出第三方、正义关系与面对面关系的同构性,它作为伦理关系的发生域,从一开始就介入并调校着面对面的伦理关系。
首先,要指明和肯定的是列维纳斯对亲密性关系的强调和论述。列维纳斯的思想开显了人与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伦理维度,这是纯粹的、超越的、甚至是神圣性的维度。他的许多表述都明确强调这种关系是社会关系(包括正义、国家和制度等)的基础和条件:“如果那给予正义之人没有发现自身处于亲密性(proximity)之中,那么正义就是不可能的。”(3)同上,第 371页;E.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trans. by A.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9.“基于亲密性,正义、社会、国家及其制度、交换与工作才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要从亲密性出发去重新发现所有这些形式。在亲密性中,存在、总体、国家、政治、技术、工作这些事物每时每刻都处在这样的点上——在自身之中获得重力的中心,为自身的事物而权衡。”(4)同上,第371页;E.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p.159.“对己之遗忘(无私)推动了正义。”(5)同上,第372页;E.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p.159.
在列维纳斯那里,他人的临近以及由此唤起的非对称的责任,这是一种原初的伦理关系。它推动着正义成为可能,乃至于作为正义、社会、国家及其制度等的基础和前提。这是列维纳斯思想的基本立场和思路,体现了伦理关系在列维纳斯思想架构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即便他在其他语境中强调了正义的地位和意义,正义的出现也没有减少、限制或消解这种亲密性的伦理意义:
正义绝非困扰的某种降级,不是利他的某种消退,不是对无端的责任的某种减少和限制,不是对于无限所具有的荣耀的某种抵消……“多”之同时性系于两方之历时性:正义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中才能保持其自身为正义——这里没有远近亲疏之分,但这里也没有走过最近之人却掉头不顾的可能;在这里,所有人相互的平等由我与他人的不平等所负载,由多出我之诸权利的我之诸责任所负载。(6)同上,第371—372页;E.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p.159.
列维纳斯主张“单纯和直接的对他人的责任是所有的正义的基础和要求”(7)E. Levinas, Is it Righteous to be?, pp.55-56.。第三方和正义的提出并没有减少、限制、消解伦理的责任,正义只有在伦理的社会之中才能保持为正义。可以说,这是列维纳斯基本的思路,也是其对伦理与正义关系的基本主张。
其次,在面对面伦理关系之外,要指出的是列维纳斯对第三方和正义的论述与强调。在列维纳斯那里,面对面是伦理的,但这是一种封闭的理想关系,它必定被打破。如列维纳斯所言,“所有的爱——除非它成为法官或正义——都是夫妻(两方)之爱。封闭的社会是夫妻(两方)”(8)E. Levinas, Entre Nous: Thinking of the Other, trans. by Michael B. Smith and Barbara Harshav,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1.。在他人之外,还有诸多第三方;任何的他人都是诸多他人之中的他人,不仅存在我对他人的责任,还存在我对诸多第三方的责任以及他人与第三方的责任等问题。列维纳斯指出:
具体的处境是更加复杂的,因为我从来不是与一个人打交道;我总是与许多人打交道,因此,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处境的背景也必须被考虑在内。那就是限制,不仅是对我的责任,而且是对我的行动的限制,它调整我的义务的模式……在他人的面容上,我听到对他的责任……但是,第三方伴随着到来:新的责任。除非某人能够通过一个清晰和正确的判断去决定他们俩人中哪个是优先的。我必须比较他们,给予计算。这是正义的全部问题。我称它为第一个暴力:在那关切中,去识别他人的面容,即拒绝只看到面容。(9)E.Levinas, Is it Righteous to be?, pp.55-56.
我们知道,列维纳斯在其形而上伦理中考察了存在和对象化意识之前的纯粹经验,并由此描述了一种异质性的他人(绝对他者)与我之间的超越——无条件的回应(责任)关系。对于列维纳斯,在这种超越关系中,伦理、宗教和形而上学是共通的,只有通过这种超越,才能打破存在和意识意向性对他人的总体化暴力。这种通过悬搁与还原所获得的经验,就是列维纳斯常说的“原初经验、纯粹经验、绝对经验”。理论上,这种通过还原之后的“我-他人”之间的“原初”关系没问题,但它总是已经伴随着诸多第三方的存在并成为“问题”。
如果亲密性仅仅是他人对我下命令,那么将不会有任何问题,即使是一般意义上的问题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疑问将不会诞生,意识也不会诞生,自我意识也不会诞生。对他人的责任是先于一切问题的直接性,它是亲密性。当第三方进入,责任被扰乱并成为了问题。(10)[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366页;E.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p.157.
这种扰乱意味着“新的责任”以及对责任的比较与计算。列维纳斯说,这是正义的全部问题。但它也是对他人(面容)的暴力,第一个暴力。虽然“我和他人”之亲密关系是直接的、伦理的,但在第一时间变得“可以比较”和“暴力”的。实际上,这进一步表明了“面对面”的纯粹关系并不能真正搁置第三方的在场。反过来说,列维纳斯之所以要通过现象学悬搁与还原回到纯粹经验,就是因为从一开始,第三方的在场就已渗透和扰乱着亲密性。
由此可见,对于列维纳斯,第三方伴随着他人的临近而来,正义问题也随着伦理问题而来。二者几乎是重叠的。并且在一定意义上,第三方正义关系要“先于”面对面关系,它是人与人关系处境的“背景”和“场所”。如Rodolphe Calin对列维纳斯正义概念的解释,正义“它首先是面对面关系得以产生的场所,即是说,是负责的自我与自我对之作出回应的他人形成非对称关系的场所,这种非对称关系对列维纳斯来说构成了社会的最基本关系——伦理”(11)高宣扬主编:《法兰西思想评论》第3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0页。。这表明了第三方和正义在列维纳斯伦理思想中的高度重要性。“我-他”关系是在“多人”的社会之中发生的——两方的封闭和超越关系恰恰是在已有的多方关系的事实基础上进行纯粹化操作(对经验的还原)和去背景化的结果。
在列维纳斯那里,第三方的进入意味着意识的诞生以及伴随的一系列哲学议题。首先,在我与他人的直接的“触发-应承(责任)”关系里,意识还没有产生,它是一个“意识尚未形成”的“情感”(12)“意识”这个概念非常模糊与复杂,列维纳斯并没有清晰地界定这个概念。但从他对“第三方、正义——意识”的关联性阐述中可以得出,这里的“意识”是一种对象化、识别、比较、计算、权衡等认知行为。大抵上可以认为是理性范畴。而列维纳斯的伦理关系的核心概念是“触发”(affection),它实际上是一个情感性的概念范畴。阶段;正是第三方的介入,意识才得以诞生。真正的意识始于第三方的进入,它是社会化的结果。列维纳斯指出:“意识诞生为第三方的在场……意识乃是第三方永久性地进入面对面这一亲密关系之中……意识的基础是正义。”(13)[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373页;E.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p.160.换言之,意识本身意味着第三方在场(正义)状态,意味着识别、对象化、比较与计算。可以说,《异于存在,或本质之外》的这个基本观点显明了《总体与无限》中“面对面”的“两方”关系经验,也暗含着对德里达的批评的回应:通过第三方与正义,列维纳斯的思考重新回到意识,以及相关的再现、秩序、现象的显现,回到了存在。它们都从第三方开始(14)同上,第373页。。这种“回到”意味着列维纳斯的思想回归了哲学(希腊),不再是仅仅作为形而上学的伦理学。
列维纳斯并没有将“第三方”与“面对面”分开作为两个独立的、先后的“阶段”。这二者是重叠在一起的。“在他人的亲密性之中,他人之外的所有他人都困扰(obsess)着我,这种困扰提出了正义,要求衡量和知识,这种困扰已经是意识了。”(15)[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368页,译文有调整;E.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p.158.从一开始,在我与他人的“亲密性”中,诸多的第三方已存在并困扰着我,对诸多他人的对象化、识别与计算(意识)——即对面容的暴力——已经出现了。在亲密伦理中,正义问题几乎无法被剥离地提出。邻人与第三方、责任关系(伦理)与正义关系(政治)是同步的。基于这种逻辑,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列维纳斯何以试图通过亲密关系(爱与责任)去构建一种对所有人的正义——爱所有人和对所有人负责。在这个意义上,伦理的非对称性不仅位于我与他人的关系中,也渗透在正义关系中——正义表现为我对所有人的非对称性亲密关系,而不仅仅是与某个人的亲密关系。这就是列维纳斯经常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我们都对所有事物和所有人有愧疚,(但)我比其他所有人都多。”(16)E. Levinas, Entre Nous, p.105.它不仅意味着伦理的爱,更多地意味着对所有人非对称的但普遍的爱——正义。
按列维纳斯,第三方不同于邻人,但也是另一个邻人,而且是他人的邻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伙伴。他人和第三方,以及我的邻人(复数),他们是一起在场的,使我和邻人、和第三方之间拉开了距离。第三方总是潜藏于他人的亲密性中。从一开始,在我和他人的面对面之中,第三方扰乱了这种亲密关系,阻止我和他人的关系变得封闭,激发了一种质疑。这种质疑开启了更广阔的视野并为社会奠基——社会基于每个人对所有人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封闭的责任。如同列维纳斯常引《以赛亚书》(57:19)的一句话所示:“和平,予以邻人和平,也予以远道而来的人和平。”(17)[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367页。邻人与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并不是在空间中远近、先后出现的,而是同时在“社会”场域之中。在我对邻人负责的同时,正义已向我提出要求:一方面,要求我与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考虑到第三方,另一方面,也要求我和第三方的亲密关系顾及到其他第三方。回应所有人——公正但不是互惠——成为正义的本质。他人不仅是为我存在,他还是其他人的第三方,而且我实际上也可能是第三方。他人绝不仅是我的他人,我对于他人也是他人。
在亲密关系中,第三方的问题仅仅是被“括号”出来的,但它始终存在并且是亲密关系的发生场所和背景乃至于前提。第三方在亲密性中临近,搅扰着我和他人的“面对面”亲密关系,激发了一种关于平等的激进请求,这种请求第一时间开启了我对面容的识别、对责任的权衡——对不可见之异质性的主题化,“言说”进入“所说”。第三方从一开始就必然要求意识(理性)的诞生,并激起对第三方正义的关切。列维纳斯说:“第三人、第四人、第五人——他们都是我的‘邻人’——的出现对最初的‘为了邻人’提出了质疑……或许,一种关于社会秩序(伴随着它的混乱)和客观化的理想的诞生、机构和国家的诞生、权威的诞生,是正义的组织所必须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更多正义的社会。”(18)E. Levinas, Is it Righteous to be?, p.51.
因此,在列维纳斯的思想中,我们一方面要强调列维纳斯对言说、情感性(触发性)和超越的原初经验的描述;另一方面必须意识到,这种伦理关系经验同时必然地要求进入到意识、理性和社会政治关系中。这两层关系虽然似乎可以通过现象学搁置与还原的方法被剥离开(作为“伦理”和“政治”两个层面的议题)谈论,但实际上是同步的、无法剥离的。
二、第三方如何在场?——面容之普遍性与正义
如前所述,我与他人的责任关系总是已包含着第三方关系和正义问题。并不是先有我和他人的关系,然后才有第三方关系;也不是先有亲密关系,然后第三者出现后才有正义问题。即便第三方从一开始就伴随和嵌入在“面对面”关系中,这里还有个核心问题待澄清:第三方以什么样的方式在“面对面”之中在场?正义如何在邻人的面容之中抵达,如何真正同样地爱邻人与所有他人?对此,我们需要深入到列维纳斯关于“面容”的论述。
在列维纳斯那里,“第三方”亦非一个经验性(对象性)的概念。他的在场依然是通过“面容”实现的。一方面,面容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对象”,而是代表着他者之他者性的在场,它是超越与不可见的。另一方面,它在显示自身的同时也已经是具体与可见的:
面容扰乱我,也显示自身,在超越和可见性/不可见性之间……他人从一开始就是所有其他人的兄弟。扰乱我的邻人已然是一个面容,这面容既是可比较的也是不可比较的,既是独一的面容也是与所有面容关联的面容,这些面容在正义的维度上是可见的。(19)[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368页;E.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p.158.
列维纳斯试图表明“面容”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不可见性和可见性、亲密性和正义、他人和兄弟等双重内涵。在他那里,面容的可见性指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识别的具体的面容——在其可见性之中,面容是可以比较的,是可以被量化和权衡的。面容在通过一种绝对的感性超越(不可见性)触发我的同时,将自己展示于众人面前,被对象化和比较。在这个过程中,伦理的亲密性与正义的衡量(理性的计算)同时发生与存在。面容既是单一性与不可替代的,但面容却始终将自身显现在公共的秩序和空间中。
一般而言,面容的显现是一个感性超越事件,它发生在“面对面的亲密性中”。但列维纳斯指出,这种显现实际上无法将自己维持在“我们之间”,面容在亲密性中显现的同时,已经将自身暴露于“公共秩序的朗朗乾坤之中”(20)[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9页。。可以看出,面容这个概念保持着一种张力,它不仅启示着不可见者的他者性,而且本身具有可见性的一面。这种张力导致了“我”和他人的关系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经是“我”和所有人的关系,因为他人之面容从一开始也已经是作为可见者呈现在公共秩序之中。可以说,面容同时是可见与不可见的:不可见是其伦理属性,可见是其社会属性。在后者的意义上,面容是要被识别、判断和比较的。“对我而言,(独一的)他人被辨识出是很重要的,但由于诸多独一无二的人是一种复数性,(因此)计算与比较——这使得独一性丧失——成为必要的。”(21)E. Levinas, Is it Righteous to be?, pp.51-52.这里,列维纳斯引入另一个要素——作为面容的在场的语言。
语言,作为面容之在场,并不导致与受偏离的存在者之间的共谋性,也不导致自足的且遗忘了普遍之物的“我-你”关系;语言在其开放性中拒绝爱的秘密性,在爱的秘密中,语言丧失了它的开放与意义,变为微笑或呢喃。第三者在他人的双眼中注视着我——语言就是正义。(22)[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199页。
在列维纳斯那里,语言是对话、启示。它既是面容的亲密性在场,也是一种普遍性和开放性的在场。列维纳斯通过语言之启示,表明了面容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正是第三方得以进入、正义得以可能的条件。语言表达了社会公共层面所有人之间的开放与同一性,这种表达本身拒绝私密性,它要求开放和意义——意义本身是公开与普遍的。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他人都进入“我-他”的关系中。语言是一种临显,同时是一种在场。这已经是进入社会了。这里,诸多他人被呈现给我。诸第三方通过他人的面容临显,形成“我们”。“我们”并不是多个他人挤成一团或融为一体,而是整个人类的在场。
列维纳斯在论述面容和语言时,始终预含着一个更高的普遍性——上帝的神性。它既是面容的普遍性,也是人性的普遍性(可能性)。列维纳斯说:“面容的现象,有必要上升到上帝。”(23)E. Levinas, Entre Nous, pp.198-199.我们可以用他所引用的耶胡达·哈莱维(Jehuda Halevy)的一句话来进一步理解:“上帝以其永远的言语‘对每个人个别地说话’。”(24)[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422页。上帝通过面容对每个人单独地言说,却言说普遍的戒令。这里面既有每个独一的人与上帝的独一的关系,也有这种关系所包含的普遍性。独一性和普遍性重叠地包含在面容之中。我从独一的他人的面容中听到上帝的普遍的戒令。我面对的面容既近又远,既是他人的面容,也是人类的面容。作为复数的第三方在他人的面容之中已经进入“我”,他们已经总是对我和他人的“面对面”关系造成困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进一步理解列维纳斯常常引用的妥耶托夫斯基的“我承担起整个世界”这句话的逻辑和内涵。
《总体与无限》的一段话集中概括了面容与第三方乃至于整个人类,亲密关系与正义的内在关联:“就面容证明了第三者和整个人类在凝视着我的双眼中的在场而言,这一环节本质上是由面容的临显激发起来的。一切社会关系,作为一种派生物,都回溯到他者向同一的呈现上;这种呈现没有任何图像或符号的中介,而只是通过面容的表达。”(25)[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第200页。这再次表明了“面容”对于列维纳斯整个理论的基础性地位,这种基础性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所包含的伦理意义,而且表现为它所包含的第三方政治意义。面容不仅请求爱与责任,而且也同时请求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列维纳斯的思想不仅是面容伦理,也是面容政治。
三、结论与进一步的问题
本文聚焦于列维纳斯的面对面伦理与第三方正义之间的内在关系:一方面,尝试指出列维纳斯对面对面之亲密关系的思考与第三方正义问题是内在重叠的,我们不能只看到他对面对面伦理的论述,而忽视了第三方和正义在列维纳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间接地通过第三方正义问题,回应了德里达等人对列维纳斯思想的批评,指出列维纳斯实际上没有逃离希腊(哲学),他最后还是“重新捡起”了意识和存在,回到了所说,即回到了可见性与哲学。这是我们通过第三方和正义理论看到列维纳斯思想的另一个图景。
在1975年的一次访谈中,列维纳斯对他的第三方和正义理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概况与总结:
无论如何,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我就总是已经处于与第三人的关系中了……从此刻起,亲近性变得问题重重了:必须要比较、掂量、思考,必须力求正义,这是理论的源头。在我看来,正是缘于第三人,我们才必需重新捡起各种组织机构,重新捡起理论本身——也就是说哲学和现象学:即对显现的阐明。只有在“公正”处——而不是在我向他人的“臣服”中——才能谈得上“正义”。要想有公正的话,就需要比较和平等:那些没法相互比较者的相互平等。(26)[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35页。
这段话总结性地点明:他人和第三方、亲密伦理和第三方正义、伦理学与哲学现象学高度重叠于列维纳斯的思想中。第三方关系总是已经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正义也总是已经镶嵌在我对他人的责任中。进一步地,正是在第三方的基础上,对面容的识别、比较计算,理性与平等的规则才被需要,组织机构才被需要。这可以被认为是列维纳斯国家政治理论的基础架构。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我与他人、与第三方的关系之间的区别:与他人的关系是前理论、前哲学、前显明的范畴;与第三方的关系是理论的、哲学的、显明的范畴。从伦理到政治,“我”不再是单纯地向某个他人臣服和负责,而是向所有人臣服和负责,这是正义、社会与政治的本质。随着第三方的进入,我对他人的非对称的责任变成我对所有人的非对称责任。按照列维纳斯,这并不是限制或减少对邻人的责任,而是增加了对所有人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正义比(面对面伦理之)爱更困难,也更沉重。
我们常认为伦理是列维纳斯思想的核心。事实上,如果仅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概念出发(区别于政治而言的伦理),这个判断显得过于粗糙。从列维纳斯关于第三方和正义的论述可以看到,第三方和正义理论位于列维纳斯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位置。诚如西恩·汉德(Seán Hand)指出的:“政治位于列维纳斯所有作品的中心,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伤的背景,还是作为一种他的智性发展之一直在变动的语境。”(27)[英]西恩·汉德:《导读列维纳斯》,王嘉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4页。我们无法只关注和研究列维纳斯关于我和他者之间非对称的爱和责任伦理,而忽视其第三方和正义,乃至于背后更多的政治思想。沿着列维纳斯的思路,本文认为列维纳斯思想的中心和落脚点是寻求一种普遍性的正义,这种正义建立在对所有的他人的承认和责任之上。
在1982年一次以“哲学、正义与爱”为题目的谈话中,列维纳斯提醒道:
“不对称的主体间性”……在这个议题上,我总是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我们对一切事和一切人都是有罪的,但是我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多。”但是对于这个观点——不用去反驳它——我立即加入了对第三方和正义的考虑……如果没有正义的秩序,那么将没有对我的责任的限制。在正义上,有必要存在衡量暴力的标准;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正义,有必要允许法官,有必要允许机构和国家;在公民的世界中生活,而不仅仅是在“脸对脸”的秩序中。(28)E. Levinas, Entre Nous, p.105.
这里,我们更进一步清晰了前文所述的责任与正义的关系。如果没有正义的秩序,伦理也是不可能的。正义并不是对责任的否定和消解,而是在我和他人的责任之间加入了对其他第三方的责任。在正义之中,我的责任是增加了。基于第三方和正义,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列维纳斯的思想高度,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的普遍关切。这种关切绝对不仅是对他人之爱,而且是对所有的他人,认识和不认识的所有人、邻人和远处的所有人的爱。
可以说,列维纳斯指出了他人与第三方、爱与正义、伦理与政治之间深刻的内在关联,并试图构建一种基于伦理之上的善的政治(从对他人的非对称的责任到对所有人的非对称责任——正义)。这为现代性背景下反思理性(对等)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但是,我们也从列维纳斯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言论)中,看到他的“伦理-政治”思想的局限性与面临的批评:
第一,伦理与政治实践的“分裂”。1982年9月16-18日,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在贝鲁特的萨布拉(Sabra)和夏蒂拉(Chatila)集中营发生的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以色列军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9月28日,列维纳斯参加了一次广播访谈。在访谈中,关于这次大屠杀,列维纳斯表现出冷静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判断,他没有谴责以色列军队,而是对伦理与政治进行了某种“切割”,对他者进行了“界定”:
问:对于在萨布拉(Sabra)和夏蒂拉(Chatila)发生的事情,以色列是无辜的还是有责任的?
答:不幸的是,对于伦理,政治有其自身的辩护(justification)。
我对“他人”的定义是完全不同……在异质性中我们可以找到敌人……我们要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有些人是错的。(29)E. Levinas, “Ethics and Politics”, The Levinas Reader, ed. by Seán Hand,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9, pp.292,294.
列维纳斯没有对被屠杀的巴勒斯坦人(这一“他者”)表现出同情与责任,而是事先“切割”了伦理与政治,界定了对的和错误的、正义和非正义的他者。这种一神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冷静的政治判断,对暴力的冷漠,让许多人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感到惊讶与失望。这被认为是列维纳斯在政治上的幼稚与错误,与其伦理思想发生巨大反差。在某种意义上,这成为列维纳斯政治上的“污点”。例如,Simon Critchley认为,政治是列维纳斯的“阿喀琉斯之踵”(致命弱点)(21)Simon Critchley, “Five Problems in Levinas’s View of Politics and a Sketch of a Solution to Them”, ed. by Marinos Diamantides, Levinas, Law, Politics, Abingdon: Routledge-Cavendish, 2007, p.93.;Howard Caygill认为,列维纳斯关于他人与第三方的区分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理念,甚至于对贝鲁特大屠杀的“沉默”(冷漠)态度有着内在的关联(22)Howard Caygill, Levinas and The Political, London:Routledge,2002.p.192.。
第二,强烈的神学背景与神学(弥赛亚/乌托邦)政治的走向。本文指出,从他人的面容的普遍性到上帝的永恒的话语,从对邻人的责任到对所有人的责任——正义,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列维纳斯深刻的犹太神学背景。这点是不可否认的。这也是列维纳斯探求普遍的无条件的爱——正义——的最根本的途径。真正的普遍性只有在神那里,真正的对所有人的爱——正义——只能源发于上帝,他在邻人面容中的普遍启示与律令。进言之,政治既作为一种暴力,对面容的暴力,它何以成为一种善?对于列维纳斯,这只能依赖于一种超越于面容的普遍政治、弥赛亚政治、信仰所引导的政治。从现实的方向看,对所有人的爱与正义是伦理的至善,也是政治的至善。在这点,列维纳斯思想背后的犹太教弥赛亚思想背景逐渐浮现出来,其乌托邦色彩也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