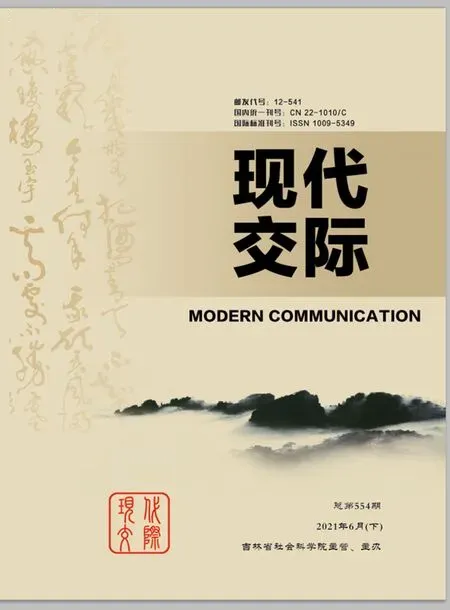探寻明清时期流人文学作品中的辽北地域剪影
张 亮
(铁岭市图书馆 辽宁 铁岭 112000)
流人即遭受流刑被流放之人,多指古代被处以免死刑罚并被发配往苦寒之地或是烟瘴之地之人。辽北的铁岭、尚阳堡两地,曾是明清时期东北地区的重要流放地,在中国流人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先后约有数十万流人从中原来到辽北,有史料可查的知名人士就达500余人。[1]谪戍到辽北地区的流人,不仅在文学、文化及教育、医药、农耕技术等领域为辽北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还在记录、描述辽北地区的民俗物产、自然风貌等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展现当时辽北地域发展历史进程的宝贵文化资源。
一、辽北地域明清时期文化流人的主要构成
文化流人是庞大流放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主要是由朝廷官员和知识分子构成。其中有触怒龙颜、舞弊犯上者,有贪赃枉法、消极怠政者,有举旗造反的暴动者,有权利斗争的失败者,等等,清朝时期更多有触犯文字狱、科场案的知识分子们被流放到此。“少年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辽东三万卫,尽是读书人”[2]114,这是明朝流人冯彻描写“辽北古城开原流人云集,知识分子成堆”景况所做的一首打油诗。清朝流人郝浴在《至日雪》中写到“安知柴水上,戍客似鱼鳞”[3]32,同样描写的是辽北流人众多,比肩接踵的盛况。流人们在谪戍地主要从事充军、戍边、垦荒的任务,但是他们在辽北地域文化发展、知识传播、民族进步等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这群文化流人为辽北大地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学作品,如因受“夺门之变”牵连被谪戍到铁岭的明朝华盖殿大学士陈循,他为铁岭留下了著名的“八景诗”及《银州重修圆通寺记》等;因犯颜进谏被流徙尚阳堡的清朝第一谏臣季开生,他留下的《尚阳堡纪事口号(九首)》是记述尚阳堡地理、民俗等方面内容的重要历史资源。此外,流人们还为辽北留下了许多被整理成集传世的诗文集,如张人纲的《集菌草》《兴会笔录》,蔡础的《沈子呓业》、孙旸的《沈西草》等。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和流放后的苦闷心境,流人们常常借诗遣怀,以敏锐的视角、广博的视野、强烈的情感,直抒胸臆,为后世留下珍贵的诗篇。辽北地域的文化流人们通过设塾讲学、吟诗唱和、道义切磋、编撰史志等形式,推动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交融进程,形成了明清时期辽北独特的文化现象,即流人文化。[4]正如余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中所言:“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二、辽北地域流人文化的发展特点
1.历史跨度大
即跨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迁移至银州古城的铁岭卫属“辽东都指挥使司”统辖的25卫之一,处于辽东边墙末端,有“极边之地”之称。以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稳定边防为目标,明廷依照“北人南流,南人北流”的惯例,开始向铁岭卫发遣罪犯,至1619年后金攻陷开原、铁岭为止,铁岭一直是明朝流徙罪犯的重要地点。[5]1929年本《开原县志》卷二《古迹》载:“尚阳堡,清初为发遣犯人之地。康熙二十一年,圣祖东巡曾诏免死人犯俱发往尚阳堡安置。”[6]113尚阳堡经历了形于后金、兴于清初、盛于顺治、缓于康熙的49年漫长流放历史。[7]132
2.地域面宽泛
辽北境内的铁岭、开原、尚阳堡、威远堡等地均曾是明清历史上的流放地,其中尤以铁岭和尚阳堡两地最为著名,这几处地点相互间距离不足百里。流放地域覆盖如此宽泛、流放地点如此密集,这在流放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虽然同是作为辽北地域的流放地,但明朝时期较为侧重铁岭,清朝时期则是尚阳堡。尚阳堡是当时盛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犯人流放地,也是被流放者中罪行相对较轻之地[8],《柳边纪略》卷一载:“尚阳堡在开原县东四十里,安置罪人始于天聪七年八月。”触犯文字狱、科场案的罪犯多被流放尚阳堡,这些知识素养高、文化气息浓的流人,为清初屯兵戍边地尚阳堡带来了文化的传承、文明的进步。
3.社会影响力宽泛而深远
辽北地区的文化流人在明清时期地域文化启迪、知识信息传播、史志文献创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推动辽北地域文明发展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清时流人郝浴创办的“银冈书院”,在当时既是流人云集纵谈名理之地,又是郝浴设塾讲学授徒解惑之处。在被赦回朝前郝浴将土地、房产、图书等资源留给了铁岭人民,成为后人的办学之资,在历时36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银冈书院为辽北培养出大批人才,周恩来总理少年时期亦曾在此接受过教育,于是这里便又有了个名字“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一门挂两牌,更加彰显出了银冈书院对后人思想文化引领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明清流人文学作品中的辽北地域剪影
流人们在谪戍辽北期间,初期是处于政治失意、生活困顿,思想所受冲击较大时期,他们常常会触景生情,仅能靠赋诗疏解情怀;后期随着对辽北地域社会生活的不断融入,流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丰富起来,他们开展了成立诗社、撰写碑文、编修史志等文化活动,如流人们时常会“陶令径开频载酒,谢公墩扫共裁诗”[3]43,吟诗唱和的流人们为辽北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辞赋,并为促进南北方文化的深入融合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由真情实感创作的文学作品,侧面展现着辽北的自然风貌、物产民俗,从不同角度记述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流人及当地民众的生活剪影,极具史料价值。
1.记述辽北的霜天雪地
北方的霜天雪地令来自南方的流人们印象极为深刻,纷纷赋诗记述。如清代人法若真《郝公行表》中的“沙流欲响,塞草不青。骨催雪冻,灰窖霜凝”[6]20,写的是初春之时尚阳堡的大风、黄沙、荒寒,短短两句诗使流人们凄苦的生活场景跃然纸上。再如孙旸在《答陈其年》中云“银州经岁半冰霜,春尽沙场草不芳”[7]111,清初时铁岭的银州古城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覆盖着冰霜,春尽夏来之时除了黄沙看不到一丝绿意。在天寒地冻中,流人们的生活越发艰辛,正如郝浴《苦中求乐》中所云“朔风暴雪弥苍天,指冻身寒夜不眠。滴水成冰无躲处,拾茅垒圈是家园”[7]102;季开生在《尚阳堡纪事口号》中同样多次提到了辽北冬季的严寒天气,如“岩风易结杯中雪,炕火难融被上霜”[7]105“凿冰十丈得泉归,却望千峰白雪围”[7]106,描写了在大雪封山的冬日里,流人们需要凿穿厚厚的冰层才能取回饮用水。这时往往是茅草屋外漫天风雪,屋内滴水成冰,被上的霜即使在火炕的烘烤下依旧是难以融化。流人们用诗歌记述了他们艰辛的生活、悲凉的情境,这些诗歌也成为考证明清时期辽北地域气候特征的有利依据。
2.记述辽北的社会形态
辽北明清时期主要的社会发展历程是由繁盛到颓败再到日渐恢复。明朝时辽北曾是人烟稠密、商业发达之地,“往来渡口船,风利乃得骋。遥遥数片帆,吹没远天影”[9]111,陈循用《蓬渡风帆》记述了铁岭马蓬沟渡口每日里帆樯如织,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周转的盛况,该诗见证了明时铁岭经济的繁荣。这一点从《辽左见闻录》中“万历初,辽东全盛,铁岭一卫,……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9]91、“盖承平日久,极天下之力,以充辽饷……繁华反胜内地”[10]等句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但是到了明末清初,受战火影响,辽北一带损毁严重,到处是断壁残垣。清《圣祖实录》载“铁岭、抚顺,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7]91。当时的辽北空旷荒凉、人烟稀少,在流人齐聚堡城之后,社会状况得以改善。“草草数间屋,言依古佛居。仅能遮风雪,大半是图书。梵唱连歌板,棋声杂粥鱼”[11]182,函可在这首《天公新构茅舍观音堂侧》诗中描述了清初古城尚阳堡虽为流放戍边地,但以满足流人生活所需发展起来的商业活动却是一应俱全的。随着清朝的日益稳定,辽北地区也逐渐转入恢复生产、重建,“多宝环收千叠翠,群湖返照一般红。玉门此日应如阔,满路春风揽辔同”[3]30,郝浴用这首《铁岭城》记述了康熙年间辽北大地始见繁荣。跨越明清两朝谪戍于辽北的流人们留下的大量诗篇,成为考证辽北地域历史发展脉络的最直接见证。
3.记述辽北的风景名胜
辽北境内拥有龙首山、帽峰山、松山(象牙山)、柴河、清河、鸳鸯湖等景观,在明清时期流人们多以龙首山和鸳鸯湖为基点,创作了许多咏颂辽北风貌的诗篇。明时流人陈循在周揽铁岭形胜后用情景交融的手法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咏铁岭八景诗》,其中的《龙首寻秋》《山郭朝烟》《柴河晚渡》《白塔横云》诗都与龙首山有关,“柴河水清浅,萦带苍烟下。夕阳唤无舟,晚渡看车马”[9]111,诗人在《柴河晚渡》诗中以动静结合的方式为后人描写了夕阳下绕经龙首山东北脚的柴河水波光潋滟、人民赶着挂有灯笼的马车从柴河渡口的浅水处往来络绎不绝、悠然自得的别样画面。鸳鸯湖是明清时期流人们非常喜爱的游览胜地,明有陈循的《鸳湖泛月》诗,清有左暐生、左昕生分别咏颂的“鸳鸯湖”佳句。“洪涛出没巨流通,扁舟明灭夕阳东。万顷茫然光霮䨴,千山倒景气鸿蒙”[12]62,左昕生的这首《泛舟鸳鸯湖》描绘了当时的鸳鸯湖面积广阔,气势恢宏。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些自然景观外,清初流人对见证历史盛衰的李成梁看花楼(又名万花楼、花楼)咏颂较多,仅笔者所见诗篇就达10余首,《辽左见闻录》载“铁岭东门外为平辽伯李成梁别墅,台榭之盛,甲于一时”[9]91,可见在明朝万历年间看花楼是铁岭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标志性建筑,后被战火所毁。“花下提戈月满楼,将军控马待高秋”[12]57“玉树琼林成废垒,琱戈锦帐忆通侯”[11]11等诗句,均是流人们睹物怀古后的有感而发,他们纷纷赋诗感叹昔日铁岭古城的繁盛、痛斥战争的残酷,表达对历史名将李成梁的景仰。
4.记述辽北的物产资源
辽北地区在明清时期林木资源较为丰富,《开原图说》云“冈峦联络,二三百里,林木丛茂”[13]。山林密布之中,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康熙本《开原县志》物产篇将老虎列为野生动物之首[14],老虎是当时威胁流人生命安全的主要因素,“葭墙频过虎,草屋任藏蛇”[7]70张恂在这首《夏日边村》中道出了流人们在谪戍地时常需要面对茅草屋外有虎频繁出没,屋内有蛇时隐时现的惊险场景。《扈从东巡日录》曾这样介绍今开原东部一带野生动物资源的分布情况,“过哈达城,城在众山间弹丸地耳。林木獐鹿甲于诸处;每合围,獐鹿数百,常开一面释之”[15]。獐鹿会时常深入流人居所“做客”,正是“野鹿来相值,闲禽坐不还”[12]70“空林峻岭鹿麋群,古戍于今静不闻”[11]161。由董国祥带领流人集体编撰的康熙本《铁岭县志》中记录了当时铁岭地区的瓜果蔬菜及主要粮食作物多达69种,如黍、稷、葱、韭、蒜、黄瓜、榛等;记述其他植被66种,如榆、槐、芍药、五味、细辛、红花等。为了生计流人们需要自食其力,辛勤劳作,“林间爵雪闻凄雁,锄下挥金种野蔬”[3]38,郝林在《重修银冈书院落成拜祀恭记》中描述了幼年时随父亲郝浴谪戍铁岭时,自力更生种植果蔬的生动场景。郝浴对辽北的主要粮食作物高粱米是情有独钟的,曾作诗《银州薥米》“薥米流脂玉液漂,东篱紫艳自妖娆。浪传茶赏强如酒,独有痴人饭一瓢”[11]101,来赞美高粱米的甘甜可口、独具特色。
四、结语
凝练的流人诗歌、辞赋,是南方文人学者留给辽北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以文字形式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饱含了流人们对辽北的热爱之情。流人文化促进了辽北地域文化的发展[16],是值得后人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整理、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