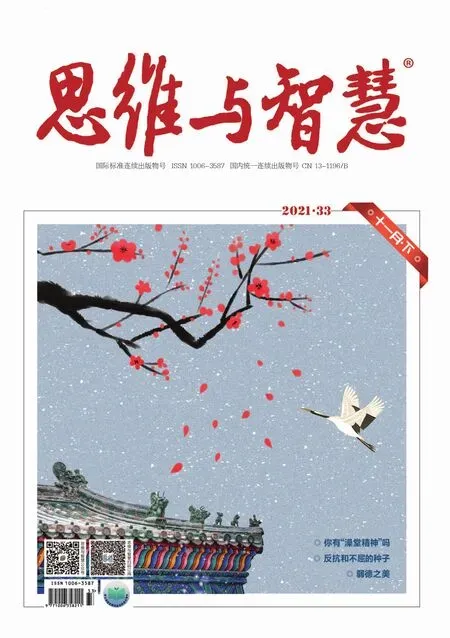反抗和不屈的种子
●张 炜

契诃夫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族,直到祖父一代才赎出了农奴身份。父亲经营杂货铺,对少年契诃夫严厉管束,让他从小站在柜台前不得离开。契诃夫回忆说,“我没有童年”,听起来异常悲凉。
《白鲸》的作者麦尔维尔十二岁时父亲病逝,他和母亲迁居乡村,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里。麦尔维尔十四五岁就投身社会谋生,干过文书、店员、农场工人,最后登上捕鲸船当了水手。
这样的作家可以列举很多,他们都有一个艰辛和不幸的童年,被伤害与屈辱的记忆跟随终生。这可以构成人们所说的写作“素材”,比起其他人,他们有更多的故事要讲。
我认识的一位有名的作家,很早就在业内赢得了名声。他生在贫穷的乡间,是被父亲从小揍大的,这位作家有了不小的成就之后,到了麦收季节要回老家收麦子。那不是收割,而是直接用手拔,那种辛苦不是现在的人能够想象的:只一会儿就要两手起水泡。
这位作家拔麦子时,因为麦根的土拍打得不干净,被发火的老父亲满地追打。父亲举着一只板凳,从这边追到那边,追累了就坐在板凳上歇一会儿。
我听了这个作家在麦地里被父亲追打的故事,笑不出来。我知道这里边有些难以言说的东西,我也说不清。不过我知道,他的写作是不可限量的。他能够在这样的年纪就取得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且之后被追打,而且是在乡亲们面前,就有非同一般的意味了。
我估计得不错,二十几年过去,这个人非但没有让人失望,还一再地引起惊讶。因为他的忍受在继续,一个长长的被虚荣腐蚀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还有更深厚的东西藏在心底,这些东西要在心里鼓胀,让他继续难过。他反抗和不屈的根扎得太深,这样的压力张力之下,他不会飘浮。
一位好的作家无论有了多么大的专业成就,多么大的名声,都不会忘乎所以。童年植下的那颗不屈的反抗的种子一直在鼓胀,试图萌发,让他不能安静。他要揭示真相,要显示力量,要将他的尊严受损的那一部分,用一生的故事加以修补。
杰克·伦敦终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刚八个月,母亲就带着他嫁给一个贫困的老鳏夫,随这个人姓。他小学未毕业就开始打工谋生,做童工,甚至做过偷海蛎子的贼,还当过海盗船的水手。他的长篇《海盗》就专门描写海上冒险。他一生的角色真是复杂,工人、流浪汉、大学生、北极圈的淘金者,还蹲过监狱。这是一个被生活蹂躏得伤痕累累的人,所以能够给我们讲出很多屈辱和挣扎的故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军医家庭,父亲购有田庄,个性极其暴躁冷酷,因为虐待田庄的农民而遭殴致死。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军事工程学校,一生都要摆脱父亲的阴影。血缘给他的东西,留下的恐惧,会在人所不知的时刻发酵。这其实是一场极特殊极痛苦的酿造。他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心潮澎湃。
《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出了最复杂的父子关系,还有兄弟之间围绕原罪、信仰的无尽辩论追究,惊心动魄,令人战栗。这种深入和诚实以及恐惧,是现代主义文学所缺乏的。关于父亲的记忆一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陷于难以解脱的折磨之中,混合着其他苦难感受,比如那场险些让他死于绞刑的案件。这阴暗与悲凄的命运融入了他的文学。
恨与爱是两种不同的力量,虽然也互有关联。我们会发现,当二者合而为一的时候,它们才是最有力量的。当恨单独地分离出来,会变得阴郁;当爱独自分离出来,会变得空泛、廉价和流于表面。爱和恨结合一体才是最强大、最无法抵御的,也是百发百中的。
(余长生摘自《意林·原创版》/图 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