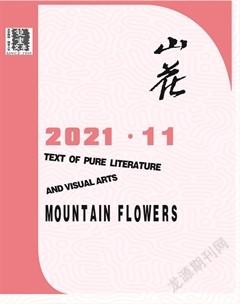父亲的树
赵以琴
1
父亲在家门前的清岩坎下种了很多树,我不知是何树。后听父亲说,这是水白杨,耐活,随便插在泥土里,它自己就茁壮成长起来了。
的确,成排的水白杨没过几年就长得丰茂起来了,生出的嫩叶绿油油真如打了油一般,我们都很欢喜。问父亲这水白杨有什么用,父亲顿了一下,笑道,这水白杨嘛——可以躲阴凉,可以占地。这占地一说与开荒性质一样。这样,我家门前的地突然之间就宽了起来,似乎清岩坎下的那条河道都是我家的了,任由我们几姊妹在河道上玩耍,在家门前淘气,也无人吼骂。地之宽、院之大,是村里各家各户无法相提并论的。
一日,天空好像被撕裂了一个洞,如柱的大雨铺天盖地而来,下得混子村人心惊胆战。村民们纷纷惊慌逃散,言说这大雨要淹没混子村,大家赶紧去高处躲避。父亲也开始周密地做着安排,让大姐搀扶祖父祖母去到外祖母家(外祖母家在混子村半山腰),趁大水还未汹涌淹没山间的各条沟壑,赶紧去。我们则随母亲去到马路坎上的操转台(播放电视的信号塔地)处,等待大雨停歇。若大雨再肆意纵横,那估计混子村就真的会消失。
但父亲不愿离开,他说要坚守到最后,若情况不对,他再逃离。我们都担心、恐惧着。还好,到了后半夜,雨逐渐小了,人们的声音也沸腾起来,说,混子村是一块宝地,老天不会收了混子村的。
第二天天明,父亲和村民们倚靠着水白杨,在浑浊的大水里捞顺水漂来的物什。有一棵特大的房屋大梁随着河水滚到了父亲面前,父亲伸出去的手抓了一个空,一滑,人落入了水中。大家疾呼,老赵,老赵,抓住旁边的水白杨树不要放。父亲紧紧抱着水白杨,使出幼年时爬树的本事,攀出了水面。父亲滑下去的一瞬间,两腿叉在一根被大水冲倒的水白杨上。若不是这棵倒下的水白杨,父亲也许就被大水淹没冲走了。
2
父亲说,洋槐花的屁股是甜的,很好吃。
我们一直深信父亲的话,赶紧用杆子挑下洋槐花,把槐花屁股上的绿壳拔去,吸吮起来。真的,很甜,我们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说父亲真会吃,就是一个香香嘴。父亲则抿嘴笑道,是也,你们老汉就是香香嘴,怎么了,不服气吗?父亲教我们吃洋槐花、吃羊子儿、吃泡儿、吃地瓜、吃茅草根,反正山间能放入嘴中的,父亲都教我们吃。
这一院的洋槐花,本是宅基地上自由生长的,后来却成了父亲的树。父亲挑选看起来精神抖擞、健康挺拔的洋槐树留下,并定期修剪丫枝,以防过于高大的洋槐树经不住风的肆虐,折断树梢,压坏青瓦、房梁,砸到睡在阁楼里的我们。
可家门前这十几株洋槐树,却发疯似的疯狂生长起来,终究还是被大风吹折了树梢。没有压坏青瓦、房梁,也没有砸到睡在阁楼里的我们,反倒是我家那一群出生不久的小鸡娃被压死了几只。母亲责备父亲说,让你砍几根树来烧火,像要你的命一样的,你看,现在倒好。
翌日,父亲剔去洋槐树上多余的丫枝,对母亲说,不能砍树,砍了我家院坝就不凉快了,不凉快鬼大二爷到你家院坝来赶场,不来赶场你的豆花饭哪个吃、你的凉粉米皮卖给哪个?是的,我家门前的一院绿,的确引来了四面八方来村街赶场的农人,都说赵家院坝是混子村最凉快、最好看的地方——开门就是洋槐树,走几步就是白杨树,再走几步就是混子大河,的确是一个极好的地方。
每到赶场天,卖鸡蛋的、卖鸭蛋的、卖大米的、卖苞谷的、卖豆子的农户提个袋子倚靠着洋槐树悠闲地卖起来;赶马的脚夫把走累的马匹拴在洋槐树上自己抽起烟来;卖猪肉的屠户卧在洋槐树下打起瞌睡来。这俨然就是一个农贸市场,对于会做生意的母亲、祖父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母亲开起了豆花饭店,祖父开起了烟酒店,父亲开起面条加工坊,这一切都要源于这一地阴凉、一院绿意。
我们几姊妹却更喜爱夜间的院子,站在树背后,用手电筒照脸装鬼吓唬彼此,六弟是被吓得最惨的一个。我们也趁夜的黑、静,爬上洋槐树,仰卧在树杈里,看明明灭灭的星星点点。用尽仅有的一点关于星空的知识,大言不惭地摆谈月宫里的嫦娥、玉兔,伐树的吴刚以及北斗星、流星等等。
无论怎样,这样的院子、这样的夜,我们是惬意的,也是舒心的。
3
四姐捡回了一把果树苗。父亲看到果树苗,哭笑不得。遂与母亲商量,把这近50根果树苗种在了后檐沟边的自留地里。自此,我家后院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果树林,最多的果树是李树,其次有些许的梨树、桃树、樱桃树,花开时分,那个香和美到如今依然挥之不去。
我们站在果林里,等待微风的到来,这样我们就能感受到下花瓣雨的浪漫。若没有风,四姐则使出洪荒之力摇动果树,我和六弟则在李子树下抬头伸手迎接花瓣,常常笑得喘不过气来。往往这时,就能听到父亲的大嗓门,吼道,你们几姊妹是憨了嘛,花瓣摇落了怎么结果果儿?我们才觉自己的行为愚蠢,立即解散队伍佯装割起猪草来。林子里蜜蜂也是不少的,六弟还被蜜蜂蜇过,哭嚷着扑到母亲怀里蹭。我家的黑虎(一只叫黑虎的狗)也在果林间疯跑,殊不知也被蜜蜂蜇了,嗷嗷叫了好一阵儿。
果子还未成熟,村里的小孩就惦记上了,总是寻着机会来摘。我们很愤怒,告诉父亲,父亲却说,那么一大坡李子,等他们摘嘛。可我们不愿意别人来摘。一次,三姐抓住一个叫肥鸡母的同村男孩,和他狠狠地打了一架。从此只要三姐在,惦记我家李子的小孩儿都会躲得远远的,他们都知道三姐是不好惹的。
六弟把还未成熟的李子摘了放在书包里,给了他的班主任。可李子涩得老师立马吐了出来,皱眉说道,你,你,你这个李子也太酸了吧。后来我们都取笑六弟。
我们把吃不完的李子摘下放入背篼里,倒进罗筛里,摆在家门前。早上还卖2塊钱5斤的李子到了下午就是2块钱6斤或者7斤了,但为了把李子换成钱,我们也不管那么多了,只要有人出钱,我们就卖,实在卖不完的就喂给猪大爷。母亲建议说,砍掉不甜不大的李子树吧,现在的人嘴巴吃馋了。父亲却又开始拧起来,说,留起嘛,开花的时候好看嘛。
4
父亲走了,家门前的一院绿色也跟着他走了,满后院的白色花瓣成了父亲葬礼上的白色纸钱。我那被岁月碾压、击碎的,我原以为不老的老父亲被我们葬在一个叫烂田湾的地方,可那里却没有一棵树,我们决定来年春天,种上一些树,一些父亲曾经种过的树。
——璧山区建立三级院坝会制度推进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