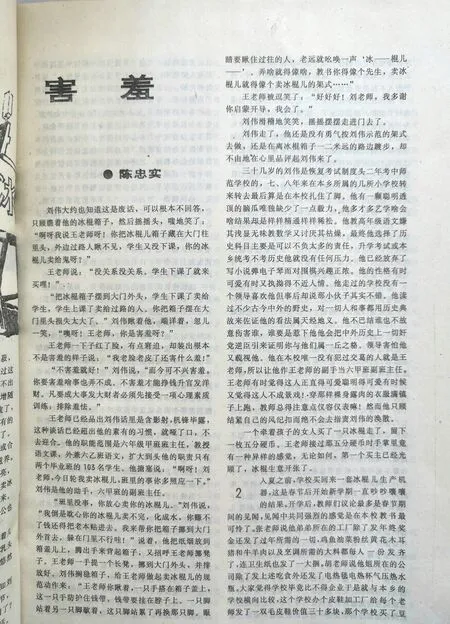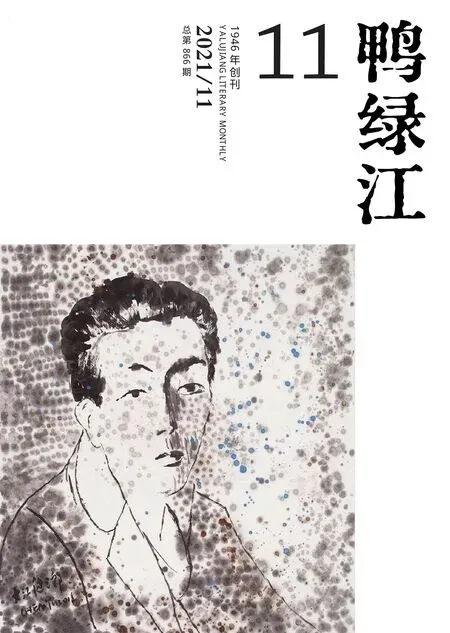陈忠实的实(主持人语)
宁珍志
1975年夏季的一个夜晚,我从辽西建平叶柏寿到沈阳太原街省军区第三招待所报到,参加辽宁省文艺创作办公室举办的创作学习班。第二天到会场,从联络员张名河(诗人、词作家)手里接过一沓会议材料,其中有两本小册子,为《辽宁文艺》(《鸭绿江》“文革”版)编印的陈忠实的两个中篇小说——一是《公社书记》,一是《高家兄弟》(均刊发于“文革”后期《陕西文艺》)。一周多的“学习班”日程安排得很满,白天听报告、分组讨论、大会发言,晚间看“样板戏”、看《春苗》、看辽宁歌舞团出国汇报演出。可我还是抽出时间,把这两篇小说看了不止一遍,自己认为好的地方还用笔画出了道道。一位三十出头的陕西基层干部的业余小说,能被《辽宁文艺》看中,当作“范本”,向全省各地的文学写作爱好者们发放,可见陈忠实的语言叙述能力委实出众。
我刚满20岁,读懂读不懂的,悟透悟不透的,即便囫囵吞枣也算完成任务了,“学习材料”嘛。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的阅读心境其实还是被一种单纯笼罩,到处是政治也就不用专闻政治了,只对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感兴趣,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故事性。借用陈忠实2008年的话来说,他的创作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时候的读,我难道在“挑选自己喜欢的句子”?第一次认识陈忠实,在语句里。翻出复读,能从当年陈忠实在政治高压下催生的“作品”中,找出生活、人性的影子,找出特殊历史时期“形势”对语言的压迫和侵蚀,找出作者紧跟时代的一种老实、严实的服从态度。这自然包括他在《人民文学》1976年第三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无畏》。《无畏》的影响面更大。
《陈忠实文集》(广州出版社,2004)没有收录上述三篇作品。陈忠实在给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畅广元教授的信中说,“文集七卷本收录1978—2003年的作品”,而“‘文革’后期的几篇小说、散文”,收录在由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评论家邢小利编的《陈忠实集外集》(西安,白鹿书院,陈忠实文学馆编印,2011)里。陈忠实的信最后说,“‘文革’中的几篇小说,今天去看,足见得当年的可笑,乃至可憎”。这是带有忏悔意味的醒悟,诚实且朴实。《无畏》之后,陈忠实不再担任西安郊区公社干部,他主动要求去了文化馆,保证自己能有相对安稳的时间,可以静下心来读一些书,“用真正的文学来驱逐、涤荡我的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寻找自己的句子》),直至《信任》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直至《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得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直至长篇小说《白鹿原》1998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其他奖项略过。
陈忠实非凡文学成就的取得,与他扎实、殷实的生活积累和文化积淀密不可分。一旦认准方向,他便蘸着自己的血、掠着自己的肉进行书写,《白鹿原》恰恰是一份生命付出的文字证明。从1973年在西安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鼓动,内心萌生写长篇的欲念开始,经过19世纪80年代几次与何启治的交往沟通,陈忠实已默默在做创作前的各种准备了。“1992年腊月二十五写完最后一句话”,《白鹿原》陈忠实整整写了六年。其间有两家出版社打探到陈忠实创作中的长篇,几次想“撬走”,陈忠实不为所动,坚守初衷,一诺千金。陈忠实回忆,自己把手稿交到何启治派来的两位编辑手上时,涌到嘴边的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竟然没有说出口,直憋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原想近50万字的长篇,初审、复审、终审,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20天后接到编辑来信,陈忠实读完“嗷嗷”叫了三声跌倒在沙发上,大喜过望。随后何启治来信,这部等了近20年的长篇终于令这位名编的兴奋达到高点,这也是陈忠实不辜负老朋友的诚信果实。
我在《鸭绿江》工作了30余年,大部分时间是编辑散文,信函、电话也与陈忠实联系过,均未能如愿获得他的佳作。我和陈忠实有过两次匆匆的会面,一次是和陕西文友在西安,一次是和军区同行在沈阳。他掷地有声的谈吐呈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厚实,脸上皱纹刻满岁月赠予的坚实,看着他的脚步,都是一阵阵踏实。陈忠实还能清晰记得《鸭绿江》,记得他的短篇《害羞》在《鸭绿江》发表过,记得我曾向他约过稿。写到此,想起小学语文课本收进的我熟悉的陈忠实散文《青海高原一株柳》:“这株柳树大约有两合抱粗,浓密的枝叶覆盖出大约百十余平方米的树荫。树干和枝叶呈现出生铁铁锭的色泽,粗粝而坚硬;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郁,绿得深沉,自然使人感到高原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它巍巍然撑立在高原之上,给人以生命伟力的强大的感召。”无须阐释,这一段即是作者自我生命的油然写照。
人生有诸多巧合。1975年夏天的省里创作学习班,朝阳地区还去了一位代表,即《鸭绿江》“文学月刊”时代的编辑室主任戴言。我们“一老一少”被推举为整个辽西组的正、副组长,遗憾的是,当年的我不晓得戴言是《鸭绿江》前辈,他也未料到我后来会到作协的《鸭绿江》当编辑,不然,该会有多少历史和现实的话题啊。戴言做过朝阳地区文化局局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地区文联主席,后调入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离休后回故乡朝阳定居。当他得知我在《鸭绿江》,我们之间的电话、信函骤然间多了起来,他说自己在编写《朝阳文学史》《朝阳诗词选》。我们谈李荔诗歌、谈朝阳小戏、谈凌源皮影,更多的还是谈论当代作家,谈李继伦、谈迟松年、谈金河,自然谈到了陈忠实。
作家对生命的忠实,不陈,每况愈新,于内心,于生活,于思想喷薄的时代景观,于读者面临的情感智慧火焰,于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审美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