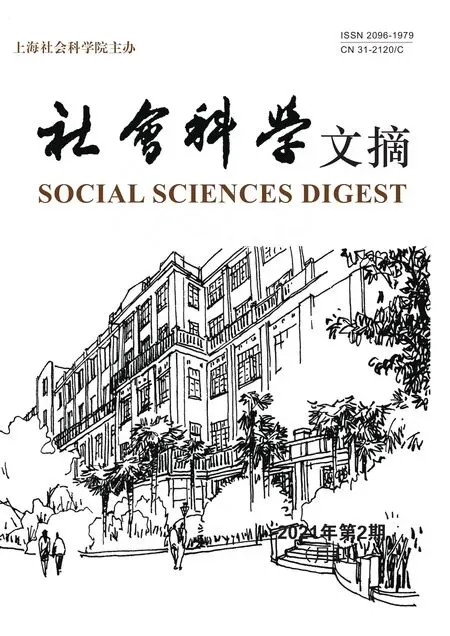历史的馈赠:城市历史时长与经济发展
文/陈海山
不同城市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见解。一些研究认为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这些“先天因素”可以解释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制度、文化等“后天因素”才是至关重要的原因。无论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因素”都偏向于从空间维度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时间维度,用地区或城市历史发展时长的差异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他们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历史发展时长越长的地区,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对于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并没有给出深入的理论或机制方面的解释。本文将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理论分析和文献综述
城市发展的基础在于人口和资本等经济要素在城市的集聚,同时城市经济要素的集聚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Bleakley and Lin(2012)、Remi et al.(2017)的研究指出,基于某种优势而率先发展的城市,即使这种优势由于新的技术冲击或历史原因不再发挥作用,城市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从而直接验证了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
对城市发展路径依赖的一个客观度量是城市的历史时长。城市的历史时长既反映了城市发展时间维度上的“路径”,也代表了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如果城市的发展具有路径依赖,则可以预计城市当前的发展水平与历史上的城市发展水平或城市的发展时长正相关。一方面,城市的历史时长隐含着其在历史上的发展水平的信息,城市在历史上的发展水平越高,代表着城市在历史上的要素积累更多,这可以通过路径依赖影响到当前城市的要素积累乃至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经济要素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城市的历史时长越长,则可能代表着城市的经济要素在持续地积累。因此,在时间维度上,城市历史时长越长,有可能代表着经济要素更早地集聚以及进一步累积,从而最终影响到当前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些研究使用跨越数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人口或城市经济数据对此进行验证:Putterman and Weil(2010)的研究认为不同国家在历史上进入农业社会的累积时长与200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Motamed et al.(2014)直接将2000年全球范围的细分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与该地区首次有城市形成的历史时间到2000年的时间差进行回归,从而在实证上表明城市的历史时长与城市当前的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
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源自于经济要素的聚集和不断累积,因此与路径依赖紧密联系的是集聚经济以及根植于集聚的密度效应。密度经济学所说的密度效应指的是经济要素的集聚提高了单位面积上经济要素的量,从而有可能影响总产出水平和生产率。Duranton and Puga(2003)通过微观建模论证了经济要素聚集所带来的密度效应来自于分享机制、匹配和学习机制。自Krugman(1991)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开始将经济要素集聚内生化,并侧重于通过理论建模讨论地区经济要素集聚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Martin and Ottaviano(2001)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指出地区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即经济要素集聚水平的提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会吸引经济要素在本地集聚,这实际上是对路径依赖进行了理论上的解释。实证研究者则侧重于从数据上验证集聚经济的存在性,一般的估计方法是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某种经济要素的密度进行回归,从而对由集聚导致的密度效应进行估计。文献最多讨论的是人口或劳动力集聚的密度效应,Ciccone and Hall(1996)的研究指出,相对于市场规模或城市规模,使用人口或劳动力密度能够更加准确地衡量集聚经济。但是,正如Martin and Ottaviano(2001)所指出的,要素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因此在使用回归方法估计经济要素集聚的密度效应时,将面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自Ciccone and Hall(1996)开始,一般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密度效应的内生性问题,被选为工具变量的主要有历史变量和地理变量。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基于某种经济要素的密度效应确实存在,只是由于变量、数据乃至地区差异,导致了所估计的密度效应弹性系数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预计,中国城市的历史时长越长,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会越高。本文的经验研究将首先对这个论断进行验证,同时本文的机制分析会从城市历史时长的视角出发,研究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即对城市的人口密度效应进行一个再验证。最后将分析中国城市历史时长与古代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现象提供一个直接的经验证据。
经验研究设计与相关数据说明
我们分三个步骤进行本文的经验研究。
第一,本文使用中国各市县在历史上持续设县时长作为衡量城市历史时长的变量,研究其与城市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依据理论分析,我们预计城市在历史持续设县时长越长,其用人口密度和人均产出等变量衡量的城市发展水平会更高。
第二,在验证了城市历史时长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后,我们使用密度经济学的一般估计方法来分析城市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经验研究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同时这部分的研究也为城市历史时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间接的机制解释。为了解决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首先引入一个与秦以来郡县制的推行有关的变量,即各市县与秦郡治的直线距离,然后以这个变量作为持续设县时长的“预测变量”。具体而言,我们将持续设县时长和与秦郡治的距离进行回归而得到持续设县时长的拟合值,以此作为人口密度的工具变量。如此构建本文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可以依靠更外生的郡治距离进一步将持续设县时长这个变量隐含的内生因素去除,另一方面则使得本文工具变量的使用更符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第三,为了进一步论证持续设县时长与城市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引入两个新的变量,即各市县明清时期进士密度(简称“进士密度”)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密度(简称“国保密度”),以论证城市历史时长与古代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研究为城市历史时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直接的经验证据。
我们以中国历史上县级行政单位治所是否位于当今城市(县或市辖区)辖区范围内,作为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是否设县的判断依据。在确定市县持续设县时长时,则遵循三个原则:第一,部分市县设县时间可以追溯到秦统一中国以前,在此我们遵循“溯源宜远”的原则;第二,在城市辖区范围内,历史上设立县级行政单位是持续的,即不发生长时间的中断,这样可以排除战乱、灾害以及疆域变更等因素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制度延续性的干扰;第三,在确认历史上的行政单位设立情况时,所设立的行政单位是由王朝中央直接掌控下的行政单位,即排除了羁縻制和土司制下的非中央直接管辖的行政单位,这主要是考虑有关羁縻制和土司制的历史记录十分模糊,无法准确地对其进行历史时长追踪。
本文回归分析中的城市样本选定为中国的县与各地级市市辖区。大多数地级市拥有不止一个市辖区,将一个地级市不同的市辖区视为同一个城市更为合理,因此,如果一个地级市拥有两个及以上的市辖区,我们将市辖区的数据加总作为一个样本。在历史上,中央王朝对西北省份的统治时有间断,这些省份各个县的历史沿革记载也较为粗略,无法对城市的发展历史作出详细的追踪,同时这些省份在地理环境上分布着大片的沙漠和戈壁等不可开发区域,引入这些省份的样本很可能对人口密度的度量产生额外的扭曲,因此我们将西北省份的样本排除。
本文使用的截面数据集的日期是2000年,之所以选择200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是可以利用最准确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其次是2000年中国的户籍制度还较严格,跨越行政边界的人口流动规模还比较小;最后是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规模的交通网络建设也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使用2000年的数据可以最大程度地排除人口流动、经济溢出和外贸等因素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即将城市历史时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准确地估计出来。
结论和启示
本文使用中国各市县的持续设县时长数据研究城市历史时长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结果发现:各市县的持续设县时长越长,经济发展水平就越高。对此,本文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机制分析:
第一,从密度理论出发,本文着重分析了城市发展中的人口密度效应,即人口的集聚会提升人均产出水平,这相当于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从理论到实际的间接机制解释。
第二,本文证实了各市县的持续设县时长越长,其在古代的资本积累水平会越高,这种历史上的资本积累最终会有利于提升当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具体而言,古代人力资本积累最终会影响到当前的人力资本积累上,而古代的物质资本积累会促进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现代产业的发展,这相当于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机制解释。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中国城市发展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从时间维度出发,对“为什么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异如此巨大”这个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证的回答。本文对于现实社会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悠久的历史可以为当前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要素,这相当于是历史对当代的一种“馈赠”。在未来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要重视推动城市发展的历史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