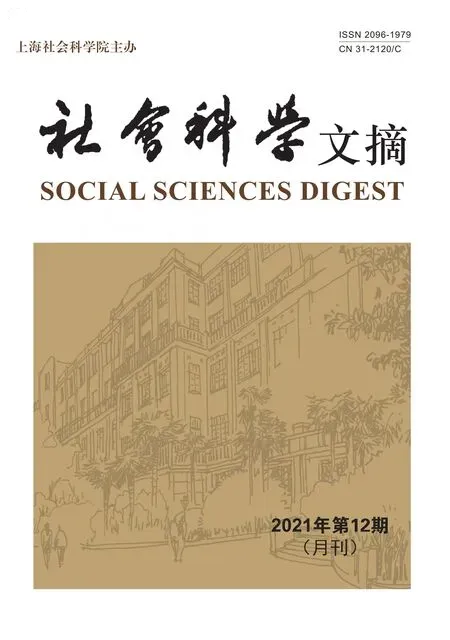鲁迅体味魏晋文脉的方式
文/孙郁
一
鲁迅欣赏魏晋文化,除了源于早期的读书经验外,也受到了晚清新的审美思潮的影响。章太炎、刘师培对于魏晋文化的理解,打破了韩愈古文运动以来的文章理念,在桐城派遗产以外寻找精神资源,曾经启示了诸多学人。不过鲁迅与他们略有不同,除了小学功底外,有着考古的心得。他不仅勘察旧迹,还抄录、整理大量的原始文献,有着一般人没有的批判眼光。他的工作可分以下几类:一是乡土资料,主要有《会稽郡故书杂集》《会稽先贤著述辑存》《会稽旧志》《会稽旧志草本》,内中有方志所遗漏的内容;二是文人作品集,现存有其抄录的《嵇康集》《法显传》《谢灵运集》等,作品有着不凡的辞章;三是古小说资料整理,代表性的有《小说备校》《古小说钩沉》,志怪、录异、志人之作丰富;四是金石类,此类抄件甚多,主要有《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名目录》等,其间不乏意外之思。这些对于鲁迅理解文学产生的背景,提供了有趣的参照。
多年间所整理的古人资料,自然矫正了诸多观念。像碑文与传记,是他一直注意的文本,在零碎的文献里,可以发现传世文献没有的片影。清末文人谈中古文学,已经注意到文化间的互动,陈三立就说:“其升降得失之故,盖与道术、政治、风尚相为表里。”鲁迅在故土人士的影子里,关注的就是生活方式、文人心态、社会制度与文章之关系。这和陈三立对于古代文化的认识也有相似的地方,只是他注重的更多的是民间文献。可见,他的研究受到了当时风气的影响。从其整理的过程看,社会学所关注的内容,也被悉数勾勒,就内容来说,比一般的士大夫多了驳杂的元素。
在整理大量文献的过程中,鲁迅发现了文外之文与诗外之诗。他对于文学概念的理解,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广义的看法受章太炎影响,认为凡著于竹帛的都是文学,也就是“杂文学”。最初鲁迅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理解的文学,是托尔斯泰与夏目漱石式的,这是狭义的观念,即“纯文学”。不过在整理乡邦文献与野史过程,寻找各类被湮灭的文字时,也印证了章太炎的看法。所以,古籍整理与翻译活动,使他往来与文与非文,诗与非诗之间,便获得了古风的滋润。许多佚文,叙事简洁,内含别趣。比如《南方草木状》,在自然间觅得清新,本草之意,天地之韵,爽目者不可胜数。《六朝墓名目录》里,远去的遗风犹在,可参之成诗者甚多,于思想不无洗涤之效。这些文献都不系统,在知识碎片里,却依稀感到古人心绪,字里行间亦带感知万物的元气。
二
对乡邦文献发生兴趣,使他从故土的风俗、习惯、信仰、礼仪中,体味到文明的踪迹,一些素材纠正了先前文人对于历史的误解。在所录的文字里,有许多背景性的信息,其中有关风俗类的,主要集中于《会稽先贤著述辑存》里;还有的是记人物的,《会稽旧志》则从《晋书》录得人物纪要多种;再则是描绘地志、山水之貌,《会稽地志》《会稽记》等所述山川河流之态,风景大可悦目。魏晋文人记叙此类遗风,不乏情趣。这些抄录的文字,比日本作家笔下的民间风情不弱。那时候周氏兄弟正在提倡民俗学,从日本柳田国男的著述中获得启示。对比周氏兄弟与柳田国男的著述,彼此有相似的地方。柳田国男《远野物语》《日本的昔话》就多记山野之趣,描绘古风余脉。民俗学要研究的就是此类谣俗之风。鲁迅在《〈会稽郡故书襍集〉序》中也有类似的心得。
故土的礼俗,蕴含着不小的学问。贺循所著《会稽先贤著述辑存》,收有《丧服谱》《袷祭图》《丧服要记》等文,作者文字简要精炼,所记古礼颇有分寸,儒家的等级制依稀可见,基本上延续了《礼记》的某些思想。丧礼以宗族的长幼之序分之,男女有别,层次分明。家族有一套道德法规,如有越轨之举,则被宗族处之。这些记录,都是社会史的边边角角,对于认识古人颇有意义。贺循笔下的会稽葬礼仪式,样式多种,让人不忘的是各种祭品、器皿的摆设与颜色,很有一种画面感。祖庙、屏风、壶、灯、神座等,都看出了彼时的风气。化古礼之繁重变为简而易行,也是贺循注意的,他的看法也体现了晋人的某种观念。魏晋时期的浙东,丧仪中人神悉尊,到了明清,已有了变化。张岱记载越人的扫墓,就有审美的意味,“厚人薄鬼”了。这个变化,周氏兄弟是看到的。其实,千百年间风俗处于流动之中,晋侍中庾纯就在西晋的丧服制中发现了与古风的不同。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里也关注过类似话题。从礼俗中看社会心理,对于理解文化的变迁之迹,都是不小的参照。周氏兄弟对于此的感受,可能比同代作家更为深切。
三
近代学者回望魏晋时代,每每于玄学与佛学纠葛不已,从中看出文化转折的痕迹。章太炎、谢无量、汤用彤不乏这类思考。鲁迅对于玄学、佛学也有兴趣,他从文人笔记中就觅出诸多思想隐喻。相对于玄学,他更关注故土文献的佛教元素。但他并没有去研究主要佛学家的著述,就藏书和辑校来说,所看重的是佛教传播和玄言里的诗文流脉,而这些经典多以魏晋时期的为多。他自己就购置了《佛说百喻经》《痴花鬘》《阿育王经》《佛般泥洹经》《付法藏因缘经》《阿育王譬喻经》《众经撰杂譬喻》《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广弘明集》等,还抄录了阮籍、嵇康、谢灵运等人的诗文。这些书籍是他进入彼时精神世界重要的参考,所得的结论也别于同代的读书人。
东汉以后的文化风气里,佛教传播改变了文人生活,对于文学与艺术的影响显而易见。鲁迅亲自抄录《法显传》,留下的文稿达39页之多,由此可以看见佛门的精神形影。《法显传》是一本远游求法之书,作者法显系东晋时期著名僧人。全书自叙域外跋涉经历,文字古雅、清隽,带出珍贵的佛教遗风,所叙访问异邦曲折故事,人文风情历历在目。文章的片段已经有小说家的韵致,鲁迅欣赏它,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在抄稿里留下大量批注,多是字句的核实和句式的斟酌心得,看得出用力之深。佛门的文字对于辞章的演进和书写的风气是有促进作用的,这是研究文章之道的人不能不了解的部分。
鲁迅对于佛经不是信的态度,而是如何化其精神,成为自己的生命的新的表达。古代的许多诗人,都能出入佛学,于辞章里有变调之美。他认为“除去教诫,独留寓言”的态度是好的。他所搜集的拓片就有许多有趣的主题,其间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他后来与青年木刻家也言及佛教艺术对于中国绘画的参照意义,也是深染于各类文献的一种心得。
魏晋的文学里,玄言诗颇有市场,与佛门艺术有很大的区别。玄言诗受到老庄的影响,一些人的文章也带有此风。他欣赏的孔融、嵇康这类文人,尤其是嵇康身上的老庄之气,鲁迅身上未尝没有。王瑶先生说:“魏晋是文人由俳优进入士大夫地位的开始,由于老庄思想的兴起,文学的观念比较清晰。”这个风气的出现,使文章充满了灵动之气,但其间也并非一成不变。他说自己厌恶身上的庄周、韩非子之气,那也有寻觅新风的冲动。而那时候一些诗人是渐渐摆脱了时风影响的。比如所抄录的《谢灵运集》《柳恽诗》等,也是扭转时风的作品集。谢灵运的山水诗,折射出士大夫的思想的变迁,将玄言诗的晦明不已变为清纯冲淡之音,佛学意识被转换为中土妙思。柳恽的多才多艺,乐府之韵,常有奇句出来。整理他们的诗作,也未尝不是考察彼时学风与诗风之关系。有学者就指出,谢灵运诗作也受到禅风的冲击,但已经不易从中看到了。这种“融合玄释”的笔法,推动了辞章的演化。作家审美的深度埋伏,需细心者方能得之。鲁迅对此的体悟,比同代的许多文人要深。
四
显然,鲁迅对于古代文化中非温吞的、叛逆的精神是十分欣赏的。在回望古代的风俗、风气的时候,最吸引他目光的是诗文中表现的洒脱、自如的风度。
东汉末年之后的文化走向,使审美蕴含了新的可能,鲁迅对于雅俗之变和台阁、山林之风都有特殊的理解。在对彼时风气的描述里,勾勒了知识人的群貌。曹植的灵动,何宴的洒脱,刘伶的狂放,都被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这些有的取自《世说新语》的描述,有的是从类书里得到的片影。对于他来说,纲常解纽的时代,知识人对于生死与功名有了另一种理解,而这种转向也决定了文章气象的不同。静止地看笔墨之迹的流变,反而是不得要领的。
在旧文献整理方面,他最为用心的是《嵇康集》的校勘,跨时有23年之久。如此长的时间沉浸在嵇康的诗文里,说是在寻找文章的变风也是对的。嵇康的文章与诗,都非彼时文人可及,自有高人之处。鲁迅欣赏他,大概因为其才气耀人,音乐、诗文均好,在文字里有多致的风采;又能够引用前人学术,打破儒家辞章的绵软之体,引老庄于诗文,通篇带有奇气;而面对邪恶政治显示的傲骨,对流行的思想加以反对,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限度。可以说,在鲁迅眼里,嵇康是风度有之,辞章亦高,全无俗儒的暮气。
《嵇康集》所呈现的文字,取自不同书籍。主要参考书有《太平广记》《文选》《世说新语》《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还从其他文献进行辑校补充。这些充满了高傲之气,远妄诞,近玄理,尚自然,精神少有奴态。其文章看出不凡的才华,那篇《琴赋》就“感天地以致和”,“寄言以广意”,意象大有庄子笔意。而《与山巨源绝交书》,则“情意敖散”,不堪于俗音,蔑视权贵,辩驳之语,笔带豪气。嵇康善作辩驳之文,《养生论》《答难养生论》是智者之言,斗士风采也是有的。既能疑古,又常出新。在生活里能够保持节操,于文章里则唱出悲壮之曲。
关于彼时的文风,《文心雕龙》有过形象的描述,刘勰以为:“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鲁迅对此是认同的。废名也认为那个时期文人作品“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可见古今学人的感受多有相似的地方。其实鲁迅的表述中,与他们略有区别,既看重嵇康、阮籍的文字,更不忘他们的行为,以及这风度背后的悖谬。那代人的精神限度也是明显的,“竹林七贤”也无不如此。在反复对比各种文本的时候,能发现众人作品其实也有矛盾的地方,像嵇康在面对复杂现象时的心得,也有反逻辑的心不由衷的一面。不看到他的悖谬与限度,要走进内心深处也是难的。鲁迅感受到了一种不自由的自由,文人的狂放背后,也有难言之隐。他说阮籍的诗写到神仙,而自己并不信那些存在。这和曹植贬低文学,其实另有所指一样,乃个体精神在环境里不得舒展的一种变形体现。“竹林七贤”的文字常有思想的埋伏,他们的美丽的辞章其实与失败感是连为一体的,所以向秀说嵇康“寄余命于寸阴”,乃一种生命的挣扎。士人风度最可感者,便是这种“傲世忘荣”的态度,忧愤而不失峻伟之姿,骎骎然于无路之途,命危而后文聪。鲁迅说后人不易学到他们的真髓,原因是没有悟到那华章后的隐秘。善于从词语中看到作者的策略和精神破绽,是思想者的特点之一,西洋人对此有不少论述。海德格尔关于“存有”与“语言”的思考里,涉及“遮蔽之澄明”的话题,就与鲁迅的体悟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
但阮籍、嵇康提供的是精英文本,那是认识彼时思想者的标本之一,而民间非精英的表述,街巷之语里的野性词语,对于鲁迅的价值可能更大。在介入魏晋文化的考察中,《古小说钩沉》是很重要的学术收获,对于他认识古代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提供了有趣的镜像,这些并没有进入晚清一些学者的视野里。从辑录文本中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的小说,形态并不成熟,稚气与简单化,影响了传播。不过,旧时的表述有几点可能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一是语言都很简朴,没有雕琢之迹,用语与日常口语接近,传神的地方是从自然语态里流出来的;二是注重人情,即便是志怪,也带着民间的普遍心绪,眷恋生命,惊异于世间的无常;三是民间传说的记录,虽有佛教痕迹,但根底还是儒、道的东西最多。因为有生死之思,帝王的生活也与常人相近,并没有都去神化帝王之迹。这里无意间折射了民间的某些观念,虽然很弱,但依稀可见古人的精神层次。
《古小说钩沉》涉及的内容极为驳杂,主要是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太平御览》《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广记》《艺文类聚》《太平寰宇记》《白孔六帖》《法苑珠林》《事类赋》等文献中辑录出来的。总体看来,所辑作品在文体上没有太大亮点,但内蕴却是社会学家最关注的。士大夫诗文所记录的社会风气,心理状态,都于此见出一二,也有人间百图的意味。一些作品记录了台阁间的权力文化的幽暗,如《汉武故事》所叙君臣之序,血腥与智慧均有,看出文化里主奴之态。一些作品叙述了战乱社会中百姓于无奈中的期冀,如《幽明录》所载永嘉之乱的故事,颇为惊异。这种想象,后来在许多民间故事里曾被借用,惨烈里的柳暗花明,抚慰着苍生的心。
这些不同风格的魏晋文献,后来曾多次出现在他的杂感文字里,作为历史之镜,反射着存在的吊诡性。他意识到了文学生态背后的政治形影,也看到生活现状对于作品的内蕴的影响力。文脉其实隐含着生活的多样性与表达的无限可能性。古人越矩的审美之思对于今人的镜鉴是意味深长的。
晚年鲁迅的言论中,魏晋资源散落在辞章深处,古代话题的背后其实是当下文化难题的显现。考其原因,一是现实的残酷产生了古今对比之意,二是不满意于远离现实的京派学者的审美意识。京派的学者在许多地方与鲁迅距离甚远,尤其周作人周围的学者的言论,在鲁迅看来,不仅误读了古人,也误读了现实。他的文章多次批评了象牙塔文人对于现实的隔膜。1934年5月所写《儒术》一文,提及儒门读书人在乱世的处世哲学,引用《颜氏家训》的资料嘲讽士大夫的苟活意识,内含着对周作人批评之意;次年所作《“题未定”草(六至九)》讨论陶渊明的作品,直接矫正了朱光潜的审美偏差,以为全面理解作家的作品殊为重要。“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文中还谈及南朝齐诗人谢朓《谢宣城集》,认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京派学者在许多领域不能与现实有效对话,那时候周作人、废名、朱光潜等人的审美意识,忽视的恰是从复杂文脉里寻找精神原色。他们远离左翼文化,也是知识兴趣的不同所决定的。鲁迅的“暗功夫”冲击了他们的精神围墙,论争里带出的震动,与其说是对古人的重新发现,毋宁说是批判理性在新文学里的一次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