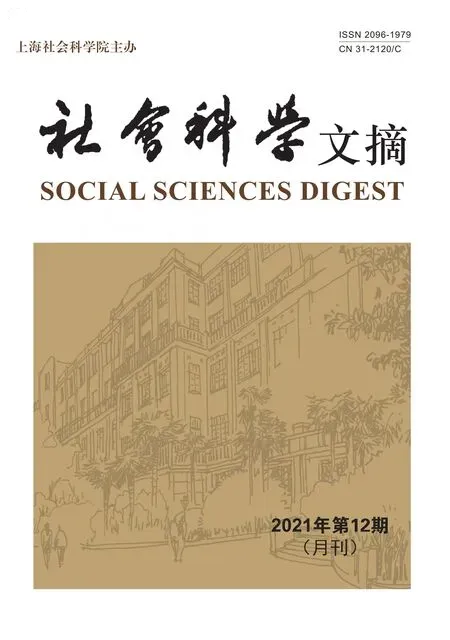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路径分析
文/祁芝红 李智
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取得了很大提升,形成了民族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国模式。“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面对(学术)话语权的结构性弱势,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成了迫在眉睫的时代课题。首先是以“传理”“沟通”为本的传播学及其话语体系建构,因为传播学除了建构自身学术话语体系,还应为中国其他学科领域学术话语的全球传播提供学理依据和实践指导,以增强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最终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话语权。诞生于美国的传播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正式进入中国大陆,至今已经发展了40余年,传播学从在中国的传播学发展为中国的传播学。在这40余年的学科发展史中,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是如何建构的,经历了哪些环节,其来路和去路何在,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反思与展望。
全球本土化: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来路
在中国传播学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是其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一方面,在知识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不得不持续译入、援用来自西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另一方面,这种译入和援用又不是机械复制,而是基于中国经验的重构和融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传播学学术发展史,既是一部西方传播学学术话语进口史,同时也是一部对西方传播学学术话语予以本土化的重构(转化)史。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就是在这部西方传播学学术话语进口史或对西方传播学学术话语的重构史中生产出来的。基于全球本土化的学术情势,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的生产一般要经历话语译入、重构和融创等三个环节。
(一)话语译入: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全球本土化起点
在20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传播研究就借道社会学、新闻学等学科进入中国学人的学术视野。而作为“学”的传播学研究正式亮相中国,则以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于1978年首次介绍传播学为标志。关于我国传播学主流研究所涉学术话语的“舶来”属性或“西方”源头,通常并无异议,但关于译介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旅行中作为第一层“过滤网”或第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往往少有关注。隐身的译介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形塑作用及其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迹线中的“起点”位置,只是在传播学学术话语的规范化研究中才发出耀眼的光芒,不容忽视。譬如,将“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学)”并普及使用,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其原意,甚至因此造成了在中国的“communication”与在其诞生地的“communication”在研究旨趣、研究对象等层面上难以逾越的鸿沟;“media”一词无论译为“媒介”还是“媒体”,都无法涵盖其源义。当语言差异之下译者选择的无奈在术语引介初步完成后悄然退场,学人开始“总把译名当源名”,将“媒介”“媒体”理解为功能性实体,中西话语符号间的所指鸿沟便应运而生。这道鸿沟形塑了“media”研究在中国传播学学术版图上的样貌,限制了中国学人对传播(活动与研究)的理解和想象。
由此可见,在跨语言、跨文化的遭遇中,流通于中国学术研究场域中的传播学学术话语自被引介开始就没有纯粹的西方与中国之截然二分,而是以“1(西方)+1(中国)=3(中国性)”的状态呈现于学术界。这个通常被忽略的“3”,或者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西化”结果,或者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化西”结果,通常而言则是“西化”和“化西”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3”(中国性)因此而成为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与生俱来的特性。最初生成“3”的话语译入则成为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起点。
(二)话语重构: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全球本土化实质
如果说话语译入是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起点,那么,话语重构则是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质。话语重构这一事实发生的原因,从表层看,除却因译者水平欠缺导致的误读、误解与误译,主要源于中英文之间语言层面词义范围(所指)的差异导致的译者选择;从深层看,主要源于译介活动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译介活动的发起与执行、译介过程中的符号选择、译介产品的解读与使用,都因“人”而起。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不管他/她是译介活动的发起人、赞助方,还是译介活动的执行者(译者)、译介产品的解读者和使用者(阅听者),从来都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时空中,其行动从来都受到特定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支配。发起人和赞助方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选择“合适”的作家作品(译介对象)、译者和出版者;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基于对自身、译介活动发起人、赞助方、源语作者、译作出版者和阅听者等行为主体各自的特性和主体间关系的理解与权衡,选择“合适”的话语符号;社会环境基于特定需求选择“合适”的译者和译品。简言之,译介选择是看似偶然中的必然。进一步具体地说,英语和其他语言(如汉语)之间“对等关系的喻说”,“只是在近代的翻译过程中建立起来并且借助于现代双语辞典而得以固定下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译介活动所处的现实社会权力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概念的引介经历多种中间语言的“接力”、多重把关人的“过滤”,意义重构的成分就更多。译语一旦诞生,便脱离了其原有的社会历史时空,开始了其在新的话语时空中寻求正当性抑或合法性的旅程。在经由译介进入中国之初,传播学学术话语就因脱离源语的语境而发生了改变。这其中有中西语言与文化差异背景下的误读、误解与误译,有译者不能保证名实相符的无奈,也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空中刻意遮蔽源语的某些内涵而凸显出中国性的价值选择。其结果则是以汉语为母语和学术语言的研究者“只把译作当原作”进行多样化解读乃至过度诠释后建构(甚或可以称为“虚构”)起来的“中国的传播学”。
(三)话语融创: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全球本土化成果
在中国学人立足中国大地的创造性学术叛逆中,传播学及其学术话语体系的西方源头被重构为“中国的传播学”。虽然迄今很少生产出纯粹的、高度概念化的本土性原创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来就是、未来也只能是西方传播学的“学术殖民地”。事实上,传播学者在徜徉、浸淫于西方传播学概念、理论后,对中国的传播现实和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正是基于传播学者的这种自我理解,居于传播学知识版图中心地带的西方话语自其被译介和引进起,就带有了“中国性”而富有本土化创新的成分。可以说,这些带有“中国性”的传播学学术话语是西方传播学学术话语与中国传统传播思想和现实传播语境相融合的产物。如果从研究旨趣的角度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分为复验派与返本派,那么西方传播学话语与中国经验的融合既典型地体现在复验派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对中国传播实践的验证性研究上,又充分地表现在返本派利用西方传播学学术话语框架对中国传统传播思想的再发现上。在复验和返本的相互激荡所营造的“开新”氛围中,一些既脱胎于西方传播学经典理论话语,又与之相区别的中国特色传播学话语开始萌芽和生长。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基于理论相对于经验的超越性,对中国这样的现代学术后发国家而言,传播学学术话语生产的全球本土化路径绝非学术策略上的自由选择。
在地全球化: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去路
加持了“中国”这一“阈值”的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其终极旨趣不止于中国之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更在于世界之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如果说,全球本土化构成了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之来路,那么,“在地全球化”则应是世界之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去路所在。概而言之,在实现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的“在地全球化”过程中,兼具全球视野和本土关怀的话语转化是基础,秉承平等对话和自然接合理念的话语译出是关键,主动设置议程、积极跨界互动的对外话语传播是最终出路,三者的有机联动同话语生产一道构成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完整机制。
(一)全球视野与本土关怀:话语转化
一门学科的话语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原初生命力和吸引力在于其本土关怀和民族特色所体现的异质性,其感召力和公信力则更多地源于其作为人类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成分所体现的同质性。世界之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的生产,一方面要顾及本土经验,贴近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表达中国特色,凸显“中国性”;另一方面要从中国经验中抽象出普世(普适)规律,或者用中国经验补充、修正“全球”理论,直至产出民族价值与全球价值同频共振的学术话语,从而凸显“普世性”。因此,“国产”传播学学术话语能否把自身的“异质性”普世化并融入全球“公共”传播学学术话语,是世界之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生成的关键所在。从“全球本土化”之来路看,“中国性”(异质性)是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的显著特质;而从人类认知机制看,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的异质性既是其独特魅力所在,同时又是其融入全球公共学术话语体系的障碍所在。那么,这个障碍能否被跨越甚而成为重构现有公共学术话语的新动力?对此,美国语言学家吉尔斯·福康涅和马克·特纳基于人类概念系统的隐喻本质提出的“心理空间”概念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概念整合理论”作出了肯定回答。如果说,现实的全球传播环境从宏观上为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的在地全球化提供了契机,那么,人类认知和概念合成的内部机制则从微观上保证了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的中国性/差异性被普世性/公共性所接纳而融入全球公共学术话语体系的可能性。
(二)平等对话与自然接合:话语译出
在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国际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环节是对外话语译介(译出)。从译介活动的一般规律看,话语译介总是从强势一方流向弱势一方。鉴于汉语等语言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传播学学术话语在国际上的结构性弱势,当前,甚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将以主动译出而非他者译入为主。译出和译入的差异不仅在于方向有别,更在于译介生态中的“时间差”和“语言差”问题。为此,要接受西方阅听者当前对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尚无相当认知的事实,认清“适应”在寻求跨文化认同中的作用,摈弃长期以来外宣翻译要“以我为主”、照顾阅听者的思维习惯是“曲意逢迎”的思想;要以概念整合理论为指导,在学术话语对外译介中基于中国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关联寻求平等对话和相互适应,继而达成“共识”,形成认同,在意义融合与概念整合中完成话语的译介。鉴于话语译介的概念整合实质,学术话语对外传播中的译介策略选择要超越二元对立的直译意译之争、归化异化之辩,追求异质话语在译介过程中经由交汇、冲突、博弈达成共情、共识、融通、聚合。由此,在各自独立的话语主体的平等对话中达成中西话语间的自然接合——用国际化符号包装本土性所指,应该成为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对外译介的至上原则。
(三)议程设置与跨界互动:话语传播
在传播全球化的今天,学术话语权的争夺更多地发生在国际场域。国际学术话语权既建基于高质量的话语生产和译介,也有赖于国际化的议程设置和全方位的跨界互动。议程设置与跨界互动是学术话语引导力和影响力的来源。因此,通过主动精心设置议程、跨界跨平台进入全球学术对话场域,成为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国际化的另一个关键所在。
1.议程设置。在信息传播全球化时代,就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现状而言,原创性本土传播学学术话语的匮乏是不可否认的短板,但中国从来不缺乏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学议题也是毋庸置疑的优势。由此,旨在建构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国际议程设置可以从发掘国际学界共同关注的本土议题入手,通过适当的方式将议题接入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和讨论的平台,逐步形成源于中国传统传播思想资源和当代传播实践且与国际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接轨的理论方法。可以明确的是,在中国之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尤其是世界之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首要问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传播学概念理论话语的全球化,而是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中国传播问题(议题)的全球化。具体地说,是在已然中国化了的西方传播学话语框架内研究对全球传播学界具有广泛吸引力的、源于中国传统传播思想资源和当代传播实践的中国传播问题(所谓“西方理论,中国对象”),并力图予以抽象化、概念化处理,从而形成携带中国基因的传播学学术话语。进而,通过国际学术对话,用世界听得懂的表述将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置入世界传播学学术话语版图中。
2.跨界互动。中国传播学议题和话语进入国际学术对话场域需要跨界互动。跨界互动主要涉及传播学学术话语(包括议题)在生产、译介与传播等各种流通渠道中的协频共振。跨界互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如国际出版、国际教育、国际会议等。以国际出版为例,中国传播学界可以创建以外文为符号媒介的国际期刊,在全球范围内组稿,并以办刊主旨确立、栏目划分等方式引导研究议题的中国化;也可以争取在已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期刊发表相关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促成中国传播问题在国际学界的学术争鸣;还可以主动向外译介、出版兼具中国传播学研究特色和较大范围普世性的学术著作。此外,鉴于特色鲜明的中国传媒生态、最具潜力的中国新媒体传播市场,面向全球设立中国传播问题研究基金,或是就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中国传播问题设立全球研究项目也是促进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走向世界的方式之一。
结语
回望中国传播学迄今4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部中国传播学学术发展史,就是一部西方传播学学术话语进口史,更准确地说,是一部对西方传播学学术话语的重构史。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就是在这部西方传播学学术话语进口史或对西方传播学学术话语的重构史中生产(融创)出来的。然而,在知识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加持了“中国”这一“阈值”的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其终极旨趣不止于中国之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更在于世界之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由此,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要以(自我)独立为指针,还要以融入(世界)为指向,不仅在于因外来话语的译入而实现的本土话语生产,还在于本土话语的译出和输出(对外传播),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是通过话语生产、译介(译出)、传播(输出)三个环节的有机联动建构起来的。如果说,全球本土化构成了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来路,那么,在地全球化则成为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去路。概而言之,中国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就是从话语生产到话语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