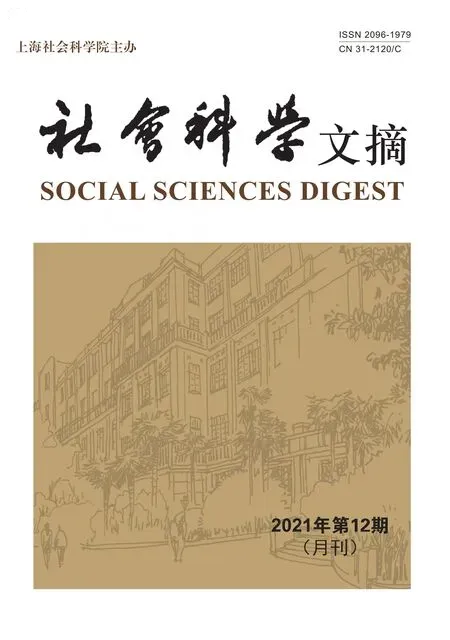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构建态势管窥
——以《社会科学文摘》(2016—2020)相关转载数据为基础
文/张爱华
百年“心魔”与时代呼声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从历史源头上追溯,不仅是持续百年的老话题,也可以说是中国学人挥之不去的百年“心魔”。这个“心魔”孕育于20世纪初。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西方哲学强势进入中国,不仅带来一个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而且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来剪裁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由此促成了“以西释中”式的中国哲学的诞生。1949年后,源于西方哲学又有独特气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压制了西方哲学,而且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进行了第二波改造,形成了“以马释中”的中国哲学。
1978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反思日趋僵化的苏联教科书式的理论模式,回归经典,潜心学理,探索结合中国实践和多元理论的中国化之路。与此同时,主动打开国门的中国理论界,迎来西方哲学更强一波的大规模进入,各种流派的西方哲学吸引了哲学界的广泛关注。而此前移居海外的中国儒家文化研究者聚集成现代新儒家学派,也借改革开放之风进入了中国,并且激发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强势复兴,催生了中国哲学的快速成长。由此,三种理论资源在中国大陆汇聚交织,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足鼎立而又相互竞争、彼此渗透的格局。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到21世纪初,中西马哲学的理论态势整体表现为:西方哲学的研究热潮持续多年,广泛渗透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在西方哲学如日中天的发展势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也开始强势发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队伍最为庞大,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又与中国实践结合最为紧密,通过吸收新的多元理论资源和积极回应中国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焕发勃勃生机。而随着中国哲学研究者的成长,从中国传统本位出发,不少学者开始强烈质疑“以西释中”的中国哲学史是否“合法”,由此而兴起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集中反映了这一诉求,并反向激发了中国哲学内部自主创新意识的快速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持续发力,预示着构建以中国为本位的哲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命题呼之欲出。
不仅是理论内部的碰撞在形塑三种理论资源的发展态势,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理论整合的走向。就现实环境而言,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强势崛起。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成功,一方面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从理论高度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中国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成为迫切的时代需求。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建设。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面向整个理论界,正式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命题。哲学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这座理论大厦最为重要的基石,回应这一重大命题的任务最直接地落在了哲学的肩膀上。
中国进入新时代发出的理论呼唤与中西马哲学百年的恩怨交织、融合渗透、对话碰撞,都在催促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新形态的诞生。然而,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伟大工程,需要学术界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摘》创刊于2016年,在创刊伊始,即敏锐地抓住这一时代大命题,密切跟踪并转载相关的创新成果。借助《社会科学文摘》这一汇聚哲学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笔者拟梳理哲学界五年来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所作出的努力,旨在为共同构建新时代的伟大理论工程增砖添瓦。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忧思与症结
2016年以来的中国的哲学理论界,整体被一种理论滞后于现实的深深忧思所笼罩,同时也夹杂着一种寻求理论突破的热切渴望。正如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等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处于文明大国向文明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学者应该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学术和思想上的支撑,然而,有的学术研究存在着“耕了别人地,荒了自己田”的研究短板。复旦大学张汝伦则指出,中国已经成为最大、最强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精神上却与之形成较大的反差,以哲学研究最为突出。
中国的哲学理论体系建设进程之所以滞后于现实发展,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分析,择其大端主要有:
一是客观上存在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后发劣势”。北京师范大学吴宏亮指出,在经济发展中,常提后发优势,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不同,后发模仿,反而可能导致由西学崇拜引发的低度自信以及理论研究缺乏引发的实证研究陷阱。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瞿宛文则根据台湾经验提出一个后发社会的学术本土化的“学习阶段论”:第一阶段是重在模仿,第二阶段是参与国际分工证明自身水平,第三阶段是反思并修正理论使其适合自身社会。理论追随比较容易,反思自身并自行摸索却较为困难,因此,需要及时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和状态进行“历史化”“问题化”的反省,才能真正进入第三阶段。
二是中国哲学共同体身陷“阐释驱逐创造”和“学术抑制思想”的思维困境。中国人民大学刘志洪等对此作了讨论,并指出这一思维困境在当今哲学界具有普遍性,“创造为上”的态度与取向亟待在中国哲学共同体中得到确立。
三是哲学学科内部存在的结构性困境。姚新中认为,学院式哲学造就了以中西马哲等二级学科为“经”、以教研室/研究室为“纬”的基本框架,不同学科之间出于竞争,会强化哲学学科的知识传递功能,而淡化理性批判思维的培养、方法论的训练。这影响了学者创新能力的提升。
除了上述存在的来自客观环境、思维惯习和学科设置等制约性条件,构建中国的哲学理论之所以不易,更为重要的是,内部理论体系建设的艰巨性。在此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哲学的中国性如何深入发掘?世界性如何安置?传统资源如何对接现代化?现代性理论如何面向未来?这些问题综合起来,都指向了中西马哲学这三种理论资源在中国的思想空间内,面向世界、立足当代、着眼未来,所能采取的最优质的排列组合和有机贯通。这一兼顾古今中西维度而又要突显中国特色的巨型理论体系构造,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既需要中西马各个哲学学科内部的持续发力,也需要有学贯中西的理论集大成者适时对其加以综合分析和全局贯通。
中国哲学的突破与建构
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过程中,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呼声最为迫切,对现状也最为焦虑。这一状况的出现,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百多年来的失落和不断地“被哲学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再度复兴,学科的自主意识逐渐上升。进入21世纪,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点燃了学者们对建立在“以西释中”基础上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
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志宏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逐渐失去了言说自身和自身言说的自主性,“传统的理论思维模式和表述方式,要么被强势的西方哲学所改造,要么为主流的理论视角所限定,以至于学界对中国哲学学科自主发展的可能性缺乏足够信心,对传统思想之于当代社会的建设性意义缺乏合理认识”。因此,“必须跳出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框架,回到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视域和实践立场”。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匡钊则提醒必须区分两种“以西释中”:第一种“以西释中”,将中国的某些思想归于“普通哲学形式”之下;第二种“以西释中”是从特定的西方哲学立场出发,对某种特定的中国思想的观点或理论的再诠释。后一种“以西释中”可能造成对中国思想材料的扭曲,对这种扭曲的警惕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由此而波及甚至混淆了第一种意义的“以西释中”。他认为,立足于对思想形式的客观把握的第一种“以西释中”,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无法摆脱的“前见”——或许只有通过这种“前见”,才有可能使中国哲学呈现为具有可公度性的世界性知识。
以上观点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针锋相对的言论。可以说,对于在多大程度上改造“以西释中”的框架,自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开始以来,学术界一直有分歧和争议,并未取得完全的共识。但是,就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影响而言,却是一场对中国哲学学科自主意识的大启蒙。
经过这场大讨论,越来越多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有意识地从研究对象自身出发,进行自主创新的研究。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关于中国哲学的创新性的体系建构工作,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中共中央党校乔清举、马啸东在对中国哲学70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后认为,当前的中国哲学领域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两条路径平行延展的态势:一是“照着讲”的学科研究;二是“接着讲”的体系构造。在学科研究方面,出现了政治儒学、企业儒学、教化儒学、生活儒学、生态儒学、道家道教与佛教生态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等多个领域。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的重建也进入实质性阶段,出现了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张立文的“和合学”、牟钟鉴的“新仁学”、陈来的“仁学本体论”、杨国荣的“具体形上学”、许抗生和胡孚琛的新道家哲学等体系性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哲学在学科性研究和体系性建构方面取得了诸多富有启发的成果,北京师范大学倪培民甚至还强调了当前不仅要“以中释中”还要“以中释西”的新思路,但还是有许多学者认为,我们并没有探索出比“以西释中”更加成熟系统的“中国写法”。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所指出的:“无论中国哲学史的西化写法的建构之功是否大于或小于解构之失,问题是,至今我们尚未发展出别的写法。”进一步,他建议,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继续深入发掘中国思想内部的“支配一切思想而又不在知识表层的深层观念”。中国人民大学姚新中等则指出,中国哲学的崛起采用的是“不对称手段”,提出了“政治儒学”“生活儒学”“生态道学”等范畴,并形成中国实践哲学的新建构;但在形上学、知识论和逻辑学等领域大多又持“存而不论”的态度。因此,他们认为:“本土中国哲学的复兴虽然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其对话语权的争夺还远远没有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图景
在中国的哲学界,最突出的印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达。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新中国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借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对此,华南师范大学陈晓斌给予了历史性的理解:“全面复制和移植苏联教科书体系确实使得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初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苏联‘三位一体’的教科书体系在整体框架结构和基本原理叙述上呈现的完整性、严密性色彩,具有一股强大的说服人和掌握群众的理论力量。”
然而,随着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占据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并长时间掌握“文化领导权”,其负面后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僵化。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突破传统的教科书模式,激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活力,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之一。对于改革开放时代前2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北京大学仰海峰总结为:从实践标准讨论开始—到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到认识论中的选择论与反映论之争及规律论与选择论之争—到主体性的呈现—到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到具有学派色彩和个人丰富创造性的研究空间”,出现了价值论、人学、存在论、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发展理论与全球化问题、辩证法研究、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献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等分支。针对这些名目繁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增长点,学术界也称之为“部门哲学”,它们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体系意识”向“问题意识”的转型。
苏州大学任平进一步将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演进过程系统化,建立起了一个理论创新图谱。第一个学术图景以“教科书改革”为轴心,以“原著选读”和“原理研究”为纵横轴,是新中国从革命转向建设实践需要的理论表现。第二个学术图景是以“文本—文献学解读”为轴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对话”为纵横轴,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中期的思想出场形态。第三个学术图景是以“反思的问题学”为轴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部门哲学”为纵横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加速发展的哲学产物。第四个学术图景是以“马克思出场学”为轴心,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践的解释学”为纵横轴,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理论创新所能够达到的新境界。
中央民族大学王海锋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取得丰硕的创新性理论成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西方哲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主动“对话”的结果。毫无疑问,从教条走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不同的理论资源开展积极对话,进而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不过,姚新中等学者也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发挥与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相匹配的主导作用,还有不少的路要走:“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人所提出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图式’与正在复兴的中国哲学和改造过的西方哲学所能认可和接受的哲学范式之间仍有不小的距离。”
西方哲学热出现消退迹象?
在构建中国的哲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些学者敏锐地觉察到,延续了40年之久的西方哲学研究热潮开始出现某种消退的迹象。
“目前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出现某种消退趋向。”北京师范大学韩震如是说。他回顾了西方哲学在新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排斥态度审视西方哲学(1949—1978),第二个阶段为以学习态度研究西方哲学(1978—2012),第三个阶段即以自信的态度与西方哲学对话(2012—)。他指出,在第三个阶段,中国学者已经更加自信,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变成更冷静的学术性审视。
西方哲学热度的降温,自然有中国时代背景和理论需求出现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但是与西方哲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高度相关。一些学者们认为,西方哲学在中国引发一轮轮热潮,类似“流行文化热”,诸多研究只是浮在表面,未能从根本上深入到西方哲学的机理。如中国人民大学聂敏里就认为,“我们先后经历了存在主义哲学热、现象学热、分析哲学热、后现代哲学热以及目前的古典哲学热”,“它们更多地反映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中国思想界特殊的精神躁动,它们在社会学层面上实际具有流行文化的特点”。
实际上,提出批评意见的学者多是西方哲学研究出身的,都高度重视西方哲学的价值。因此,他们发出的批评之声,矛头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哲学研究中那种不作精深思考的浮躁倾向。正如张汝伦所分析的,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未能深入西方哲学的堂奥,未能打通整个西方哲学史,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越来越学术工业化和知识化,忽略了西方哲学研究应该也是我们哲学研究的一种途径与方式”。
值得重视的是,赵汀阳指出,在西方哲学热潮背后,其实能看出中国的理论偏好,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西方哲学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他分析了中国传统精神的特质:重视心理而忽视逻辑,倾心文学性而不是理论性,善于灵活解释而短于理性分析,倾向人文关怀而不是科学。正是“这些偏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选择。被选中的西方哲学,或多或少用来与中国思想互相印证”。所以,他呼吁“中国思想真正缺乏的是理性的怀疑论、逻辑分析和理论化的方法”,应该遵循“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加以重视并吸收。上述的这些批评意见和学术反思,实质上反映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客观历程——从“心急火燎”的拿来主义向“脱离喧嚣”的消化吸收的重要转型。
因此,对于当前西方哲学热出现某种程度的降温现象,也可以这样理解:与其说西方哲学热出现某种消退迹象,不如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沉下心来,逐步摆脱仅仅是追逐热词的表层研究,转向更加理性的学术审视,进而开展从哲学机理中汲取真正营养的深度研究,其目的也在于汇入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系统建构的大潮流中。
中西马汇通:可能的框架和倡议
综上所述,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的视角,审视近些年中西马哲学领域取得的创新性发展,可以看出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中国性”在迅速成长。最为耀眼的是,中国哲学领域近些年的发力,其主攻方向就是寻求对“以西释中”框架的突破,重点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挖掘自有的“中国特质”,探索自身的发展理路。而脱离了教条主义束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中国当代实践,夯实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加速了“中国化”的进程。西方哲学的研究则开始进入相对冷静的理性审视期,着眼于扎根中国的理论土壤,积极寻找深度“本土化”的切入点。
第二,中西马哲学融合深度在不断加深。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理论的自我封闭,在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重点是儒学的对话中,理论体系变得更加丰盈、更加开放。而西方哲学研究,正由不自觉地被中国传统思维过滤进入自觉意识的本土化改造这一更高层次。最值得观察的是,中国哲学领域对“以西释中”框架的反叛。这当然不是完全脱离现代哲学的“复古迷思”和彻底放弃中西比较视野的“自我放飞”,而是对过往机械填鸭模式所造成的对中国哲学本真深度压抑的一种修正,是中西马哲学以更加“舒服自洽”的方式实现有机融合的重要表现。
不过,尽管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构建呈现出中西马哲学加速融通的趋势,但是学界对中西马哲学的汇通方式仍存在很大的分歧。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其最终的历史形态究竟是怎样的?终极答案肯定有待于在今后的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发展中揭晓。对此,作为“局中人”和“过程人”,我们现在很难精准描绘出来。不过,众多研究者一直为这一命题贡献智慧,预测或倡导未来可能的理论大框架或大方向。
例如,姚新中等提出构建“大哲学”的理论方向,以便使当代中国的哲学能从不同的文化土壤之中汲取更加丰富的资源,突破本土哲学、西方哲学对立的窠臼。这一“大哲学”既包括规模上的“大”,即自觉地把哲学问题放在整个哲学历史发展和哲学各学科互通的语境中来理解;也包括视角上的“大”,即从全球意义和中国长远需要来提出并回答问题;更包括方法论上的“大”,即把哲学作为渗透于其他学科并为之提供思维方式指导的宏观方法论。
又如,赵汀阳提倡一种“新概念的哲学”。他认为,西方哲学不足以反客为主地将中国哲学安置在其空间里,但是中国哲学也不可能将西方哲学安置在既有空间里。尽管不少人提出中国哲学将像吸收佛学一样,最终消化掉西方哲学。但是,他认为不可能:一种外来知识要被化为己有,必须拥有比外来知识更大容量的思想空间;西方哲学的思想空间比中国哲学更为广阔,至少多出逻辑学、知识论和怀疑论等维度,更有新发展出来的分析哲学、科技哲学等。他认为,在未来,“也许是唯一的可能性,是共同创作一个足够丰富而可共享的思想新空间,即一种新概念的哲学”。
此外,还有更多学者的相关探索,受到篇幅的局限,本文没有一一列举。不过,总体而言,受到学术发展客观阶段的制约和主观上的审慎态度,目前学界所能提供的多是比较开放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倡议。这样的框架或倡议无疑有利于中西马哲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继续融合发展。
如果放眼于更长远的未来,也许可以将中国当前阶段所积累的中西马哲学融通的成果视为一个中间过渡形态。因为,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最终形态还可能是高度融通了中西马哲学的、实现有机统一的一体化哲学。在这其中,中国哲学将找到充分演绎自身古老智慧的“中国写法”,破解接续传统与现代的历史难题;经过分析哲学“元语言”检验的西方哲学的现代因子将更加自洽地融入中国语境;而作为来自西方哲学体系又深度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官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是沟通中西方哲学的最佳桥梁,理应承担更大的使命,为此也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和更强的力度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加速融通,开放自己的理论体系,提供更加适宜的思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