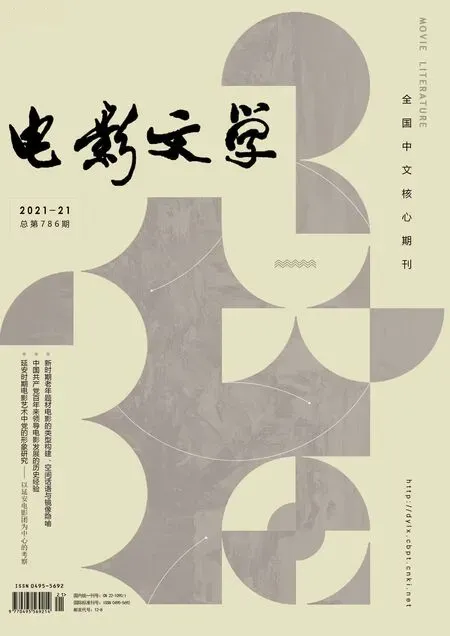基于《革命者》的主旋律电影类型化讨论
芦甲川
(中原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国产电影基本可以被分为主旋律电影、文艺/作者电影以及类型电影三类。长久以来,三者之间泾渭分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中国电影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后,主旋律电影开始出现类型化倾向,包括制作与宣发模式以及具体电影语言的运用等,在实现自身票房影响力的同时,也为国产电影迈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由徐展雄执导的《革命者》正是其中一例。
一、走向类型电影形态的主旋律电影
对于主旋律电影这一中国特有的电影艺术形式,其具体定义一直众说纷纭,一般来说,从其倡导者、主要表现内容与承载的精神来看,主旋律电影可以视为“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大力倡导和扶持的,反映其政党思想观念和政治诉求,反映血雨腥风的革命历史斗争,反映现代化建设的雄壮步伐和波澜壮阔的改革生活,以歌颂正面人物和光明事件为主,弘扬民族文化,表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并传达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创作态度的电影”。而值得注意的是,主旋律电影的概念之所以莫衷一是,正是因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不断从异质资源中汲取养分,赋予主旋律电影新内涵与新形式,让主旋律电影显示出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数十年来,主旋律电影一直在开拓自己的创作空间。
而其中一项重要的转向便是,越来越多的主旋律电影有了较为清晰的类型电影样态。正如学者指出的,“主旋律电影要提升其在市场上的吸引力,一个有效的策略是积极吸收类型电影的经验,以类型化叙事来提高其与观众观影心理的契合性和对观众的吸引力”。如林超贤的完全可以被视为警匪动作片的《湄公河行动》、尹力将主旋律与爱情片相嫁接的《云水谣》、为国庆献礼的《我和我的祖国》等更是喜剧片意味浓厚,让观众于身心的娱乐中充满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可以看出,类型片原本就密切贴合市场的叙事模式得到了主旋律电影的充分借鉴,观众们的审美喜好得到了主旋律电影的积极回应,而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正是这一类类型化主旋律电影得到的回报。
首映于2021年7月1日的《革命者》,其主人公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一的李大钊。电影显然肩负着从李大钊的相关故事中,增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观众中的吸引力与凝聚力的重大责任。电影要如何与观众实现情感交流、知识传递和思想沟通,尤其是要争取年轻的、远离“革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艰难年代的观众,将他们转化为笃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新青年,这无疑是有一定难度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进行了融合各类型范式的尝试。
二、《革命者》的类型范式
在《革命者》中,观众实际上可以感受到传记、悬疑等电影的类型美学或范式特征。首先是传记片范式。毋庸置疑,《革命者》最为突出的类型属性是传记片。传记电影“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允许想象、推理、假设,并做合情合理的润饰”,《革命者》正是采用了这种叙事策略,片中真实与虚构相融合、伟大与平凡相辉映、高尚与卑鄙相对照。电影中李大钊所组织的开滦煤矿大罢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无疑是吻合历史材料的;而小偷徐三、乞丐庆子等“小人物”的相关情节,则带有一定的虚构和润饰色彩;电影以张作霖穿戴整齐并被摆布动作照相情节,暗示他在各方势力中骑虎难下,以蒋介石一边听《天官赐福》接玉玺,一边让特务对共产党员大开杀戒,暗示蒋的野心及阴狠,这些更是出自合理的艺术想象。
只不过相对于传统的、往往以线性时序来展开叙事的传记电影而言,《革命者》有意打乱了时间顺序,从李大钊临刑前的38小时出发,借由他的所思所想,以及其他相关者的回忆,让现在与过去不断交织,来展现人物的漫长一生。由此,电影规避了平铺直叙有可能带来的乏味无聊,并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多种转场,如由狱中临刑前要剃头的李大钊被泼的一盆冷水,马上过渡到毛泽东洗冷水浴的场景,从而引出时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与图书管理员毛泽东的一段交往,使得38小时具有了无限拓展的可能性。
其次是悬疑片范式。在传记范式之外,《革命者》实际上还有悬疑片的意味。由于电影对历史的尊重,在观影过程中,尽管电影中也表现了我党依然在积极地组织对李大钊的营救,但观众并不会产生“营救究竟成功与否”的悬念,而是已然知道了38小时之后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结局。但电影依然制造了悬念,即人物“怎么牺牲”、李大钊与张氏父子有过怎样的交集等,提升着观众对人物命运的关切。电影中充分表现了张作霖对要不要杀李大钊这一影响力巨大人物的犹豫之情,设计了张作霖将释放李大钊的请愿书和要杀死李大钊的各方电报放在一个天平上的情节,而天平微微地倾向于“处决”那一侧。观众便和此刻的张学良一样紧张。随即电影从张学良的视角,讲述了约十年之前,二者曾经在上海的一段关于报童阿晨被俄国人打死,二人都想为报童讨回公道的“巧遇”。既埋下了伏笔,又将观众的注意力转移了,实现了“绞刑”这一信息的延宕。当这一段叙事完成的时候,观众便能理解,为何张学良主张保住李大钊,因为在尚是热血青年的他眼中,李大钊是一个真心实意为百姓谋利的人。而随着蒋介石在嫉妒、忌惮等心态下的“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电文被加上,悬念解除,观众意识到张作霖至此下了杀死李大钊的决心。电影靠直观的天平、时间断点的设置和不同叙述视角的运用,成功地营造出了悬疑氛围。
除此之外,《革命者》实际上还显现出了一定的家庭伦理片范式。由于电影由各叙事碎片镶嵌而成,这也就为电影从家庭生活的角度塑造李大钊提供了便利。尽管在传记电影中,传主的家庭生活也是常见的叙事内容,但《革命者》中这一部分的闪回叙事是从李大钊妻子赵纫兰的视角出发形成的,并且电影为凸显李大钊曾经享有的优渥物质生活与天伦之乐,在影像风格(包括布光、用色等)上有意使其与其余几段叙事区分开来,因此这是值得单独探讨的。在赵纫兰的回忆片段中,电影与家庭伦理片一样,既以唯美的意象烘托出了人物的抽象情感(如周末在外野餐时,李大钊一家在蓝天白云绿地间欢笑大闹),又介绍了现实为主人公坚韧情感关系制造的波折(如赵纫兰焦急地在人间地狱般的医院寻找丈夫,李大钊为同志的伤亡悲哀地靠在妻子身上等),同时还展现了亲子之间亲密、健康、满怀爱意的关系(如李大钊子女对他的祭奠和“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的询问等),恰好与电影中阴郁、掺杂了利益纠葛的张作霖、张学良的亲子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三、《革命者》的类型化启示
《革命者》的类型化尝试,对于后继的主旋律电影是有启示意义的。
一方面,《革命者》如《集结号》等电影一样,让电影人看到了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可能。类型电影被称为成年人的童话,它为成年人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现实矛盾的替代性解决方案。正如托马斯·沙茨所指出的那样:“类型的基本文化对立或者固有的戏剧冲突代表着它最为基本的、决定性的特征。任何类型的持续受欢迎,说明了这些对立的无法解决和不可协调的本质。”而传记类型片,所满足的则是观众无法拥有跌宕起伏的人生、无法出类拔萃、无法感受另外一种身份下人情冷暖与世事无常的遗憾。在《革命者》这样的电影中,李大钊以及蒋介石、张学良和毛泽东等人的人生片段被以李大钊不同的人生节点展现出来,观众得以追随人物进入另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时空与关乎民族命运的身份中,获得一种未知性审美体验。在观影过程中,观众实际上和传主一起振臂高呼,出生入死,在“壮烈的牺牲”中重新认识何为“高尚的生活”,这显然迥异于观众在电影院之外简单宁静、日复一日的生活。简而言之,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有着宽广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与《风声》《集结号》等的创作分别严格按照悬疑谍战、战争类型进行规划不同,《革命者》完成的是一种类型的拼接。这在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短片“拼盘”后无疑是更进一步的尝试。主旋律电影因其性质注定了它针对的是最广大的观众,其目的是尽可能让所有观众得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感召,然而类型电影却是市场细分(Marketing Segmentation)下的产物。即在市场调研后,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和消费能力,集中人力物力分别制定营销策略,最终实现降低成本、最大化盈利的可能,例如,针对喜爱暴力美学,崇尚侠义、冒险精神者拍摄武侠片与西部片等。就对受众的划分而言,主旋律与类型电影存在一定的矛盾。而《革命者》所进行的类型拼接,就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这一矛盾。电影中的传记片类型特征,吸引的是喜爱历史,对英雄人物有崇拜之心、秉承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观众;而其悬疑类型片特征,则又吸引了好奇心强烈、喜爱惊险刺激情节、对现实生活感到乏味的观众,这一部分观众又不乏年轻群体;而电影中的家庭伦理类型特征,则又满足了具有婚姻生活经验的年长者观众的心理期待。由此一来,电影的受众群就得到了开拓,更多年龄不同、社会阅历不同的观众能沉浸在叙事之中,认可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代表的精神。
诚然,《革命者》并非如《风声》等那样类型化程度较深的主旋律电影,电影在统合影像自身表现力与意识形态言说上也并非无可指摘之处,如电影在最后以混剪展示不同群体的人纷纷对着镜头齐声呐喊“我相信”,以作为对李大钊的信念“从一个人的相信到所有人的相信”主旨的呼应,并试图将观众纳入到这一情绪之中,这未免因偏离了之前的叙事策略而显得突兀。但瑕不掩瑜,相对于近年来纷纷折戟的如《血战湘江》等主旋律电影而言,《革命者》在建构一种新型认同机制上的诚意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一部建党献礼电影,《革命者》在有限的时长里,围绕李大钊这一革命先驱,为观众呈现了那段共产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火热年代。而传记片、悬疑片以及家庭伦理片各自的类型化叙事方式,有效地帮助电影实现了以小见大、以点带面,让观众得以串联起李大钊一生的多个侧面,贴近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在当代积极运用类型化策略的主旋律电影中,《革命者》显得尤为闪耀,电影除了再次证明类型化叙事嫁接主旋律精神的可行性之外,还提供了一种拼接多种类型的范式,让年龄与阅历各异的观众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电影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毫无疑问,主旋律电影还将继续发挥其宣传、教化作用,而其在创作上的探索与革新也不会止步,其类型化尝试还将呈现出更为异彩纷呈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