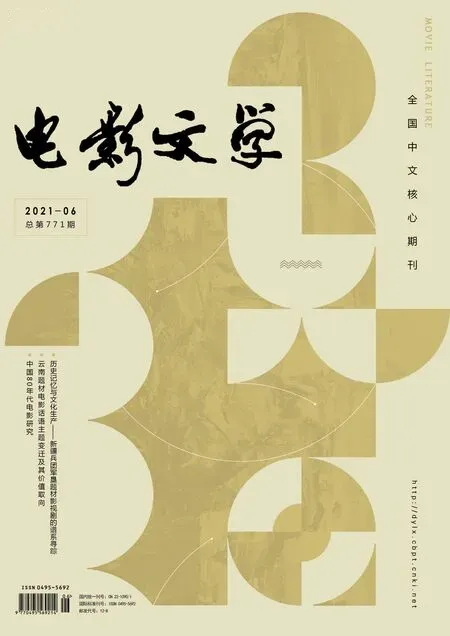亚历斯·冯·华麦丹电影的诡异风格与人性伦理
吴 颖(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荷兰导演、编剧亚历斯·冯·华麦丹的电影以非理性的反常叙事奠定了诡异风格的基础,在题材上多以北欧家庭或家庭关系题材为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人伦悖逆、心灵扭曲和道德失范。其电影的内在精神既有游戏的一面,又有严肃的一面。前者在于对既有秩序和人性异化的冷嘲热讽,后者在于在电影中为现代人探索一种更符合人性的存在方式。
一、非理性的反常叙事
亚历斯·冯·华麦丹的电影无一例外地追求情节的离奇,以反常规的故事情节将观众置入电影的陌生情景中。这一追求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潮流的兴起是相适应的。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一切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价值都受到质疑。人们曾依靠理性建立起人的存在的目的论和道德论,以为存在的意义寻求答案,并赋予这种意义以超历史性,相信它具有某个确定的中心。但正如德里达所言:“这里没有中心,在在场-存在模式中,中心是不可想象的……它是一种使无数符号替补的游戏得以进行的无定点。”这一表述道出了后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精神,那就是“非中心化”。表现在电影中就是放逐了电影艺术的教育功能,以戏谑、嘲讽、反叛的姿态来替代以往电影中或隐或现的价值宣扬和说教功能。
亚历斯·冯·华麦丹电影的反常叙事首先表现在他善于创造一种失衡的故事起点。他电影中的人物往往一出场就处在一种反常的情景中。《阿宝》中32岁的阿宝未出过家门,阿宝的父亲把一个女性朋友带回家,试图传授阿宝一些基本的社交礼仪,由此开始了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恋情。《妙在大门后》中,一对农村夫妇请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家庭教师,由此开始了一段几经波折的三角恋。《伯格曼》中,穴居人伯格曼突然出现在某个富有的郊区,敲响了一户小康之家的大门,随后展开一场神秘古怪的入侵。借用某一人物的突然出现或某一事件的偶然发生打破原有关系的平衡以形成强烈的结构张力,是亚历斯·冯·华麦丹构思故事的常用手法。
其次是人物功能的反常规。传统的电影艺术,人物都是承担了固定的功能的,甚至按照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来看,角色就是功能,所有文本中不外乎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敌对者与帮助者这几组两两对立的功能。但在亚历斯·冯·华麦丹的电影中,角色的功能性质被大大弱化了,人物行动的目的和动机都变得反常。《夺命裙》围绕一条充满热带风情的裙子,讲述了一个个充满暴力的喜剧故事。年迈的老妇人换上令自己年轻的裙子,以引起丈夫的爱欲;火车验票员着魔般爱上裙子的图案,固执地追逐着裙子的主人;画家的女友面对疯狂的陌生男子不是反抗与拒绝,而是陶醉在他轻声细语的“我爱你”中等。这些怪诞的故事偏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解不开的心结,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触点。
再次是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情节反转。《妙在大门后》中,导演将情节转折再转折:中年农民夫妇家中,妻子为丈夫请了女家庭教师,丈夫冷落了妻子而向家庭教师表达爱慕,但又不敢做越礼之事。此时剧情突然发生转折,妻子非常渴望得到一个孩子,拼命鼓动丈夫“解放自己”。剧情再次转折,生了孩子的家庭教师要带着孩子和丈夫去城里住。妻子决定留下孩子、杀掉家庭教师但未能成功,而丈夫选择杀掉了妻子,家庭教师则独自带着孩子离去。影片描绘了复杂三角关系所衍生出来的迷惑与不顾一切,情节峰回路转。在他的诸多影片中,都无从找到角色的稳定不变的行为逻辑。
最后是“打破第四面墙”。叙述者与故事中的角色乃至接受者之间的界限都被打破了。故事中的角色不仅会向叙述者讨价还价,还会面对观众抱怨。这就是亚历斯·冯·华麦丹在《服务生之死》中进行的极具先锋性的实验。故事从一个服务生的工作开始,他的情人来到他的餐厅用餐,但似乎引不起他太大兴趣。他的工作很无聊,情人又老又丑,家中还有个常年卧床的老婆,这么无聊的剧情真的是对不起观众。然而从这一刻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不只我们觉得剧情无聊,服务生也觉得无聊,于是他愤怒地冲入作家的家中,向作家抱怨自己的生活太无聊,剧情太无趣!戏剧中有一种说法叫“打破第四面墙”。在舞台表演中,左右和背面是属于舞台的,正面是观众,而观众和演员之间虚拟的一道墙就是第四面墙。德勒兹认为,电影的效用就是把人从日常生活的视角中解放出来,表现为任意视角的重现。通常来说,我们看到的电影是上帝全知视角,或者角色主观视角。显然在这部电影中,作者将任意视角运用得淋漓尽致。
二、生存异化中的人伦背反
亚历斯·冯·华麦丹的电影大多都是家庭题材,或者至少涉及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等家庭伦理关系。当导演嘲弄式地将家庭关系扭曲呈现时,诡异与荒诞就无可避免地成了他电影的主调。
他电影中的家庭,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家庭成员关系的淡漠。家庭不再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港湾,而似乎是一个类似于监狱的行使规训功能的社会机构,每一个个体只剩下软弱无力的法定义务和本性中的那点占有欲。《阿宝》中,阿宝是一个成年男子,可对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整日只会用望远镜来偷窥别人。他很想看电视,可从来没看过,因为父亲不让他们买电视。为了反抗父亲的权威,阿宝抓住每一个机会与他作对。母亲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反抗丈夫,却曲意维护儿子。当父亲请朋友回家培养阿宝社交技能时,整个家庭就陷入了微妙复杂的关系中,所有的家庭角色所应承担的家庭功能和责任毁于一旦,家庭成员由相互取暖的关系变为相互伤害。
与家庭情感的淡漠紧密相关的是个体欲望的压抑。人的部分欲望可以在家庭中得到合法的满足,当家庭不能对这种欲望进行有效规训和满足时,就诞生了种种非理性的行为——出轨:《北方小镇奇谈》中男人的妻子想成为宗教圣女拒绝行房,而她的丈夫只好觊觎别人的老婆。恋物:《夺命裙》中火车验票员着魔般爱上裙子的图案。偷窥:《北方小镇奇谈》中的邮差最喜欢的是拆小镇居民的信件等。这类主题在亚历斯·冯·华麦丹的电影中无处不在,他的敏锐之处在于通过人物的心理扭曲呈现家庭人伦的崩坏。
现代人生存境况的虚无和无意义被亚历斯·冯·华麦丹通过家庭题材得以具体呈现,家庭的沦陷已经用最直接的方式向我们宣告了生存的无意义、道德的虚伪。亚历斯·冯·华麦丹的暴力是不带任何怜悯的。西部片中也充斥着赤裸裸的暴力,但所表现的是在秩序还未建立的生存环境中人们相互残杀争夺生存资源的残酷,隐含着对文明秩序的呼唤。然而亚历斯·冯·华麦丹电影中的暴力却是一种美学追求,电影中角色的暴力不是为争夺,而是一种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本能。这在他的电影《博格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博格曼这个流浪汉带着一种原始的覆灭的气势来到一个光鲜富足的家庭,他带着庞大的计划和目的。片中关于暴力手段的表现,有种恐惧而冰冷的诗意。博格曼要做的并不是占领这座豪宅,当他们扼杀了生命,“改造了”花园离开时,带走了这家的三个小孩。片中有段戏表现了在花园里的舞台表演,仿佛各种符号和意象的表述,其中那个有芭蕾功底的女人,观众曾在她游泳时看到过她后背的手术伤疤,大抵她也曾是光鲜文明人家的孩子,如今的她,仿佛是那三个孩子的未来。《博格曼》有一股冷漠犀利到骨子里的风格,不时还闪现着鄙夷、戏谑的味道,人性中潜在的暴力部分在这部影片中被合乎情理和逻辑地由意识转化为行为,而且来得干脆利落。
正如布列松所说:“你不能束缚观众,而是要让观众爱上你。你必须让他爱上你表达事情的方式。”亚历斯·冯·华麦丹做到了这点,他没有束缚自己,更没有束缚观众,虽然他的电影诡异而古怪,但在细思回想时,又不能否认迷上了这份诡异和古怪。
三、道德荒漠中的人性重构
亚历斯·冯·华麦丹用充斥其间的心理扭曲和暴力揭露了现代社会的人伦失序。他既揭露了现代人在意义的荒漠中生存的痛苦与不幸,又嘲弄着理性所建立起来的使人异化的秩序。固然,他的电影在诡异中诉说着深刻的绝望。然而,游戏、癫狂、诅咒却并不能完全概括他的电影精神。在诡异风格背后,仍隐藏着一些令人慰藉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他在剥去层层的文明伪装之后,还原出的最真实而又最宝贵的人性。
《施耐德对决巴克斯》讲述了两个杀手之间的对决。但在这部以杀戮为主题的电影中却最能体现导演对人性正面价值的肯定,哪怕它是以某种曲折的方式显现的。施耐德和巴克斯平时都是有着正当职业的普通人,但背地里他们都会干一些暗杀的业务。不同于一般为钱财而杀人的杀手,他们两人在选择目标上都有一定的原则。杀手公司最初将此次杀人业务安排给他们时,他们都因某些原因不想接手,但当听说对方是一个儿童杀手时,他们又拿起了猎枪。“儿童杀手”这一说辞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不容拒绝的理由。这是影片中第一处体现杀戮的原则即保护弱者原则。第二处是当施耐德已经埋伏好,正聚精会神地瞄准时,发现巴克斯家中仍有其他人。为了不伤及无辜,他暂时放下了手中的枪。同样,巴克斯在察觉到危险,准备大开杀戒时,先是将家中那些不速之客驱赶走以免误伤。不伤及无辜是杀手的第二个原则。当施耐德发现了杀手公司老板梅尔滕斯的编造谎言让他们相互残杀的阴谋之后,他也并没有停止杀戮。因为他必须解决掉威胁自己和家人生命的危险因素。因此自保是杀戮的第三原则。影片的最后,施耐德已经解决了巴克斯,只剩下在危机中一反常态变得出奇果断干练的巴克斯的女儿与其对决。弗朗西斯卡被逼入一间小屋并被施耐德从窗口缴了械。当施耐德举着枪小心翼翼地进入小木屋中时,与他相对的是赤裸身体的弗朗西斯卡端坐在破旧的沙发上,施耐德此时放下了他的枪退出了房间。因为他明白,弗朗西斯卡脱光衣服意在表明一种解除威胁的和解。影片的主题在施耐德放下枪的那一刻得到了升华,对一个赤裸的生命的尊重乃至信仰令他宁愿牺牲自保原则,恻隐之心战胜了他的杀戮本能。
结 语
虽然在亚历斯·冯·华麦丹的电影中总是不断重复着心理扭曲与暴力的主题,但这并不是导演真正的趣味所在。他的电影蕴含着一种不破不立的气质,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批判现实,同时又期望在价值失落的时代重新发掘人性中的闪光点,并以此作为价值失落时代人类社会行为原则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