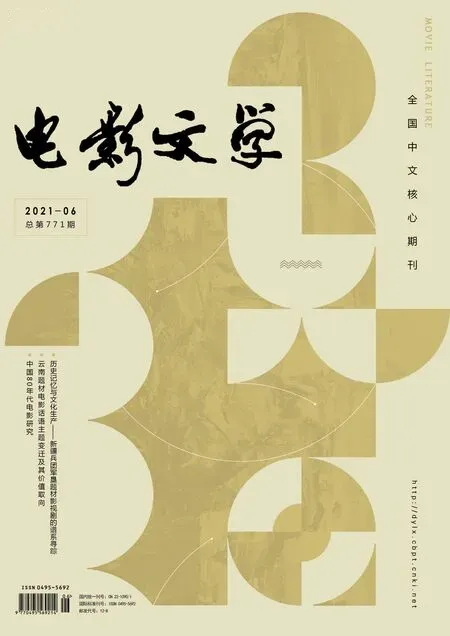用丰厚的民族化内涵赢得和打动世界
——中国电影“走出去”的编剧路径思考
林雪飞(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随着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持续推进。电影作为最具号召力的现代大众艺术形式,不但在国内文化产业领域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而且其参与世界竞争的能力也逐渐增强。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屡获国际奖项,票房收入连创新高,国际影展举办次数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影片打入国际院线。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品牌”,已经真正征服了国际市场?
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年度票房方面,近年来美国电影的海外票房一直稳定在接近300亿的水平,而中国电影的海外票房只有美国的2%~3%。单片票房方面,国产影片海外票房纪录一直由《英雄》保持,该片全球总票房1.77亿美元,国内票房仅为2.5亿人民币,海外票房占比超过80%;此外,《战狼2》总票房达到8.7亿美元,海外票房1790万美元,占比2.06%;《唐人街探案2》总票房5.4亿美元,海外票房却仅为270万美元,占比0.5%;《流浪地球》截至2019年上半年总票房6.99亿美元,海外票房接近7000万美元,占比10%左右。显然,绝大多数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仍主要来自国内市场,这与中国人口红利不无一定关系,而其在国际市场角逐中的成绩并不那么乐观,中国电影还正在“走向世界”的路上跋涉。
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经受“消费者”的拣选,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文化产品,都必须依靠过硬的品质和优良的质量,只有真正优秀的产品才能赢得世界的认可和尊重。然而豆瓣数据显示:近年来国产影片的评分大多低于6分,平均评分更一度由2012年的5.12分降至2016年的4.4分,而4分以下的影片2012年占比26%,2016年则增至4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电影整体的质量现状。所谓“叫座不叫好”,正是对国产影片质量认知的最直接描述。电影观众作为这种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是最有资格对其进行质量评价的“评判者”,他们可能会因为娱乐需求、明星效应、营销吸引等因素走进影院,从而为“票房”贡献一份力量,却不会在观影后为自己并不满意的影片违心叫好。因此,这种“票房”高企而“口碑”低迷的背反现象背后,正是广大观众对中国电影整体质量还不大认可的残酷现实。因而,当前中国电影创作必须首先从提升质量上下功夫,用真正高品质的作品去打动观众、打动世界。
一部好的电影作品,应该在各个环节都“精工细作”,需要编剧、导演、表演、后期等多部门的协同努力。但一般来说,编剧是电影创作的第一步,剧本也一直被视为“电影的灵魂”,“一部电影的命运几乎要由剧本来决定”,“一个导演可以拿到一部伟大的电影剧本拍摄成为一部伟大的影片;……但他绝不可能拿到一部糟糕的电影剧本而拍摄成为一部伟大的影片”。因此,提升国产影片的质量又必须首先从编剧入手,从创作的一开始就努力制作出高质量的剧本,进而拍摄成高品质的影像作品,使中国电影真正成为一张精美的国家名片。
一、题材:时代现实的深刻书写
百年中国电影有着坚实的现实主义传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渔光曲》《风云儿女》《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八九十年代的《天云山传奇》《人生》《芙蓉镇》《老井》《本命年》等作品,都以清醒的现实意识与反思精神深刻地书写了当时的社会和人生,清晰地呈现出不同时代的典型特征和主体风貌。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大众狂欢的娱乐主义甚嚣尘上,中国电影创作的精英意识“出走”,现实主义精神也明显弱化。不少电影剧作,特别是致力于国际市场的商业大片,都极其热衷于历史题材,如《英雄》《无极》《夜宴》《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赤壁》等。从表面上看,这些影片都特别强调重释民族历史和文化,但实际来讲,历史观念的虚无、思想价值的模糊、故事情节的不经推敲、人物塑造的随性等弊病,几乎在每一部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它们最大的看点在于外在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宏大华丽的视觉效果,而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与当下的现代中国相去甚远,甚至与古代的传统中国也有很大差别,不禁令人有些迷惑。就连主旋律影片,也多倾向于关注现当代历史,通过重述某些重大或典型的历史事件,重现刚刚过去时代的“已然”特征,宣扬具有承继意义的民族精神,如《建国大业》《集结号》《风声》《十月围城》《南京!南京!》《铁人》等。倒是一些“小成本”剧作,常常喜欢涉及现实题材,如《小时代》《失恋三十三天》《滚蛋吧肿瘤君》《何以笙萧默》《私人订制》等。但这类影片对于现实生活的表现却又比较“表象化”“个人化”,或记述某些个体的经历,或宣泄某种个体的情绪,本质上疏离了时代大潮的表现,甚至闭门造车地描写主观想象的生活,回避了社会本质的揭示,最终也未能呈现出当今中国的清晰面影。“纵观世界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史,不管是默片还是有声,不管是黑白还是彩色,不管是胶片还是数字,能够真正留在电影史上作为里程碑和航标灯的作品,90%以上都是表达一个国家某个时代主体生活和主体精神的作品。”由此看来,目前的这些电影剧作尽管票房收入可能还不错,但经过历史的沉淀与淘洗之后,恐怕都难当“经典”之称,无法成为21世纪中国电影的标志性成就。
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日新月异,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新的时代还需要我们细细地品味与审视,世界也正对这样的中国充满了好奇。于是用艺术的方式记录和反思当下的社会和生活、向世界展示崭新的中国形象,现实主义自然就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个必然选择和一种必要回应。但现实主义绝不仅是对现实世相的简单描摹,而必须真正揭示社会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切实触及时代的灵魂。现实主义创作是一种严肃的时代探索,需要创作者具有“善于发现”的深邃目光,并不断深入地观察和思考生活,勇敢地将笔触潜入社会机体的深处,深刻地书写出新世纪中国真实而独特的时代内涵,既展现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也直面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每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作品都必须表现一个宏大的主题,传达一种崇高的思想,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实的存在是丰富的,现实主义的表现也应该是多面的、多元的、个性的。不同的作品完全可以从某个细小的、单一的或个人的角度切入,只要真正讲好了一个特有的中国故事,让人们从中领悟到真切鲜活的时代、社会、人生和人性,那就是成功的。至于这个故事,不管是伟大,还是卑微;不管是温馨,还是悲伤;不管是歌颂,还是批判,只要能够使人获得某种“真”的认识,引起某些“实”的关注,引发某种“善”与“恶”的思考,那就是有意义的。《我不是药神》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的创作题材直接取自当下中国的现实生活,无溢美,不隐恶,以一个最普通的小药商的个人经历为叙述主线,折射出更多普通中国人遭逢重大疾病时的残酷生存状况,大胆地揭示了当今时代中国某一侧面的社会真实,也涉及了现代企业经营、医疗制度改革、法与情、人性的善恶等多重颇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尽管影片的艺术表现并不完美,但仅就题材内容来讲,由于贴近生活实际、直指社会问题,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剧作实际也获得了豆瓣9分的好评。现实生活永远是艺术创作最丰富而坚实的资源宝库,新世纪的中国值得也亟须中国电影创作更多独具慧眼的发现和独具匠心的表现。
二、内涵:人文精神的含蓄表达
电影是一个复合的“叙事—表意”系统,叙事作为显在的结构,意则表现为其背后隐喻的精神内涵,不仅包括“事”所直接标示出的时代之韵,更包含“叙”所透露出的创作者的精神之思。叙事的丰简自然关系到影片质量的好坏,而表意的深浅也直接影响着影片品格的高低。严格地说,不具有表意功能的叙事是不存在的,每一部电影剧作总要体现一定的价值观倾向,传递着或隐或显、或深或浅的思想意蕴,这正是电影的文化品质。但精神蕴含的传达绝不是口号的呐喊,也不是简单地说教,而应是一种深沉含蓄的心灵启悟,以深度和厚度为其价值之因,以影响效度为其价值之果。世界电影史上的许多隽永之作,都是因为蕴藏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具有长久广泛的情感熏陶、思想启迪和精神引领的作用,而显示出超时代、跨民族的精神价值。
中国文艺创作一直有着自觉的人文关怀意识,世代都留存有不少深蕴人文精神内涵的经典之作。作为现代新兴的艺术形式,电影的发展历史虽然并不长,但其中也不乏人文内蕴斐然、人文风采飞扬的优秀作品。但随着文化市场竞争的愈演愈烈,电影的商品属性日渐凸显,“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观念迅速挤压了其创作的精神空间。一些剧作为了迎合大众的欣赏趣味,片面追求“笑果”、色情、暴力、血腥等“愚乐”式的刺激体验和奇观化的视觉效果,却忽视了人性追问、思想探索、精神提升、灵魂净化等艺术内涵的开掘。《大笑江湖》直言“草根”属性,由东北“小品王”赵本山及其徒弟小沈阳等参与主创,凭空杜撰了一段出逃皇后和流浪鞋匠相遇江湖的浪漫爱情传奇,情节荒唐恶搞,滑稽无聊,可以说没有什么精神内涵可言,品格也不出庸俗谐剧之右;《让子弹飞》标榜“中产情趣”,借用文学著作《夜谭十记》“盗官记”的情节构架,却将历史荒诞化、叙事电游化、精神虚幻化,大大降低了原著冷峻批判的色彩,剧情基本演化成了一出土匪斗恶霸的热闹惊险的喜剧,其人文精神价值与文学原著相比确有差异,也与导演姜文早期创作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无法相比;《英雄》《无极》等堪称“大师”创作,由知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等耗巨资打造,但影片在人文精神内涵方面却也显得苍白,无甚值得称道之处,无法与曾经的《红高粱》《黄土地》等经典剧作相提并论。《小时代》则被视为“新锐”的代表,是80后作家郭敬明的跨界之作,影片内容虽涉及青春、爱情、友情等母题,但实际上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沉浸在对奢侈生活的夸张描写之中,以耍帅炫富为噱头,没有现实的反思,也不进行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精神价值也实在不高。综观新世纪的中国电影,似乎确是患上了某种“文化贫血症”,人文精神缺失、思想价值跌落已成了不争的事实,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电影质量危机的根本原因。
“中国电影的第一要义是精神”,其创作必须尽快从忽视精神内涵追求的错误中清醒过来,以人文精神作为剧作艺术思考的内在支撑,含蓄地传达中国文化思想的深邃内涵。谢晋曾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当下中国电影创作就格外需要创作者的深邃思想,以便深刻洞察社会和人生的内面,并借助恰切的艺术方式进行独特的思考,歌颂真善美,弘扬正能量,积极引导人类的精神发展和价值追求,为未来承担一份责任。《流浪地球》之所以能够赢得国内外观众的大量赞誉,除了科幻特技的炫目震撼,对人类生存的忧患意识和坚毅执着的担当精神,也是打动观众心灵的重要因素。电影创作不要低估观众的欣赏品位,作为当前观众主体的中国中青年群体,由于文化素养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具有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力,越来越重视精神的享受与追求,娱乐消遣固然也是他们观影的一种需要,却不是唯一的需要,“直”“露”“浅”“俗”,没有一定内涵容量的作品,无法满足观众日益发展的精神需要。内涵性表现,才是中国电影创作追求的一种新的趋势。
三、美学:民族化色彩的深化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电影创作对民族化的认识一直是比较积极的,现代著名导演费穆早就曾断言:“中国电影要追求美国电影的风格是不可以的;即便模仿任何国家的风格,也是不可以的,中国电影只能表现自己的民族风格。”在如此明确的民族化创作观念引导之下,中国电影史上也确实涌现出了不少“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的优秀剧作,使中国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电影的某些特质。
新世纪之后,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同质化”趋势,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追求更加强烈,特别是商业大片的创作,更是极力炫耀民族化元素,彰显民族化色彩。《英雄》就是颇具代表性的,它被国外观众誉为最具中国色彩、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风格的影片,拥有强大的吸金能力和良好的国际口碑,但在国内号召力不强,差评不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的评价,究其原因还在于不同接受主体对“民族化色彩”的歧异理解上。国外观众因带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强烈好奇,很容易就沉醉在影片充分外溢的浓郁民族氛围之中,感叹于其充满诗意的瑰奇艺术魅力,自然会给出超高的肯定。而国内观众和影评人基于对自身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谙熟,对中国电影民族化的要求也更为深邃,比较倾向于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综合考察,很难轻易满足于过分外化的民族性表征,也就必然会得出否定的结论。尽管存在争议,但不管哪一种观点都没有否定“民族化”之于电影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有志于“走出去”的中国电影,更应充分借鉴其经验,弥补其不足,不断深化创作的鲜明民族特色,确立自身独立的美学品格,以吸引更多的世界瞩目。
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应该是一种现代化的个性艺术表现,既不能固守一成不变的传统民族本性,也不能一味迎合西方的趣味。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应该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既涉及电影艺术的内容,又是涉及电影艺术的形式”,并努力达到“电影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前中国电影创作的民族化追求与表现,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偏颇和不足,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提升。
民族化不是“中国元素”的机械叠加。所谓“中国元素”是指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如:长城、熊猫、武术、京剧、书法、青花瓷、旗袍、饺子等。作为影像叙事的典型意象,它们本身就凝聚着浓浓的民族文化色调,但这种色调如果仅仅停留在背景的层面,就只能是外在的、凝固的、有限意义的。电影创作只有创造性地使用“中国元素”,将它们与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激发它们真正的文化活力,生成更加丰富的民族文化意蕴。《功夫熊猫》虽是好莱坞制作,但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元素”,以熊猫为主角,以中国功夫及其意蕴为主题,以古代山水为背景,又配以中国风的服饰和食物等道具,演绎出了颇具趣味的系列故事,散发着浓烈的中国文化气息,吸引了不少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的观众的目光。“中国元素”属于中国,中国电影创作对它的应用具有天然的优势,关键还在于如何深入地理解和巧妙地使用。
民族化也不是民俗化,更不是陋习的猎奇。民俗是琐碎的、细节性的民族生活风俗,电影对于民俗的书写固然能体现出一定的民族化思维和精神特色,但往往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电影创作一味地沉浸在古老民俗的渲染中,就会削弱影片时代精神和力量的展现,忽视民族文化中向上向前的精神取向。特别是一些愚昧落后的风俗和奇观式现象,还可能造成对民族化的误读。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封建大家庭姨太太房前“点灯”的风俗,《菊豆》中封建家族内部乱伦与杀戮的扭曲现象,等等,作为单部艺术电影揭露与嘲讽的主题探索,这样的选材自然无可厚非,更何况两部影片还较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民俗与主题的关系,但如果整个中国电影创作都集中于民俗与奇观的方向,那么必然会造成民族化色彩的单一与迷失。而且,电影的叙事毕竟与文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影像和画面表现的聚焦效果很容易放大风俗与奇观的视觉冲击,给观众造成强烈的心理刺激,从而掩盖对其真正意义的发现与追寻。中国电影的民族化美学品格,应以明朗为色调,创作要不断探索实现民族化色彩丰富与深入表现的路径。
四、艺术:叙事的优化与完善
电影本质上是一种叙事的艺术,除了由题材和内涵所决定的思想性,艺术性也是它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思想性表现为内容,那么艺术性就表现为形式,内容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才能得以表现,没有高超的艺术性,不仅会直接影响思想性的实现,而且也绝不能称为优秀的作品。我们常说:中国电影必须讲好中国故事。所谓“讲好”,就是要选取恰当的艺术形式,建构完美的艺术结构,运用精妙的艺术技巧,汇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借此完成电影故事的叙述和思想的表达。这一艺术过程也可以被称为“叙事”,好的叙事应该“既包括对于创作者而言的讲好故事、述说动人、出乎意料的惊奇情节创意等,还包括作品对象富含情感内涵显露方式、具有新鲜奇异的构造形态和抓住观众心绪跌宕起伏的效果”。对于一般的观众而言,观影首先感知到的就是影片叙述了什么事,怎么叙述的,而评价影片质量的首要标准也正是看这个“事”叙述得好不好,即艺术性如何。简单的一句“不好看”,多半并不是指影像不够悦目,而是对影片叙事艺术最朴实的否定。
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创作,为了满足观众的视觉需要,特别重视技术的提升,因此单从技术层面来讲,中国电影的水平几乎已经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无几。“但相比起技术进步、产业格局的布排来看,叙事水平的提高和变化的幅度却未尽如人意”,干瘪、混乱、粗糙、虚假、幼稚、低俗、套路等问题普遍地存在于剧作的叙事之中。当年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无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究其实质,它表达的还是对影片《无极》叙事的极大不满和犀利批评。此外,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表达的吐槽,就更不胜枚举。虽然这些对中国电影批评的表述,往往都带有一定的个人情绪化色彩,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部分观众的共同感受,其中有些还是颇能切中肯綮的,需要中国电影创作者冷静思考。
叙事是电影创作的整体性设置,无法依靠拍摄时的临时技术处理来掩盖,因此需要在剧本创作阶段就充分优化。电影剧本的叙事必须兼顾文学性和电影性。这里的“文学性”与一般文学作品的要求基本一致:情节要引人入胜,未必一定多么曲折,但起承转合的节奏要舒张有致,并应该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和良好的完成度,偶尔合乎情理又出人意料的精心设计,也能给人以格外的惊喜;人物塑造则要立体、鲜活,人物性格应该随着情节的发展而显示出一定的成长性,人物言行要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和生活的实际;情感表达要充分、适度,不夸张、不造作,又必须具有一定的感染力;结构要根据情节推进、人物塑造和情感表达的特点与需要精心构置,不落窠臼和俗套;技巧运用要得当,不炫技,也不吝技;艺术风格要个性化,更要创新等。而所谓的“电影性”,即“剧本应该体现出电影作为一种视听结合的综合艺术之特征,编剧要注重运用电影思维和蒙太奇技巧来叙事写人,传情达意”,注重剧本叙事的视觉直观性和画面感,注重环境(画面背景)的描绘,使剧本能够适合直接的拍摄使用。
绝对完美的叙事也许是不存在的,但不断锤炼和完善叙事艺术,为观众提供流畅、清新、优美的艺术享受,也是电影创作者必须承担的责任。《流浪地球》在改编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时,对叙事确实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时空的高度集中、节奏的紧凑、冲突的激烈、画面的粗犷、描写的细腻、“工业风”的浓烈氛围等,都是影片叙事艺术成功的关键。但某些细节的表现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对于主人公刘启和刘培强父子情感变化的交代颇有些突兀,前面由爱转恨的原因是通过补叙的方式完成的,但突然的穿插不免有打断情节节奏和情感连续性之嫌;后面的和解则姗姗来迟又过于仓促,令人感觉颇不尽意。还有某些人物的语言和细节的表现,有时也稍显刻意,不免让人有些瞬间“出戏”。但瑕不掩瑜,而且这些小问题都不是“不治之症”,如果经由剧本创作的进一步优化,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加以解决,长此以往,自然能够推升中国电影叙事艺术的整体水平。
五、类型:积极探索创新
在电影中讨论“类型”问题,其实涉及“类型电影”和“电影类型”两种差异性的概念。所谓“类型电影”,“是电影工业化及其商品化的产物,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娱乐消遣需要而创作出来的具有某种可复制性,甚至批量化生产的电影系列产品”。好莱坞的类型电影创作最为成熟,喜剧片、西部片、犯罪片、歌舞片、灾难片、科幻片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西方类型片形态。而“电影类型”则是依据题材或艺术表现等标准,对电影进行归纳概括而得出的不同种类,如农村题材电影、战争片、爱情片、武侠片、谍战片、喜剧片、恐怖片等。严格地说,中国电影中并没有西方概念意义上的“类型电影”,所谓不同类型的影片,多是从“电影类型”的归纳意义上而言的。虽然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一些中国电影工作者也开始思考和讨论中国“类型电影”创作的问题,但目前在理论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在实际创作中也没有出现具有完全类型片要素的某一类系列产品。中国电影创作依然坚持个性化的艺术追求,没有创作者愿意只遵循模式化进行创作,也没有创作者仅进行一种类型的创作,所以中国所谓的某种“类型片”都是归类而成形的。一部剧作总会有类可归,但在这种类型中的不同作品,一般也是要求个性显现的。
现代艺术生产要使自己的产品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创新。虽然“类型电影”未必是中国电影创作的唯一出路,但鉴于其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电影创作者也越来越重视“电影类型”的积极创新。因此,作为编剧,在剧本创作时也要进行“类型”的辩证思考,以明确自己的创作追求及方向。目前,中国电影类型创新实际包含着两种可能的方式:一种是新类型的创造;另一种是多类型的融合。新类型的创造,就是要打破现有电影创作常见的类型局限,“无中生有”,不断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和观众需要的新的“电影类型”种类。“青春片”就是近年来中国电影艺术的一个新创造,它适应了时代普遍流行的怀旧情绪与思潮,含情脉脉地书写着那个我们曾经的青涩年代的美好回忆,引起了一大批80后、90后观众的深切共鸣,如《致青春》《匆匆那年》《同桌的你》《青春派》《初恋未满》《左耳》等。同时,新类型的创造还应该包括某一类型创作中“次类型”或新风格的创造。如喜剧片就是一个较大的电影类型种类,其中周氏的无厘头喜剧、冯氏的贺岁喜剧等,都已形成较独立的风格,并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可以称为“次类型”或一种固定风格。那么,突破这些现有类型和风格的创作,自然也是创新的表现。而多类型的融合,则是要打破原有的单一类型的创作限制,将两种或多种类型的特色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能给人以新感受的新类型。新世纪以来的不少电影创作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的尝试,如《紧急迫降》将灾难片和主旋律电影结合;《人在囧途》将公路片和喜剧片融合;《白日焰火》将犯罪和爱情合并;《唐人街探案》将警匪和悬疑推理交织等。其实,创新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的,必须充分发挥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努力为“已有”添加些“未有”,给人以新的发现、新的感受。
艺术的探索永无止境,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已经到来,“最好的时代”需要脚踏实地的创作去创造,从电影剧本的创作开始,编剧要为中国电影“走出去”迈出坚实的第一步,美好的未来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