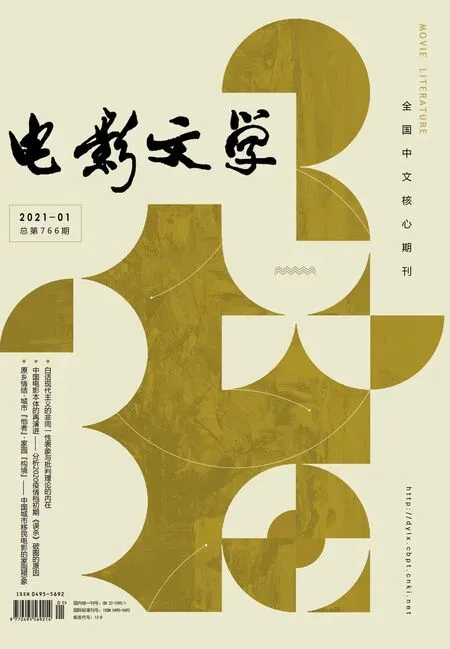电影《春潮》中的存在主义哲学探析
王文中 王怡真
(陕西科技大学 设计与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春潮》是由杨荔钠导演在2020年于爱奇艺平台上映的作品。故事通过对三个不同年龄段女性的不同的生活境遇的记录完成叙述,片中的三个女性其实就是现代社会中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的代表,导演通过对她们的描写,为观众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现实社会中人物生存现状的图景。在影片中,导演以一种真实客观的视角对事件进行再现,以一种诗意的、纯粹的方式,将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冲突、悲欢离合娓娓道来,去探究和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们生存的现状和生命存在的意义。
影片中,三个主角人生中所发生的一切,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她们的生活显得是那么烦闷和平淡,但正是在这种破碎的日常化的生活表象中,才潜藏着能够表现出人性本真、震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所触及的无疑是人们对于荒诞现状、人类生存状态以及生命意义的思考与探寻。20世纪兴起的存在主义哲学为人们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自诞生起,存在主义哲学就致力于对人的存在、生存、反抗等问题进行深入解读。在这个日益浮躁和空虚的时代,世界显得越发荒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日益失去了安全感,陷入了一种迷惘、空虚的无望状态,生命的存在本身有没有意义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影片《春潮》正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阐释了一场祖孙三代的生存悲剧。
一、“荒诞”的人与世界
(一)世界与人的对立
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世界是荒诞的”。加缪认为“荒诞”是由于人单一的、合理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期望与这个世界不按这种期望进行的矛盾所产生的。这种世界与人的对立正是荒诞感的源泉,也是造成人们生存悲剧的重要原因。
电影《春潮》中三个女性生存的悲剧无疑与当时荒诞的社会状态有着紧密的联系。纪明岚年轻时与知青下乡的郭建波父亲相遇,为了获得城市户口与更好的晋升通道,她抛弃了真正的爱情,选择和郭建波的父亲在一起。但好景不长,不久后,社会环境的变化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为了保全自己和女儿,纪明岚通过一封检举信和领导面前的哭诉同丈夫划清了界限,但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举动虽然保全了自己和女儿,却也换来了家庭的破碎与女儿的怨恨。在她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什么阳光大道和坦途,只有接踵而至的痛苦与磨难。纪明岚度过的是悲剧性的一生,她的生存状态揭示出了当时社会对人的异化以及人在异己世界中的孤独。不论世人经历怎样的苦难,世界仍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漠然理性的态度永恒存在。
(二)“自在”与“自为”的对立
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将人的存在划分为两种:一个是“自为的存在”,即脱离了本质的人的主观存在;另一个是“自在的存在”,即人自由进行选择的权利。从逻辑视域出发,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如果没有“自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便无法成立。在电影《春潮》中,世界的荒诞性还体现在“自在的存在”对于“自为的存在”的干扰和阻碍。由于世界的荒诞性,郭建波的人生充满了意外和偶然。年少时,幸福美满的家庭被母亲生生拆散,敬爱的父亲也被母亲诬陷不知所终;成年后,被人强奸怀上郭婉婷,本以为走上正轨的人生,又回到了起点;接受了女儿的存在,回归家庭后,又承受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嘲讽和排斥。在她的一生中,“自为的存在”总是被“自在的存在”所阻碍,世界总是在她充满希望之时予以重击,而她所求的平淡生活也永远如镜花水月般一碰就碎。
人们在荒诞的世界中被剥夺了希望和自由,每个人都成为自身世界的局外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是仅存的自由。反抗,正是加缪所认为的“荒诞人”对待荒诞世界的正确态度,也印证了他“不求永生,竭尽人事”的生存哲理。
二、我反抗,故我存在的“荒诞人”
加缪在他的哲学著作中用西西弗来表现“荒诞人”的形象。在希腊神话中,诸神命令欺骗了他们的西西弗把一块总会滚回原地的巨石推至山顶,希望通过这种无休止的重复劳动施与西西弗最严厉的惩罚。但西西弗没有被压垮,他在无尽的绝望中一次又一次地推着石头,永远不向命运屈服。西西弗是悲壮的,但也是幸福的,因为他的命运属于他自己,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荒诞人”。影片中的郭建波同样如此,她明知无休止的反抗给自己带来的并不是幸福和坦途,而是折磨与痛苦,她认识到“自为的存在”在“自在的存在”下反抗的无能为力,但仍乐此不疲,这种反抗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一种方式,是支撑她存在的基石。尽管她的人生是痛苦的,但她的人生是属于自己的,所以我们应当想到,郭建波同西西弗一样是幸福的。
郭建波的反抗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正是支撑她存在的意义。在影片中,郭建波与主编的一段谈话令人印象深刻,主编让她面对现实,放弃对拆迁、怒杀、暴力等新闻事件的报道。在扭曲的社会现实压迫下,在大多数同事对社会的痼疾视而不见的时候,她勇敢地站了出来,与荒诞的世界进行对抗,这一刻她的形象与主编等向荒诞的社会现实屈膝投降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荒诞人”的形象在这一刻被拔得无比崇高。尽管她在孤军奋战,但是这种为了摆脱压迫要求自由的欲望,不仅维护了她个人的尊严,也维护了整个人类的尊严。她“荒诞人”的形象,在与母亲的对抗中更是体现得极为鲜明。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中,纪明岚召集老年合唱团来家里排练,乱糟糟的人群使得逼仄的空间更为拥挤,她故意放水,将人赶走;母亲与她的相亲对象聊天,她千方百计地破坏。就像她在片尾长达八分钟的独白所说的,“你想我找个好男人,有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着我现在的样子”。这是她对纪明岚伤害她父亲的报复,是对纪明岚长期控制的报复,是对纪明岚剥夺她母亲权利的报复。但是,其实这只是她“自为的存在”向“自在的存在”所压制的一种扭曲的反抗。
在《春潮》中,人物为了生存的自由所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成为贯穿全片的线索。导演通过对郭建波的描写,向观众展示了“荒诞人”反抗的本质和意义。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世界在片中所呈现的状态一直都是对立的,而这种对立正是“荒诞人”反抗精神的凸显。
三、反抗:生命存在的真谛
萨特在《存在于虚无》一书中写道:“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生活是无意义的。”加缪的观点和萨特殊途同归,他认为我们的生活中的虚无是由未来的生活总和造成,而未来的生活又是受“自在的存在”掌控的,是不属于我们的。既然如此,那么生命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是存在主义向世人提出的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春潮》是一部探究生命存在的本质的电影,郭建波的一生毫无疑问是痛苦的,但并不是失败的,她通过自己的反抗,在母亲的压制和掌控中、在充满偶然性和荒诞性的世界中、在不可捉摸的命运中,创造了可能。
世界是荒诞的,人的生活是虚无的,但相信生命的意义也是一种价值选择,这种选择是“自为的存在”的充分体现,也印证了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如果人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存在便失去了意义,成为抽象的存在。因此“自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是生命的本质,其意义实现于意识的反抗与世界的永恒对立之间,在存在的自由与有限的命运之间。
在电影《春潮》中,三代女性的人生印证了存在主义的这一原则。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她们都处在爱情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纠葛之中,为了更好地活着不断做出选择。对于纪明岚来说,牺牲爱情与郭建波的父亲在一起,换取城市户口;检举丈夫与其划清界限,以家庭的破碎换取自身的保全,这些都是她的选择。郭建波与社会现实抗争以换取情绪的宣泄,与母亲互相折磨以满足自己的报复欲望。郭婉婷生活在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为了更好地生活,她不得不摒弃了童年的天真无邪,在母亲和外婆之间左右调停,像个大人一般思考问题。
在影片的末尾,导演设置了一个长达十分钟的超现实主义手法的纪实镜头。水从砖缝渗出,流经医院,流经礼堂,来到学校,最后聚成淙淙溪流,汇入河流。郭婉婷带着崔英子跟着水流自由地奔跑,在河水中欢快地嬉戏。这段旅程是一段净化心灵的溯源之旅,在这里,郭婉婷所代表的不再仅仅是她自己,也是纪明岚和郭建波的一种精神寄托。通过这段旅程,她们的人生得以回溯,所有的苦难和罪恶都被洗涤。郭婉婷笑着对镜头泼水的样子,象征着一种解放,也是一种新生的宣告。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指出,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存在于人自身之中,与人的存在融为了一体。不同的生长环境导致每一个独立存在的人在面对问题时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正是这种“自为的存在”使人获得了自由,进而完成自我的塑造,为“自在的存在”赋予了真正的价值。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残酷、理性的世界进行抗争,尽管纪明岚、郭建波和郭婉婷的命运是荒谬的、结局是悲惨的,但她们就像西西弗一样一次又一次站起来,以不断的反抗证明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最终,在导演营造的那个超现实主义的空间中,“自为的存在”终于短暂地战胜了“自在的存在”,她们生命的意义也借此得以体现。
世界的“荒诞”,最终会导致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影片《春潮》为观众展示了一个荒诞的世界,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以及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贯穿全片的始终。导演通过对电影元素的运用,将抽象的存在主义哲学具象化,将“荒诞人”“自为的存在”等哲学概念物化为片中的角色,让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存在主义哲学的理念。她们的生活平凡而普通,经历的磨难也是很多人隐藏在内心的伤痛;一次次的重击,使她们坠入深渊,但是她们仍选择奋发反抗。在这一过程中,生命存在的意义不再取决于上帝,而取决于她们自己,这就是生命本真的力量,通过她们命运的荒诞和对于自身存在的思考,人们必将获得更多直面苦难的勇气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