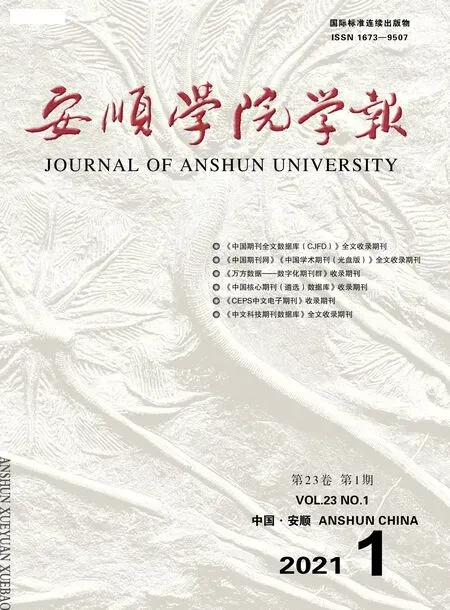安顺大屯契约中的中人社会身份初探
杜成材 吕燕平
(1.安顺学院旅游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2.贵州省屯堡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安顺561000)
贵州省屯堡文化研究中心吕燕平教授近年在安顺西郊大屯村搜集到的契约文书679件,比先前孙兆霞教授在安顺东部屯堡吉昌屯所发现的多二百余份,是安顺一带屯堡村落中集中性发现的契约中数量最大的一宗。大屯村契约最早的一张立于乾隆三年(1738年),此后多数立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期间,民国时期份数也不少,契约时间跨度二百余年。除田地交易契约之外,还有房屋及地基、山林买卖契约,以及分关契约等类型。契约反映了晚清以来安顺西门屯堡民间经济交往、社会活动的情况。从契约形制、内容以及交易特点看,土地、房屋、庙田买卖契约,当契,分家产契约等,既承袭了古代契约的传统格式,又呈现出近代以来安顺屯堡自身习俗和经济生活的现实性,鲜活再现了晚清以来滇黔驿道安顺沿线屯堡社会历史的多个面向。
大屯村契约中,“中人”的称谓有“凭中人”“凭议人”“凭中”“中证”“原中”“原中人”等几种。大屯契约所见的中人,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威望和声誉,能为契约双方当事人所接受。本文以《大屯契约文书汇编》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辅以吉昌契约文书。选取了丁、李、赵、向、胡、吴等姓氏的买卖契约作为分析、比较的主要对象,从中人的家庭地位、中人与缔约双方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中人群体等角度考察中人的实际身份,尝试展现晚清民国时期屯堡村落的社会关系与秩序。
一、中人身份概述
契约是双方当事人依据国家成文法和地方习惯法,共同协商订立的买卖、借贷、抵押等各种关系,需要共同遵守的条款、文书。乜小红教授指出,契约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多有存在,中国在进入私有制社会后,自商周以来就是契约关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体现形式。[1]
在清代契约中,“中人”称呼主要有凭、凭中、中见、中证人等几种,是契约订立过程中除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参与者。高大敏从历时性角度对中保人的起源进行了考证,认为汉代已经普遍出现中保人参与订立契约的情况,唐代有专门的中保人职业群体,宋元以后,中保人制度随着契约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中人”“中保人”名称基本固定下来。[2]李祝环认为西周以来,中人便作为第三方参与契约签订,只是不同时期称谓有所不同而已。 学界对“中人”的研究角度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从法律史角度探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协调问题[3],二是中人的“面子”与民间社会角色问题[4],三是中人的中介作用[5]。作为土地交易契约生效的必备要件,中人身份体现了缔约双方当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处的人际环境与社会地位。借助中人,缔约双方当事人达成局部社会的平衡关系。中人的社会身份能够使双方当事人接受,同时还应具有相对的资信能力。常见中人为保、甲、村正副,或为宗族尊长、族邻、地方士绅等,这些人多具有乡村公共生活代表的身份,在其生活的区域内具有相对权威性。[6]中人作为传统民事契约成立要件之一,在缔约双方中起到中介、见证作用,以保障契约的成功订立。值得一提的是,郭睿君研究发现,在订立契约时双方选择的“中人”之身份,不拘于地位、经济、威望,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实际需要,在其特定的乡土社会网络中,亲疏、远近、尊卑自由组合的结果,自身品质良好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中人。[4]因此“面子”的大小并不是选择“中人”的绝对标准,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亲族担任中人,妇女也可以作中。前者是为了避免亲邻权产生纠纷,后者则是因为当时妇女寡居现象多且专主家政而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
从大屯村契约的形制和内容看,屯堡契约继承了唐代以来基本定型的固定格式:文首交代契约交易的类型及立契人,随后写明立契原因,接着交代土地田产来源,再写田产四至,然后是买受人,接着是双方责任,最后是中人、出卖人、代字人等等的签署、画押以及立契时间。[7]民间熟人社会的契约精神跃然于纸上。有的买卖契约上有官府钤印,一方面表示官府对买卖双方交易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作为缴过契税的凭据,受到法律保护。与此相对,未加盖官印的则为白契,多常见。白契在执行中受到民间乡土熟人社会诚信体系的制约,使人们自觉地遵守信用规则、履行契约内容。虽然没有钤印,但也具有红契的形制与内容,起着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契约在中人的见证下,规定有交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如规定土地房产按约定交易后,若有房族子侄及异姓人等异言争论,由卖主承担,不与买主相干。
二、大屯契约中人身份类型
大屯村契约中人的身份,既体现了中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地位,也体现了中人与契约双方当事人的社会关系。叶显恩先生研究徽州文书后认为,土地买卖必须有中人,中人大多数都是卖主的族人、姻亲、近邻或地保等等。[8]这为我们从事中人身份的探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吴欣基于徽州契约文书的分析后认为,中人身份除了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关系之外,还包括了官民关系、主仆关系。针对中人身份的日趋复杂化,吴欣提出了“中人群体”概念。认为中人群体并非具有共同特征的固定人群,而是一个因与当事人有着某种关系而形成的临时性的群体。[9]从这一分析角度出发,大屯契约文书中的中人身份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地方基层首领和乡绅
岸本美绪指出:“人们在选择乡绅作为保护者时,其标准并不在乡绅与土地所有或国家权力间的关联性,而是乡绅在地方社会中实际的保护能力。”[10]基层社会中,乡绅充当着首领的角色,对人们起着一定的保护作用。《民国二十七年吴少臣免兵役呈文》显示,吴少臣“幼失怙恃,既无伯叔、终鲜兄弟,祖业无遗田园……生活饥馑,移依外家讨田躬耕度日,终岁劳动尚难养育妻子。……惟民孤子,又系户长,若应征前往不独宗祧无承,妻弱□□□□家,将成饿殍。情不得已只得据情叩恳。钧长鉴核,准予免役”[11]439。呈文末尾的证明人有“主任齐忠甫,保长丁作周”。在当时联保制下,保长是国家行政官僚体系在基层的末梢神经,代表着国家行使基层社会治理职能。这份呈文中先是交代服兵役是国民“应尽天职”,当时正值“抗敌御辱”的非常时期,理应入伍当兵,但考虑到参军可能“宗祧无承”、妻子将成饿殍的严重后果,希望能够免除兵役。文中除吴少臣之外,尚有县长刘姓、主任齐姓、保长丁姓等三人。从呈文看,受宗祧观念影响,保长的权威需要宗族的支持。
(二)宗族亲长及族人
依血缘关系亲疏,同族的族长、房长具有相对较高的权威,一般族众与立契人的亲属关系较近,再就是与立契人同姓的族人,关系较远,契约中没有标示出伯、叔、弟、兄、侄等称谓。具体而言,大屯契约的中人群体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中人纯粹由族亲构成。如《道光元年丁国盛立分关文契》[11]27,丁国盛将陆地分与丁朝纲名下,中人由伯国茂、国秀,叔国雄、国兰共计4人构成。又如《同治十四年丁朝纪分关文契》[11]33,丁朝纪和母亲邵氏将田产、地业、房屋、园子、坐基等家产分授次子元星,中人共有8人。依次为亲长曾姓、李姓各1人,妹弟徐姓1人,堂兄1人,堂叔1人,堂弟3人。二是中人有兄长、有外姓。如《乾隆三十五年陈文达、陈文光立卖科田文契》[11]630,陈姓将坡田出卖与丁处名下为业,“凭兄”陈文绅、陈文灿名字之后,又列出异姓中人7名。三是既有亲长、弟侄,又有外姓。如《嘉庆二十五年胡绅、胡上圣、胡上顺卖房屋地基文契》[11]645计有12名中人,其中堂叔1人,堂兄3人,堂侄2人,胞弟2人,另有林、邵、吴、丁姓各1人。四是由卖方同族弟辈和买受人同姓的人作中。如《同治四年丁维星、丁双星、丁祥星顶粮田文契》[11]661,丁氏三兄弟顶粮田与徐天成、徐天福兄弟二人名下管业,中人有出顶方堂弟丁小贵、丁全妹2人以及同姓的丁玉星,顶受人同姓的徐应林,另有第三姓王玉春,共计5人。五是中人由卖方同姓人和买方同姓人共同构成。如《光绪□四年丁玉星卖陆地文契》[11]677,丁玉星同子汝贤、连生将祖父遗留分授本己名下陆地出卖与徐国清名下管业,中人有徐国泰以及丁治星、丁灿星共3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五种情形均非个例。周进等学者分析了同姓中人普遍参与土地绝卖契约的原因后认为,与出卖人同姓的中人大量参与,是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一项重要的契约规则。同姓中人既是出卖人的土地共同所有者,也是出卖人的担保人,这是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问题在土地绝卖契约中的反映。[12]传统农业社会中,个人从属于某个家庭、家族,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并不能脱离其家族,在缔约时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亲族的影响。作为家族共有的土地,在家族中某一个或某几个成员将要改变土地权属关系时,事先要征得家族其他部分成员的意思表示。这种表示最为直接的形式,就是与出卖人一起见证出卖的全过程,并在契约上签字画押,体现出宗族对契约制度的影响。
(三)妇女
大屯村契约中,妇女作为中人并不鲜见。第一种情形是其他人立契,妇女作为家中长辈参与作中,如《民国三十四年丁日生、丁日用立卖明水田文契》[11]101,丁姓两弟兄将父置之业水田二块出卖与亲族丁学礼名下为业,原中人丁少益,凭证人丁少荣、母丁邓氏。又如《民国二十九年丁学起卖水田文契》[11]97,丁学起将水田连同田边大小树木一起卖给丁日智名下,原中人丁汝亮,凭中人共有3名,依次是:丁亮华、吴思远、丁刘氏。第二种情形是其他人立契,妇女作为唯一中人,如《光绪二十六年丁焕星当陆地文契》[11]371,丁焕星将本名下陆地出当与丁河星名下管理,凭中只有丁李氏1人。第三种情形是妇女立契,与之有亲缘关系的家族内部其他妇女与亲族一起参与作中,如《光绪十五年赵吴氏顶田文契》[11]137,赵吴氏将祖父、丈夫移遗留本名下田出顶与丁富星名下管业。中人有赵应为、赵应贵、赵应富、赵应发、赵应试、胡赵氏、齐赵氏、胡永升。第四种情形是妇女立契,本人和其他人一起作中,如《民国二年向刘氏、仝(同)子清妹、老三立卖明科田文契》[11]85,向刘氏将祖父遗业分授本己名下之田出卖与丁汝富名下管业耕安,凭中人张柄奎、周子明、陈有洋、张柄仙、白云清、向刘氏。后两种情形的契约中,立契者寡妇居多。
(四)立契者本人
立契者本人请人代书契约,自己承担中人身份。如《民国二十一年李皮氏、李毓仁、李东生卖园子文契》[11]513,李皮氏与侄子、侄孙一起,将祖父遗留分授本己名下园子出卖与堂叔娘李叶氏名下管业耕种,原中人丁汝庸、凭中人李皮氏。
上述第三类中人身份,在大屯契约中存在比较普遍。第四类中人身份,比较罕见。这两类中人涉及的契约显示出当与族外人订立契约时,为了保证契约的效力,会倾向于寻找同族的人乃至较多的人担任中人,并使这些临时被召集起来的人为自己作证。清代法律中对妇女在家庭财产分割时享受的份额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这就为妇女参与财产处分提供了法理基础。妇女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在特殊情况下,基于家族中的身份与地位、个人威信及家族中的人际关系,会从幕后走上前台,承担中人角色。
三、中人参与交易呈现的特征
契约所见,大屯的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交易大多是在村级市场内进行。在以村落为中心相对狭小的地域内进行,主要是同村人尤其是宗亲房族之间的交易,其次是在城地主与在乡地主或佃仆之间的交易。宗亲、房族、地邻,基本在本村辖地内,与族外异姓者交易,大多也是本村范围内。因此,大屯土地交易契约中,体现出较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在“亲邻先买权”规则的实行方面,相当一部分在宗族内部进行交易。如契约直接注明“出卖与族叔(叔祖、叔母、叔娘、婶母、堂叔、胞叔、胞兄、胞弟、嫡堂兄)某某名下管业”,还有一部分是同姓族人,只有极少数是异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契约均未有“先问亲邻”的文字说明,这是与安顺东门屯堡吉昌屯契约区别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大屯契约中没有“先问亲邻”的文字记载,但是从契约中买方大多为亲邻的事实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代表“亲邻先买权”在大屯村一带的消失。赵晓力认为,契约内的略写或不写,恰恰表明这种习惯己经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意识中“固化”下来,成为“不言自明”的事情。[13]由此可以得出,“先问亲邻”这一规则在安顺西门大屯一带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相比之下,安顺东门外吉昌屯一带“先问亲邻”的文字说明,则表明亲邻无力或无心买受。由此可见当时安顺东门和西门的社会关系存在一定差异。
二是交易的土地、房产,绝大多数来源于祖遗产业,如“祖父(伯父、丈夫)遗留分授本己名下”,少数为“所置之业”“本己所置业”;存在两人以上的多位卖主共同出卖祖产的行为。大屯交易的土地、房产超过60%来源于祖遗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屯的土地归家族所有的情形比较普遍,个人对土地只拥有管业权。如契约所见,某某氏母子几人,某某氏同某某氏(妯娌),某某氏同子、同孙,某人同子、同弟兄等数人共同出卖土地、房屋、借银,将所有这些人的名字都写在契约第一列文字当中,从而消除宗亲房族人等不承认土地、房产买卖的情况。
三是同姓、亲房承担中人身份的情形比较多。大屯村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房产交易契约均有同姓中人的参与,主要参与居间询问买主、说合、见证交易过程以及签字画押等事宜。画押的中人人数多在4人及其以上,若算上单列的“原中”和“凭中”,一般有5~6人。6~8人极为普遍,甚至有多达14人。 例如《乾隆六十年王秉信、王秉义、王文林、王文盛卖房基墙苑文契》[11]579,王秉信、王秉义同子侄将瓦房、地基墙苑连同粪塘出卖与堂弟王秉孝,中人有万姓、吴姓、李姓各1人,周姓、丁姓各2人、王姓堂叔2人、胞兄1人、堂弟3人,堂侄1人,共计14位中人画押。又如《光绪二十二年丁河星出抱约文契》[11]369,丁河星将长女招婿吴发妹以承宗祀,中证人有丁姓房族7人,李姓2人,齐姓7人,卢姓1人,共计17人。再如《同治□□僧圆慧卖庙田文契》[11]467参与画押的中人共计20人,其中与买主李植昌、李培昌同姓的中人有3人,异姓中人有徐姓3人、丁姓6人、周姓2人、吴姓2人、胡姓、王姓、杨姓、赵姓各1人。
相比之下,同时期安顺东门屯堡吉昌屯的土地买卖契约中,中人数量一般只有1~3位,亲房或同姓参与作中的不多。宗亲房族人等,作为宗族势力的典型,只有在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土地、房产的交易才能获得公认进而产生效力。据吕燕平调查得出的结论,大屯村有丁、周、李、左、徐、赵、王、胡、万、卢等10大老姓,民间传说此前五姓为“征南”而来,后五姓为“填南”而来,左姓已无,遗留有“左家巷”地名。在大屯村契约持有人中,也没有发现左姓持有者,其余九大老姓后人均持有契约。[11]序言9-14
大屯村土地契约呈现出零散的交易特征,与其驿道上产粮区的区位特性密切相关。大屯地处安顺城西坝区,村落北靠大山,东、南、西三面地势较低,东、西两面有溪流自北向南流,在村落东、西门楼外各自汇集成面积约1亩见方的水塘,为人们做饭、洗衣以及水稻种植提供持续的水源。大屯一带土质肥沃、地势起伏、水源充足。地理与气候因素叠加,促使大屯成为安顺著名的产粮区之一。喀斯特峰林谷地地貌导致土地呈现出零散分布的形态,导致土地交易呈现零散态势,加之百姓财力有限,不大可能形成集中连片的土地交易。咸同兵燹,社会不靖,加之各民族杂处以及自然灾害,使得大屯一带的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百姓贫苦。“为因乏用”,人们只能出卖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房屋乃至牛圈、粪坑。喀斯特地貌下以粮食生产为主业的区域,使得土地只能在村级土地市场狭小的空间内进行小规模分散交易。经济活跃性受限,土地交易不够发达,产粮区很少有人能冲破“农本商末”传统的桎梏。血缘和地缘结合形成的乡族共同体,以及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血缘宗法关系,在大屯村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中人群体,影响着土地交易的全过程。
结 语
依据大屯村发现的679份契约文书,分析中人的身份、中人参与下的土地交易诸方面内容。从临时性契约关系所形成的中人群体,窥探中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地位、与当事人的关系,进而探讨屯堡人对契约及契约所代表的社会秩序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晚清以来大屯土地交易的样态,人们由于家庭缺少用度、易业置业等因素,将祖遗产业,如田地,房屋地基、院墙等出卖。中人参与的土地交易,反映了晚清以来安顺西门屯堡尤其是大屯的经济社会状况。土地交易活跃程度不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宗法关系影响。对晚清以来大屯土地、房产等交易个案中出现的中人身份的探讨,有助于较为全面地认识晚清以来安顺屯堡区域的土地制度。由于方志、家谱等地方资料的发掘不够和土地交易个案的丰富度欠缺,对屯堡土地制度形成系统、完整的掌握,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马鞍山市博物馆馆藏契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