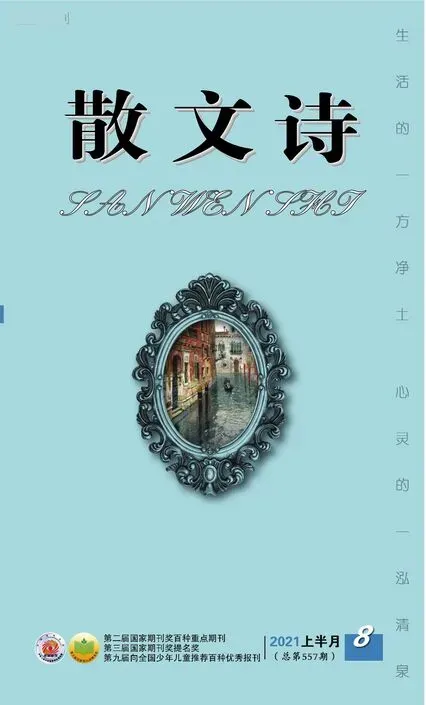车巴河纪事
王小忠
热 爱
来车巴河边已经很久了——他想在山林里找到龙胆花,在坡地边捡到地耳,也希望在河边碰上一块含玉的石头。
事实上,他更期盼从深沟里刮来的风将他带到那片草原上。那样,他就可以放声歌唱,还可以和他们喝酒、打牌、聊天,诉说这段时日里的欢乐和艰辛。然而,大家都忙着耕种,谁都知道,埋在地里的种子已腐朽,但大家依然等待立春,等待惊蛰,等待雨水……
多么热爱那一切,可载运时间的那辆大车已经走了很远。杨树叶上栖息的飞蛾们只留下空茧壳,它们在余晖下独自仰望空荡荡的蓝天。
你们不曾知道的秘密——
他在车巴河岸边就那么等待着,失落着,希望着。
你们不曾理解的苦衷——
他在车巴河岸边,看着野猪撕扯青稞架,看雪花一片片从山头飘来。
他知道,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生好那盆火。不再有过多的奢望,他只想听着风的呼啸,静静度过这个寒冬。
他多么热爱眼前的一切,可夏天已经过半。他想,如约而来的秋风定然将他重生。
刀 告
迷醉的歌谣来自远方,来自金色的草原和吉祥的花滩。
太阳跳出云海,朴素的车舆带着清脆的响铃,寂静的早晨神圣而安详。
天地一片空寂,空寂里万物生长。
千年前,盗匪和马帮留下刺刀与灰烬。
千年后,他牵着小红马,来到名叫刀告的村庄。
门前是白塔与经幡,桑烟袅袅,经幡猎猎,从不辜负尘世的慈悲。
屋后是数不清的蚁虫,它们忙碌搬运,从不辜负时光馈赠的富裕。
万物沉静,茫茫大雪下,唯有四周的柏木安静地生长,它们在雪的滋润下,静静守护刀告的安详。
落 日
……落日下,高耸的雪峰正在收拢大地之广阔。
空荡。辽远。苍茫。寂然。
黯然无语的是,静静的村庄……
暮色诞生妄想。
桑烟诞生虔诚。
寂静的刀告村,在雪峰与草地之间,是甘南唇边诞生的黑色珍珠。
寒 冷
风停了,雪更大了。
扎紧皮袄,搓着双手,小红马打着秃噜。
都不说话,只沿车巴河岸行走。一直要走到光盖山顶,才能看见那片草原上。
河水迟缓,浮冰撞着柔软的岸。这是三月的甘南,虾米从岸边的浅冰中潜入河底。
依然沿河岸行走——雪停了,风更大了,脚步越来越慢。
这是甘南的三月,他要守住河流,守住岸边的嫩绿,也要坚持走进草原腹地。
要继续沿河岸行走,再不能沉默下去了。不能歌唱草原,骑手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四 月
已经是四月了,车巴河还是没有完全解冻,但它宽广、干净,像甘南的天空。
他依然摆出在春天的样子,尽可能保持光鲜容颜和有力步伐,画好心中的原野,昂首走过石矿村。
早就忘记了悲痛,也不再因为那些花朵的枯萎而抱憾。可他不经意间又看见了远方的群山,墨色的森林和刺目的白雪,再次让他跌进寒冬的阴冷和恐慌之中。
车巴河两岸依旧没有春的气息。
四月,车巴河岸只有风在狂虐。
养护在大棚之下的树苗,静静注视着地面上的阴影,它们也为无法点缀季节而暗自惭愧。
大路上人群攒动,枯枝在冷风中摇晃,天空之蓝让四月的甘南空荡而荒凉。
这蓝,这净,这空荡与荒凉之下,他无力爆发内心蓄满的恨意,也无力爆发蓄意很久的笑声。
河 岸
走出小二楼,穿过那条巷子,就到车巴河岸边了。
他总是喜欢在岸边走,因为岸边有许多野花。岸边的花,都可以叫做格桑花,都像他一样,渴望生活的美满与幸福。
他在柏木林里见到过铁线莲,在小二楼墙角处也见到了。无法数清,它们挨挨挤挤,相互缠绕,不说话,神情低落,有些忧伤。
原来,幸福的花儿也是有心事的。
车巴河岸七月的早晨还是有点微凉。金色阳光下,马匹进山了,赶马的老人并不孤独。他每天重复着从村口赶马出来,当落日跌入眼眶,他就和岸边的格桑花打成一片,让七月有了欢声笑语。
然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总是喜欢揣摩暮色背后的秘密,住在这里的他,也总是喜欢在事物的变幻里抒发悲欢。
如果我们怀揣明灯,何惧夜晚漆黑与漫长?
河岸边的那些花尽管低落、忧伤,但不哀怨,它们依然健康地生长着。
有了那些格桑花,河岸,就有了金色的光芒。
柳 絮
从高处下落——十分缓慢,优柔寡断。已经是初夏了,过时的柳絮才开始飘落。
它们拥有飞翔的翅膀,却无法久住空中。
它们落在车巴河中,挂在红桦的指尖上,突然间令人心生孤单。它们勾起他小时候的梦,那些黑白的梦,就是雪白的羊群找不见回家的门。
人们依旧沿着阳光转圈,劳动,休息。大地不寂寞,也不拒绝草色的青绿和荣枯。
他走出那个阴冷的小二楼,穿过巷道,踏上那座陈旧的木桥,从柏木林里回来,只带一朵柳絮。柳絮是旧时的记忆,发白而失重。他将它掌在手心,发觉少年时多次梦见的火狐和豹子已渐渐模糊。
他真的感觉到了茫然,他想,当他再次看见春天里的梅朵全部开放,它们也必将从一场盛大的约会赶向死亡。
秋 风
时光里守护河流的勇士,就是那些密密麻麻的青稞架。此时,秋风已来临,它们站在岸边,腹背受敌,但从不放弃。架上的青稞饱满,饱满的青稞在高原蓝天下打盹做梦,青稞的梦充满了明亮和温暖。
鸟雀们从遥远的山林结伴而来,围着青稞架歌唱。更远处的山林里,豹子在生育,水纹的新衣闪着油光。夜深人静的时候,狼也会走出山林,望着小二楼上的灯光,在青稞架边蹭了蹭干瘪的身子,叹息一声,又跌入黑暗之中。
秋风不停地吹刮,田野越来越空,道路越来越长,雪正在空中。空中的雪望见了河岸边的勇士,也望见深林里的搏斗与厮杀、亲昵与拥抱。
雪知道这个世界的秘密,因而它停在虚空里,静静观望。
雪始终没有落下来,而秋风的脚步很快。
太阳躲藏起来,不肯露面,整个村子都显得十分沉重。
等河水冻僵之后,一切就会安稳下来。那个时候,就可以守着火炉,让年轻的梦找到肥沃的土地。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仍必须在车巴河边寻找秋风之手没有收尽的颗粒。因为,他需要一个强健的体魄,才能安然度过寒冷的冬季。
大场里堆放着粮食,梿枷声惊醒了山林里酣睡的野猪,野猪的梦带着金色的希望。有了希望,就有了更多的精力。但在野猪未来之前,他必须赶到小二楼广播室里,他要将野猪的梦告诉给秋风,告诉给那些路过的、他爱的和爱他的所有人。
它 们
阳光爬满窗台,内心却生出一些空虚,生出失落的温床。
睡莲,吊兰,还有说不上名字的这些来自南方的花朵,它们持有着慵懒与妩媚。
而他同样拥有一片炽热的心灵,他把这些最美丽的植物带进生活,然后,盛放三千世界里的安详与和谐。
谁能给他适意和愉悦?
超然觉悟的时候,那定然是曼珠沙华在盛开。那些虚幻的花语引领着他,走向无穷的精神高地。人间的爱和仇恨,不可预知的死亡和黑暗,都在一起生长。
他视它们为亲人,这样,心怀里太多的污秽,就会在意念的花语里暗自消除。
然而,这是在车巴河,寒冷的风吹皱岁月的容颜,高挂的月照耀孤独的客房。他同样视它们为亲人。薄雪下,挺立的桦木燃着火焰,那是他唯一拥有的一座人间天堂。
洮 河
霜冻遍布大地,雪覆盖四野,狼会沿村子嚎叫,鹿和豹子会窜出山林,野猪也会在村子四周散步,河道两岸的松树黑油油连成片,阴森可怖。
岸边,柳树掉光了叶片,徒留光枝,光枝也似乎被冻僵,失去了随风摇摆的力量。
唯有洮河沿东北流淌,在高山与田地间,如委蛇而行的闪着光鳞的巨蟒。
他站在窗前。
一直到巨蟒被黑夜吞噬,一直到天边泛起明亮。
森林里的喧闹没有停歇。他站在窗口太久了,心生怠倦。这个时候,他最想听荨麻咬伤那个女子手背的故事,也想念那个行走在陌生街头的男孩。他想把这一切带到梦里,那样,就可以安静下来。然而,那样的安静过于短暂。
从风雪中归来的男人们偶尔也从窗前走过,他们在昏暗的路灯下稍作停留,满带愤怒与疲惫,之后消失在遥远的天边。
他站在窗前,看着月亮的光晕。要起风了——
他仍沉浸在自己的联想里:是啊,住在这里太久了,理想,
就会变成永不歇息的洮河之水。
秘 密
霜落下来,寒气就裹住了他的理想。守着温暖和明亮吧,还有什么比好好活着更令人留恋?
柜子里存放的薄荷早就没有了清香,而野艾诞生的火焰却燃烧着空空的心,还有什么比温暖更令人神往?
尘世给了他白雪的晶莹和恋爱的勇气,寒霜给了他坚冰的坚韧和追求的激情。
但必须适可而止,因为,这样的梦幻令他羞愧。
河岸边的那些树木站在黄昏下,还没等到舒展,就已被迫接纳寒冬的冰凌。
雪也落下来了。
雪落在他心上,盖住了他的想象,也盖住了去菜市场的路。这场雪让他理解了光阴的难言,也理解了岁月的疲惫。
而霜与雪还在继续——
还在继续的生命,从雪和霜的世界里依然萌生着新绿。那么,就让他把永恒的光明移到只属于他的这间客房里吧,因为他知道,也懂得,只有一颗纯粹的心,才能坚守住美好的理想。这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就在这风雪包裹的小二楼上。
但他知道,也不会告诉任何人,恐惧就是他的秘密。
红 桦
他在车巴河岸边愉快行走时,内心的惊悸和不安,就消失了。
站在车巴河岸边,站在风口处,突然间,回忆就充满了甜美。
草原斑驳,苍茫,空阔,但他无力返回到年少,也无力抽尽记忆的伤感。他知道,阳光的金箔会在时间里闪耀成巨大的宁静,即使无风的时候,它们也和他的想法一样,在光阴下渐行渐远。
风是他忠实的伴侣。
那些青山绿水下的村子和村子上方徘徊的月亮,它们看不见他在小二楼上摆放着的瓶瓶罐罐,也看不见那些瓶瓶罐罐里的静寂与幸福。一张低矮的桌子,就是他的全部,他多么珍惜阳光的温暖和月光的清凉呵。
艾草和淫羊藿晾晒在窗台上,散发着永久的清香。每次暮色莅临,他会习惯性地打开窗——依然是风,巨大,无形,带着时间的翅膀,慢慢将他空旷的人生填满。
他知道,不是每样东西都能落籽成光芒万丈。但他相信,车巴河激越的流水,不是他唯一的抒情,这唯一的河流,一定会让他在河岸边沉静如晚秋的红桦。
他就等待那一天,他要返回草原,带着清香的礼物,和那些探出地皮的青草融为一体,点亮理想与幸福的灯盏。
买 菜
从贡巴菜市场出来时,沙棘林旁边那条路上的行人少了许多。
黄瓜,西红柿,菠菜,这些让他身体不断充盈的物质,此时变得十分沉重。
拎着它们,平静地走过那条路,天色就暗下来了。
草原已萧条,枯叶无牵无挂,随风飘零。
山羊跳在台阶高处,伸长脖子,努力摘食挂在枯枝上的叶片。
高台之上的转经人,一言不发……
他提醒自己,要让心灵之灯照亮简单的幸福。
但他知道,接下来,他依然要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对昏黄的墙壁。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会想起遥远抑或根本不存在的米格尔街——尽管命运布满了绝望,而生活依然需要兴高采烈地进行。
孤 独
寒冷冬天的清晨,他裹紧衣衫,去了小二楼对面的那座大山之上。群山广大,苍茫的不仅仅是森林,还有平日粗糙而拘谨的森林之下的青稞地。
苍穹之上的群鸦跌入蓝色,白色,或紫色画板。
他就此迎着鸦群的身影,也缓缓跌落青稞地之苍茫与空旷。
乱而有力的茬草,是立于时间之上金色的生命。
他找到了热爱,也找到了能燃烧自己的颜色。
可他立于山巅,背着风,无限感慨——朝阳啊,请你将孤独写入永久之大地。
风 雪
从扎古录回来,天色已经很晚了。村委会小二楼上的那盏灯还亮着。那盏灯显得微弱而孤独。
卸下从远方驮来的碳,月亮就躲进了云层。
要去山后打水。看不见幽暗深邃的井水面,但他知道,水面上身影早已破碎。
天越来越晚,风越来越紧,围着炉火,他们说着草原、牛羊、风雪,也说起那些年爱过恨过的女人,说着说着,就忘记还要走很远的路。
外面又落雪了——
其实,冬天早就来了。他只是不愿提起冬天,不愿说起寒风。
后半夜,他送他们走出院子,风雪更大了。他不在乎。寒冷的夜晚里,斜飞的风雪会给他编织怎样一张绵密而不可出逃的网?
——春天一直在心底。尽管如此,他依然想着风雪中的牛羊,想着那些年的快乐和这些年的悲伤,冰冷的钢丝床整整叫了一夜。
冬 雪
雪一直没有停。
牛羊惊慌,衰草瑟缩,去扎古录的路铺满冰凌。
一直到沙冒大庄,才赶上那辆马车。
天地就是一辆马车,载着寒冷和疲惫。
一直到八什卡这个寂静的牧村,没人说话。
他们都在心底盘算着一个令人不安的词——黑夜。
不能让大地荒芜,也不能让家园空寂。
冬雪覆盖着四野,唯有满天飞雪让他们铭记,慈悲一直就在河岸边的红桦林里,它火亮的纹身正为我们搭建一座阳光的庙宇。
冬 至
车巴河被冻僵了——
他还是不敢过河,也做不出精准的判断,内心只有“如履薄冰”这个词。
不敢过河,就无法走进柏木林。那么多松柏站在天空下,没有声音,也没有表情。
他只看到它们的冷清和过于高大。
他只喜欢那个小院子。
那个被寒风吹透了的小院子此时也失去了表情,麻木而冷漠。但他不得不热爱,因为,春天有花朵,夏天有蜜蜂,秋天有落叶,冬天也有路灯和星光。
他不得不热爱,因为,路灯和星光照亮了他的命运,也照亮了他的身影。
小院子又灌满了风。那天是冬至,他从车巴河岸边回来,突然便想起夜的漫长。
是呀,漫长的一夜过后,寒冷会加重。
他惧怕的并不是寒冷,而是和那盏灯对视的焦虑,以及无法原谅自己荒废青春的可恨与无助。
早 春
雪下了一天一夜……
中午,太阳只露了一下脸,天又阴沉起来,下起了雪。
已是早春了。
从小二楼遥望远方,依然不见绿意。
一群乌鸦在窗外的青稞地里,它们争抢着他抛出去的一粒红枣、两粒枸杞。
对面的柏木林里,是一群饥饿的野猪,它们抢夺三朵刚探出头的野芍药。
悠闲的是一群山雀,它们停在电线上,用各种俊俏的姿势向春风挑战。
他坐在雪地上,独自冥想——
做只山雀就可以自由飞翔。不过他也担忧,班地亚随时会将猎枪瞄准长空。
一切都无法安稳下来,悸动的时节里,唯有车巴河不动声色,在大雪下静静流向扎古录。
他要离开了,让他留恋的不是河岸边的暴雪与寒风,而是即将来临的春天。
春天已经有了消息。
然而,风雪依旧从沟垴深处刮来,一路吼叫着,翻卷着残枝败叶。
唯有那一片沙棘林,在早春里头顶金黄。
暮 色
早上,他要去遥远的贡巴菜市场,在固定的那家铺子里买上烧饼,然后回来。
中午,他从小二楼旁边那条巷子穿过去,来到车巴河岸,坐在冰凉的石头上,试图找回自己。
下午,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他依然要去岸边,看着摇晃的河水,看着岸边渐渐枯败的各种草木。
暮色下,他就想挤进那些草木之中去。
深夜来临的时候,他还想拎着烧饼,踏过那座独木桥,慢慢走进柏木林,去看看那些无牵无挂独自飘落的枯叶——它们,如何涅槃?而又如何重生?
等到真正离开车巴河岸的时候了,这条河岸却变得陌生起来——冷清,孤寂。
可他依然不明白,世间那么多的仇恨和爱,为什么总是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