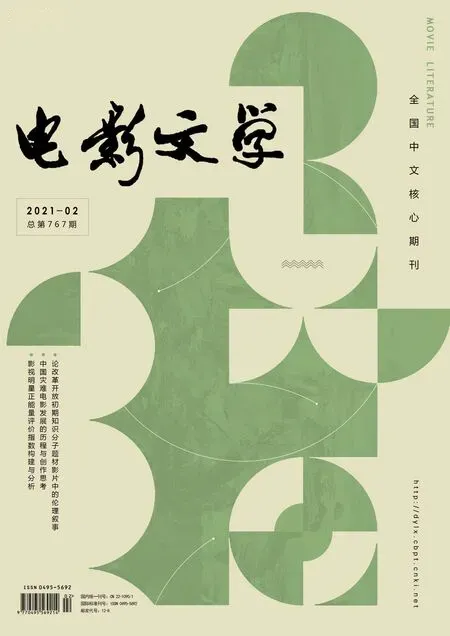《柔情史》的镜像和自我建构叙事解读
刘 晶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一、影片中镜像关系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即是指将“我”通过对自身或他人作镜像的考察,从而看到理想自我的形象;也是指通过镜像映照整个社会的问题,并试图做出改变。《柔情史》中的镜像关系如下:
(一)“照自己”:母女间共生的镜像关系
电影《狗十三》中李玩在狗身上找到了自己“被丢弃”的影子,构成了一种同化的镜像关系;电影《维诺妮卡的双重生命》中素不相识的波维与法维,通过心灵感性构成了自我认同镜像关系;电影《七月与安生》中七月和安生,她们在对方身上释放自己的压抑人格,构成了一种“误认”镜像关系;而电影《柔情史》将视角聚焦于一对普通的母女,正如万千家庭一样,女儿与母亲的关系并不友好,她们在争吵中加深了对彼此的理解,进而在生活中透露着彼此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同样构成了一种认同镜像关系。
影片《柔情史》主要运用相互呼应的文本形成提喻结构得以实现建构镜像关系,呈现母亲与晓雾如生命连续体般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影片中的母亲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将生活希望寄托于晓雾,晓雾虽已成年,却每天接受着母亲事无巨细的照顾,虽然她们互相指责,彼此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相互取暖的人,存在共生关系。另一方面,母亲的价值观在晓雾身上刻下了深深烙印,如:母亲每天防他人窃取晓雾书稿和自己诗歌的创意,防晓雾男友占她的便宜,防邻居摔倒赖她们,防没有血缘关系无法享受公公的遗产……晓雾从骨子里坚持日子要坏着过,认为优美旋律的音乐是不真实的,对自己好的男朋友像假的等,就是在延续母亲的价值观,构成另一种共生关系。此外,影片中呈现出一个对仗,母女间互相折磨,当彼此受不了后就分别去谈恋爱,试图通过恋爱化解生活苦闷、缓解生存问题,两人恋爱都失败了后又回家,继续折磨对方。
(二)“照社会”:家庭秘密与社会人际关系的镜像关系
影片看上去是公共话语闯入家庭生活的私人空间,呈现日常起居间的口角诟谇,但实则是想通过揭露蕴含在家庭中的秘密,映射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揭示父系家庭模式中女性生活的不独立。影片中未在场的丈夫、残疾恋人、师兄、离过两次婚的张宪、装疯卖傻的爷爷、闲云野鹤的道长、大腹便便的邻居等老弱残死的男性,形成社会权利圈,让处于弱势的女性依附于他们,让女性为了能获得蝇头小利取悦于他们,最终沦落为将能让自己过上舒服的生活作为择偶标准,似乎晓雾是最有骨气、最独立,将张宪玩弄于股掌之中,又“主动甩了”张宪,实则是强势下的脆弱自卑。这不是影视作品的夸张性处理,而是对现代社会两性生活的真实写照。此外,人际关系伪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影片中通过妈妈语重心长地叮嘱永远不要和男朋友说自己家不幸福,也不能让邻居知道家里没有男人,以免被他人欺负等台词,揭示真实社会人际交往中伪装现象之冰山一角。
二、人物的自我构建
“他者”是拉康哲学的核心词,分为“小他者”和“大他者”,其中,“小他者”是指镜像阶段中一种在场的想象;“大他者”是指文化结构和社会法则的符号秩序。影片中母亲、晓雾在与“小写他者”互动过程中建构自我,在“大他者”中建构母女关系。
(一)中国母亲形象的自我构建
影片作品中母亲形象呈现类型化倾向——勤劳慈爱、父亲客体的象征意义。但是,电影《柔情史》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在影片中未设计母亲的角色名字,让其处于“身份缺失”的状态,意味着是对大多数母亲形象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回归真实的世俗生活,呈现了母亲不柔情的一面。杨明明导演在采访中提道,影片名中的“史”字,代表着在日积月累中形成了此番近况。母亲的不柔情就是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建构而成的——她和丈夫并不是因为爱情才在一起的,而是因为婚后有了孩子不得不在一起的。晓雾还没上大学丈夫就去世了,丈夫死后恶邻居欺负她们孤儿寡母,使得她早已厌倦了与他们为邻的生活。她本来就没有稳定的工作,再加上房屋拆迁后又没了房子出租费,晓雾上学又需要花钱,她就没有舍得买房子,选择和公公生活在一起。公公只字不提房屋继承和遗嘱的事儿,搅得她心神不宁;公公的精于算计,让她感觉自己在他那里占不到一分便宜。丈夫、娘家人的角色缺位,才逼得她学会用市侩、算计的眼光去看待人际关系;才华方面不得志,所以她才通过对晓雾在生活中事无巨细的控制刷存在感;物质上的不富足,迫使她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过日子,甚至在自己创作的打油诗里面期望吃草解决生计问题。
(二)晓雾的自我构建
晓雾的不柔情史,是生活细节日积月累所导致的,她在不算高温暖的家庭环境长大,爸爸去世后,妈妈手里攥着钱不买房子和爷爷去挤二居室,生活上的不方便与空间上的不独立都让她很不满,甚至让她感觉妈妈眼里只有钱。为此,她拒绝去理解别人,也拒绝理解他人,认为最可怜的活法就是为了理解;她不相信无条件的宠爱,用过激的方式“自我保护”,坏着过日子。表面上这是晓雾的自主选择,实则蕴藏着这个家庭的悲剧。
(三)“大他者”中构建母女关系
母亲身份主要是一种家庭角色。以《柔情史》中母亲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年女性,都以家庭生活为主,缺乏社会的存在感,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她的生活经验,所以她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事无巨细地控制子女的生活,用她们的市侩和封建迷信指导着子女的生活,试图通过照顾子女来实现自身价值,最终形成母亲付出感强、子女愧疚感强的母女关系,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影片通过呈现内耗、消耗的母女关系,引发观众深思如何构建健康的母女关系。
代际间权威与自由之争。《柔情史》在各大电影节上映,外国观众都产生了情感共鸣,杨明明导演总结道:“世界上所有的母女关系都是一样的,女儿经常跟自己的母亲过不去。”母亲代表着权威,试图用自己的观念去塑造晓雾;但影片中小雾在胡同滑着滑板车的长镜头,以及故宫里皇后服饰游客照的意象,都预示着晓雾爱自由、不服管,她势必会摆脱母亲的影响。代际文化的较量,她们终究会在试图改变对方的道路上学会妥协,形成各美其名的母女关系。
金钱控制下情感异化。杨明明导演在采访中提到“女性总是承受更大的压力,生存层面问题很容易就强加给下一代”。影片虽然未像张爱玲小说一样塑造母性的沦丧,但是将象征贫瘠、饥饿意象的牛奶、羊蝎子、瓜,和她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在餐桌上呈现母亲催促晓雾去工作挣钱、钓金龟婿的场景,揭示金钱控制下情感的异化。
《柔情史》通过展示不柔情的母女,既让观众感知到母女共生的镜像关系,又映射了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在母女不柔情的自我建构史中,“小他者”“大他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