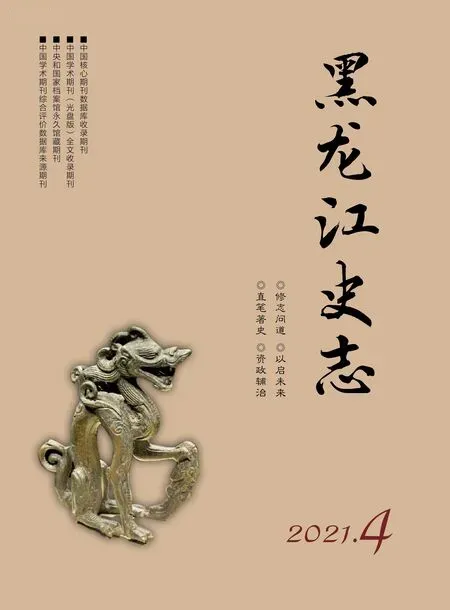年鉴专记类文献的发展与使用
徐佳佳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0)
在当前地方综合年鉴的主体正文基本由各类条目构成,但由于条目存在内容浅显、容量有限,难以全面、深入反映事物发展全貌等缺点,一些地方综合年鉴会收录一些专题文章来弥补内文条目的这些问题。这类专题文章不是对原始资料的简单收录,而是针对某一问题进行全面研究、阐释、介绍,属于三次文献。在当前的地方综合年鉴中,这类文章多被归于专记、专文、特载等栏目。本文为表述方便,将这类文章统称为专记类文献。
在近年地方综合年鉴的发展过程中,专记类文献得到了较快发展,已经成为了各类地方综合年鉴广泛使用的一种新型重要体裁。但由于目前学界对于专记类文献的系统理论研究较少、地方综合年鉴专业编纂人才匮乏等因素,专记类文献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选题不精、内容单一、来源渠道窄等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专记类文献发展的过程,分析国外及晚清民国以来本土年鉴在使用专记类文献中呈现的不同特点,透析目前本土地方综合年鉴在使用专记类文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找原因并提出对策。
一、年鉴专记类文献发展始末
当代地方综合年鉴对专记类文献的使用是有历史渊源的。国外年鉴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使用专记类文献作为对内文的补充。晚清年鉴传入中国之初,本土年鉴模仿西方年鉴编纂方式,也吸纳了专记类文献作为本土年鉴的重要内容。至民国时期本土年鉴迎来发展的“黄金十年”后,专记类文献更是被当时的各类年鉴广泛使用,成为本土年鉴的重要体例。
(一)国外专记类文献的使用
专记类文献在欧美、日本等年鉴发展较早、较速的国家有较长的使用历史,直到目前专记类文献的使用都很普遍。在一些国外年鉴中,专记类文献会归于特集、评论等固定栏目并被长期收录。专记类文献是欧美、日本等国年鉴提高内容竞争力、树立品牌优势、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
在英国出版时间较早的《不列颠百科年鉴》是一本以《不列颠百科全书》为蓝本,以记录上一年世界各地政治、经济、科学发展的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性年鉴。除了正文之外,这本年鉴长期邀请一些世界科学、文化、政界名流为该年鉴专门撰写相关文章,或者对一些焦点人物进行专访,并将这类内容置于卷首,通过设置“commentary”“feature”等栏目,凸显专记类文献的重要地位。如《不列颠百科年鉴》1996卷邀请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为该年鉴撰写了研究论文《the outline of engeering world》,文中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框架进行了判断和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日本的《朝日年鉴》在卷首设置了特集栏目,用来记录过去一年中人们较为关注的各类经济、社会、生态事件。如《朝日年鉴》1995卷的“特集”栏目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战后50年表》记录了二战后日本每年的大事,另一部分就是针对1994年日本气候异常,邀请日本气象局的专业人士为该年鉴专门撰写的《气象异常,94夏》,该文就属于一篇专记类文献。
随着年鉴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工具被广泛传播,新兴经济体纷纷渴望利用年鉴传播本国文化,加强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沟通。20世纪60、70年后之后新加坡、南非、埃及等国家陆续编辑出版了大量年鉴。这些新兴年鉴出版国在编纂年鉴的过程中,也大量使用了专记类文献,且在使用方法和内容设置方面都较为灵活,有较多创新。如由南非通讯和信息部主编的《南非年鉴》,其主体内容基本就是由一篇篇严谨的专题文章组成,这些专题文章围绕人口、能源、文化和体育等主题展开完整论述,与国内地方综合年鉴的专记类文献的内容、写法基本类似。
总体而言,国外年鉴对专记类文献的使用总体上呈现几个特点:一是注重完整性。国外专记类文献大多内容、结构完整,对研究对象的发展前因后果有较完整的介绍,一些带有研究性质的文章,大多具有较为完整的论证过程,不采用片段式的小节或者摘要。二是题材丰富。专记类的文章体裁、题材都比较丰富,既有综合性的新闻报道、也有专访,还有调查报告、学术论文以及综合性的述评等,既有记叙文、说明文,还有议论文。三是带有论述性。专记类的文章中大多是三次文献,对原始材料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加工,夹叙夹议,带有较高的思辨性和参考价值。四是主题鲜明。专记类文献大多围绕一个主题从特定的角度深入探讨,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立场,较少泛泛而谈。五是来源广泛。专记类文献的来源十分广泛,作者群体十分庞大,使得国外专记类文献具有多样化的内容风格。
(二)晚清民国本土年鉴专记类文献的使用
年鉴在晚清时期从西方传入中国。晚清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年鉴既有中国人翻译的外国年鉴,如卢靖组织翻译出版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也有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编辑出版的年鉴,如《上海年鉴1852》。这些年鉴在框架结构和内容体例等方面大多延续了当时国外年鉴的风格。其中《上海年鉴1852》中《徐光启记略》《略述中国人的科学——算术”》等章节,都属于结构完整的文章,记录的内容也没有年度限制,文中既有记叙也有议论,语言平实、简洁,属于专记类文献。
到民国时期,我国年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不仅出版的数量、种类大增,而且逐渐摆脱西方年鉴对本土年鉴的桎梏,能够根据自身实际需要灵活使用各种年鉴体例、设置年鉴的内容。充分利用专记类文章凸显各自年鉴的特征和价值,是民国时期本土年鉴质量不断提高,出版逐渐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无论是官修年鉴,还是民营出版机构主编的各类商业年鉴等,专记类文献都被广泛使用。
民国时期官修年鉴发展较快,南京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编修了大量的年鉴。为方便读者参阅、凸显年鉴的文本特色,这些年鉴广泛运用了专记类文献。如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出版的《全国银行年鉴》1934至1937卷中,大量采用了专记类文章。如《全国银行年鉴》1935卷中第一章《近年一年之中国银行业》也是“内分现势,兴格,储蓄银行法,营业,金融问题等五端,完全根据本室所集资料,逐一作事实上之叙述,兼作理论上之批判”。
民国时期,民营出版机构编辑出版的各类商业年鉴占据了年鉴出版业的主体。为凸显不同年鉴的内容特色,提高年鉴的可读性、信息量、参考价值,专记类文献也被大量使用。如民国时期申报馆编辑出版的3卷《申报年鉴》就大量采用专记类文献。如《申报年鉴》1933卷首的《一年来之国难》就是记录1932年以来的社会变化发展的综合性文章。
除了综合年鉴,民营机构出版的各类专业年鉴,也大量使用专记类文章。如1934年电声周刊社出版的《影戏年鉴》中,置于卷首三篇“特载”即《电影界元老郑正秋逝世》《胡蝶女士光耀国际衣锦荣归》《阮玲玉一代一人滥情自杀》对1933年中国电影界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详细记录和评论。
民国时期,在个人主编的年鉴中,专记类文献也被作广泛使用。在胡祖荫主编的《民国廿六年儿童年鉴》中,收录了《耶稣圣诞节的故》等文章。
总体来说,民国时期的传记类文献运用较为广泛,使用的方式也比较多样和灵活。从内容方面看,这些专记类文献,既有专文、特稿、和专题新闻报道等,也有对某一领域、学科、部门或者某一专题所发表的系统、完整的综述或评论。
从文章来源看,民国时期的专记类文献来源广泛,既有编纂机构自身编辑、记者、工作人员撰写的文章,也有特邀的出版业同行、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所作的论述。这些人大多对相关行业、研究领域较为熟悉,是专记类文献内容质量的重要保障。但该时期的专记类文献并没有整合放在一个固定的栏目,位置也没有固定,而是编辑们根据需要放在年鉴卷首或者正文中间。
(三)20世纪80年代后本土年鉴对专记类文献的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年鉴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编辑出版的各类年鉴较少,年鉴编辑出版的理论也较为薄弱。这一时期出版的少量年鉴框架结构简单,体例较为单一,对专记类文献的使用不多。20世纪80年代我国年鉴编辑出版工作全面重启,地方综合年鉴开始由各级政府机构主持编纂,并逐渐成为当代年鉴编纂的主体,占据了当前年鉴出版业的主流地位,年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过由于民国之后年鉴编纂工作长时间中断,当代年鉴应如何编纂并没有清晰的思路,一时间各类年鉴体例纷纷被尝试采用,专记类文献就是其一。如《江西年鉴》从2002年创刊到2020卷,均设置了专记栏目,用来专门收录条目以外反映江西社会经济发展面貌的专业文章。《上海年鉴》从2000卷开始设置专记栏目,用来收录过去一年重要的政治、经济大事件,2001卷、2002卷虽没有设置专门的栏目,但仍然在卷首收录《上海百年之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记录近年上海的重要发展变化的专业文章。此外,《吉林年鉴》《山东年鉴》《广西年鉴》《长春年鉴》等省、市综合年鉴在近20年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也都广泛使用了专记类文献。
可以说,作为当代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体裁,其价值和作用已经被各级地方志机构认可,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成为地方综合年鉴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当前年鉴专记类文献存在的问题
随着近年来专记类文献被年鉴,尤其是地方综合年鉴广泛使用,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记不专,内容不特
专记类文献不同于年鉴内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内容的记录较为全面、深刻,能够进行理论化的论述,但一些地方综合年鉴的专记类文献常出现选题不精,内容不专、不特的情况。如《江西年鉴》2002卷专记中的《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1921—2001)纪略》一文对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的发展历程按时间线顺序进行了简单梳理,这种表述并没有对文献进行深入地加工,也没有得出比较清晰的结论,并没有起到通过专记弥补条目缺点的作用。这类简单梳理内容的文献并不适合置于专记之中,放置于附录资料中可能更为合适。
同时,还有一些专记类文献选题大而化之,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文献内容缺少多次加工,大多拼凑而成,这不仅影响了专记本身的质量,还容易造成专记与年鉴内文大量重复。如《江西年鉴》2006卷专记中的《“十五”期间江西经济建设与社会快速发展亮点回眸》中将“十五”期间的经济总量、工业发展情况等用大量数据说明,而这些数据在内文中的工业、财政税收等大的类目中都有记录。
(二)记录对象较单一
当前地方综合年鉴专记类文献记录的对象大部分是政府工作,如《江西年鉴》2002卷到2020卷,这19卷年鉴的专记共计发表了56篇文章,其中17篇都是以各类主题教育为主题,平均下来一卷就有一篇,其中2006卷和2010卷的专记中各有2篇记录主题教育的文章,主题教育的内容偏多,涉及社会生活、文化生产等其他方面的主题内容的专记类文献就相对较少。虽然各级政府机构和组织开展的各类主题教育等活动有其价值,但专记栏目过多记录主题教育活动,影响了年鉴记录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也让主题教育这一内容的展示视角过窄。
(三)文献来源单一,书写风格公文化
梳理各级地方综合年鉴的专记类文献的来源,大多来自各级政府行政单位机构,鲜有邀请行业专家、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学者以及社会名人为专门年鉴撰稿的。过度依赖政府机构供稿,不仅影响了年鉴质量的提高,而且使得专记类文献的书写风格也日益公文化。如《江西年鉴》专记栏目的文章,基本都是向各政府部门约稿,这些稿件大多由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根据工作内容编写而成,具有很强的公文色彩,思辨性不强。《山东年鉴》1994卷“专记”的《艺术的盛会 人民的节日——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成功举办》一文记录了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举办的盛况,并对活动的特点和意义做了评论,但在写法上也有明显的公文色彩,多用总结、报告式的方法表达观点,官话、套话较多。这种表述方式削弱了专记类文献的学术价值、存史价值和文献参考价值,对提高读者对年鉴的阅读兴趣和年鉴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利的。
(四)专记类文献的名称、内涵尚未确定
目前,在各级地方综合年鉴中,专记类文献被归于专记、专文和特载等不同的栏目。虽然这些栏目都刊登专记类文献,但是名称不同,显示了编纂者对专记类文献不同的认识,也说明何为专记类文献尚未统一。
《江西年鉴》创刊至今,专记类文献均归置于“专记”栏目中,而该年鉴的“特载”栏目专门用于收录未经反复加工,没有评论性质的二次文献。《广西年鉴》2019卷将专记类文献设置在“特载”栏目中,但该卷年鉴的“特载”收录的5篇文章,除去两篇领导讲话及《政府工作报告》等资料性文献外,《壮乡腾飞结硕果 砥砺奋进谱新章——改革开放40周年、自治区成立60周年 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这篇综述类专记文献也在该栏目中。将专记类文献与未经加工的资料文献设置在一个栏目中,表明该年鉴编纂者对于专记类文献特征认识的模糊。又比如,《江苏年鉴》2018卷的“特载”栏目收录了2篇文章,即江苏省统计局撰写的《锐意改革立潮头 开拓创新谱华章——江苏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社会发展分析》《践行新理念 谱写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从内容上分析两篇文章属于专记类文献。在这里,“特载”与“专记”“专文”的概念基本没有区别。
《上海年鉴》则设了专记、专文两个栏目来专门归置专记类文献。该年鉴编纂者认为“专记”记述内容一般是特别重大的工程、代表发展方向的新的事件;“专文”除了一般的反映重大事件的真实全过程外,可以客观地对事件产生的原因、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验教训等作适当的记叙。
目前专记类文献设置的栏目不同,内涵、属性和定义在认知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不仅影响了专记类文献的编纂,对于开发、利用专记类文献,并借此提高年鉴的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也是不利的。
三、当前年鉴专记类文献问题的产生原因
当代年鉴,尤其是占据年鉴主体地位的地方综合年鉴,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大体有以下两点:
(一)理论研究基础较为薄弱
无论是专记类文献的编辑出版问题,还是专记与专文、特载等不同文章的区分与使用问题,本质上还是对专记类文献的认识不够。目前,大部分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者对于为何要使用专记类文献、如何编纂专记类文献,较少从深层理论方面进行思考。尤其是对于我国年鉴发展历史,专记类文献的使用与发展变化等内容缺少深入的考察,造成在使用专记类文献时的差错。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地方综合年鉴与方志在工作方面并轨后,一些缺乏年鉴理论积累的编纂者在寻找年鉴编纂理论时,盲目借鉴方志的书写规范、框架体例等,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年鉴志书化”的趋势。借鉴方志理论本身并无不当之处,但由于对年鉴专记类文献发展过程乃至年鉴理论缺乏研究和积累,一些年鉴编纂者在借用方志发展经验时,认为专记类文献是方志特有的体例,本土年鉴在借鉴方志体例之前从未使用过专记类文献,因而专记类文献如何使用,应当根据方志的编纂规范来实践。这一观点正是缺乏对本土年鉴理论缺乏研究所致。可以说,缺乏较为深入和丰富的专记类文献理论研究,是目前专记类文献的使用价值尚未充分发挥、编纂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专记类文献编辑出版弹性较大
2017年12月中指组出台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年度内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料可采用特载、特辑、专文、专记或其他形式集中汇辑”。2020年,中指组出台的《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又表示“年鉴可采用特载等形式重点收录年度具有重大意义或特殊意义的文献资料,收录资料应当严格控制数量”。从中可知几个问题:一是专记类文献并不地方综合年鉴的必备体例,并不要求每一本综合年鉴都要用到专记类文献,是否需要收录专记类文献需要编纂者根据实际需要把握,因此相对于其他年鉴体例,专记类文献的编纂实践并不是特别多,编纂时出现问题后的研究也不是很多。二是由于对专记类文献的使用不做硬性要求,造成各级地方综合年鉴的编辑出版规定中,对于如何使用专记类文献,也没有具体的、硬性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中只要求“特载等形式收录资料应当严格控制数量”,即只规范了专记类文献的数量,对于专记类文献的其他编纂标准和要求没有具体规范。这样就造成专记类文献是否运用得当全靠编纂者自己把握和摸索,如此大的弹性对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者,尤其是刚入行的年鉴编纂者而言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而出现一些问题也实属正常了。同时,正因为较难把握编纂标准,一些地方综合年鉴在一些年份会取消专记栏目,如《山东年鉴》2013卷和2014卷。
四、解决当前年鉴专记类文献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年鉴编纂出版理论研究
一是从本土年鉴的发展中汲取经验。我国年鉴从晚清传入后就不断根据本土的实际需要,在年鉴的编纂思想和主旨、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人才队伍培养以及年鉴传播、使用与研究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较多有益探索,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好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但由于对这段本土年鉴的历史较少梳理和研究,使得当代地方综合年鉴在专记类文献乃至整个年鉴编辑出版理论方面缺乏深入研究,造成当前年鉴的理论发展推进较慢。因此,无论是为了解决当前地方综合年鉴专记类文献的编辑问题,还是促进当前我国年鉴的发展,从本土年鉴自身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可以成为一个有益尝试。二是从国外年鉴的发展中借鉴编纂经验。现代年鉴源自欧美,但经过漫长的传播,年鉴已经成为全球文化进行交流的媒介,借鉴世界各国优秀年鉴编辑出版经验是丰富本土年鉴编辑出版理论,提高本土年鉴编辑出版水平的重要途径。欧美、日本等传统年鉴出版大国在专记类文献的使用方面已经积累了较多经验,美国《世界年鉴》《国家地理儿童年鉴》等至今仍在大量销售的年鉴在专记类文献的使用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我们要利用好专记类文献,还应该拓宽眼界,从国外年鉴编纂经验中寻找适合本国年鉴发展的举措。三是从跨学科发展中汲取编纂经验。目前,在史书、志书乃至一些科普读物和工具书中,专记类文献都有被广泛使用。因此与相关学科展开编辑出版理论、实务等方面的交流对话,借鉴其他出版物在使用专记类文献过程中的经验,可以让年鉴在专记类文献的使用方面取长补短,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但借鉴经验不应当是机械照搬,只有结合当前各类年鉴发展实际的情况下,根据不同年鉴编纂主体的需要充分利用专记类文献,才能够促进年鉴编辑出版的快速发展,否则还是会难以发挥专记类文献的价值,影响年鉴质量的提高。
(二)扩宽专记类文献的来源渠道
纵观民国时期本土年鉴及国外年鉴的发展过程,在专记类文献的来源方面都是多样化的。无论是民国时期官修的《中国经济年鉴》《铁道年鉴》,还是民营出版机构出版的《申报年鉴》《航业年鉴》等,在收录专记类文献时,都会向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高校、学术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学者、新闻出版业从业者及文化名流等约稿,以此丰富专记类文献的内容。国外年鉴也大多如此,如《朝日少年少女理科年鉴》1979卷就邀请了朝日新闻社科学部、外报部、国立科学馆、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等机构的专业人员为该年鉴专门撰写专记类文章,提高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反观目前我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机构过度依赖政府机构供稿,在专记类文献的体裁、内容、书写风格等方面都较为单一,影响了专记类文献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年鉴编纂机构可以在保证内容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对专记类文献这一相对灵活的体裁,尝试扩展文献来源,以此增强年鉴内容的竞争力。
(三)提高年鉴编纂团队的综合素质
专记类文献能否进行恰当的处理、使用,与是否拥有一个专业的编辑团队有重要关系。专记类文献由于自身内容的专业性、编写方法的灵活性等各种因素,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些问题的把握都需要年鉴的编纂者有对于年鉴整体编辑出版框架、内容、书写风格等多问题的整体把握,处理好就会变成年鉴的加分项,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年鉴的品质和特色。因此要做好专记类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还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年鉴编辑出版团队。我国当前年鉴,尤其是官修地方综合年鉴恰是缺少专业的编辑团队,大多数官修年鉴的编辑团队较少吸收各界专家,大多官修年鉴是由地方志工作机构中的年鉴处(年鉴社)工作人员完成,不仅人数少,而且缺乏对年鉴的发展,缺乏广阔的视野,因而对专记类文献的选题、内容搜集、编辑排版等难以作出高效、具有前瞻性的把握。因此,在年鉴质量竞争日益激烈、在专记类文献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加强编辑团队的组建,加快当代年鉴人才培养,广泛鼓励各行业专家学者加入编纂队伍,为当代年鉴编辑出版提供专业保障,可以成为增强当前地方志综合年鉴专业性的一个重要举措。
注释:
①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5卷)[M].上海,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1934,引文为该年鉴“例言”,第12页。
② 杨军仕,王守亚.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M].方志出版社,2016,(3):140.
③ 林德珍.论“专记”“专文”和“专题调查”在年鉴中的不同作用[J].上海地方志,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