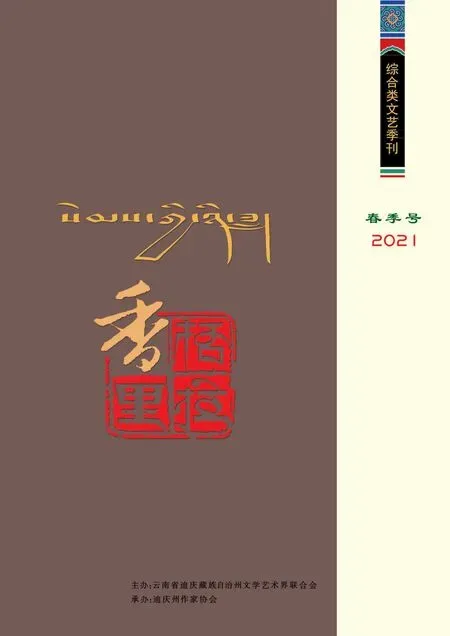小说二题
◎彭跃辉
小说二题
◎彭跃辉
祭湖
一
天刚蒙蒙亮,次仁和他的师傅就向着山谷出发了。
次仁背着一个双肩包,包里是此行的干粮和祭湖所需的物品,另外还有一只装满河水的塑料桶。河水是次仁昨天从山脚下的大河里背上来的,师傅说,去雪山下的央吉湖祭湖求雨,要把大河之水倒进湖里,求雨才会成功,圣湖才会赐给村庄甘甜的雨水。
在这之前,旱情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为此,村长带着一帮人来到寺里,找到师傅后献上哈达说:“上师啊,就像婴儿刚出生,母亲就断了甘甜的奶水。这包谷刚长过膝,就再也见不到雨水啦。请您无论如何, 也要到央吉湖走一趟,为四乡八寨的生灵祈求甘霖。”
村长说这话时,次仁望向经堂一旁的菜地,菜地里的辣椒被太阳晒得垂头丧气,没有一丝精神。
次仁没有去过央吉湖,央吉湖在次仁的眼里既清晰又模糊。
次仁和师傅出门之时,看见包谷叶还在打着卷儿瞌睡。山谷里没有风,次仁和师傅沿着日渐干涸的溪涧逆流而上。次仁记得, 往年这个时候,山谷里会开满粉白的碎米花, 一簇簇、一片片,鲜艳夺目。而今,在太阳的暴晒下,只剩下一些枯干的花瓣还挂在枝头上。
次仁跟在师傅身后,开始一步一步向山顶进发。
次仁今年 18 岁,师傅六十多岁,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 5 年的时光。
次仁是 14 岁那年入寺的。那一年,他即将初中毕业,准备参加中考时,父亲因一场意外事故去世了。从那时起,次仁成了一名孤儿。出殡那天,村长请来了师傅和附近村子里的几个喇嘛,为父亲念经超度。等一切事了,他就跟随师傅来到了如今的寺庙。
寺庙像一座四合院,建在离村不远的半山上。正房是一栋经堂,两旁的厢房是伙房、僧舍和储物间。通常,寺里只有他和师傅。听师傅讲,寺里原有不少出家人,还有一个活佛,活佛圆寂后,寺庙就一年比一年冷清了。
次仁入寺后一直跟随师傅,在寺里,师傅教会他念诵经文,使用法器、制作酥油花和朵玛,并让他学会了诸多的法事仪轨。清早,他就起来为佛像点上酥油灯、供上净水, 然后开始洗脸刷牙、烧水打茶。吃过早点, 师徒俩要念一个多小时佛经。然后,他就开始为寺里唯一的一块菜地浇水种菜。他会种很多蔬菜:青菜、洋芋、番茄、芫荽、黄瓜, 应有尽有。冬天的时候,他还会在菜地一角搭上塑料温棚,种上白菜、菠菜、萝卜、大蒜等耐寒的蔬菜。这里海拔不到 2000 米,气候温和,只要有地,人们都会种上包谷、青稞、大麦和蔬菜,一年下来,大都会有一个好的收成。
次仁入寺头两年,大凡有村人相请,师傅都会带他去念经祈福。这两年,随着师傅年事渐高,除了在寺里念经,就是闭关,一般的法事只是让次仁前往,次仁觉得师傅已经越来越脱离俗世了。
二
天越来越亮,一声声清脆的鸟鸣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走过一段松树和栎树交混的山梁,次仁和师傅驻足回望山下,见河水环绕村庄,高大的核桃树掩映着青瓦白墙,村庄上空升起了一缕缕淡蓝的炊烟。
“这里真是一个殊胜的地方!”师傅说。
次仁没有接话,次仁看见了西姆家的房子。西姆家房顶上的经幡是次仁用竹竿插上去的。
次仁记得那天西姆的爸妈为西姆举办成人礼,师傅和次仁应邀前往祈福。在师傅的带领下,西姆一家来到大门外,首先面对神山敬香祈福,然后又踩着西姆妈妈从松树上撕下的松针走进家门。在温暖的火塘旁,西姆的妈妈为西姆穿戴新衣:先穿水红的大襟短祆,再穿宝蓝的丝绸坎肩;先系蚕丝纺织的腰带,再穿绫罗缝制的黑褶裙;先配腰间的银坠饰,再挂胸前的护身符。最后,穿上代表成人的高跟鞋,系上象征待嫁的红头帕。穿戴一新的西姆站在一袋新米和一块琵琶肉上面,仿佛一朵初绽的红玫瑰。诵经声后, 桑烟升起,亲朋们给西姆挂上了洁白的哈达, 唱起了祝福的歌谣……
次仁想起西姆,眼前总会出现一朵带露的玫瑰。
不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太阳照在雪山顶上,雪山金黄一片。
想起央吉湖就在金黄的雪山下面,次仁的心里充满了期待。
次仁问师傅:“师傅,我们真的会求到雨吗”
“会的!”
“为什么?”
“因为心诚则灵!”
这话师傅说过多次,师傅说,一个出家人,面对佛陀、面对佛经,身、语、意虔诚, 才会有所获、有所悟。
太阳慢慢升高,金色的雪山慢慢变得洁白,次仁的脸上也渗出了密密的汗珠。
“凡事欲速则不达!”看到次仁走路时快时慢,步伐凌乱,师傅说,“要想抵达目标, 需要凝神静气,匀速前进。”
越往上走,树林越是茂密。长时间的干旱, 双脚踩在落叶和枯枝上,发出“咕嘟、咕嘟” 的声音。
“师傅,祭湖为什么要用河水,不能用其他的水替代吗?”次仁问。
“这是祖辈传下来的,具体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但世间万事万物,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因果之间,变化万千,这就是所谓的因缘和合。”
次仁似懂非懂,却也断了继续提问的念头。
一只鹰停在半空,静静俯视着山林河谷。
这时,次仁的电话响了,是远在城市的张先生打来的。张先生先是询问师傅和他的近况,次仁一一回答,末了,张先生告诉次仁, 他想过段时间到寺里住上几天,问次仁需要他带点什么?
次仁用眼神询问师傅,师傅摇头,次仁说不用了。
张先生一年当中总会抽几天时间跑到寺里,和师徒俩同吃同住,师徒俩念经的时候,他会在一旁默默坐着。闲暇之余,便和次仁一起挑水种菜。他还和次仁一起种树,苹果、梨、石榴、紫李,张先生希望能把自己亲手栽种的蔬果带回城市。次仁喜欢玫瑰,他们便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栽满了玫瑰。
有时,张先生也会像师傅一样,总会讲一些让人费解的话。张先生喜欢比喻,讲起城市的生活,说高楼是钢筋的丛林,地铁是奔跑的蚯蚓,马路是孤独的河流,灯火是失眠的眼睛……张先生说他很羡慕次仁的生活, 希望退休以后常住寺庙,过担水种菜、饮马劈柴的日子。次仁记得曾经有一次,他和张先生坐在屋檐下,一边看星星,一边听师傅念诵经文,次仁看见张先生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三
气温越来越高,树荫下散发着一股腐叶的霉味。走到一个山脊,师傅提议休息一下。次仁拿出包里的矿泉水递给师傅,自己也拿出一瓶喝了起来。
森林寂静无声,一只松鼠伏在一棵冷杉的枝桠上,一动不动望着他们。突然,又一跃而起,落在另一棵冷杉上,倏忽不见。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一只红脚鸡从面前的一棵麻栎树下刚露出身子,又匆匆忙忙窜向深林。
次仁想起入寺前,总是喜欢来到寺后的草丛里,用下扣子的办法去捕野鸡,师傅看见了,不仅会放走野鸡,还会收走绳扣。
“师傅,您还记得您放走的那些野鸡吗? 其中有我布下的扣子——”。
“记得!每次见你们鬼鬼祟祟的样子, 我就知道准是要干坏事了。”
“为什么要放走它们?”
“佛祖在未成佛前尚能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为师作为一个修行之人,如果视而不见, 不去搭救,那修行还有什么意义?”师傅说, “世界上的花鸟虫鱼都是生灵,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修行的目的不仅仅是会背诵多少的经文,还在于对大千世界怀有慈悲之心。”
一缕阳光穿过树林,在师傅身上投下斑驳的树影。
次仁望着师傅,眼神有些迷离。
“远离贪嗔痴,远离一切执着……”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师傅的声音。
就像内心无法抑止对一把弦子琴的喜爱, 次仁觉得自己始终无法像师傅一样离垢修行。
弦子琴是阿爸留给次仁的礼物,一直挂在僧舍的床头。每次看见它,总会想起阿爸在闲暇之余又唱又跳的情景。
次仁的阿妈去世早,阿爸从小把他拉扯大,不仅把一身的琴艺传给了次仁,还教会次仁很多唱词和舞蹈动作。次仁每次拿起它, 歌声总是不由自主想往外飞:
对面江岸之上,
有只仙鹤落脚。
仙鹤翩翩起舞,
宛若仙女下凡——
……没有风,山林闷热难奈。次仁记得小时候每到夏天,总会背着大人到大河边游泳,次仁喜欢在大河的波峰浪谷里起伏沉降的感觉。每次去,他总会在脑海里设定一个上岸的地点,然后劈波斩浪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力游去……累了,就把自己用沙埋起来, 看蓝天白云,想山的外面。大山阻挡了次仁的目光,有时,他真想顺流而下,看看山外的世界。
有一年夏天,西姆跟着次仁去大河里游泳,不料被河里的漩涡裹住,卷向水底,是次仁拼了命把她从水底拖出来的。那一次,他们都喝了不少水,也几乎同时被河水卷走。次仁和西姆一起长大,一起学习跳舞。
西姆跳舞的时候像一只天鹅,总会引来人们的赞叹。在一次学校举行的联欢会上,他俩一起为全校师生表演了一段弦子舞。那天, 在学校的操场里,次仁拉动弦子,西姆舞动长袖,边唱边跳,引来了师生如潮的掌声和喝采声——
四
越往上爬,次仁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僧袍似乎也成了一种负担。无数次机械地迈动双腿之后,村庄已被他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阳光在树林间飞舞,天空没有一丝下雨的痕迹。次仁甚至怀疑,持续不断的旱情是不是他冒犯了天神造成的——几个月前,他擅自打开了寺里常年紧闭的一间厢房,把厢房里朝向大河对岸阴山的石头阳具翻转过来, 摆成了朝天空坚挺竖立的造型——他曾经听师傅讲过,阳具对准阴山,是过去村里为祈求一方阴阳平衡、风调雨顺而专门请石匠雕凿而成的……
一朵白云从对面的山头上冒出来,又牵来了另一朵白云。
山坡上,树林里,到处是五颜六色的杜鹃花。山下虽然干旱酷热,但因这里临近雪山, 杜鹃花还能蓬勃开放。在这里,次仁终于闻到了一股潮湿的味道。
看到如此迷人的风景,次仁掏出张先生送的手机,对准眼前的杜鹃和山林拍摄起来。次仁想:要是张先生在这里,看到这样的景致,会不会激动得手舞足蹈?
张先生喜欢摄影,有各种长短不一的镜头。次仁司空见惯的东西,到了张先生的镜头下,总会充满美感和新意。有时,张先生也会手把手教次仁摄影:“看,这是光圈, 数字越小代表光圈越大,数字越大代表光圈越小;这是广角,使用广角可以达到前景大远景小的效果……”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次仁初步掌握了远景、近景、特写的拍摄技巧, 也逐渐对摄影产生了兴趣。每次用手机拍到自己满意的作品,次仁都会用微信发给张先生,张先生也会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张先生每次来,都会把拍摄到的事物用数据线连接到随身携带的电脑里,一张张挑选,又一张张删除,上百张照片,有时只会留下十几张保存起来。
张先生也曾拍摄过西姆,有穿盛装的, 有唱歌跳舞的,张先生说,在他拍摄过的所有人物里,西姆是一个最为灵动的人。
五
吃过一些干粮,师徒俩再次振作精神朝着央吉湖的方向爬去。
越往上走,海拔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每走一步都让人气喘吁吁。次仁看着师傅稳健的步伐,心里顿时充满了敬佩之情。密林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树胡子,如纱似幔,一层层,一道道,纵横交错。师傅一边撩开那些树胡子,一边寻找前进的方向。
次仁记得西姆也有一条洁白的纱巾,是西姆在城里的表姐给她买的。去城里的演艺公司跳舞之前,西姆曾经系着它,找到次仁, 希望次仁能跟她一起到城里跳舞。
西姆说:“次仁,跟我一起去城里跳舞吧,你的舞跳得那么好,一定会成为一个明星的。”
“我不能去,我已经是一个出家人了。”次仁说。
“你还年轻,不能在寺里呆一辈子。”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师傅,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了。”
“为了师傅,你愿意放弃自己一生的幸福吗?”西姆的眼里溢满泪水。
次仁褪下手腕上的一串香柏念珠递给西姆:“留作纪念吧,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西姆接过来,又使劲掷还给次仁:“我不要,我只要你跟我一起去城里跳舞……”
六
穿过一片草滩和灌木林,师徒俩终于来到了雪峰之下。
曾经无数次仰望的雪峰,此时在次仁的眼里显得寂寞而又骨感。白雪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炫目的光。
央吉湖静卧在雪峰下的一个山坳之中, 融化的雪水汩汩流过砾石滩,流过青草地, 流进湖里。
西斜的太阳照在湖面上,湖面云蒸霞蔚, 静谧安然。
按照师傅的吩咐,次仁先从双肩包里拿出经幡,顺湖拴在两棵坚实的灌木上。接着, 他折了一些高山落地柏的青枝,又检来一些干柴,堆在湖边。一切准备妥当,次仁拿出藏香,一支支点燃后插在湖边,然后拿出水果、糕点及一些奶酪放在藏香周围。摆完祭品, 他点燃从寺里带来的松明,架上干柴,再把青柏枝覆在干柴上面。不一会儿,桑烟袅袅升起,次仁又从包里拿出一袋装有青稞、稻谷、玉米等代表五谷的袋子。打开袋子,次仁用手抓出五谷,洒在青柏枝上。随后,他从湖里掬来湖水浇在上面,青烟越发浓重起来, 笔直地升向高空。这时,师傅一面高声念诵经文,一面把桶里的河水倒进湖里……
不一会儿,湖面上开始聚拢起一层雨雾。雨雾越来越大,渐渐覆盖了整个湖面,并向四周漫去,隐没了雪峰。突然,一道闪电刺破雨雾,接着,一声惊雷在头顶轰然炸响—— 雨来了,雨终于来了!先是急促的雨点,然后又变成瓢泼大雨。冰凉的雨水顺着头发钻进脖颈,师徒俩赶紧把僧袍举过头顶……
回去的路上,久旱的山路开始变得湿滑起来。
暮色四合之际,次仁看到了烟雨笼罩的村庄。
就在这时,师傅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石块, 身子不受控制朝下摔去……
次仁急忙伸出手,却不料抓了个空。
——师傅的脚被摔断了,但他还是忍着痛不吭声。次仁把师傅背起来,艰难地向村庄走去。
临近村庄时,背上的师傅说话了。
“次仁,等我的脚好了,你就去城里找西姆吧!”师傅说。
“不,我要跟师傅在一起。”
“你俗念难断,尘缘未了,走出去闯一闯,也许对你对我都是一件功德——”
“师傅,请您不要再讲了!”
……
漆黑的天空下,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
一头悲伤的牛正在老去
如果一颗念珠代表了一种烦恼,那么人的一生是否真的要经历 108 种烦恼?
听到二儿子说要把那头老牛卖了的时候,扎西爷爷一天的烦恼就开始了。烦恼开始的时候,正是扎西爷爷捻动念珠早祷的时候。扎西爷爷觉得,一个人的一生要经历千千万万个烦恼,如果每捻动一颗佛珠,就能消除一种烦恼,扎西爷爷愿意每天捻动千遍万遍,让 108 种烦恼中的千千万万个烦恼在手指的一次又一次捻动中悄然溜走。
扎西爷爷每天早上起来,洗过脸,第一件事就是往佛龛上的酥油灯加满酥油,点上灯,再往净水碗里添满净水。点上灯的佛龛渐渐地明亮起来,屋子里开始升腾起一股家的味道。这个时候,扎西爷爷坐在佛龛边他专属的位子上,二儿子一边打着酥油茶,一边回过头来跟他说话。
“牛贩子明天要上门来看牛了。”二儿子说。听到这话,扎西爷爷的手无由地抖了一下,他的手指偏离了刚刚捻动的念珠的位置。
“卖了也好,早就不中用了。”扎西爷爷呆楞了片刻才闷声说。
就像手中的念珠捻动了一轮又一轮,卖牛的话题也已经说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说到这个话题,大家都要不欢而散。扎西爷爷有一次甚至对二儿子说,除非我死了,不然你想也别想。说过这话以后,他的心里又非常后悔,他想他不该用这么重的口吻跟二儿子说话,他能理解二儿子的苦衷:家里只有四个人,他、二儿子、二儿子媳妇和小孙女寄在家里的一个还不满周岁的重孙小扎西。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很多时候确实忙不过来。有一次,二儿子跟他商量,说家里那么多地, 种一半都吃不完,干脆荒一部分就算了。他一听,立刻黑了脸就对二儿子吼:“这是一个农民该说的话吗?说这话是要遭报应的。” 从那以后,二儿子再没有说过撂荒的事。很多时候他就是这样,口硬心软,好像吼叫声才能维护他在家庭里的权威。
二儿子没有说动父亲,就打电话给城里的大儿子和三儿子。大儿子和三儿子的话更让他烦心。他们说种地又苦又累,一年到头也找不了几块钱。他们说地不要种了,牛也不要养了,家里一年的粮食和肉钱由他们分担就行了。“您就享享清福吧!”他们说。听到这些话他就生气,他依旧在电话的一头使劲吼:“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没有这些地养活你们,你们还能在这里说这些风凉话?”
扎西爷爷正在郁闷地喝茶的时候,二儿子媳妇就抱着他的重孙小扎西进来饭厅了。看到这个虎头虎脑的小扎西,他的心情开始慢慢好了起来,烦恼也好像拿走了一半。他的大儿子和三儿子跑城市里去了,他的孙男孙女也全都跑到城市里去了。他们偶尔回来一趟,还没能讲上几句话又跑了。还好小孙女的儿子小扎西在城里无人看管,抱回家来让外公外婆带。自从小扎西来了,沉寂了多年的家也慢慢恢复了一个家该有的生机。
小扎西在家里所用到的一切都是小孙女购置下的。奶粉是进口的,必须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喂。水在一个玻璃瓶里用电插座恒温着,不能烫也不能冷。他还有自己专用的脸盆、澡盆、毛巾,还有专用的奶瓶、饭碗和汤匙。有一次扎西爷爷想用自己的茶碗喂小扎西酥油茶,小孙女看见后马上制止道:“爷爷, 孩子小,不能用大人的碗,也不能让小扎西现在就吃盐。”他想不通,他养大了三个儿子, 个个都健健康康,怎么就轮到小孙女来指手画脚?再说,他也没有传染病啊!
吃过早饭,扎西爷爷就朝着牛棚走。趁着太阳刚刚升起,露珠还没有从草尖落下, 他想把牛牵到河边草多的地方去放一放。他来到牛棚里,给牛鼻子套上绳,一边抚摸着牛脖颈一边跟牛说话:“扎西,今天我们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扎西是他给牛起的名字,和他也和小扎西的名字一模一样。“现在小扎西来了,我这个老扎西不中用了,你这个中扎西也得走了。” 扎西爷爷和牛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絮叨个没完。“下一世你一定要投生在一个牛多的家庭里, 这样你就再不会寂寞了。”牛仿佛听懂了他 的话,甩甩头“哞”地叫了一声。
扎西爷爷把牛从牛棚里牵出来的时候, 他感到人和牛一样都老了。他觉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话简直就是一句屁话, 人一旦老了,也就成了累赘。人老了不值钱, 牛老了还可以卖点钱。他想牛和人的区别可能就在这里。他已经记不清牛在牛棚里关了多少日子,他想它一定忘了外面的天和地是什么样子了。自从那年家里的拖拉机代替它耕作以来,它就再也没出过牛棚了。
扎西爷爷在牛棚里拿了一根竹竿当拐杖, 一人一牛慢慢地朝着村外的河边走,拄杖落地的声音和牛的脚步声在村巷里清晰可闻。他记得他的小孙女曾经给他买过一根拄杖, 拄杖上还有电筒可以照明。他虽然不常用它,但家里有老人来的时候,他都会拿出来给他们看。村子一如既往的冷清,不再是过去牛嘶马叫人喧闹的那个出工的场景了。大一点的年轻人跑到城里打工去了,小一点的孩子都去了集中办学校点,寄宿在学校里。现在, 村里既没有人养牛,也没有人养马,酥油和菜都是从镇里买来吃。——扎西爷爷觉得,这世道真是变了,变得他越来越看不清这个世道了。
这世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扎西爷爷想破了脑袋也没有想起来,只记得家里最早的变化是从火塘开始的。那个他的阿爸阿妈坐过的火塘,那个延续了一辈又一辈的火塘突然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记不清是在哪一年了,二儿子说家里也要改革了, 改革要从火塘改起。二儿子说火塘灰烬多, 第二天起来打扫麻烦,家具和炊具都要擦上半天。二儿子就把扎西爷爷的爷爷置下的铁三角扔到了牛棚边,换上了崭新的铁皮炉子。铁皮炉子关上阀门就看不到火苗,看不到火苗就仿佛缺少了温暖。二儿子说盘腿坐着吃饭不舒服,把火坑也拆了,换成了木质的藏式沙发,换上了崭新的褥子。扎西爷爷觉得别扭,但他什么都不说,尽量让儿子折腾。可他一直认为,喝茶时还是盘着腿踏实,但儿孙们都不喜欢盘腿,他们说盘腿连喝茶都要噎着似的。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二儿子说要把茶桶也换了,换成搅茶机。他喝过搅茶机搅的酥油茶,那是在大儿子城市的家里喝到的。搅茶机里搅的酥油茶很均匀,但他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是柏木的清香?还是城市的酥油不地道?后来他想明白了,那是缺少了岁月积淀的一种味道,那味道无形无色, 但它真真实实地存留在你的心里,始终攫住你的心,让你欲罢不能。“你连茶桶都要换,要不要把我也换了。”他这样对二儿子说。从那以后,二儿子就没有再提过换茶桶的事, 茶桶也保留了下来。
扎西爷爷知道二儿子对他有很多怨言和不满,最大的怨言是小时候不让他继续读书一事。他让大儿子和三儿子一直读书长大, 然后跑到城市里去上班,而让二儿子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让他辍学去放生产队的牛。二儿子很喜欢读书,辍学以后一直跟大儿子识字,大儿子进城读书以后跟三儿子学习识字, 三儿子进城读书以后跟村里的老师学,还学算术。他发现二儿子喜欢读书,就对二儿子说: “书读多了容易傻,不读书还不是活得好好的。”二儿子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用一种无法言明的目光看着他,看得他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连续疼上好多天。
扎西爷爷有时觉得二儿子的改革是专门针对他的:他辛辛苦苦一辈子置下的东西二儿子都要改革掉。房子换成了大玻璃的,厨房和操作间也被隔离起来。家里的石磨不见了,木碓不见了,牛犁地时候的犁铧也不见了, 统统换成了冷冰冰的机器。这些机器就像一个个魔鬼,开动它的时候仿佛会被它吞噬。后来扎西爷爷看到村里其他的人家也换上了机器时,他的心才慢慢平和下来。
边走边想,一人一牛就走到了村口。村口的石头上,老铁匠还是坐在那里晒太阳。老铁匠坐在村口的石头上已经好多年了,见到有人来,老铁匠灰暗的眼神才会露出了一丝亮光。扎西爷爷记得,他年青的时候曾经请老铁匠打制过犁铧,用了多少年都不曾磨破。老铁匠打制的铁具像老铁匠一样灰暗、粗糙,渐渐地,村子里再没有人请老铁匠打制过铁具了。失业后的老铁匠整天坐在村口的石头上,人们也仿佛忘记了他曾经是一名铁匠。老铁匠看到一人一牛,激动地叫了一声: “扎西”。一人一牛听到叫声,立马停下脚步。老铁匠尴尬地笑了笑,说:“我喊牛呢! 好几年没有看到这头牛了,以前它可是出了名的顶架高手,也是犁地的一把好手。”扎西爷爷回头看看牛,觉得牛有些得意。“谁都有年少英雄的时候!”扎西爷爷似乎在回答老铁匠的话,又似乎是对牛和自己说。
扎西爷爷把牛牵到河边。河边的草滩上, 青草绿得发亮。看到发亮的青草,牛有些迫不及待,牛加快了步子。牛超到扎西爷爷前头的时候,扎西爷爷就骂:“扎西,你这个老不死的,想把老子拖死啊!”牛没有理睬主人。自从牛被关进牛棚以后,夏天,它吃从地里割来的还没有成熟的燕麦;冬天,它吃晒干了的玉米秆。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它就和人一样吃地里的青菜和白菜,牛都快记不清青草的味道了。
走上河边的田埂上时,扎西爷爷仿佛看见了自己的老太婆。老太婆还在世的时候, 常常走在河边的田埂上,割上一篮自家地里的燕麦或者白菜给牛吃。此时,扎西爷爷仿佛又看见老太婆躬着腰,背着一篮燕麦一步一步向他走来。扎西爷爷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揉了揉眼睛,眼前的情景又消失了。老太婆在世的时候,扎西爷爷很烦自己的婆娘,看不懂电视要问他,听不懂汉话也要问他。现在, 他的老婆子再也不来烦他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清静得有些过分。
扎西爷爷把牛放在草滩上,自己也在草滩上坐了下来。河风轻轻地吹着,阳光在草尖上跳来跳去。河对岸的公路上车来车往。他看着公路上各式各样的车辆,默默地计算着他远在城市里的儿孙们回来的时间。他曾经跟随儿孙们到过不少的城市,在他眼里,每个城市都一模一样:高高的房子、拥挤的车流,以及飞机里、火车上、商场里对他皱眉头的人。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对他皱眉,是他大儿子的孙女一语道破了玄机:“祖爷爷,您身上的酥油味太重了 !”是的,这辈子,他身上的酥油味是怎么洗也洗不清了。他想不通,儿孙们也是从小喝酥油茶长大的,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 怎么他们身上没有,而他就有?直到老的一天,他才突然明白,原来,他和他的儿孙们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两个世界的人。现在,村里人越来越少,很多父母都搬去了子女生活的城市。二儿子和二儿子媳妇也想去, 只是因为丢不开他才没有去。他记得二儿子曾经隐隐约约地跟他说过,当时他想也不想就对二儿子说:“你们想去就去吧,我只想老死在这个家里。”他不明白那些没有人情味的城市怎么就有那么多的人想去,在城市里头破血流也依然坚守着。他想起城市里那些滚动的电梯,有好多次,他哆哆嗦嗦地想踏上去却始终没有成功。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耻辱和遗憾!
……扎西爷爷发觉自己越来越喜欢沉溺于往事了。扎西爷爷知道,喜欢沉溺往事的时候,就是人最衰老的时候。当他想从往事的河流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一条毒蛇悄悄地抬起头来,愤怒地瞄准了他的身体。这时, 一直在扎西爷爷身边吃草的牛看见了,牛大叫了一声,牛头狠狠地向毒蛇甩去——毒蛇被惊走,扎西爷爷也被牛的叫声惊醒:他看见一条毒蛇正匆匆忙忙向草丛深处蹿去……
第二天早晨,扎西爷爷依旧在饭厅里捻动念珠,二儿子抱着小扎西送走了那头也叫扎西的牛。
彭跃辉 1967年 8月生于维西塔城。24岁前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创作期, 有小说、诗歌、散文在《西藏文学》《边疆文学》等省内外刊物发表, 24 岁后主要从事新闻采编和行政工作,曾任迪庆州政协秘书长、迪庆日报社社长,2019年10月退休后,重新开始文学作品阅读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