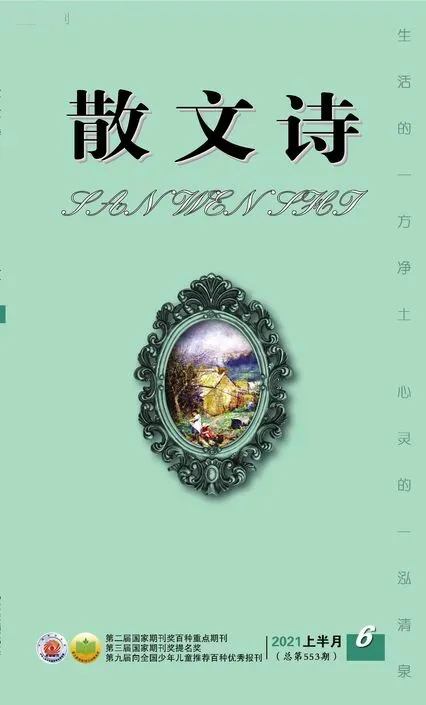新时期散文诗的发生语境与审美流变
◎周根红
1915年7月1日,刘半农在 《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7期发表了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1918年5月, 《新青年》第4卷第5期发表了刘半农的散文诗 《卖萝卜的人》。因此,刘半农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翻译、创作、并且使用散文诗概念的人。1927年,鲁迅出版了散文诗集 《野草》,这是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至今算来,散文诗在我国的发展已有百年历史。1949年后,我国散文诗经历了短暂的发展,开创并形成了散文诗创作的局面;“反右”和 “文革”时期,散文诗不断受到批判,创作陷入低谷,几乎处于消亡状态;1980年代,我国散文诗发展出现了真正的高潮;新世纪以来,散文诗的发展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时期30多年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巨变,给散文诗带来了哪些变化,散文诗发展究竟存在哪些特征,对此问题的研究无疑能够整体性观照新时期散文诗的发展,进而发掘散文诗创作的当代意义。本文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参考、借鉴和采用了已有的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试图展现散文诗发展的全景式图景。
一、政治宽松的发生语境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散文诗的发展比较缓慢,对散文诗了解的人知之甚少,创作散文诗的诗人也很少。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 “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 “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双百”方针,成为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指导精神。“双百方针”的提出,为建国后文艺创作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散文诗也由此获得了新的生机。
建国后,散文诗发展的重要开拓者是郭风和柯蓝。1956年,郭风在 《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散文诗 《叶笛》,吹起了散文诗的号角;1958年8月,柯蓝出版了散文诗集 《早霞短笛》(作家出版社),收入作者从5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散文诗200余章;1959年2月,郭风把陆续发表的散文诗作品结集为 《叶笛集》(作家出版社)。 “两人的作品相比照,柯蓝成功地解决了用散文诗歌颂工农兵英雄行为的问题,而郭风的田园牧歌把歌颂甘甜美妙的新生活和歌颂故园、童年统一起来。”柯蓝在 《早霞短笛》的 《后记》中写道:“党中央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响应这个号召,挑选了几首先在上海发表……由于这种散文诗的形式,十几年来我们文艺方面不曾出现。……我深深地感到今天突然出现,不仅写的人不习惯,编辑同志感到不习惯,恐怕连读者也不会习惯。”但是,郭风和柯蓝散文诗发表、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掀起了我国散文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短笛”和 “叶笛”也成为建国后散文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作品,并且成为当时散文诗创作的两种审美风格。50年代中后期,在党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散文诗坛出现了一些带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能较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心态的作品,如艾青的《养花人的梦》、流沙河的 《草木篇》、李耕的 《脚迹》《啊,山村》、刘湛秋的 《春天吹着口哨》《碑林漫步》《潮声》、顾工的 《绳桥》《军邮袋》、 许淇的 《黎明》《缄默的爱》、 王中才的 《炊烟》《海月》、徐成森的 《劝告》等,显示了散文诗生机旺盛的生命力。
然而,随着 “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 “大跃进”运动的开始,“左”的文艺思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受到摧残,散文诗当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写散文诗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散文诗几乎销声匿迹,只以 ‘花边文学’出现在一些报纸副刊上,文体建设处于倒退局面,只有极少数人致力于散文诗的创作,如女诗人王尔碑就以其清丽柔美的散文诗闻名于70年代,被称为 ‘流云诗人’。”20世纪60年代后,柯蓝的 《早霞短笛》被姚文元点名 “批斗”;流沙河的 《草木篇》被定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受到粗暴批判,作者也被定为右派并入狱;徐成淼的 《劝告》也受到批判,作者也被定为右派并发落到贵州山区。散文诗的发展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而陷入低谷。
散文诗的复苏和繁荣是在70年代末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散文诗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期。1977年,诗人朔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张志新烈士的散文诗 《只因》;1978年,李华岚的散文诗集 《赶海集》出版,成为新时期第一本散文诗集;1979年,刘湛秋的 《写在早春的信笺上》和刘再复的 《雨丝集》出版;1981年,郭风的散文诗集 《你是普通的花》出版,并在 《人民文学》1981年1月号上发表了理论文章 《我和散文诗》;1981年至1987年间,郭风、柯蓝主编的 “黎明散文诗丛书”先后由花城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了5辑共46册;1984年,郭风、刘北汜主编的 “曙前散文诗丛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叶金、田一文、羊翚、刘北汜、陈敬容、郭风、莫洛、彭燕郊的8部散文诗集。此外,一些散文诗选集也大量涌现,如由孙玉石、王光明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 《六十年散文诗选》;由李耕、秦梦莺主编,作家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 《十年散文诗选》;1987年,由郭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散文诗选》等。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5月13日,中国散文诗学会在北京成立,柯蓝、郭风同时担任了学会的会长,艾青担任名誉会长。一系列散文诗集、散文诗选本和散文诗组织的出现,预示着散文诗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新时期散文诗的繁荣和发展,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政治思想的解放,为散文诗创作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改革开放以后,文学逐渐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从政治工具中解放出来,在经历文艺思想的调整后,重新回到了文学的审美领域。“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加快了生活的节奏,时间在增值,感到时间紧迫的人,一方面,需要短小轻快一点的文体来调节精神生活,一方面,渴求内心的自由,使心海中明潮暗汐都能显露出来。散文诗正好能适应这种社会的客观的需要。”
二是改革开放后人性的解放,促进了散文诗的主体自觉。“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的个性和自由发展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尊重,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人的生存环境和思想环境都比以前开放,散文诗创作领域的作家展开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爱情、友情、大自然以及人自身等全方位的探寻和思索,但是,这三十年不仅仅是时间的纵向排列,这个时期人的物质精神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人性的解放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也使得散文诗人自觉寻找着散文诗的创新与突破,散文诗得以蓬勃发展。
三是改革开放后的思潮活跃,为散文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技法。改革开放后,我国文学思潮蓬勃发展,西方文学思潮大量涌入,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朦胧诗等潮流不断,各类现代主义写作方法纷纷成为作家创作的理论工具。散文诗人在这一文化语境下不断汲取这些文学思潮的营养,丰富着散文诗的创作技巧。尤其是80年代新潮散文诗的流行,培养了一大批在当下仍然具有极大创造力的散文诗人。
二、80年代散文诗的审美特征
80年代,政治语境的宽松为散文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散文诗的作者队伍逐渐壮大,散文诗的文体自觉意识进一步加强,出现了我国散文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创作高潮。散文诗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表达方面,逐渐突破 “十七年”时期的艺术惯性,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从工具性向审美性的回归。 “十七年”时期的散文诗作品,仍然处于 “工具性”的追求,散文诗作品大都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赞美新人新事新风貌和讴歌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柯蓝和郭风的散文诗集 《早霞短笛》和 《叶笛》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此外,许淇的 《骆驼》对人民坚韧品质的赞美、刘湛秋的《春天吹着口哨》对新时代和新生活的赞美和憧憬、流沙河的《草木篇》以草木比喻人民的精神等。新时期的七八十年代,散文诗开始朝着现代化、多元化方向发展。虽然这一时期的作品仍存在着 “十七年”时期散文诗的余响,但是,又呈现出新的文学风貌。郭风的 《鲜花的早晨》《灯火集》,柯蓝的 《果园集》《拾到的纪念册》,刘湛秋的 《写在春天的信笺上》,那家伦的 《红叶集》,王中才的 《晓星集》,许淇的 《呵,大地》,哲中的 《大漠的歌》,李耕的 《不眠的雨》,等等,这些散文诗集,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新时期的火热生活;弘扬时代精神,反映了改革开放时期人们五彩缤纷、多姿多彩的心灵世界。这里,作家的经历丰富,视野比较广阔,他们所注目的不再仅是身边的生活琐事,而是从生活矿藏中进行开掘提炼,有讴歌赞美,有沉思,有辨析,有批评讽刺,人生忧患,爱情友谊,生命现象,自然景观,无不是散文诗所撷取的内容。这一时期的散文诗,“不再单纯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文学的政治宣传教化功能,加强了对文学的审美功能的理解和对审美主体的研究,承认文学的各个门类的社会功能的差异性、创作个性、文体自觉性、读者欣赏兴趣等艺术特质,特别是文学的主体性得到高度的重视,1986年还被称为 ‘文学主体年’。 ”
其二,散文诗创作的艺术变革,现代意识进一步增强。新时期初年,以柯蓝、郭风为代表的散文诗风格影响到了当时的散文诗创作,形成了一股清新、欢快、质朴的散文诗风。然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散文诗不再注重一事一物、一人一景式的写作。散文诗人在创作技巧和形式方面进行了多样探索和尝试。秦兆基说,“他们尝试写抒情散文长诗,多重变奏的散文诗组,他们把目光从现实人生、自然界投向历史,甚至投向物质世界的内部;他们把笔触从物境转向心境:意识深处不自觉的活动;他们追求主题的多义性、不确定性,他们用散文诗去评诗、评文、评画、评史,想把感情和理性揉合起来。”虽然 “十七年”时期的散文诗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如艾青的 《画鸟的猎人》《偶像的话》采用了寓言体形式;华嘉、流沙河、田一文、李耕、许淇、刘湛秋等作家的散文诗在抒情、叙事和哲理的融合方面进行了探索;此外还有联组散文诗 (如流沙河的 《草木篇》、包玉堂的 《山花寄语》等)、书信体散文诗 (如柯蓝的 《一束短信》和 《我……》等)。但是,散文诗文体探索的解放则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一方面,这一时期散文诗的类型丰富,出现了报告体散文诗、纪实体散文诗、政治体散文诗、旅游散文诗、体育散文诗、探索散文诗、杂文体散文诗、书信日记体散文诗等。在长篇散文诗方面,也出现了如钟声扬的 《月亮,在我上空》、邵燕祥的 《麻雀篇》、闻捷写的 《桔园颂歌》、刘再复的《他的思想像星体在空中运行》等,都在三千字以上,甚至上万字。另一方面,在创作技法方面充分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开拓了散文诗的审美领域。80年代出现的新潮散文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所出现的散文诗创作潮流。他们在散文诗中注入了深沉的思索,融进了愤怒、哀怨、追悔、茫然若失等种种色调,正如秦兆基先生所说的,他们 “或作蹉跎岁月的追忆,或为被摧残扭曲的灵魂祈祷,或进行对失落的爱和温馨的寻找”,同时,朦胧诗人们将无数带有暗示性、象征性和导向性的意象带入散文诗中,使散文诗显示出强烈的虚化或隐化特点。其中脱颖而出的李耕、耿林莽、许淇、晓桦、灵焚、周庆荣等散文诗作家,尤为值得注意。灵焚的 《飘移》《房子》《异乡人》,以漂泊无依的审美意识超越了现实时空的思索;许淇的 《天鹅》《列宾》《西洋画册》注重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开掘;周庆荣假名 “玛丽·格丽娜”出版的散文诗集 《爱是一棵月亮树》,对 “爱情”“母爱”“自爱”等主题,进行了一次人生淋漓酣畅的歌唱。
其三,从轻快明亮到诗意的反思,注重抒发内心感受。“十七年”时期,柯蓝和郭风所开创的轻快明亮的散文诗风格成为当时散文诗创作的固定范式,抒发的情感有着政治一体化特征,缺乏个体意识。新时期以后,诗人们的内心在饱受 “文革”折磨后,对社会、人生进行了苦难、反思、悲戚等风格的深刻思索,提升了散文诗的人性色彩和生命意识。如郭风晚年的散文诗从过去生活的牧歌发展为对人生的沉思和领悟。他的 《你是普通的花》中的许多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世界的混乱和内心的孤独焦虑中,寻求心灵宁静和人格完整的独语者,把自然景象的描绘出神入化般引向内心气象的喻写,是这些散文诗的特色”。李耕在1979年 “归来”后发表的 《春笛九章》《生命的回音》《初春》《耕耘者之歌》等作品, “具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沧桑感,但爱情与信念使他能够节制个人命运的哀戚,并注意从自然隐微的生命中提取美丽的灵魂,因而具有婉丽而又深沉的品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叶梦为代表的女性意识的散文诗 《雨季的情绪》《月之吻》《梦中的白马》等。叶梦以女性潜意识的深层心理,触及了女性的身体欲望,形成了独特的抒情氛围。
三、90年代散文诗的审美特征
90年代至新世纪伊始,散文诗创作队伍进一步扩大,风格更加多样,作品数量激增。如:1991至1992年,严炎主编的20册《散文诗作家丛书》和 《腾飞线诗丛》(哈尔滨出版社);1989年底至1990年,黄神彪和栗原小荻主编的20册 《中国皇冠诗丛》(广西民族出版社)也包含着散文诗集;1994年至1996年,曾仕龙主编的《南粤散文诗丛》(广西民族出版社),海梦主编的 《散文诗作家丛书》和 《当代散文诗精萃》(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邹岳汉主编的 《散文诗金库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规模最为庞大的,当数由敏歧、田景丰主编的 《中国99散文诗丛》(广西民族出版社),原计划出版99本,实际出版共五辑110本。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散文诗作品单行本在各地出版,如刘虔的 《大地与梦想》、洪烛的 《你是一张旧照片》、王幅明的 《男人的心跳》、李松璋 《愤怒的蝴蝶》、谭仲池的 《岁月与梦幻》、彭燕郊的 《夜行》、皇泯的 《一种过程》、倪峻宇的 《岁月的涛声》、亚楠的 《远行》、莫独的 《守望村庄》、邹岳汉的 《时光流水》《青春树下》、文爱艺的 《时间的翅膀》《文爱艺散文诗集》、谢明洲的《蓝蓝的太阳风》、王宗仁的 《遥远的拉萨》《青藏风景线》、梅卓的 《梅卓散文诗选》、念家骏的 《远方,有一片绿洲》《东风如歌》、林登豪的 《边缘空间浓似酒》、桂兴华的 《新年酒吧》、田景丰的 《穿过秋林》、蔡旭的 《敞开心扉》《微笑是最好的笑容》《椰岛踏歌行》《散步的诗:椰城思绪》、王志清的 《生命场景》、韩嘉川的 《水手酒吧》、李耕的 《粗弦上的颤音》、丁芒的 《扫云集》《依然戈壁》、严炎的 《送你一束温馨》、王尔碑的 《寒溪的路》、潘永翔的 《心灵之约》、赵丽宏的 《落英缤纷》、喻子涵的《孤独的太阳》、耿林莽的 《五月的丁香》、王剑冰 《在你的风景里》、徐成淼 《燃烧的爱梦》、黄神彪的《随风咏叹》、方文竹的《美人香草》等。粗略来看,这一时期散文诗的创作呈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散文诗的都市幻象与都市意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都市空间的崛起和城市现代生活的语境下,一批都市题材散文诗开始出现。如徐成淼、许淇、刘虔、桂兴华、方文竹、韩嘉川、灵焚等散文诗人,都创作过现代都市生活和城市景观的散文诗。这些散文诗作品对现代都市文明、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抒发了内心的时代感触和人文思考。如徐成淼的 《环绕的双星》、韩嘉川的 《水手酒吧》、林登豪的 《都市叠影》等,在对八九十年代城市宽松服和紧身衫、夜总会的狂妄、都市的噪音等都市幻象进行书写的同时,发出了 “遥远的梦魔”、酸楚的浪迹、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人性的贪婪等思索。徐成淼在80年代末发表文章呼唤散文诗的都市意识,并认为,“文学中的都市意识,突出表现在作品人物 (包括作者)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主体对客体有战胜欲求;外部世界无论多么喧闹,人物却始终保持一定的自我空间;他们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有清醒的主体意识;强烈地追求着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思索着人生的奥秘。作为源于现代都市生活的非常年青的文学品种的散文诗,自然应以都市意识为其神髓。”这一都市意识直接影响到了90年代的散文诗创作。90年代散文诗的都市意识突出表现在散文诗作品中流露出的流浪、孤独和漂泊精神。邵彧双的 《遥远的孤独》、柯蓝的 《踏着星光远行》、郑明的 《心旅》、喻子涵的 《孤独的太阳》、唐钢的 《韶华独旅》、亚楠的 《远行》、陈华梅的 《灵魂的漂泊》、崔峰的 《苦旅》、张筱的 《漂泊之魂》、喻子涵的 《孤独的太阳》、李耕的《孤旅》等,无不笼罩着漂泊、流浪、孤独、惘然的情绪。这种流浪和漂泊情结,不仅反映了散文诗人的复杂的精神世界,而且折射出过渡、转折、巨变时代所必然要经历的彷徨和阵痛。
其二,散文诗审美疆域的进一步拓展。沿着80年代末新潮散文诗的道路一直发展,90年代的散文诗创作在艺术表现手法和审美疆域方面进一步拓展。90年代的散文诗人自觉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文学创作理念,追求现代化的表达,注重融合多种文学表达方式。邹岳汉曾说,“老一辈的散文诗作家,如耿林莽、彭燕郊、李耕、许淇、敏歧、刘湛秋、王尔碑、孔林、王宗仁、唐大同、徐成淼、纪鹏、海梦、邹岳汉、陈文和、那家伦等人,则从承继散文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传统一端发起变革,逐渐实现对自身早期作品较为平实的超越,沿着各自的路径去探求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散文诗发展的潮流。对照他们各个时期出版的个人散文诗集,我们不难看出其艰辛的然而也是富有成果的探索历程。”尤其是彭燕郊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 《德彪西 〈月光〉语译》《漂瓶》《无色透明的下午》《风信子》《溶岩洞,音乐不朽了》《混沌初开》等。李振声曾这样评价彭燕郊的《混沌初开》:“地标性建筑物一般的长诗 《混沌初开》,诗中那个精神漫游者,与整个人类最优秀的精神 (诗人称之为 ‘光’)之间的对话、诘难,凌厉的自我反思,思想的强健和阔大,足以成为近年已不多见的有关人的精神深度和宽度的一个象征。”李振声还将彭燕郊的这种精神探寻与鲁迅 《野草》联系起来,认为像 《站台》这样的诗涉及到了对 “不确定性”的亲近感。总之,90年代的散文诗注重散文诗自身的文化和哲学品质,更深刻地表现了 “现代人”对于现实和历史的思考。
其三,面向自我的个性化抒情。90年代,散文诗的创作既走出了 “十七年”时期的政治抒情,也走出了80年代的集体抒情,更加面向自我内心。90年代,文学领域出现了一股个性化写作的风潮,散文诗的创作也折射出了这一特点。如果说80年代散文诗的主体逐步强化,逐步复位于创造主体,那么90年代散文诗创作愈加获得了 “表现自己”的自觉性。如刘再复写于1995至1999年间的 《天涯独语》,他把这本书看作是自己的 “心传”和 “心灵史”,其作品多写漂泊不定的心灵感受,是其心灵苦旅的真实记录,艺术底色深沉、悲壮。他在 《我找到了自己,而且忠实于自己》一文中说: “真正强大的,真正成为创作动力的,只有心灵中那些迫不及待地迸射出来的情感,是那些久久郁积于胸中的痛苦。”王宗仁一直致力于高原的书写,他说,“我对高原每一处风景的描写,都蕴藏着我骨子里的情感,或爱,或恨,或怨。我自信,一个感情枯萎或感情畸形的人是写不出动人诗篇的……我越来越这样要求自己:读自己的散文诗也要获得审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
四、新世纪散文诗的审美特征
新世纪后,散文诗的发展、创作和理论更加走向自觉和多元。邹岳汉先生曾这样归纳散文诗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经过60年几代人的努力,散文诗体式变革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写作题材由即景式的 ‘小感触’扩展至对社会生活以至精神领域全方位的反映;作品结构由比较单一转为多层、繁复;主题由单纯强调宣传教化提升至服从诗人内心的召唤、人文的关怀和诗美学自身的要求;语言由常规的明白晓畅过渡到掺入暗示、喻意、多义、重构等个性化处理;审美情趣由传统的侧重 ‘意境美’‘哲理美’转向现代的侧重纷呈迭出的意象之美;对散文诗本质的认知由部分人倡导的 ‘散文诗是既不属于诗也不属于散文的独立文体’的模糊观念,逐步地自觉地回归到 ‘散文诗乃诗之一体’。”新世纪散文诗呈现出各种特征,借鉴着各种文学创作理论,其中有几个特征比较重要。
其一,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批判意识的凸显。新世纪散文诗创作逐渐突破了八九十年代散文诗的个人内心抒情的书写范式,比较注重现实生活,有着浓厚的现实主义倾向,体现了深沉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意识。正如彭燕郊所说,近年的散文诗,摆脱了自居于 “小玩意儿”和流连于 “风花雪月”的老套,增强了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的大气和厚重。现实关怀也成为散文诗人共同的呼唤。散文诗人不再仅仅满足于自我的内心表达和情绪宣泄,他们希望用散文诗的形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干预社会现实生活,重塑散文诗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感。这无疑显示了一种积极的现实关怀与文学共识,是对当下文学境遇的一种真切的体认,也是一种由诗歌界内部产生的良性反响。正是这个意义上,耿林莽认为散文诗 “可以展现大宇宙,表现大悲痛、大思想”,新世纪散文诗人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等进行的书写,突破了简单层面的还原,而是有着浓厚的批判意识。当然,新世纪散文诗的现实关怀,更多地表现在对都市现代性的批判和物欲横流社会中精神丧失的批判。如李松璋、陈计会、耿林莽、周庆荣、韩嘉川、喻子涵、莫独、梅卓、堆雪等散文诗人的作品。
其二,思想的深度思索。思想性是新世纪散文诗不断追寻的创作目标。这一时期,散文诗人注重从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感知世界、思考世界。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散文诗更加注重对历史、民族、文化的深度思考。如爱斐儿的 《废墟上的抒情》、黄恩鹏的 《过故人庄》、洪烛的 “西域”系列、唐朝晖的 《中国瓷》等都交杂着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沉叩问。另一方面,新世纪散文诗对生命、死亡、孤独、灵魂、存在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周庆荣的 《我们》《有理想的人》,李松璋的 《水晶或尘埃》,栾承舟的 《结合部》,徐俊国的 《故乡辞》《自然碑》,等等,已把目光投向对 “人”“理想”的思考,对 “生存情怀以及思想进行自然状态的守望”。尤其是 “我们散文诗群”所提出的 “意义化写作”,把重点聚焦于 “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写出与当下的生存意义、生命意义有关的情怀。拒绝无病呻吟,拒绝心胸的阴暗与狭隘,让日常情感升华到做人的情怀高度,明确诗歌文学作为社会心灵公共话语承担者所必须具备的健全品格”,提升散文诗的境界和写作者的情怀,成为散文诗创作的内在要求,既是对新世纪某些散文诗创作动向的一个小结,也是未来散文诗努力的一个新的开始。
其三,再次掀起了乡村热的创作潮流,散文诗写作的家园意识不断增强。乡土题材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新世纪以来,散文诗的乡土创作热情超过了八九十年代,成为新世纪散文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涌现了一批散文诗作品。如陈志泽的《守望·走不出故乡》和 《守望乡土》、任剑锋的 《眺望家园》、谢克强的 《远山近水》、陈爱民的 《聆听水声》、刘向民的 《乡村时代》、莫独的 《村里村外》、韩宗夫的 《稻草人的村庄》等。一大批以创作乡土散文诗的诗人涌现,如肖建新、张道发、李皓、马亭华、周大强、张抱岩、洪放、曼畅、空间、司舜、蒋伟文、耿翔、陈衍强、陈亮、洪州、徐后先、海叶、白红雪、海生、海夕子、周本贵、郭长玉、陈亮、李茂鸣、王晓利、常华敏、雨翁、邓杰、姜桦、龚立华、蒋旻、黎梦龙、刘鸿伏、山珍、周鸿等。除了坚守乡土、乡土牧歌式的散文诗外,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一个倾向是,乡村写作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城乡差异视野下的写作,如李邵平、陈德根、马东旭、潘永翔、蒋伟文等。
其四,悉心表达自己 “诗意的栖居”,倾力描绘灵魂的诗意漫游。新世纪以来,散文诗人更加注重对自我生存空间的诗意表达,努力建构散文诗的诗学地理,如叶梓对于甘肃胡杨林的书写、堆雪对西北、宋长玥对青海、亚楠的 “新疆远行”、耿翔的 “长安之书”、陈劲松的 “青海高原”、王小忠的 “甘南草原”、洪烛的“身体里的西域”、徐俊国的 “鹅塘村”等;同时,还有一些散文诗人在历史人文、精神高度、表达手段等方面坚守着散文诗的艺术探索,如陈计会、黄恩鹏、李茂鸣、丹菲、宋晓杰、语伞、爱斐儿、陈茂慧、李轻松、李见心、李明月、郑小琼、雪漪、喻子涵、谭延桐、庞白、崔国发、陈旭明、莫独、十品、周庆荣、灵焚、冯明德、箫风等。总体来说,这些散文诗人,或立足于生活的大地和区域,或深耕于散文诗的艺术追求,或针对某一类题材进行持续书写,从而形成了独树一格的诗学风格。
注:
①秦兆基: 《中国现当代散文诗七十年》, 《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66页。②秦兆基: 《中国现当代散文诗七十年》, 《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66页。③王珂: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建设的历史回顾》,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83页。④秦兆基: 《中国现当代散文诗七十年》, 《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66页。⑤杨雅星: 《寻找漂泊回归——新时期以来散文诗精神流变》,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3页。⑥黄伯谋: 《中国散文诗发展管窥》, 《广西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46页。⑦王珂: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建设的历史回顾》,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43页。⑧秦兆基: 《中国现当代散文诗七十年》, 《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第67页。⑨黄伯谋: 《中国散文诗发展管窥》,《广西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47页。⑩许林: 《试论世纪之交散文诗的三股新生潜流》, 《克山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第44-45页。⑪王光明: 《论当代中国散文诗》,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第19页。⑫王光明: 《论当代中国散文诗》,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第21页。⑬杨雅星: 《寻找漂泊回归——新时期以来散文诗精神流变》,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14页。⑭李振声: 《诗心不会老去 写在 〈彭燕郊文集〉出版之际》,参见孟泽、季水河编 《默默者存——彭燕郊创作研讨会实录暨论文选》,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⑮李振声: 《诗心不会老去 写在 〈彭燕郊文集〉出版之际》,参见孟泽、季水河编 《默默者存——彭燕郊创作研讨会实录暨论文选》,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⑯王宗仁: 《遥远的拉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⑰邹岳汉: 《从寂寞到繁荣:中国散文诗60年的辉煌历程》, 《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散文诗精选》引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⑱王山: 《“纪念中国散文诗90周年颁奖会暨 《中国散文诗90年 (1918—2007)》研讨会”在京举行》, 《文艺报》,2007年11月13日。⑲灵焚、潇潇主编: 《大诗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⑳灵焚: 《因为诗歌,我们多了一种热爱世界的理由》,见灵焚 《女神》,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