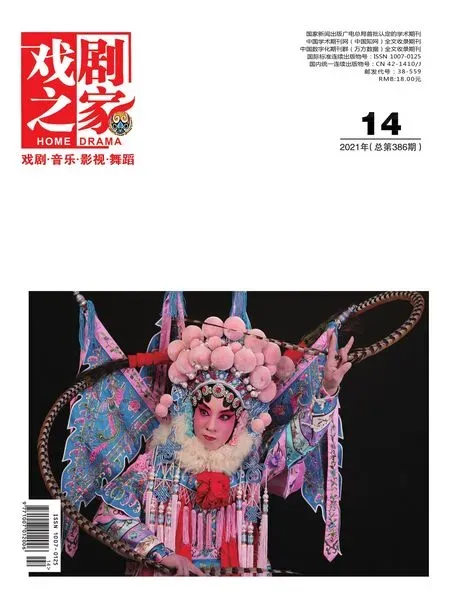从《发土地证》和《烧毁旧地契》谈古元的视觉叙事
潘艳飞,夏 强
(1.东北大学 辽宁 沈阳 110819;2.鲁迅美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4)
1947 年间,古元先后创作了多幅反映土改的作品,题材直接来源于他在东北农村下乡的经历。1947 年7 月,东北局动员一万二千名干部组织工作队,下乡开辟群众工作,古元到哈尔滨五常县周家岗参加土改,这里是土地改革的重点村,在这里,古元跟村民一起生活劳作、朝夕相处将近三个月,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其中反映东北土改的作品有《抓地主》、《起枪》、《发土地证》、《烧毁旧地契》以及《七斗王把头》和《暴风骤雨》插图等,这一系列土改作品反映了东北村民们面对土改时的不同心态,以及在不同土改阶段群众心理上的骚动和生活上的变化。本文将从这一系列土改作品入手,并主要以《发土地证》和《烧毁旧地契》这两幅作品为比较对象,解读其题材内容、表现形式,探寻其视觉叙事的话语方式和意义的存在语境,及其隐含的精神理念。
古元一系列反映东北土改的作品主要创作于1947-1948年间,1947 年9 月初《东北日报》刊载配古元插图《七斗王把头》的故事,这个故事同《暴风骤雨》一样也是以周家岗为原型,描写了周家岗村民七次斗地主王把头的过程,以及从中得到的教训。这个故事刊发的时间较《暴风骤雨》早了三个月。古元以木刻的形式创作了该故事的插图,其中一幅描述了“金牌子回到了群众的手里”,古元并没有落了窠臼地去画村民们的笑脸,而是以小圆刀刻画了手部特写:近景处一只粗糙的、沟壑遍布的、经年劳作的手,小心翼翼地将一个八角星形的金牌子捧在手心,金牌子熠熠发光,远处村舍、田地、马匹安静祥和,这种象征的意味加深了画面的凝重感、分量感,更好地表现了文章的内容“周家岗群众血汗制成的金牌子,又光华闪耀地回到了群众的手里”;另一幅描述了“请财神爷上车”,这位“财神爷”处在画面中心位置,蔫头耷脑、神情沮丧,无力地倚靠在驴车栏杆上,表现了“财神爷”即将失去财物的心情,画面上方光屁股的小孩子跑在驴车最前面,画面右边是负责押运的、握枪的民兵看着“财神爷”,左边是村民意气风发地走着,和“财神爷”沮丧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车夫则在前面回头用手指着“财神爷”,似乎在说“活该,你自作自受”,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财神爷”这个典型地主身上,突出了土改工作批判的重点。
《暴风骤雨》插图的创作也是在同时期展开的,当时住在老乡家的古元遇到了下乡深入生活的周立波,周立波邀请古元为自己的小说配插图,于是就诞生了反映我国土改运动的长篇名作《暴风骤雨》,该书反映了东北农村封建势力的垮台,以及农民中间新人物出现的复杂曲折的过程。他们在合作的过程中,都住在农民家里,除了参加农会的各种活动以外,周立波就是趴在住户家的一个三条腿的半圆桌上整理稿件,随后把文稿交给古元,古元坐在土炕上点着油灯画插图,最后周立波的小说完成了,古元的插图也随之诞生了。他们都是土改运动的参加者,亲身经历和感受过土改中的人和事,加之对生活环境的细致观察,使画面人物栩栩如生,动势、姿态、表情丰富准确,对细节的刻画深入到位。古元作品中农民穿的靰鞡鞋以及爬犁、苞米楼子、磨盘都极富有东北的特色,使整体和局部有机结合而趋于完美的统一;《东北日报》于1947 年12 月25 日始图文连载《暴风骤雨》这部长篇小说,并于1948 年4 月由各东北书店发行。
作品《起枪》发表于《东北日报》1947年8月23日第四版,描述了村民斗败地主,被压迫的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把曾经压迫他们的地主看押了起来,从地主家院子里挖出好多枪支和财物,围在被挖出来的枪支周围的人们兴高采烈,而地主则扭头偷眼窥视,面露不甘。《起枪》反映农民从曾经受压迫的地主那里夺过来斗争的武器,开始翻身作斗争,他们从思想上开始觉醒起来。
如果说《抓地主》、《起枪》是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觉醒和抗争,表现农民翻身,那么《发土地证》和《烧毁旧地契》便是彻底推翻了压迫的象征。《发土地证》和《烧毁旧地契》两幅作品的背景都安排在象征封建堡垒的城门楼附近,留给在场的村民们的空间狭窄逼仄,正如村民被压迫的、艰难的生活。作品的视角是从侧面俯视,在高墙的对比下,人显得矮小,只占据画面底部的部分,《发土地证》图中如龙卷风般的云和《烧毁旧地契》图中升腾的火焰象征着翻了身的农民打破了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内心的渴望就像冲天的火光,心里翻腾的巨浪犹如滚滚浓烟,这一切都宣告了背负在农民身上几千年的封建压迫走向灭亡。
《烧毁旧地契》与《发土地证》都描绘了村民们的群像,不同之处在于人们的观看状态。在《发土地证》中,画面左边有一人背对着我们,光着上身,太阳照出他黝黑的皮肤,他高举着土地证满意地看着,顺着他的视线方向往前又看到有一小群人在讨论着什么,其中一个面对观众的人手中拿着土地证,侧头和旁边的人说话,画面中间一人上台领土地证,古元刻画了其接土地证的瞬间,点明了主题。还有几个人蹲在近景处的楼角附近在观看,其中离城门楼最近的一个女人则倚在楼墙边,虽然我们看不到她的脸,但能感觉到她探寻的、若有所思的眼神,在画面上方,即城门楼的上面,一个背枪的士兵在巡逻,士兵旁边立着一个警钟,土地证的颁发在政府的组织下井然有序。
而《烧毁旧地契》表现的是农民翻身的狂欢场景,不同于《发土地证》中有探寻、犹疑、观望的态度,《烧毁旧地契》中每个人都是狂欢的一员,都参与其中。画面近景处有敲鼓的四个人,边敲边舞,动作各异,专注投入,他们平分在画面上,互相之间的距离相等,形成了一个半圆弧,而没有画出的另一半则是留给观众,观众仿佛被一种吸引力牵引到画面中,就站在村民们的身边,和他们一起舞起来。在四个舞者之后,位于画面中央的是一个站在高处的、戴着草帽的赤膊农民,他双手高举旧的地契,欲将其投入火中,他黑色的背脊在熊熊火光的映衬下特别显眼,也特别有分量感,所有人都睁大眼睛,目光都看向燃烧的旧地契,屏息凝神,面露崇高和坚毅。在面对观众的位置,一人扬起手中的长叉,将一张正在燃烧的地契高扬起来,与画面右边振臂高呼的人共同加强了画面的动感。
通过两个画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古元刻画了农民群众在其中不同的参与状态,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农民群众的反应与政治环境和东北的历史情况息息相关。
东北与延安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东北没有延安相对稳定的环境,日本侵略奴役东北十四年,期间进行了严酷的压制和奴役文化的宣传。日寇的统治通过原有的封建势力延伸到农村。县、村、屯的警察、特务以及协和会、兴农会、合作社、配合所等统治机构,都由地主掌握。当时东北农村的土地,除了经日寇强占的约为东北耕地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开拓地”、“满拓地”,及日本人的“私有地”之外,余则仍操纵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农民终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此种土地集中的情况,在蒋军控制的地区,除将“开拓地”、“满拓地”变成“‘国’有地”外,并无丝毫的改变。长期以来封建及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更加复杂。“八·一五”东北光复后,1946 年“七七”,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批准了农民收回土地的要求,随后动员一万二千个干部,组织数百个工作团,深入农村,协助农民进行翻身斗争。
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面对复杂的情况,出现了“斗争运动不彻底,还严重存在着‘夹生饭’的状态”这一现象。究其原因,一则是日本投降后,仍旧是“缺乏主见,甚至是彷徨的……含着毒素的……这个毒素包含着日本的奴化思想的残余,以及传统的封建思想,顽固的、退步的、腐败的、迷信的、盲从的、奴性的等等污秽的成分”。二则是“领导不敢大胆放手,没有贯彻群众路线,犯了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毛病”。因此不同的人所持态度不同,有真正动员起来的、有观望的、有阳奉阴违的,甚至还有“地主狗腿冒充积极分子,篡夺运动领导权的”。
土地改革的初期,村民们心里是有顾虑的,他们长期受着深重的压迫,对于地主存在害怕的心理,将政府派来指导土改的工作队视为“新鲜物”,没有从心理上承认接受,因为自己“从未这样密切地跟政府的人打交道”,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因而零敲碎打,每次因为一个问题,斗斗就算了。结果,群众和“王把头”二十多年的血海深仇无法得报,因而就不能打消群众的顾虑、满足群众的要求,也就无法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所谓“翻身”,顾名思义是身子翻过来,而实际斗争中更重要的是“翻心”,也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情感,成为一种革命主体,这对于经历十四年双重压迫的东北群众而言是很困难的。这从《七斗王把头》历时一年五次斗争都失败,以及群众对斗争感到疲乏、不感兴趣中可见一斑。第七次斗王把头,欲逃走未成的王把头依然顽抗,问问题假装不知,满嘴胡扯,这时“有人上去就是打几个嘴巴,说:‘老杂种操的,到这个时候你还敢拐着弯子骂穷人呢?谁是群小鬼儿呀?王八犊子!’一脚把他踢倒在地下,几十根皮带棍子没头没脑地打起来,直到他大声喊叫着‘我说,我说,我有金牌子。’又三天以后,全村一千多人,男女老少,每人都手拿一根棒子或皮带浩浩荡荡地把王把头拉出来就打,群众吹着号、打着鼓,高声叫着‘打元宝’、‘打汉奸’、‘给穷人报仇’的口号,从村南头一直打到操场上,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公审斗争”,⑦这个时候群众才彻底翻了身,又翻了心。
面对土改人们的心态是不同的,广大贫苦的农民群众,感到有了生存的依据,有了得到土地和财富的希望,以及有了脱离贫困和灾难的希望;而中农出现了动摇和疑虑,他们想到自己的土地会不会受到威胁;至于地主富农则会觉得震惊,他们会感到借以剥削的工具将要丧失了而负隅顽抗。东北局发现存在的问题后,在《东北日报》上发文《平分土地运动中的几个问题》,在文中详细阐释土改运动中“雇贫农路线”和“团结中农跳出圈子”等几个重要问题,并一再重申满足群众需要的重要性。后期,经过从上至下的政策指导及实际斗争中的经验总结,没有了“两面光”的思想,不存在“明分暗不分”的现象,分配的土地、房屋、牲口、粮食确实到了农民手里,土地改革才彻底取得了胜利。“据松江省五常、珠河等六县七月中旬不完全统计:起初浮物(金银、衣服、杂物)共值二百亿元,其中金子一项,即达一百零五斤之多。群众追回这笔血债之后,完全解决了生产中的粮食、牲畜等困难,安下了家底。”
上面提到的松江省五常县正是周立波和古元所在的土改重点推进的地方。古元作品《发土地证》和《烧毁旧地契》是于1947 年下半年在《东北日报》刊登出来的,东北局的发文是于1948 年年初刊登在《东北日报》上的,古元的土改作品给了东北其他地区可以借鉴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东北土改的成功,中共才掌握了广袤的农村基层,使征兵、征粮工作拥有了稳定的渠道,为后来的中共全面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东北古元是第二次参加土改,在延安时期他就参加了土改并于1943 年创作了作品《减租会》,对于土改他有一定的经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人们心态的变化,并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发土地证》和《烧毁旧地契》这两幅作品中的围观者就是他根据画面的需要构思设计的,这两幅画中围观者的不同表现了土改斗争不同阶段人们心态以及生活上的变化。他的目光始终在群众中,他不是在一旁观看,而就是群众中的一员。《烧毁旧地契》中的场景,是一个带有集体狂欢性质的庆祝仪式,也是对“翻身”带来的解放力量的盛大展示,更因村民们凝聚着的集体意识和民族认同而深刻与隽永。
古元作为一名版画战士,将延安的优良传统带到东北,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传播中共的方针政策,阐明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激起东北人民翻身解放的信心和斗志。古元以刀笔为斗争武器,始终坚持一切为群众的创作方式和艺术道路,与广大人民群众情感相融、骨肉相连,这是他作为文艺工作者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将心血付诸刀笔,创作出富有激情、战斗力的作品,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对当今社会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关寄晨(文)古元(图):《七斗王把头》,《东北日报》1947 年9 月9 日第四版。
②周立波(文)古元(图):《暴风骤雨》,《东北日报》1947 年12 月25 日。
③曹江,古安村:《刀笔激情——回望古元在东北》,《美术》。
④古元:《起枪》,《东北日报》1947 年8 月23 日第四版。
⑤古元:《烧毁旧地照》,《东北日报》1947 年7 月4日第四版。
⑥醒华:《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概况》,《群众》1948年第50 期,13-14 页。
⑦关寄晨(文)古元(图):《七斗王把头》,《东北日报》1947 年9 月9 日第四版。
⑧社论:《东北日报:平分土地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正报》1948 年第2 卷第25 期10-11 页。
⑨醒华:《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概况》,《群众》1948年第50 期,13-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