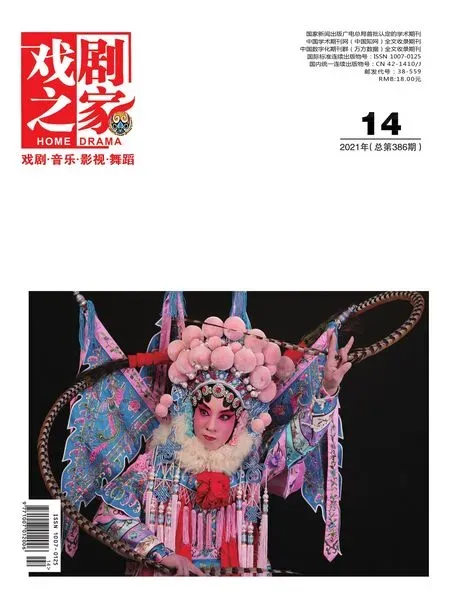论左翼电影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如何成为国歌
贾璟婕
(河南大学 音乐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一、左翼电影音乐的产生与发展
(一)电影音乐
20 世纪30 年代初,美国有声电影传入中国。1929 年开始,《百老汇歌舞》、《爵士舞王》、《纽约之光》等有声故事长篇开始在国内公映,国内民众对此颇有兴趣,于是各大影院纷纷开始更换有声电影设备。1933 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世界电影院调查统计:中国电影院已有200 余家,其中有90 家影院装配有声电影设备。1931 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公映,引起了社会轰动,并且传到了南洋一带,开启了中国有声电影的新篇章。
上海是电影音乐发展的温床,各类商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联华公司、明星公司、天一公司、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百代公司、中华歌舞专门学校、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班等,各类电影公司、唱片公司、歌舞演员培训学校应运而生。主要是因为:其一,上海的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内忧外患、战火频仍的年代,租界内生活却相对稳定。其二,上海作为中外贸易中心,不仅在物质层面上对百姓产生了影响,在精神上也促进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共融性。其三,经济的繁荣使上海充满了商机,洋人商人纷纷办起了公司、工厂。
(二)左翼电影音乐
在中国电影萌芽的初期,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1932 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唤起了民族抗日救亡的激情,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电影的传播方式来宣传鼓舞阶级斗争。香艳歌舞片和武侠神怪片不再受欢迎,百姓更多的去影院观看抗战题材的故事片。
1931 年1 月,党文艺工作小组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钱杏邨、夏衍、郑伯奇等人作为左翼作家进入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同年10 月,田汉也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进入艺华影片公司任顾问。共产党人在电影公司任职工作,开始创作左翼剧本并参与左翼电影拍摄,标志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开端。
1933 年,聂耳、任光、张曙等人在上海成立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研究苏联优秀的革命音乐,讨论与创作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1934 年,田汉与聂耳、任光、吕骥、张曙等人成立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他们有意识的参与到进步电影音乐的创作中,为进步电影音乐创作了大量抒情歌曲和群众歌曲,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喜爱与传唱。
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背景
(一)《风云儿女》电影故事
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1934 年春以夏衍同志为首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了新的左翼电影音乐阵地——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桃李劫》作为电通公司拍摄完成的第一部影片,1934 年上映后便一炮而红。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影片主题曲《毕业歌》,也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喜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广泛传播,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之一。
在《桃李劫》电影故事快要写完的时候,电通公司请求田汉创作具有革命激情的电影故事。具有娴熟创作技巧的田汉很快就完成了有十五个章节的《风云儿女》电影故事,并交给了电通公司的孙师毅。
电通公司很重视《风云儿女》这部号召青年革命抗战的电影故事,但当时田汉正忙于话剧创作,并且经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不能公开露面,于是请夏衍同志为《风云儿女》写电影文学剧本。1935 年1 月下旬,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夏衍任编剧,许幸之任导演、吴印咸任摄影,参加影片拍摄的主要演员有王美人、袁牧之、顾梦鹤、谈瑛等,这个电影制作团队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
(二)《义勇军进行曲》主题曲
田汉把《风云儿女》的电影故事交给电通公司后,突然有一天他思如涌泉想出了电影的歌词,但手边没有稿纸他只好用香烟盒子里面的衬纸写下了一段歌词,没过多久(1935年2 月19 日)田汉就被逮捕。夏衍拿到剧本后发现了里面夹着的歌词,聂耳从孙师毅那儿听说影片《风雨儿女》需要谱曲,于是他找到夏衍问起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他念了两遍歌词后,激动地对夏衍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聂耳在国内写成初稿,1935 年4 月15 日,由于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将曲谱带到日本,最后的定稿4 月下旬从日本寄回。
《风云儿女》是电通公司出品的第二部影片,产生于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背景下的一部国防电影,1935 年5 月24 日上映,剧中两个东北青年流亡到上海,梁质夫因接近革命而入狱,出狱后北上参加抗战,不幸牺牲,另一个辛白华听到好友牺牲的消息后舍弃眼前的安逸逐渐觉悟,最终走上了抗战前线。剧本的主旨是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压迫面前,从苦闷、彷徨奔向民族民主革命。
《义勇军进行曲》在电影的片头字幕出现时就响起,以激昂的情绪开头,直奔电影的抗日主题。影片的最后,辛白华参加抗日战争,他和阿凤高举着火把,与千千万万拿起武器的劳苦民众,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走上抗日救亡的战场而结束影片。这种首尾呼应的手法,让观众观看完影片后,能够在精神上感到震撼鼓舞,实现了创作这部影片的初衷。
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49 年9 月21 日-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收到应征国歌632 件,歌词694 首,9 月27 日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78 年3 月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新的国歌歌词,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由于大家对新的歌词各抒己见,产生了不同的声音,1982 年12 月4 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 年3 月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在众多应征的国歌中《义勇军进行曲》脱颖而出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影的公映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创造了条件。30 年代,日本对中国一系列惨绝人寰的侵略,以及共产党内部遭到的一系列打击,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国人需要一种使人情绪高涨,斗志昂扬的歌曲传唱来振奋人心。影片的放映,以及影片首尾两次出现的主题曲,加深了国人对《义勇军进行曲》的认识,为歌曲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第二,《义勇军进行曲》歌曲传递出坚韧不拔、无所畏惧的民族气势。歌词方面,聂耳进行了再加工,原歌词“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后经过聂耳和孙师毅的商量改成两遍重复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加上了“前进!前进!进”,经过修改后的歌词使音乐唱起来更为铿锵有力。旋律方面,采用明亮稳定的G 大调,前奏是主和弦的分解和弦伴奏音型,旋律开始用弱起的属音落在强拍的主音上,之后三遍“起来”也是主和弦的分解和弦,起于弱拍属音,并不断加强,音域越来越高,从而推向高潮。节奏方面,聂耳受《国际歌》、《马赛曲》的影响,使用了进行曲风格的四二拍,不过节奏更加明快。三连音和休止符更是用的惟妙惟肖,全曲出现了五次三连音,前奏的六个小节中就出现了三次,仿佛预示着号角已经吹响,结束句两遍完全反复的三连音,象征着沉着肯定的气势。休止符也是加强坚定不移的战斗情绪,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冒着敌人的炮火”中,“到了”、“炮火”这两处节奏的休止表现的非常坚定。
第三,在成为国歌前《义勇军进行曲》就名扬中外。
1935 年12 月9 日,北平高校上千名大学生在寒冷的冬天上街游行,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1936 年6 月7 日,在上海公共体育场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刘良模指挥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活动近千人参加。
在抗日军队中,《义勇军进行曲》是八路军和新四军高唱的战役之歌。
1938 年,110 名东南亚的归国华侨一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从新加坡返回中国参与到抗战中。
1940 年,刘良模、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与美国华侨合唱团共同在美国录制了由宋庆龄亲写序言的《起来!》唱片,并将销售唱片的收入全部捐献给中国抗日救国。
1944 年7 月,中、美、苏、英、法为首的同盟国即将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美国国务院拟定代表五大国音乐的节目单,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是唯一一首代表中国的作品,与其他国家的国歌、爱国歌曲作为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
1944 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候,抗日军队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进行改编,用西班牙语传唱,作为抗日歌曲传唱鼓舞士气。
1949 年9 月21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无党派人士徐悲鸿、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宗教界代表刘良模先后附议《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国歌。
第四,《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写照,更是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信仰。我们欣赏音乐,不仅仅欣赏音乐作品,更多是要从音乐作品的外部去欣赏理解音乐文化。《义勇军进行曲》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首获得广泛认同的精神文明产品,它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文化写照,它能够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时,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对中国民族精神文化的认同,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凯旋之歌。
四、结语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左翼电影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不仅是歌曲本身唱出了民族坚韧不拔的气势,更是其所赋予的文化象征意义,它是我国抗日救国的文化引领,我们要弘扬革命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李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