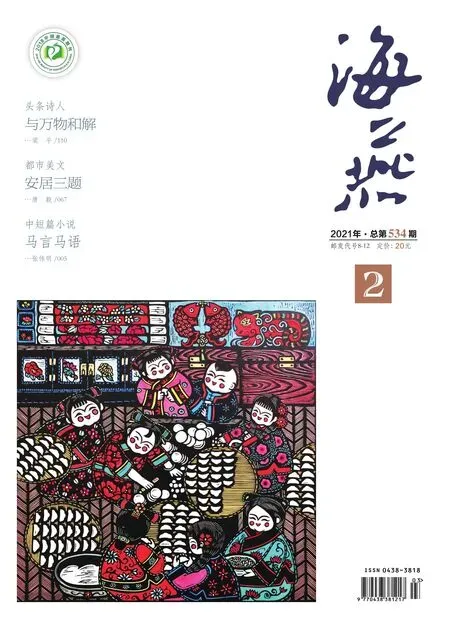戏一折
文 阎秀丽
爹的眼睛随着娘的手在移动,嘴闭得很紧,像一条线。
有风从半敞开的窗户里飘进来,吹得桌子上的书哗啦啦的响,有细细的灰尘颤颤地飘落。
娘的胳膊举得很高,却没有把端着的药碗送到爹的嘴边。娘知道,爹不轻易张嘴,但是她知道该如何让爹把药喝下去。
随着哗啦啦的响声,爹的目光从娘的手上移到书上,眼神痴痴的。
那是一本剧本,已经泛黄,上面的字也有些模模糊糊。线装的书,岁月已经在那些纸上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剧本的右下角,龙飞凤舞地写着爹的名字。
娘看了一眼爹,轻轻地叹口气,把被风翻起来的页码压平,并且把碗放在了上面,拿起一条毛巾擦拭着爹的嘴。
爹的目光也被碗压在了下面。
想唱一段?娘的声音轻得像风,但是翻不开被压着的剧本。娘说,想听你唱《秦香莲》。
爹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紧闭的嘴颤颤地张开,张得大大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声音不成调,但是却搅动着屋里的空气热闹起来,爹的眼神也似乎变得清明了些。
唱吧,我听!娘的眼睛雾蒙蒙的,她已经盛好了一匙药,快速倒进了爹的嘴里,娘同时说道,唱得真好听!你唱戏啊,谁也比不了!
爹曾是村里小剧团的团长。
那时候的爹风华正茂。过完年一进正月,他就会找几个人跑前跑后地张罗起戏来。他身兼多个职务,编剧、舞台设计、演员,有时候也兼打杂。小剧团可以缺任何一个人,但是不能缺他,缺了他,戏排练不了也演不成。
因为有了爹,小剧团办得风生水起。
爹的戏唱得也极好。他唱得最拿手的就是“黑老包”,史上最是铁面无私的清官。爹的声音粗犷豪放,音域宽广,好像就是为饰演“黑老包”而生成的。那时十里八屯的人知道有爹的戏,都早早地赶来,都喜欢听爹喊那几嗓子:升……堂……
那一嗓子,气吞山河,声震九霄。配合着“王马张赵”四校尉的堂威,随着那惊堂木“啪”的一响,直喊得让人热血沸腾。那种威慑之力让每一个看戏的人都为之精神一紧,神色也凝重了很多。
急促的锣鼓声后,丝弦之声顿起,爹唱得酣畅淋漓,观众看得如醉如痴。人们不鼓掌,以免扰了戏台上的规矩。只是眼神更加专注了些,跟着哼唱的人也多了起来,在台下形成了一股压抑着的暗流,悄然涌动。爹也唱得越发起了劲儿,声如裂帛,龙虎之音交融,行云流水,声情并茂。
娘喜欢听爹唱戏。听戏的时候,娘的眼神迷离,似乎蒙上了一层雾。娘说,爹唱戏能唱到人心里去。
后来村里有了电视,有了电脑,也有了手机。人们都窝在家里看电视,打电脑,玩手机,就是没有人再唱戏。爹跑前跑后张罗了好几天,演出那天,零零散散的几个老人,还没等唱完一场,就被一阵阵小北风刮回了家。
爹在台上唱得如醉如痴。娘抱着小孙子,在台下听得泪流满面。小孙子盯着台上的爷爷,目光星子般清澈。
娘说回家吧,没人听了,回家唱,我听!
爹说,戏一旦开始,即便台下没人,也一定要唱完,这是老祖宗的规矩!
唱完了那场戏后,爹就“封箱”了,他把所有的行头和戏服收拾起来,规规矩矩地摆放在一个大木箱里。
他的动作很慢,慢到时间好像就此凝滞,直到娘用一把大铁锁“咔哒”一声锁住了箱子。
爹有什么东西也似乎在那一瞬间被锁在了箱子里。
爹看着娘的眼睛说,人这辈子啊,就是一折子戏,喜怒哀乐啥都得经历。从拉开大幕那天开始,总会有谢幕剧终的那一天……
娘转过头去,把爹的话揉进眼泪里。
娘听爹的戏听了一辈子,直到他躺下,直到他不认识人。娘记不住那个饶舌的名字,叫什么“阿尔茨海默症”,只是说爹人老了,就变傻了。娘似乎已经习惯了爹不记得熟悉的亲人,包括她自己。
娘有时候痴痴地看着爹,叹了口气说,唱得恁好,咋就不会说话了呢?
娘翻出了爹誊写的剧本,放在他的面前。恍惚间,娘仿若看到爹的眼睛里有流光在闪动。
唱了一辈子戏,是不是也想听听戏?娘说,我给你唱,你听。
娘扶着爹靠在被子上,把桌上那本泛黄的剧本打开。
与驸马打坐开封堂上,听我把从前事细说端详……娘的声音很低,好像是从心底最幽深的地方一句句地哼出来,在娘和爹之间滚来滚去。
爹的手慢慢地抬起来,举到胸前,然后又举到颌下,手掌张开,又从腮颊处捋到身侧。
娘笑了,眼睛里却已是闪闪烁烁,说,你又没带髯口,捋什么捋!
娘继续唱着,和着爹喉咙里咕噜噜的声音。
屋里的声音渐渐轻下来,只有娘那悠长悠长的声音环绕着爹。娘把爹的身体一点点地放平,然后把剧本放在爹的枕边。
有风吹进来,把娘的声音吹得走了形,也把剧本吹得哗啦啦地翻了过去。
翻开的那页纸上,是爹当年端端正正地写的两个大字“剧终”。
娘的眼泪洇湿了那两个字。
小孙子从门外跑进来,嘴里咿咿呀呀地唱:与驸马打坐开封堂上,听我把从前事细说端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