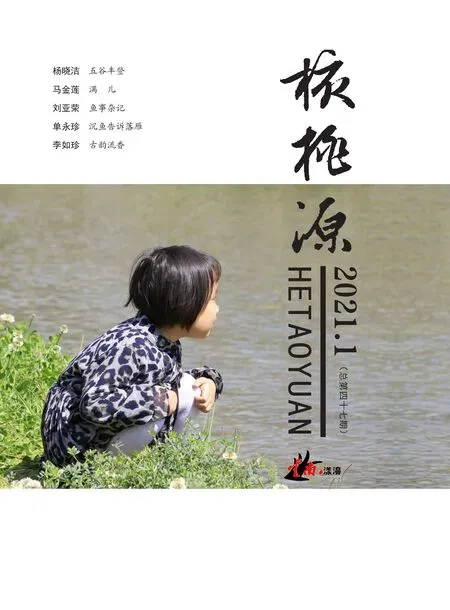隐痛的村庄
1
我指着一堆茅草说:这是瓦。祖父说这孩子是憨包。这就是瓦,我还说,祖父摇头。我抱起一捆茅草往肩上送,茅草刺穿了衣服,嵌进了我胸前的肉,我惊叫着丢下茅草。祖父被我的尖叫声吓抖了手,扭头看我时,镰刀喂在了并排捏草的手指上。一朵绽放的血红在草上铺开,夕阳在张家林场嘲笑似地看着我们。血汩汩,没有停止的意思,祖父坐在地上,抓起一把苍白的泥,揉细成灰,敷在那排手指上,血浸染着泥灰,在指尖画着一幅血光之景。蔓延。凝固。断裂。脱落。祖父手上的泥灰,在血染中呈现不同的姿态。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祖父在撒上泥灰的时候,嘴角明显地痉挛了一下,“咝”了一声并下意识地抬高手,高于心脏位置。他右手握住左手,并以指头压住血管,以此阻缓血液的上行,宛似膜拜。
顺着祖父抬高的手掌,我看到了掌后的小屋呈红黑色,好似还在燃烧,灰烬遍布。再看眼前的老人,脏兮兮的满嘴燎泡,捏着的那把镰刀刃口泛着冷冷的寒意,风卷般割着慢坡地上的茅草。祖父是一把镰刀,被生活磨薄磨亮,与泥土的磕绊中,那些原本坚硬的石头也被削瘦了不少。无家箐就是被削瘦的地域之一。昨晚,山上的小屋在一场山火中被点燃,势如破竹,待祖父从屋里跑出之时,隔壁曾方大伯家的屋顶已到处散布火光,这火犹如纵横的奔马,在风中迅速包围了祖父的小屋,来不及拿什么东西,先去赶牛,圈里的牛在火中赶不出,越打越往角落里钻。源于对烟火的恐惧,庞大的牛在火光映射下如此怯懦,祖父心急如焚。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噼噼啪啪,乒乒砰砰,一些物事消于无形,一些物事发出碎裂的闷响。注定这场灾难在风中会向另一个山头掠去的,直到小屋烧完殆尽。祖父万念俱灰,牛窝在圈里定会变成黄烤!好在一把燃烧的茅草从屋顶掉下来,落在牛后,燎疼了那群怯懦的牛,烟雾弥漫中它们终于迈出了火圈,火辣辣的疼与无边的黑暗,让这群温顺的牛勇气顿生,在山中四处奔突。
失去家园的祖父有点颓唐与失落。多年苦心营造的小屋,一夜之间只剩下光溜溜的一个自己。受惊的牛循着旧日的路径,从山中回来,大片的毛卷曲着,神情萎顿。这群牛也失去了家园。在一溜废墟中,祖父翻捡着一些没烧完的物件,铜锣锅、三脚架、水瓢、脸盆,烧掉一半的水烟筒和垮塌的塑料水桶……牛圈还冒着烟,墙角下落了一层厚厚的黑灰,翻开灰,一只只半生不熟的鸡,黑一面,白一面,挨着地面的那半还保留着它毛羽的颜色,一股股焦臭味与粪味混杂一起,熏着这片山野,熏着祖父内心涌动的怒气。曾方的父亲,那心冷似铁的“老赖宝”(村里人对他的称谓),哆嗦着瘦身板,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这无名之火。
骂也没用。祖父也鬼火冒三丈高。这是瓦,乡村的屋檐。我又一次嘟哝着。祖父吼到,瓦个屁,瓦会燃烧吗?木头才会。我想,祖父说的木头,该是在骂老赖宝,咒他怎么不被火烧死。只是,祖父的这把火烧向了我,烧向了自己,烧着了他的手掌。
这火是老赖宝点的。祖父忿忿地分析到。火头起于屋后的一片灌木地,老赖宝每次方便都习惯抽烟,烟头乱丢。那晚,他方便完就回屋睡觉,风口上的烟头先是将干燥的玉米叶子印出黑点,中心由黑变红,并呈圆圈状,不一会就出现了小火苗,并逐渐向小屋逼近。这一切,在山中没有丝毫预兆。夜静悄悄的,又旋起一阵风,火爬上了小茅屋。这个夜便热闹起来。
无眠的夜。热烈的燃烧。
无家箐的天空塌了。好在祖父还在,曾方还在,老赖宝也还在,四壁空空,一片狼藉。
2
一时间,无家箐烧房事件作为村里的一件大新闻在村中爆炸,老赖宝成了新闻聚焦点。他的“出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其一贯的冷漠与阴骘引起的猜想;二是祖母的传扬。
乡村女人在隐秘事件的传递中总独具天分。在村中,祖母见人就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述这场山火,最后总不免一句,“老赖宝这泡屎把房子都屙没了!”众人都觉得这老赖宝惹人恨,然后,在众人的安慰声中祖母长叹一气,满足地走了。祖父每天在无家箐割茅草,修竹条,砍木料,修葺小屋,我暂回下营。
在下营的这段时间,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自己开火(自己做饭),这阵风先从村中那个小庙吹出。逢初一、十五,村中的老人(以女人为主),也有一些常生病的中年女人都聚集于小庙,洒扫庭除,挂表记功德,烧香祷祝一番,每人拿些柴米油盐,拼伙吃一顿素斋,再聊一些张长李短的家常。祖母也是信徒之一,我每次去那些老人都让我在塑像前磕头,磕一个头就给我一个小糯米粑粑或是糖果,我乐此不疲地挨着磕过去便基本吃饱了。她们更多的时候是边折纸钱边扯些毫无边际的白话。
刘家奶奶说她家里吃好的都选在初一十五,专门不给她吃。王家婆婆又说她家儿媳更可恶,连油都锁在柜子里,想吃都拿不到。于是,每人都拿着自家的那本经书在那儿念着,念着念着便有人引发了灵感,他们不给吃你就自己做了吃,跟他们分锅,想吃什么做什么。过不了几天,这些庙中飘动的风与影被村中的那些儿媳妇、妯娌们捕捉,婆媳间、妯娌间的争吵比烧房事件还轰动,如火如荼之势烧开了村庄的宁静,一场有预谋的分家分灶行动便由暗到明地拉开幕来。
作为这场“灾难”的见证者,我缄默。沉默的我在庙中听到了诸多的流言,一些老人为了排遣内心的不满,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了儿媳 ;也有一些儿媳,在听信这些流言之后,便真将流言演变为实际。我无法辨别它们之间孰前孰后,谁因谁果,但它们就真实地发生在我的村庄里。在我的叙述里,杨婆无疑是突出的。她将四个儿女都叫回家来,并要求每个儿女每年给她多少粮食,每月给她几块钱,然后一个人小锅小灶煎炒着岁月,她的脾气越来越怪,婆媳间争吵不断,赡养她的大儿子渐渐心冷,母子间的亲情好似被每月的粮食所买断。
祖母也被这阵风卷入其中。祖母逝前一年,在三叔家大门旁搭建了一个小棚,烟熏火燎自得其乐。好在三叔脾气温和,米、油在屋里,随祖母高兴取用,不管怎样,这事在村中传扬开来,总不那么体面。
淋巴癌晚期。祖母在祖父70 岁生日那天,诊断书上这样判决到。在下营,我发现,很多赡养(或不赡养)老人的儿女都如我三叔一般,关注的只是老人的吃饱穿暖问题,疾病,是定要到挨不了时才会去看的。而一去看,往往都是从村一级开始,由小到大地演绎着中国的行政序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回到村中等着,一些则以另一种方式回来。魂兮归何处?魂在他乡。当然,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祖母的病逝与我的父母以及他们兄妹的疏忽大有关联。“你这个老不死的”,这句话在村里被无数的儿女挂在嘴边,而此刻,一语成谶,祖母的确不是老死的,她是病逝的。在村中,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在家里养病的那段时间里,祖母乖了很多,话很少,不再自己做饭吃了,每天由三叔和亲友们带去医院输液,然后在家养着,说是养病,其实是等死。这个等死的过程,对于祖母来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我的眼前突然又现出了祖父这一句歇斯底里的话:“我死都要抱着你的一只脚进土”,多么残忍的一句话,其中包含着多少对婶子的怨愤不得而知,但却影射出乡村老人的孤独、无奈和恐惧,我逐渐发现,在村庄里,对外很多老人都是骤然被癌症击垮的。
我在想,这些患癌老人跟老赖宝内心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击垮他们的也许是癌症本身,更多的则是孤独。是恐惧。是内心深处最软的部分。而造成老赖宝阴骘的是冷漠,亲情间的隔膜,与村人的距离感。人际之间的隔膜引起了孤独,引起了恐惧,况且这些不仅存在于村庄中,还广泛存在于家庭内部,存在于大千世界。老赖宝也是在回下营后的一个夜晚,离开了人世,哪怕到死前,他都那么执拗地不要儿女回来看他。
有时我们同情弱者,对弱者怀有恐惧,实则是惶恐自己成为其中之一。
下营这些单独开火的老人,包括我祖母在内共有二十余位,这些家庭内部,那些被曲解的亲情因为缺乏沟通、缺乏交流、经济匮乏而疏远,焦虑甚至变成了怨毒、恶语。在我的乡村,我体验到了被误解的痛,这种被人为割裂的疼痛永远存在着,在村子里活着,直到其中的人消弭依然延存着。
3
很多时候,我们居住在一些物质丰裕的世界时,往往感受不到一些真实的东西,诸如很多城市人大抵都在做着一个乌托邦的田园梦。地域与精神世界,有时是相悖的。
下营,是亲情变异与纲常正常的矛盾体。我居于其中,痛并幸福着。
4
为了给我结婚凑钱,父亲卖光了他所有的牛。此前,父亲的身份是牛贩子。
看得出父亲的不舍。那片茅草被山火点燃,戳我肉的茅草刺噼啪噼啪爆出一串串“米花”来,这是生命燃烧的必然爆裂与回馈。而父亲的牛,卖了后连钱都没揣热乎就一叠地全转递在我手上。牛贩子父亲将这点成本递我之后,他就完全失业了。
村里有很多失业的父母。村里路生与独儿分家后,一个人在死狗箐种地,那天为摘一个箐边的南瓜被瓜藤绊了一下,顺着山坡滚进箐沟,头朝下插在稀泥里,再没起来。赶丧的独儿抢进小屋,与媳妇一起翻找着他的存折、钱款,直到翻出床垫下的塑料口袋,将新旧不一的七千多钱拿到手后才去箐沟里搬路生,然后草草下葬。村人都说,死狗箐真死了条狗,路生连狗都不如。
父母的事业是养活儿女,儿女的呢?
在下营的很多巷道里,我目睹着这些活场景,一种被割裂的痛感病态似的上演着。被巷道切割的乡村很多是不完整的,乡村的巷道深处,总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隐秘,面对这些隐秘,我选择沉默。
下营村右手边第四条巷道的第三个拐角深处,垃圾阿三再没出过这门去捡垃圾。车祸是位不打招呼贸然造访的仇人,截断了她的腿,也截断了她自力更生的能力,她不得不在女儿女婿的颜面下过活。肇事者承担医疗费用后,还一次性补偿了她十八万的营养费,而这十八万换来的只是每餐的残羹冷炙,比饭菜更凉的亲情在这院落里散布着。冷暖自知,饱饿无人问津。我在一次借锄头的契机中推开过这门,接近了这位双腿残缺的老人,她神经已被恐惧和孤寂错乱,苍蝇落脸上都不再赶一下,而口中喏喏着的是“我饿……我饿!”。我饿,这近似求乞的语气从面庞的褶皱中流出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了一丝求死的欲望。她想死,我可以肯定。我第一次从一个活人的眼里看到了求死的欲望,那么强烈,那么肯定。她一定遭遇了比车祸更为无情的伤害。
断片似的影像。暗流澎湃的巷道!
据说,她临死时突然清醒了。她不再叫“我饿”,而大叫着“我的腿,我要我的脚!”手在空中乱抓着,惨然而逝,生命凄然而止。她最后的神情被钉在了这个院落的阴暗里。也许她最后的一个梦竟是噩梦,一个捡垃圾的梦。那一晚,月缺的很残,被黑暗占领得只剩一钩。后来再到她家那巷道时,我耳畔还在回响着“我饿!”的声音。那拉长的声音如这条巷道般那么深邃,那么深刻。
5
父亲的肋骨断了三根。母亲的脊柱滑脱两节。家里的水井彻底干涸。祸难像是剧情复杂的桥段,暗藏着主线连续在家中播放。
父亲的肋骨是被牛撞断的。那天,父亲将他最后的牛出手后,牵着牛往村里的屠户家送去。这是条温驯的牛,一条与父亲最为亲近的牛,膘肥体壮。在下营的巷道里,牛随父亲缓缓地走着,夕阳放大着人与牛,在那些土墙上落下些温暖的光影。村中的河流三月前就干涸了,暮色中的河谷显得黯然,一股呛人的泥尘气息被一牛一人撩起。临近屠户家,牛显得有点躁动,不安地喷着粗气,到门口时牛突然撞向父亲,猝不及防,跌撞中,父亲将牛缰绳递到了屠户手中,再从屠户手中接过钱,踉跄着脚步回到家中。这一夜,父亲毫无睡意,先是想着牛,想着想着一翻身,浑身冷汗直冒,胸口锥扎般疼,掀开内衣,胸前鼓起拳头大的一包,触摸不得。父亲强撑了一夜,鼓起的包鼓胀异常,在乡村医生明辉阿大的摸按下,接上断裂的肋骨敷上药,那一刻,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滚下,洇湿了一片土地,一排深刻的齿痕。
在父亲肋骨断裂的这段时间,下营遭遇了亘古的旱灾,整个云南大地被旱魔侵袭。菜园中那口用瓢即可舀水的井水位逐渐下降,最终干涸,村中那些自流的水井也大面积枯竭,田地大量荒芜,牲畜无精打采。只有那口老井,滋养着全村百姓。那天,母亲挑起水桶往回走的时候,腰弯下去就再也直不起来,两桶水洒在了路上,画出一大片疼痛的轮廓。“陈旧性腰椎滑脱,尾骨第3、4 节”,CT 检查报告上说。我注意到了“陈旧性”的表述,我突然间如鲠在喉。我看到了片子上母亲洁白的骨节中的间隙,在腰椎“陈旧”的这段时间里,母亲经历着怎样的苦难?一个人将疼痛演变到陈旧,注定是伟大的。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干旱的这段时间,在父亲肋骨断裂的这段时间,在母亲腰椎陈旧的这段时间,我的乡邻们,将储水的PC 桶带回来,在里面装上细沙,加上洗涤剂,在水泥路上反复滚动,刷洗干净,然后每天为我家装满了水桶。
父亲将卖牛钱交我手的时候,正是夜最深的时候。
6
无家箐祖父的小屋到这时已彻底倾塌了。对此,我杜撰了一个场景:8月13日,3:25,大风,暴雨。我曾多次写下这样的一些时间,最近一次该是去年,那本黑色笔记本的右上角有一摊墨迹。“我愿你我名字永远在一起,不管是请柬还是墓碑上!”收到这短信的地点就在长坡岭山地里,那时,我正在为祖母的墓填土。
我不可能笑,但我竟然笑了。
村里很多人都笑了。鞭炮齐鸣,一些人逝去的同时,一些新人又组建新的家庭。乡村的历史,以季节的方式递进着。很多村人,在端土为祖母填土的同时,正盘算着闹洞房的节目。这就是下营的生活!
与我有关的很多村落里,或是中国的很多村落里,在某些时间段,婚姻多么像一场闹剧,畸形的情爱发酵了,形成一些电视电影力荐的畸形情爱剧。在婚姻里,我看到了年仅15 岁的堂表妹结婚了,结婚一年不到又生下孩子,再过半年又离婚了,离婚不到半年又成家了。婚姻犹如过家家一般,据我所知,这些早熟的婚姻是没有法律认可的,生下孩子连户都没法落。但这股潮流汹涌异常。在我的身边还有着一位30 多岁的女人,嫁一位60 多的四川人,开一辆十几万的车天天外出打麻将,女儿在昆明上初中,男的在家做木匠……
村里的光棍的数量与早婚的女人成反比。我无法去根究这种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而且我发现,这种现象是普遍的,随处可见的。下营作为其中之一,在村中我看到了少年的争夺,中年的困惑,晚年的孤独,我看到了诸多外流的打工少年再没回来,我看到村中结婚彩礼的飙升,我看到一堆堆老去的父辈愁云惨淡。谁也无法阻止这些事件的发生,一场婚恋的灾难降临在村庄上空,如一团黑影,逐渐加重,藐视着这片土地。
而我,也被时光藐视着。
那晚,我在笔记本上抄录下那条短信。一摊墨迹泄露了我的心事。
7
祖父小屋垮塌的那晚,整个村庄一阵痉挛,我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