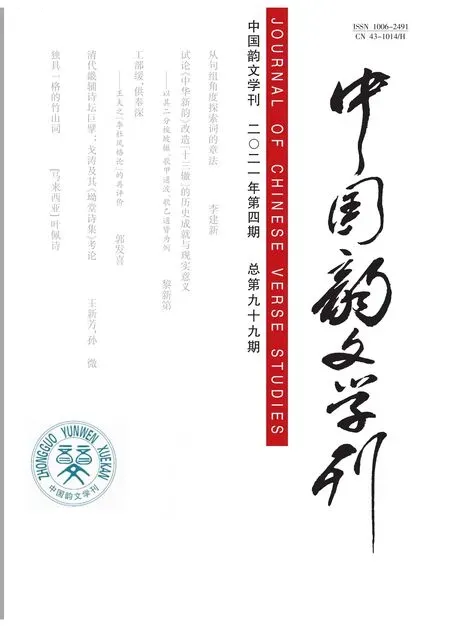词学研究的新范式
——肖鹏、王兆鹏《重返宋词现场》评介
刘荣平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建立,必在旧范式体制内积聚良久,形成新的核心要素及其力量,最终在旧范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范式。新的范式通行既久,其局限或又有显现,又为更新的范式所替代,某种意义上学术研究就是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替和拓展,有此更替拓展,学术研究才能够不断前进。
肖鹏、王兆鹏先生的《重返宋词现场》(以下简称《现场》)是一部研究词作的专著,他们主张研究词作要重回历史现场和地理现场,运用实地田野调查和数字技术全景观照等方法,对8篇名家名篇进行重新解读,研究方法细腻而新颖,得出了许多与过去研究不同的结论,卓然挺立,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从此书所取得的实绩来看,我们认为已建立崭新的词学研究范式,必将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所谓新的词学研究范式是借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实地勘查、文献考据、心理分析和文本细读相结合,力求发掘词作原意,揭示作家创作真实心态的一种研究格局。
著者为什么选取范仲淹《渔家傲》、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欧阳修《朝中措》、贺铸《青玉案》、秦观《满庭芳》、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姜夔《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淞江》进行解读?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些作品属于写实类词作,特别适合实证解读;其次是这些词作涉及的现场,都是著者往日曾经生活游历之处,历史与现实的激荡,在著者心里长期驻扎过。这也告诉我们,读万卷书同时还要行万里路。我们解读词作时在词作选目上常常感到难以下手,而著者早已烂熟于心。平日有学,写作时方能立说。
一 研究方法的创新
传统的词学研究主要是基于历史文献,对词作进行编年考证、背景分析、主旨阐释、字句注释。这虽能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提升文学素养,然而因为方法单一,许多词作名篇的研究存在着不符合创作原意的解释,甚至是较为严重的误解。要消除这些误解,仅在文本上进一步索解效果不佳,必须有方法的突破才能收到显效,而突破者通常是在学术研究中创新意识较强的人。
肖鹏与王兆鹏先生都是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培养出的词学博士,同门同届,学界并称为“唐门二鹏”。肖鹏先生在博士毕业后一度从事传媒研究,近年又回归词学研究。他将视觉艺术技巧和传媒研究的方法融入词学研究,曾出版卓越的创新性成果《宋词通史》,新天下学人耳目。他研究词学的基本方法是运用田野调查勘验的手段和现代心理学分析,还原文学创作的历史真相。《现场》一书特别重视影视拍摄专业的“机位”概念,努力寻找作品的视觉原点,可见他的传媒研究对词学研究的影响。每解读一首词作,好比要拍一部电影,在哪里拍摄、有哪些主角配角登场、历史当下的事件如何,都必须弄清楚才好拍摄。如果没有长期从事传媒工作的经验,很难想到这一点。王兆鹏先生博士毕业后一直从事词学研究,成果丰硕,为当今词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近年倡导的系地编年的年谱研究法,为历史人物事迹研究和作品编年系地研究建构了新的理念与范式;又把数字人文技术与古代文学研究相结合,已产生很大影响。唐门“二鹏”同时注意到了现场这一独特视角。地理现场的勘查,在他们看来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仍是他们的渊博学识和求索精神。
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此词语汇多有重复,100字的篇幅竟重复22字,且前后文意有不能统一之处。词的前面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后面却大写周瑜,可见没有“淘尽”;写周瑜后又说“人生如梦”,周瑜如此完美,又为何说自己“人生如梦”;词中所写历史事实多出虚构,历史上的赤壁大战发生在蒲圻赤壁,苏轼深明洞晓,他却用“人道是”黏合在黄州;词中所写“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景象,今天的黄州已不复可见,南宋的陆游、范成大实地踏勘时也没有看到。种种令人困惑的疑团,一直困扰着对此词的解读。可以说,从古至今,都没有人对此词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若无新方法新途径,只能是重复前人的见解。
著者对黄州赤壁做了实地调查和卫星定位测量,考清了黄州赤壁附近长江水道的变迁,今天黄州赤壁已离长江水道1200米之远,不再濒临长江。且长江经过黄州城时是由北向南流过,只是到了黄州临皋亭附近才改成由西向东流。苏轼谪居黄州时,多次乘一叶扁舟从临皋亭出发向北到赤壁游玩,《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他坐船北去眺望而作。著者认定词人的视觉原点应在江面的小船上,这样才符合作品的观察视角。词首句说“大江东去”,实际场景却是“大江南去”。著者认为“大江东去”的描写,“是艺术化了的风景”,由此苏轼开始词的全篇夸张虚构。他把黄州看作“故垒”,又说“乱石”“惊涛”“千堆雪”,皆状黄州赤壁风景,虽与实景不合,倒也好理解,因为诗人每多夸张之言。不好理解的是词的下片。说赤壁大战时周瑜迎娶小乔,其实小乔9年前就嫁给了周郎;说周瑜手持羽扇、头戴纶巾,“谈笑间”就灭了曹军,没有那么容易的事;而苏轼打趣说这些都是他“神游”所得,不经意间就泯灭了历史与现实的不合。他从神游中感悟的“人生如梦”,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著者细勘苏轼贬谪黄州期间所作全部作品,认为黄州期间有两个不同的苏轼,一个是写作《前赤壁赋》的苏轼,超凡脱俗,频频追问人生的真谛;一个是写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苏轼,眷怀得失,倍感人生挫败。“赋东坡”和“词东坡”见证了词人矛盾的心理状态。“词东坡”更近于真实的苏轼,他把他内心的挣扎完全呈现给读者,没有一点保留。他还紧抱着英雄梦,想建立如周瑜那样的功业。最后他举杯“酹江月”,表面看是祭奠他的偶像周瑜,事实上是在叹息时光的流逝。他已47岁,而周瑜破曹时只有34岁,他确实有些等不及了。此词尽管虚构,但真实地展现了苏轼内心的搏斗和挣扎。没有展现内心世界搏斗和挣扎的文学,不一定是感人的文学。苏轼此词很好说明了这一点。幸赖著者发掘此词的真义,我们才对此词有更深的认识。
再如范仲淹《渔家傲》词,字面没有透露出多少历史信息,初看起来不过是一首写在外征战将士思归的作品而已。著者认为此词有高度的纪实性,所以运用实地勘查和卫星定位搜索,希望找到这首词创作地点、创作时间、创作心态、创作主旨。经勘查和考索,著者确定这首词的写作地点是在庆州(今甘肃庆城县),写作时间是庆历二年(1042)秋,其时范仲淹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影响范仲淹写此词最直接的事件是宋夏之间的定川寨之战,宋军在此战中惨败。有了以上勘查发现,词中的“风景异”“四面边声”“嶂”“孤城”等描述,都能找到符合历史情景的解释。而于“燕然未勒归无计”,著者认为不是范仲淹“归无计”,而是士卒们“归无计”;而于“将军白发征夫泪”,著者认为不仅仅是指范仲淹流泪,更是指士卒们流泪。著者进而论定“庆州的范仲淹,走出了贬官耀州的低落情绪,有一种迹近圣人的献身情怀,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就是在这里形成并践行的。”此论发前人所未发。
其他六篇词作的解读,都得力于方法的改进。我们看到因方法的改进而带来许多新结论,他们的研究,已超越千年来解读词作的传统方法。这一崭新的贡献,既得力于数字技术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变革,更得力于著者上下求索的革新精神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
二 研究结论的可信
无论哪种研究,最受关注的是他的研究结论是否可采信,新的研究方法只是通向研究结论的一种手段。《现场》得出了许多新的研究结论,新结论往往更容易受到挑战。
如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一般都认为是辛弃疾江西提刑任满后,转任京西转运判官,路过赣江造口时题壁所作,抒发的是辛弃疾欲上前线抗金而不得的失意情绪,“青山”象征着阻碍抗金的势力,而抗金收复失地的力量将会冲破阻碍,如浩浩汤汤的长江东流一样不可阻挡。这样讲似乎也说得过去。然而读了《现场》一书,方知原意实非如此。
著者认为这首词“短小得不能再短小,却又复杂得不能再复杂”。他们的关注点,首先是词的写作时间。一般认为此词作于辛弃疾剿灭茶寇的淳熙二年(1175)秋天,著者则认为作于淳熙三年(1176)秋天,是辛氏接到京西转运判官任命后极度失望时所作。其次是对“书江西造口壁”的理解,一般认为“辛弃疾是先在郁孤台登临远眺,写下这首词,然后再路过造口题壁的”。这一结论与现场情景不符。站在郁孤台上眺望,既看不到深山,也听不到深山里鹧鸪的叫声。著者认为作于造口,才完全符合此词的创作实景。或曰今天造口已淹没在万安湖中,著者凭什么考察造口周边的地理环境?实际上,著者查证了历代文人笔下的造口周边环境描写,与辛氏所写完全吻合。尤其是同时代的杨万里多次描写造口的情景,与辛词吻合。再次是“中间多少行人泪”之“行人”,一般认为是指逃难的隆祐太后一行人,流泪者也指隆祐太后一行人,也有人认为指从中原南来的几十万难民。著者认为行人即辛氏自己。初看起来,难以相信“行人”是指辛氏自己,以辛氏之强悍,他怎么可能流泪?他用诱降的手段捕获茶寇800余人而一日杀之,“祸莫大于杀已降”,故在茶寇平定之后,朝廷只给了他一个从六品文官京西转运判官,虽官升一品,实际上是让他远离军队。初读《现场》时,我觉得“行人”是指辛氏自己的结论,难以置信。我甚至一度认为“行人泪”是指那些被杀的茶寇及其家属的泪。待细读《现场》后,才发现自己的理解有误。著者用辛词证辛词,断定“中间多少行人泪”的行人,是指辛弃疾自己。“行人泪”是他自己的“英雄泪”。这一点,我现在已完全认同。似还可补充苏轼的《临江仙》为佐证:“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用行人指自己,辛弃疾当然也可用行人指自己。再次是“青山遮不住”,遮不住什么?一般认为青山是反面的象征,它遮不住抗金的洪流。著者认为青山遮不住的是江水,江水无情地流逝,流去岁月光阴。辛氏作此词时已37岁,他想到还不能到前线抗金,这对于作为志士的辛弃疾来说,是多么焦虑的事情。况且他还是一个“归正人”,能不能上前线,还真不好说。这样就把词解释得非常到位。再次是“西北望长安”,曾引起过争议,有人认为应该是“东北望长安”,因为南宋都城在郁孤台和造口的东北,这就把词讲得死于句下了。著者认为,应将“长安”理解为朝廷,“这个北望的行为,是在造口驿”,“望”体现了辛氏心存魏阙的忠诚。辛氏是不想离开赣州到襄阳赴任,这一点也是著者的发明。百炼钢也只得化为绕指柔,辛氏此词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含蓄。
秦观《满庭芳》的研究结论也具典型意义。自来读此词的读者,都是把这首词当作男女艳情词来读,特别是词中“多少蓬莱旧事”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男女情事。联系到秦观40岁前风流追欢的个性,不这样想也不容易。著者经过考证,“里面提到的‘多少蓬莱旧事’,绝不是什么男女艳遇之事,而是他与文章太守和众宾客之间的风雅之事”,文章太守指越州知州程师孟。“画角声断谯门”,是说在蓬莱阁上听画角,是他难以忘怀的深刻记忆,“这个景象符号,也出现在秦观与程师孟的唱和中,而不是与歌妓的唱和中”。著者认为秦观在会稽逗留的八个月里,未见有艳遇的记载。《满庭芳》不是别妓词,而是秦观写给老太守程师孟的话别之词、感恩之词,他借用男女之间的倾慕委婉地对知州大人表示依恋和感激。苏轼对秦观“销魂当此际”句表示不满,认为他学柳七作词,秦观也表示接受批评。此中原因不是与词写男女之情相关,“关键是用男女之情来比喻和形容士大夫之情,让人觉得有点腻味”,这是苏轼批评秦观如此作词的原因。著者认为,此词或与越剧装饰性表达有关,如“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写喝酒,就有一些装饰性词语,显得舒缓。著者认为拿男女相恋和分手,来比喻朋友间的友谊和离别,确实有不妥之处。如果此词确实用越剧唱腔来唱的话,我觉得倒没有多少不合适,越剧常常由女子演出,她们着缙绅之服,女扮男装,演出各种剧情。所以说,此词中的主角是男是女不重要,如果秦观借用越剧唱腔那样的借代写法,把抒情主角设定为女性(事实上越剧唱腔都主要是女性在唱),以女性口吻写与太守的离别,倒也非常地切合。
其他六篇词作的研究结论也是可采信的。如欧阳修作《朝中措》是想告知新任扬州太守刘敞要趁着年轻享受生活;贺铸《青玉案》词写一场邂逅美女的单相思,情圣贺铸因貌丑而感到自卑,不敢大胆追求所爱;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所写是张氏面对各种打击和忧患,需要表白,自证完美;姜夔《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淞作》暴露了词人自尊自爱的心理,也折射了词人作为一介江湖谒客内心的迷茫和挣扎,他要寻求与古人陆龟蒙的结缘,至死也没能实现。这些研究结论都为往日论者所未能注意,又特别令人信服。
三 研究范式的意义
一种研究方法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范式,是因为这种范式能够得到大家认同和跟从,具有普遍的意义。研究范式既有学理上的必然性,又有实际上的可操作性,方能为人所接受。王兆鹏先生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建设”,参与者已达百人之多,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现在又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魏六朝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建设”,也说明学界对他近年研究的肯定。
先说学理上的必然性。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会一直精彩地持续着,文学作品的解读也会在读者与作者的交流中不断前进。读者冲破封闭走向开放,而封闭一直会顽强地存在着,所以冲破力须占据主导地位。文本的结构有显性与隐性之分,由显性走向隐性,是解读文学作品的必然之途,向隐性结构进军,走向胜利的曙光。词由于其“寄兴深微”的体性特征,求解之征途更为漫长,搏斗与交战总是此起彼伏,更加上作者普遍把自己的寄托以泯然无迹的方式融入词中,以求符合比兴之根本大法,词之阐释歧义将无法达成完全一致,阐释家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但在尊重基本事实上的阐释会被更多的读者、研究者所认同。过于张扬自我主观阐释而不合历史实际的解读,将会在时间长河中被淘汰。《现场》一书的学术理念,应该说与传统学术研究理念并无根本的区别,都是在追求最完美的解释,而追求的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
次说实际上的可操作性。著者熟练运用Google地球测量工具对作品现场进行地理测量,这种方法事实上简便易学,可以说今天研究者都能学会。然而由于古今地理的变迁,我们看到的现场已不是历史现场,这就需要进行古今现场的沟通与衔接。故著者每求助于地方志和诗文集,以求明了古今地理现场的变化,如仍不能沟通与衔接,著者会进行现场勘查,进一步获取信息,“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举凡历史、地理、天文、气候、历法、水文、地图等学科的知识,著者都能运用自如,于历史事实索解甚明。著者又能运用人格心理学等学科知识来分析作者的心理变化轨迹,做出恰当的评说,使人确信当时作者为什么这么写。现场勘查,今天的研究者未必都能做,这是难点所在。现场勘查并不是游历一番,拍几张照片,访问当地名胜古迹那么简单的事情。如著者索解范仲淹《渔家傲》“长烟落日孤城闭”到底是什么情景时,特意选择在深秋季节拍摄当地的落日景象。选择公历2016年7月20日下午8:00拍摄地球阴影图,公历2016年9月16日下午6:00拍摄地球阴影图,以确定落日方位。“初秋季节落日光照方向,正好与马岭河谷延伸的方向一致”,这就证明了《渔家傲》词的高度写实性。这样的研究已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显然不是简单的现场勘查。可以说,这本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只有虔诚的研究者能够沉潜其中,并熟练掌握。但此著研究方法的普遍适应性,又是不争的事实。
读者不禁要问,《现场》的研究范式,目前仅在词学研究领域取得成功,是否也适用诗歌、散文乃至一切古代文学文体作品的研究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此范式的普遍意义之一。读者又有可能要问,这8篇词作文本的差异很小,面对复杂的古代文学作品文本,这种研究范式是否适用?答案也是肯定的。笔者用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尝试研究郦道元散文名篇《三峡》,发觉完全可行,只是目前还没有写成论文。《三峡》文本的复杂性不言而喻,“从袁山松到盛弘之的《荆州记》(成书约于432—439年间),再到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古代中国作家呕心沥血,前赴后继,竟然用了上百年工夫,才成就了这一段经典在情感上的有序和语言上的成熟”。我们相信,随着《现场》一书研究范式的推广,研究者会用此书范式研究更多的有复杂内涵的古代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