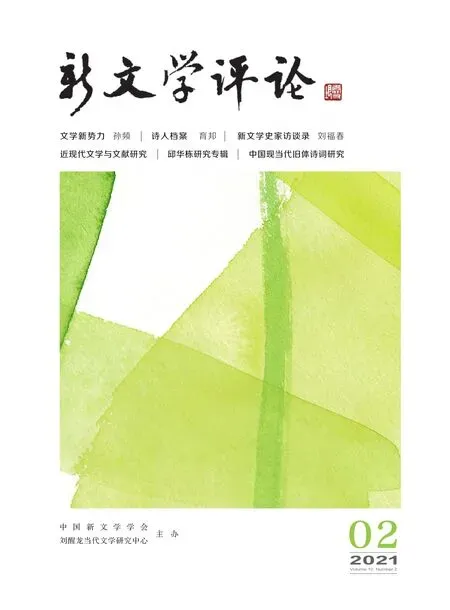地方性诗歌的生态拓展
——论哨兵诗歌的生态书写
□ 汪树东
哨兵诗歌在当代汉语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个性鲜明,辨识度较高,颇得读者和诗歌评论家的好评。关键在于,他曾长期居住于湖北洪湖,大部分诗歌都围绕着洪湖的自然方物、人世沧桑展开,自然意象密集,人生感喟深沉,语调沉郁,多采用叙事性手法,被诗歌评论家视为地方性诗歌的代表。但我们若能够从生态批评视角来审视哨兵的三部诗集《江湖志》《清水堡》和《蓑羽鹤》,我们可以看出,哨兵是极富生态意识的诗人,他对现代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忧心如焚,亲近自然,敬畏自然,渴望融入自然,体验生命的美妙境界。在诗歌《秋日札记》中,哨兵写道:“大隐隐于野。写作/ 让我过上了禽兽一样的日子。/ 在洪湖湿地。我可能是一只白鹳/ 可能是黑脸琵鹭,也有可能是五步蝮蛇,/ 是蠢獾……哦,面对自然,/ 我以人言为耻,拒绝书写、表达。”常言道大隐隐于市,但是哨兵说大隐隐于野,摆明了对城市的拒绝姿态与对乡村、大自然的热衷之情。至于他说过上了禽兽的日子,并不是道德的贬义,而是理想的呈现,是价值的生成,意味着野性、自然、生态,也意味着拒绝文明的虚伪和虚无,返本归根,与道同在。老子曾说道隐无名,大自然拒绝人言、书写和表达,哨兵要写诗,当然需要人言与表达,要代替那些受伤的自然生命发出呐喊,呼吁人们尊重自然,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地方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忧思
洪湖是全国第七大淡水湖,湖北省第一大湖泊,原为长江冲毁堤坝沉积而成,清朝初年面积最大时曾达749平方公里,20世纪50年代曾大规模围湖造田,使面积锐减至348平方公里左右,目前大致稳定于此面积。该湖动物植物种类繁多,生机勃勃,是中国生态系统保存较好、水质唯一整体达到二类标准的大型淡水湖泊,也是我国重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被誉为“湖北之肾”。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洪湖曾遭遇严峻的生态破坏,主要是周边工厂、城市大量排放生产、生活污水,大面积的围网养殖造成水体富营养化,野生动植物日益减少,大量猎杀野生动物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对于洪湖的这种生态危机,诗人哨兵非常敏感,以诗歌形式表达了他的生态忧思。他的长诗《水立方》曾这样歌咏洪湖,“水立方兮,洪湖/ 这天赐的水玉——透明 / 庄重,圆润。世界 / 炫目兮,乃诗歌 / 吾命……”。洪湖被诗人视为一块透明、圆润的水玉,使得世界炫目,促使诗歌诞生,由此可见洪湖之美。但现实中,洪湖正遭到可怕的生态侵蚀:“这块可以同时望见 / 湖中春秋的湿地,曾是众鸟和我的 / 出生地,但现在,却只是圈养者 / 与县城中年人共同开掘的鱼池—— / 重型挖泥船轰隆隆兮,渔村恍如 / 战国,已成回忆和欲望的集散地。苇根浮水 / 皎白,仿佛古楚无处安放的 / 断肠。”所谓圈养者,就是那些一度把洪湖的70%湖面用网围住的水产养殖户,而诗歌中的县城中年人应该是试图把百里洪湖改造成养殖场的投资者。对于这些人来说,无论是洪湖,还是洪湖的动植物,本来就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当它们被转换为可计数的金钱时才有价值,所以他们不会在乎洪湖的生态环境,不会在乎那些水鸟、苇草的生死。而在诗人看来,那纷飞的禽鸟,那水下草原般的水生植物,还有洪湖的原生态都具有价值,因此他才对重型挖泥船肆意挖掘洪湖感到愤慨,看到被挖出的苇根感到悲伤。
可以说,现代城市生活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功能,作为弱势的乡村几乎没有抵挡城市生活方式殖民的力量,有些时候甚至抵挡的意愿都无法生成。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涌入城市,与大自然为敌;没有涌入城市的乡村人就会像哨兵的长诗《水立方》所描绘的圈养者、县城中年人一样,主动把乡村、把洪湖及其湿地变成城市生活方式的殖民地,肆无忌惮地掠夺其自然资源,破坏其自然环境。因此《水立方》中的“申:形体渐灭”一节中就写到洪湖县城和渔村交汇地的污染问题,那里的护城河塞满了塑料垃圾袋、工厂排污暗管、小动物腐尸,“人民,早已遗弃朝饮坠露/ 夕餐落英的古楚风俗,只需 / 与小贩和糖果 / 交易,需要小甜蜜和噱头 / 自娱……”。“朝饮坠露,夕餐落英”的古楚风俗展示的是前现代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完美图景,而紊乱的现代生活却只关注生存的物质需要,不关注更为宏大的自然生态,因此显得极其丑陋鄙俗。当然,更为丑陋的,是现代人无视自然生命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例如在《水立方》的“酉:重归太初”一节中,哨兵写道:“但在茶坛 / 在世界的核心—— / 春秋代序,万物 / 不服从生物学和植物学,只服从 / 楚地的政治经济学:一纸有关土地 / 拍卖的合同,有关消亡与 / 速朽的书,如千年前的灭楚 / 密谋和盟约。而那些 / 三代世居孤岛的原住民 / 睡莲的穷亲戚 / 常候鸟,已服从 / 县城经济学—— / 偷猎中华秋沙鸭 / 烹白琵鹭 / 按世界的口味 / 厨艺,变成水禽的 / 世仇。”所谓土地拍卖,就是把洪湖及其湿地的使用权拍卖给私人老板,任由他们去开发,或建养殖场,或修度假村,只为钱财密谋。至于那些贫穷的原住民,就偷猎中华秋沙鸭、白琵鹭。中华秋沙鸭、白琵鹭都是濒危水鸟,也是国家法律保护动物,当那些洪湖原住民铤而走险,不惜触犯法律去猎杀时,他们多么利令智昏啊,多么疯狂啊!当然,这也与国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有关,大部分中国人看到像中华秋沙鸭、白琵鹭这样的水鸟,首先想到的只是如何吃掉它们,而不是欣赏它们的生命之美,保护自然生态的完整性。
消费主义社会早已经建构了不计其数的全球商品供应链,把全球各地都笼罩其中,任何地区都不能幸免。那些发达繁华的城市负责提供知识、高科技产品、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像洪湖这样的偏远之地只能负责提供水产品、农产品,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商品,加入全球化的商品流通体系中。在咄咄逼人的城市面前,洪湖自然是处于弱势地位,任人宰割的。诗人哨兵就在诗歌《在子贝渊》中就写到洪湖的悲苦地位:“趴在洪湖边的鱼行和水产品交易所/ 是我们的 / 而顺着乡村公路拐出去的 / 载重大卡,是你们的 / 拖着野鸭、桂花鱼、螃蟹、乌龟 / 和小禽兽,犹如拖着 / 我们的影子,东去武汉 / 或南下广州,再空运 / 至日本、南韩及世界各地 / 只扔下 / 渔棚 / 和我们 / 困在荒野 / 仿佛世界的垃圾 // 而那水草丛生的洪湖 / 只是一枚绿胆。你们已取走 / 这些:兽性、甜美,在子贝渊 / 在我们的苦楚中”。那一辆辆载重卡车运走了洪湖孕育出来的野鸭、桂花鱼、螃蟹和乌龟等,把那万千生灵简化为商品、消费品,再简化为交换中的货币数字,这就是消费文明的残酷!因此诗人说最终留下的鱼棚和人好像是垃圾,洪湖好像一枚绿胆,给人品尝的只有苦楚。也许那些品尝着洪湖孕育的野鸭、桂花鱼、螃蟹和乌龟的消费者,从来就不知道这些自然生灵和洪湖之间的关系。当他们大快朵颐时,洪湖就得不停地交出万千生灵,超负荷地运转,直至最终生态崩溃,偃旗息鼓。
雾霾是现代文明造成的空气污染,主要污染源来自工厂释放的烟尘、汽车排放的尾气等。像洪湖这样工业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应该没有雾霾。但是覆巢之下,没有完卵,雾霾也曾一度笼罩洪湖。这让诗人哨兵百思不得其解。他的《霾:PM2.5之诗》写道:“没谁知道霾为什么落在洪湖。但有人找到 / 新词PM2.5,替换了空气。在洪湖 / 汉语已无力表达这些:虚无,还有 / 活命的东西。多年前 / 我只是十来岁的少年郎,在湖北 / 眺望南岸,就可以望见岳阳楼 / 矮似村庙,汩罗江细如小溪 / 多年来我一直与古楚和唐宋为邻 / 住在世界的外面,见山不是山 / 看水不是水。活到现在 / 这把年纪,我怎么可能操心新词 / PM2.5 呢。而霾 / 又落在洪湖,就算我坐在岸边 / 像个少年,想把爱过的山水 / 再爱一次。但我已看不见我爱的世界 / 在哪里。在洪湖,我一直在替古人 / 担忧空气”。虽然诗人长久生活在洪湖,好像避居世外,可以和大自然、古人交往,但是他和洪湖并不能摆脱雾霾的纠缠。当雾霾笼罩一切时,诗人又该如何面对大自然呢?清洁的空气,应该是生存最基本的条件,当现代文明制造出雾霾时,这种文明就已经摧毁了人的立身之基础,那么它又有何继续存在的理由呢?若现代工业文明、消费文明不向生态文明转向,人岂不迟早会自毁前程吗?
二、野生动物的生活史和悲剧命运
除了对洪湖地方性的生态危机深表关注之外,诗人哨兵还非常关注洪湖野生动物的生活史和悲剧命运。翻开他的几部诗集,读者可以发现他的许多诗篇都是以洪湖的野生动物为题,例如《洪湖螃蟹的生活史》《水雉》《甲鱼》《鳝鱼》《蓑羽鹤》等等。哨兵早期的诗歌尚未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对其他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尚缺乏足够的体悟,但是到了《清水堡》《蓑羽鹤》两部诗集里,哨兵就已经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建立了众生平等、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能够突破物种的藩篱,让诗意的笔触在野生动物和人的命运之间自由穿行,抒发出包容万物的生态大爱。
《有关洪湖的野生动物及其他》一诗可以视为哨兵早期关于洪湖野生动物的代表性作品。从此诗看来,哨兵非常关注洪湖的野生动物,对它们的外貌形态、生活习性较为了解,例如他在诗中提到洪湖共有187种飞禽,还直接描写了中华秋沙鸭、红脚鹬、小天鹅和獐鸡,又提到洪湖共有30种兽类,以及两栖纲的大蟾蜍、爬行纲的龟鳖、鲤鱼和白鳍豚。哨兵具有难能可贵的生物学知识和精细观察的科学精神,体现了一个生态诗人的可贵素质。但是他此时尚没有颠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会不由自主地以人类的审美标准和功利标准来衡量洪湖的野生动物,例如他写道:“都是些像狗獾和河鹿样笨拙 / 丑陋的生灵。这里不出没敏捷的身影 / 尖锐的牙齿。两栖纲里唯一只有中华大蟾蜍 / 也叫癞蛤蟆,容貌酷似多年前一部电影里 / 敲钟的男主角,以麻蚊子和苍蝇为生。但 / 它的血,可疗治夜半惊哭的童年和尿床的顽疾”。说狗獾和河鹿是笨拙丑陋的生灵,明显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偏见使然,其实在大自然创造的万千生灵按照它们自身的标准来衡量肯定不会是笨拙丑陋的。至于说癞蛤蟆容貌丑陋,它的血可以治疗人类的某种疾病,无疑也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审美偏见和功利主义惯性。
当然,诗人哨兵是敏感的,随着对洪湖更深情的投入,对大自然的体悟更深刻,他很快便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阻隔,建立了众生平等、尊重自然生命的生态伦理。例如他在《接近黄昏》一诗中写到接近洪湖的黄昏在沼泽地看到两窝蛋,“白色光洁是水蛇的,麻褐色是鹌鹑的。/ 作为万千种细小的生灵,我和它们 / 站在一起,被黄昏注视了 / 整整两个小时……”。在此,作为人类的一员的“我”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和水蛇、鹌鹑一样的万千种细小的生灵中的一种,众生平等的意味自然流露。
正是建立了众生平等、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哨兵才会对各种野生动物的悲剧命运感同身受,为它们的不幸呐喊,呼唤人们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颟顸态度,尊重它们的生命和自由。他在诗歌《夜宿屈原村》中曾写到自己在秭归屈原村买下一只小麂子,把它放归山林。他还说自己并不是人性悲悯和所谓的道德优势,“我恨这一口/ 杉木笼,被小麂子噬咬 / 磨啃……在我听来 / 这种吱吱的响声,如锥 / 坚心,几乎包涵了这个世界 / 所有的不幸、绝望和哀痛……笼门 / 打开的一瞬,望着那个小家伙 / 幽灵,从面前消失 / 甚至还来不及看我一眼 / 就在山林中隐身,我真希望 / 这头幼兽,能攀上断崖、雾岚 / 和那些我根本无力去登爬的 / 绝境……”。诗人哨兵不愿意看到小麂子在死亡的恐惧中啃咬木笼子的绝望样子,他不愿意看到其他自然生命被囚禁,被死亡威胁,他希望其他自然生命也能够享受自由,因此他把小麂子放归山林,重返大自然。诗人能够把对自由的珍爱情怀扩展到像小麂子这样的自然生命身上,可见他早已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





三、处所意识与自然皈依


处所意识的第一个表现,无疑是对栖居之地的自然生态的熟悉和热爱。城市人生活在高度标准化、同质化的环境中,和大自然相隔遥远,因此根本不存在对自然生态的熟悉和热爱之问题。但是对于哨兵而言,洪湖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也是他的灵魂皈依之所,因此他经常出入洪湖,对当地的人文水文、动植物等生态情况了如指掌。在《有关洪湖的野生动物及其他》一诗中,哨兵曾说洪湖有187种禽类、30种兽类、50亿尾鲤鱼;在《对洪湖的十二种疑问》一诗中,哨兵则指出洪湖有65种底栖动物、169种浮游动物,其中原生虫44种、甲壳虫70种、轮虫55种;而在《湖中祭祀》一诗中,哨兵又指出洪湖有499种细弱生灵、428种低矮植物。对于哨兵而言,对洪湖动植物种类如数家珍,绝不是卖弄生物学知识,表达的是他对洪湖的殷殷关切之情。





四、结语


当然,哨兵诗歌的生态书写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例如人类中心主义的杂质尚未蜕尽,生态整体观尚待更为精美的建构,生态视野也需要进一步扩展。不过,我们相信,诗人哨兵肯定能够为我们贡献出更多更美好的生态诗歌。
注释:
①哨兵:《江湖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②哨兵:《清水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③哨兵:《清水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④哨兵:《清水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
⑤哨兵:《清水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⑥哨兵:《江湖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⑦哨兵:《蓑羽鹤》,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⑧哨兵:《江湖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⑨哨兵:《江湖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⑩哨兵:《清水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