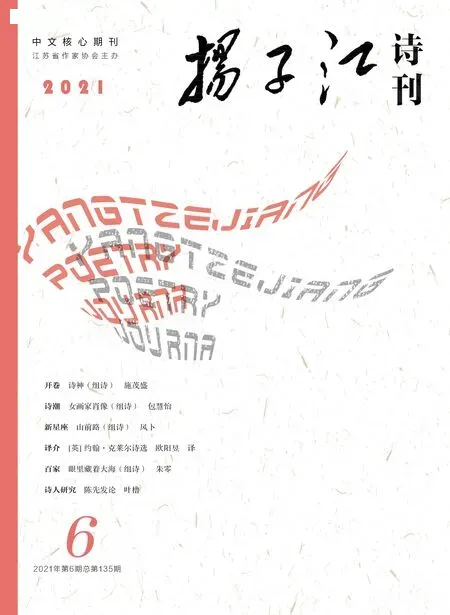为词语辩护(组诗)
周 鱼
短暂春日
四月欢快起来了。
阳光打在身上,像小雨。
某个行人像上帝一样收起黑伞。
街边一对情侣在林荫下找到对方的嘴唇。
两朵茉莉躺在冰凉的铝制座椅上,
发出微微的白马驹的鼻息。
清空练习
我抓起那些我熟悉的事物,以及
未知的事物,填满这只袋子,
这是为了什么?为了
那鼓胀的感觉?
这可真奇怪。
不扼杀一只袋子的用途,
尊重这一点,日复一日地喂养它。
但每个晚上我会再把事物一样一样
从中取出。通过变化去巩固
它的容量,也巩固
它成空的能力与本性。
写作之一种
我坐在野外餐桌前
吃鱼。
我吃鱼的肉,
不是为了吃鱼的肉,
我为了吃出它的
一根根刺,不将其
吞入我个人体内。
鱼肉,输送进
我个人,经由我单个的口腔、
味蕾,抵达我单个的胃;
鱼刺,必须从我的口中
吐出。那些分明的、比肉
强韧的、尖利的、靠近
本质的,
必须从我个人的舌上
送出。最后我吃
整条的鱼尾,
我把它整个尾部的骨头
吐出,吐出这上帝锻造的
一节流利而生僻的
非工艺品。我要将
所有它们
送返给这个野外,
埋到
土里。冰冷的土,
温暖的土。人子的
土,大地的属性。
送往人们的脚会经过的
土里,人们最后会将
自己也埋进的土里。
我将它们置于
我希望我的词语最终
能处于的地方。
灯房
灯,许多的灯,不同颜色的灯,
曾悬挂在屋顶上。后来,她陆续摘掉
红色的灯,摘掉黄色的灯,摘掉紫色的灯、绿色的灯……
蓝紫色的灯、银灰色的灯、藕荷色的灯……
最后还剩一盏灯:整个没有灯的空间是一盏暗了的、最大的灯,
她把它也摘掉——于是,
所有颜色的灯,在空间空缺的空间里,又一盏一盏地
亮了起来,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
它们看起来与之前的灯完全一样,但只有她知道
它们变了,在一种不变之中。只有她携带
这变化,携带一盏从前她也看不见的灯,一盏
微型的、沉默的、内置的灯。
一盏与外部任何颜色的灯盏都有所不同
又不会去遮盖它们的光亮的灯。
为词语辩护
伊琳娜向空白之页
道歉,她说
那些词语
破坏了
我的和你的
宁静。
可是我目睹这件事
在不可能中
屡次发生:
词语,帮衬
寂静,向寂静
提供了
一间地下室
或一条逃逸之路。
寂静,沿着
词语的指示牌,
铺开一片茂密的树林,
乘着词语的翅膀,
一步步
升往高高的
月夜。
而词语,继续留在
低低的地面,
像榕树掉落下的一颗颗
被遗忘的黑褐色的籽,在
它们裂开的言说中,
在嘈杂中,准备
护送新的寂静。
爱的真相
洋葱,
我在试图将你剥开。
一层又一层。
那么多人都
写过你。
你的复杂。
我试图也接受
你同样的诱惑。
可是一开始我警觉到
你的花招全来自笨拙的内核。
为了它,我愿意接受你
狡猾的阴谋。
我愿意沦陷在
一层层裸露出来的那个答案里。
最后的最后,你最里面的
那个东西,当最后一瓣
揭开,那里如同缺席。
但仔细看,用我整个的心
与身体去看,用我
被你辣出的眼泪去看,
用我全部的危险与毁灭去看,
我就会看到它,
就是这个,
它是那么小,那么
单纯,凝聚着,
那么美好,虚空而安静。
夜祷
睡眠松开口袋。
手向床边摸索着,像水
不断试探着岸。抓住
一张长着上帝面孔的纸。
草地上的一只瓮,
藏着一只月亮,等你循着地上的
脚印而来,往里倒进更多的水。
生命有尽期,而它永远不会被装满。
母亲
她每次出现在
我的诗里,都像
一种病。但不仅仅
是她的,原来也是我的病。
可能,每一次,是我在
执拗地寻找
自己的病源。
带着一点诧异,像在医院
替一个人取到
还散发着打印机温度
与油墨味儿的报告单,上面
却写着我的名字。
世界的街道
只要向我的窗外望去,就能望见
一条街道。竟然如此轻易,
望见一条街道,并且经由它,
望见了世界上所有的街道。
你当然会说,这怎么可能?如你所想,
在此时此刻,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
与我相隔万里的街道,有被瘟疫
占领的街道,有烤焦在炮火中的
街道,有比起我窗外这一条更加甜蜜的
被秋阳抹了一层装饰的街道。但
就像卡瓦菲斯描述的那座
由一个人在它的角落浪费生命的城市
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之于那个人而言)
我的确在此刻感觉到这条街道像一个
窗口,向我敞开了全世界的街道,
敞开了一条有意义的街道,就在我将它凝视的
一分钟里。仅仅凭借着它的那些
简单元素:孕育着芒果的
树木、走过的女人、一阵响鼻之后
安静下来的摩托车、转动不歇的灯箱
路面上切分的几何线条、角落里的白猫
依偎着大片昏暗的阴影,我发现自己
痴迷于对它的观看,仅仅因为
它让我感觉到夜晚的这个时间确实的存在
与房屋围栏之外确实的动静,仅此而已。
这一分钟里,
我想,我收到的暗示
足够了。我想,
这条街,一条简单的街道,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