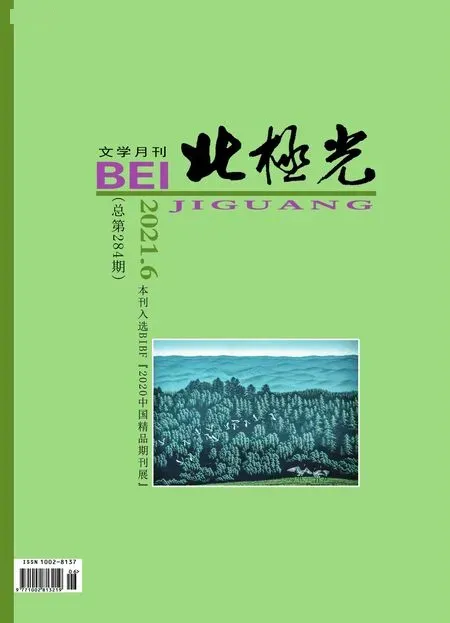春风
□蒋冬梅
小贞家院里,有一株杏树。小时候,每到杏花开放,满院的芬芳,花开时候的一些旧事,一待花开,便会浮现。
那年,家里似乎是出了事。那时还是早春,杏花还没有落。
小贞已经有些天没看见爸爸背那个黄色的军用挎包上班了。那包里装着白珠子的算盘,红皮皮的账本,蓝颜色的钢笔,还有一些叠得整齐的钱币。爸爸是个会计,好比旧社会的账户先生。无论别人怎么在车间里弯腰弓背、挨累流汗,爸爸从来都是稳稳地坐在会计室里拨算盘,记账本。无论劳力薪水的涨落,公差报销的多寡,年终奖金的加减,哪一样不在爸爸的算盘珠子底下,拨弄着,掌握着。
可是,那个晚上,小贞看见爸爸把黄挎包收拾得整整齐齐,用心擦拭了那方算盘,然后用一个丝绒的袋子套好。把平日在家做账用的几只钢笔也都找齐整,装进盒子,就连那些硬币,都从大到小分类,然后用一条条的牛皮纸卷起来。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在完成一种交代。
最后爸爸对妈妈交代,他刚一张口说出:“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可是就连这几个字,也被妈妈极力压制的哭声给掩盖住了,连同剩下的交代一齐给吓了回去。
奶奶突然来了,在小贞的记忆中,奶奶从来没有来过。妈妈和奶奶的关系不好,小贞从懂事时起,妈妈就像讲故事似的讲她们的战争。这战争和天下所有的婆媳一样,找不到真正的缘由和道理。妈妈的说法是,因为头胎生了女儿,奶奶嫌弃所以不给哄孩子。但是,有次爸爸和妈妈吵架时,爸爸说:“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女人,婆婆给你哄孩子来的,你伸着手跟人家要口粮!”妈妈就驳他:“每月眼巴巴的,粮本上就那些定量,让她把村里的粮份带来,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妈妈说的并没有错,粮食靠供应的时代,到粮店看看,人人拿着红皮粮本,数着上面的米粒,手里的白面口袋,常常只能买到一袋子底的粮食。
这次奶奶从七十里外的乡下来,穿着一件蓝涤纶上衣,露出里面白色土布衬衣发黄的领子,脚上一双褪色的黄胶鞋,从鞋上的破洞里看见奶奶脚上连双袜子都没有。小贞十岁,像所有伶俐的女孩子一样,会唠大人嗑了。尽管她和奶奶见面次数很少,可她还是抓着奶奶的手模仿大人那样问东问西,让人觉得心里热乎。最后小贞摸到奶奶藏在内衣口袋的一沓钱,奶奶哆哆嗦嗦地掏出来,给小贞和弟弟一人一毛钱买糖吃去。
更奇怪的是,姥姥也来了。姥姥是从二十里外的乡下走路来的,还背着一些鸡蛋。远远地看见姥姥迈着熟悉的八字步,刚一走进胡同口,小贞和弟弟就冲过去围住姥姥,听着有气管炎病的姥姥熟悉的气喘声,追着她问一连串的问题。
姥姥看着奶奶那双张了嘴的黄胶鞋,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知道奶奶在针线活上手拙,家里农活又多,一双鞋得做上大半年。夜里,姥姥就翻箱倒柜倒腾出妈妈的旧布头,连夜就做了一双青帮白底的家常布鞋。第二天早上,奶奶在炕上穿上,喜欢得一步就迈下了炕。姥姥吓了一跳,嗔她:“看你身量小,劲头可不小,我看,你还能帮衬帮衬他们两口子!”
半夜了,突然听见很响的敲门声。院门的门板很厚,但那响声仍然非常的响亮。爸爸起身去开门,小贞听见有马嘶叫,踏蹄,咣里咣当地走进院子。除了小贞他们两个孩子,大人们全都站到院子里去了。小贞就扒着窗子看,看见三舅舅牵着一匹红色的马,大声嚷着:“走了一千里地呢,这马后屁股戳伤了,已经烂成坏疽了,得赶快杀了!”
动物不会说话,疼痛是看不出来的。马屁股上一个血糊糊的大口子,肌肉一下一下痉挛着,可它还是照常站立,照常吃料,像是没有神经不知疼痛似的。妈妈找了块毛巾蘸上药水,想给马擦擦伤口,三舅舅老倔的声音斥责她:“老娘们啥也不懂,净瞎整。”爸爸低声劝她:“天亮去看兽医吧”。妈妈不敢对三舅舅来火,就对爸爸使性子,把手巾往爸爸身上一甩,带着哭腔唠叨个不停。
安置好了马,姥姥进屋帮着三舅舅脱鞋,那鞋已经脱不下来了。走了上千里,脚上的泡破了一茬又一茬,血水粘住鞋帮了。爸爸抱着那只脱不下鞋的脚,叫了一声三哥,就开始流泪。他哭他的三大舅哥,牵着七匹马,走了上千里路,只卖掉了六匹。现在拖着这匹受了伤卖不出去的马回来了,就算是顺利卖掉所有的马,也只不过能赚到半匹马钱。所有的希望,都在这匹受伤的马身上破灭了。
很多年以后,小贞才真正知道了那件事情的原委。那时候,正是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胆大有头脑的人,都开始想办法发家致富了。大家都在摸索着做买卖,也没个经验,也没有规范,很多人都有过赔钱的教训。那七匹马正是爸爸为了赚钱,挪用了公款,从内蒙古托人贩卖回来的。三舅舅翻山越岭地跑了无数个小村子,才卖掉了六匹马,还剩下的那匹受伤的马卖不出去了。
爸爸致富尝试第一次就那样失败了,姥姥和奶奶就是来帮助照应孩子和帮着还债的。后来,他们一说起这件事,总听见爸爸调侃妈妈说,不是怪你吗?总拿我比县长,逼得我投机倒把想赚钱!据说,妈妈从前在农村时,生产队长追她追得狠,后来那人到县上做了县长。
那天夜里,全家除了孩子,都不可能睡着。院子里那匹马打个响鼻,摇动脖子上的铃当,前蹄踏地弄出声响,小贞听见爸爸对三舅舅说:“挺欢实,能挺到天亮,天亮就送去兽医站!”
天刚蒙蒙亮,爸爸走到院子里,发现那匹马还是死了。那马就拴在杏树底下,趴在那像是睡着了,杏花落在它身上,像斑点一样好看。爸爸在杏树下呆立着,妈妈惊慌地跑来,没有主心骨的她,突然像个小孩那样大哭起来,不停地说着“你想挣钱想疯了?这个家算完了!”这话比马死了,更揪疼每个人的心。姥姥叹口气,把她拉进屋子去了。
接着家里点灯,起身,吵嚷,小贞蓬着头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匹刚咽了气的马。她的小手刚一摸到马的身体,发现它还是热乎乎的。马身体上的毛短小坚硬,很光滑的,带着草原的味道。弟弟也折腾起来,穿着后背漏洞的破背心,他稚嫩的娃娃音还在叹息着:“它还没跟咱们玩一次呢!”
妈妈一直在哭着收拾这收拾那的,却什么也收拾不好。爸爸在她的唠叨声里不停地抽烟,他尚年轻的脸上,有掩饰不住的慌张。等抽光了一盒香烟,也被妈妈骂得麻木了,他站起身,使劲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像是给自己打气似的,骑上自行车出去了。
天亮的时候,爸爸找来了屠宰工,带着一些工具,在院子里给那马抹脖放血,很快就剥下马皮,收拾肉和内脏。整个院子充斥着动物尸体的味道。爸爸已经平静下来,恢复了他干事的那种韧劲。他一平静,全家也都平静下来,三舅舅背上一些鲜红的马肉,走村串乡去卖了。姥姥架上大锅,把剩下的肉和下水烀熟了,爸爸骑着车,妈妈抱着个用白布蒙上的大盆坐在车后座上,到远一点的居民区叫卖去了。到最后拢拢账,到底还得借三百块钱才能把挪用的公款还上。
小贞看见过妈妈每月拿回来的工资条,上面是固定的数字,三十三元九毛二分,就是不吃不喝,三百块钱也得还上整整一年。那以后,妈妈的唠叨没有停,可她也拼命地攒钱还债。她省着花每一分钱,家里常用的那种瓶装的友谊雪花膏,被一种散装的便宜货取代。那种廉价的散装货,倒是有一种浓烈的香气,香气萦绕在每个人的脸上手上。每天早上小贞和弟弟的两个煎蛋也变成了一个。一个鸡蛋饼,爸爸总是用筷子从中间分均匀,然后看着两个孩子吃得馋吼吼的,就重重地叹气。
有一天,小贞和一些孩子采黑天天果吃,这是在小城路边就能找到的浆果,有个孩子说,你爸爸单位里面有大片的黑天天秧子呢,于是他们就出发去找,到了那,发现黑天天果然又大又多。小贞端着个掉了漆的搪瓷茶缸子,边采边吃,弄得手上嘴唇都染成了紫色。她从一堵豁了口的围墙看到里面有大丛的黑天天秧子,就钻了进去,那个院子里充斥着刺鼻的味道。她好奇地扒着窗子往里边看,却看到爸爸戴着黑胶皮围裙,正在一个大水池前弯腰忙活着。大水池里都是黑乎乎的水,爸爸把一只只猪头放在黑水里拔过毛后再捞出来。
小贞惊呆了,手里满满一搪瓷缸黑天天“砰”的一声掉在地上。爸爸出来了,戴着那个大黑胶皮围裙,小贞的身后站着刚刚赶上来的孩子们,他们都惊呆地张着染成紫色的嘴,露出紫色的牙齿。爸爸用被松香油泡得白胀胀的手指,抹掉了小贞脸上的泪水。爸爸挪用公款,虽然及时还上了钱,可还是被调动了岗位,分到拔毛车间。他那本该做账的手,每天拨弄着几百只猪头在黑水里搅动,泡得手指白胖胖的,像患了白癜疯。
心细的爸爸发现,妈妈那双结婚时买的,已经补了很多次的旧皮鞋后跟上,又多了补丁。
谁也不会想到,小小身量的奶奶,竟然有那么大的能耐,为了帮爸爸还上那三百块钱,她很快就把小贞的四轮童车改成了一辆卖冰棍的推车,做了一只木箱,箱子里面衬上棉垫做的保温垫,用白色的油漆粉刷了,写上两个红色的大字:冰棍。她穿上一件白色的确良大褂,拢起花白的短发,戴上一顶白色的确良帽子,推一箱冰棍沿街叫卖去了。她有一副好嗓子和一个大胆子。虽然已经五十多岁,可她的嗓子依然很脆生,喊一嗓子冰棍嘞,小半条街都听得见。奶奶叫卖很有力气,走路也很有力气,活着也仿佛有无穷的力气似的。
五分钱一根的冰棍,奶奶一天能卖上两百根,并不长的小街,她来来回回地转,不管多么深的胡同,她都要钻进去。奶奶戴的白帽子,晚上回来摘下来,都是黄黄的汗渍,妈妈怎么洗也洗不出来,有时候,她洗着洗着,就哭起来。在这样的哭泣中,他们婆媳的矛盾,慢慢就解开了。
那时候,小贞家住的平房要两家公用一个厨房。对面人家姓张,是山东人,赶大车的,一家八口人就指着男人赶大车,日子很是艰难,那家的山东女人常常趁着小贞爸妈上班后,偷偷舀他们米袋的米。小贞妈没心没肺的,总没发觉,倒是姥姥来了之后多了个心眼,扯段黑线埋到米里,然后假装出门,回来后把米挖老深,也找不到那黑线。姥姥断定每次大米都被挖去一手掌深还有余。姥姥性子急躁,妈妈怎么也拉不住她,只得任她在院子里一边筛米,一边大声嚷着:“这大耗子,都钻进人家米袋来偷啦!”
那山东女人长得人高马大,眼睛很大但并不俊,还漏神,嘴巴极大,笑起来看得见两颗银色的镶牙。她是那种外貌粗糙却极有心机的人,在偷米被发现之后,每当两家女人都在厨房做饭时,她总是手脚麻利地一边往大锅里贴玉米饼子,一边和小贞妈讲从前在山东时的饥荒。她说话时总爱哥哥妹妹地叫,以示亲近。她讲从前他们怎样苦,怎样穷,直讲到让小贞妈慨叹不已,偷米的事完全忘到脑后了。
山东女人心眼儿活,从他们的平房出了巷子口,就是电影院。日日黄昏时分,一辆辆自行车叮铃铃驶来,人声攒动等电影开演。山东女人看出门道,每天傍晚就把着那口大锅,操两把锅铲,炒一大锅葵花子或花生,像练一套拳法似的,左挥右洒的,炒熟,上筛,熟练地抖进一只垫了花布的柳条筐,然后就擦粉,梳头,倒饬完了,挎着筐出门,专挑人多热闹的地方去。那时政策刚刚放开,人们还是心存芥蒂,她并不叫卖,只是看人脸色,看准了是买货的人,她迅速地用一只白色搪瓷茶缸,装一缸瓜子,换两毛钱。她眼光很毒,只不过一袋烟的功夫,一筐瓜子就卖完了。夜里,两口子灯下将那些毛票子数清楚,那屋子里就响起低低的笑声。
很快,山东女人家漆了红色的木箱上,摆上了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前后院的人,见了面都要道一声喜。山东男人和儿子为了显摆,硬拉着小贞和弟弟过去看电视。可是每天都去,他们嫌烦又不好意思赶。有一天,两家公用厨房的煤炉上,一壶水正在轰响,小贞和弟弟出门时,就被妈妈千叮万嘱,到人家看电视要会看脸色、知深浅,可是,看着看着,突然电视黑屏,山东女人拨掉了电源插销,却骗他们说停电了,弟弟傻傻地和人家粘着,追问什么时候来电。小贞抬眼看对面自家屋内通明,气得胀红脸甩手跑出来,正看见山东女人家炉上烧着水,她生气掀下壶盖子丢到炉坑去了。
妈妈在屋子里听见对面山东女人叫嚷着找壶盖子,心里明知是小贞的歹劲上来,还不是山东女人嫌孩子日日去看电视,怕费电字。小贞妈心里酸酸的,一边唠叨日子穷苦,一边擦着那双刚从修鞋铺拿回来的旧皮鞋,她心里有气,褚红色皮鞋偏偏涂错黑色鞋油,弄到红一块,黑一块,她定睛一看,又气得直哭。
从那以后,妈妈再不许孩子过去看电视,弟弟为了人家能带着他玩耍,只好每日给那些大孩子当小支使,小跟班。比如小东说要玩跳马,可谁来当这马呢?大家一致看向弟弟。弟弟才恍然大悟,马上半弯着身体,等着那些孩子排队从他身上跨过,他们跨了一轮又一轮,总不停下来。正好小贞走过看到,上前叉着腰,挨个点着骂他们,然后,那帮孩子集体罢黜弟弟,他连小支使小跟班也没得当了。
一天清早,小贞睁开眼睛,眼见得白糊糊的一片。原来,纸糊的棚顶竟然掉了下来,低到每个人的鼻尖。爸爸起来张罗着找人帮忙吊棚,买棚纸,打浆糊,买竹条,中午的酒菜烟火,算下来,债务又加了一截。
眼看着人家一天天发起家来,自家的债台偏又越垒越高,实在逼到没了办法。爸爸又打起了做买卖的主意。有了贩马的教训,爸爸再也不想做投机买卖了,他想做一些稳当的小本生意。特别是看到对门山东家,从连大米饭都吃不上,衣服尽是捡人家的穿,到买上电视,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他越发觉得,还是稳稳当当脚踏实地好。
一个星期天早晨,小贞看见爸爸用自行车驮着一大麻袋东西回来。姥姥帮着拆开包一开,全是芹菜。姥姥低着声音问小贞妈:“你敢去卖呀?”小贞妈说,菜都批回来了,不卖咋办?就低着头挑芹菜,分扎成小捆。小贞也跟着挑,她学着大人挑出那些黄叶子,用一根黄色的稻草把芹菜捆起来。
爸爸犯着错误,不好出去叫卖,妈妈就叫小贞跟着。妈妈用长方形的筐装满芹菜,推着车子就上街了。一直走到十字街口,这个十字街口,四角分别开着旅店,饭店,包子铺,馄饨铺。每家店铺的招牌上,打头都写着国营。妈妈把菜筐放在一棵大柳树底下,刚想叫卖,就看见两个穿着税务制服的人,她就吓得躲到树背后去了。等那人走远了,妈妈又围着那筐芹菜转悠,看见走过的人,想上去拉人家过来又不好意思。这时候,小贞一急,就学着奶奶的样子,叫卖起来:“芹菜,新鲜的芹菜贱卖喽!”妈妈回头看到小贞瘦瘦的样子,自己扎起的小辫子歪扭着,一双眼睛瞪得又大又亮,她鼻子一酸,这孩子懂事了。
很快买芹菜的人就多了起来,一些嘴快的妇女七嘴八舌地说:“还是买个人的菜好,挑得干净,态度还好!”“就是呀,国营商店再不改改,怕是要黄铺子喽!”还有一些人在观望,也有人因为嫉妒在冷嘲热讽。有的说:“看着吧,哪天再来一阵风,就把这些小贩子刮进去了。”妈妈本来就有些害怕,听了这些话,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这时候,一个正在挑菜的干部模样的人对她说:“怕啥?你靠自己的力气发家致富,没什么丢人的,大大方方地干吧!”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鼓励着。妈妈觉得心里热乎乎的,等她和小贞卖完了菜回家时,小贞坐在自行车横梁上,车后座上是空空的菜筐,小贞问妈妈:“明天咱还来吗?”“来,一定要来!”妈妈用轻快的语调回答她。
天凉了,冰棍不好卖了,奶奶家里也要秋收,该赶回去了。有一天晚上,奶奶在灯下,打开一个白手巾包,里面零零碎碎的钱,数一数,一共八十块。这是奶奶五个月来,走街串巷,风吹日晒挣来的。奶奶把钱交到妈妈手里,她们都哭了,都说不出什么话来,连姥姥那么伶牙俐齿的人,都哭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中秋的时候,西瓜最好卖。爸爸每天下班回来,趁着天亮就到胡同口的大树底下,摆上一堆西瓜。走在街上,远远地就看见爸爸戴顶草帽,坐着个小马扎,前面的案板上几片切好的西瓜。一张脸晒得黑红黑红的,像个农民了。那双记账的手切起西瓜来,也是利索干脆,叫卖起来,也是张口就来,不费力气。日子渐渐好起来,小贞和弟弟每天早上,一人能吃上两个煎蛋了。弟弟上幼儿园背的零食包里,开始有了饼干、蛋糕这些从前只能在柜台前看上两眼的食物。爸爸每天起早摊黑的很辛苦,但是他也很高兴。因为,他每晚回来,都要守着一张小桌,呷几盅酒,兴致上来时,还唱上几句红灯记。小贞知道,三百块钱的债务早已还完了。
三年后的秋天,爸爸摆摊已经摆出经验来了,也有了不少主顾。人们都叫他大成子,总是能听见人们在说着,上大成子那去拿把芹菜,上大成子那去弄块熟肉,上大成子那去,上大成子那去。家里的经济,从妈妈花钱越来越敞的手,就能看出来。小贞和弟弟的零用钱由原来的一毛两毛,变成了一块两块。他们常常跑到小街上去,敢大手笔地买一条八毛钱的烤明太鱼。弟弟的玩具,不再是玻璃弹子,而是一台能上发条的小汽车了。弟弟拿着小汽车到胡同里去,那些从前欺负他的孩子,排着队等着玩那台能上发条的小汽车。
胡同对面,有一家国营的旅社。爸爸在那卖西瓜时,每天都能看见一个南方女人,领着个黄瘦的孩子进进出出的。有时候,也见到一个黑瘦的男人带着他们进出。大家都说,他们是南方人,到北方来做木材生意,结果赔了钱,现在没有了盘缠,那男人只得到医院里卖血。爸爸知道了,每次有切开卖不完的西瓜,就叫过那个孩子,给他吃,那家女人千恩万谢,爸爸总是说:“我也裁过,赔过,现在政策好,只要肯干,你们早晚能翻身!”也许,看到他们,爸爸总是能想起那匹死去的马和那些债务吧。
那一年快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开始往家置办年货。很多从前有钱也买不到的食品,不用批条子找关系,也能买到了。小贞爸爸妈妈轮流往家里搬东西,今天她搬回一条鱼,明天他带回一筐蛋。不只小贞家,大家的日子都变得好起来,每家门口都在用喷灯烤着猪头和猪蹄,那些大肉和下水在大锅里烀出诱人的香气。有一天,小贞看见妈妈拿回一个很大的草袋子,打开一看竟是满满一包苹果和桔子。弟弟拿起一个就啃,那苹果太大了,啃到一半他就饱了。这时到粮店去,每个柜台后面都好像有一座米山、面山。粮本一递进去,出粮口就能源源不断地淌出大米和白面来,小贞妈妈蒸了满满三大锅馒头,馒头出锅时开着花,像是人笑得合不拢的嘴。
小贞开始惦念着过年的礼物了。往年过年时,妈妈顶多买回两条粉色的头绳,给小贞在辫尾束起两朵花。女孩子们都蹦蹦跳跳地跑出去,比一比。可是今年,小贞想要一件新衣裳。她六岁那年,大姑来看她时,给她在百货商店买了一件粉色的娃娃服,上面有漂亮的蝴蝶结和蕾丝花边,小贞拿到手里就喜欢得不放开了。可是,爸爸算计了一下,那件衣服花了大姑六块钱,而一件普通的衣服顶多两块钱,最后,爸爸在百货商店找熟人把那件娃娃服退掉了,换了一件两块钱的花布衫,省下的四块钱,给小贞添上做了学费。这件事情过去了好几年,小贞想起来,两只眼睛还禁不住涌出委屈的泪水。
有一天,爸爸突然搬回来一个大箱子。他还拿出一个很高档的盒子,很正式地交到小贞的手中。小贞打开一看,是一件粉色的公主衣,就跟从前被爸爸换掉的那件娃娃服一模一样。小贞把它包好,站着凳子把盒子搁到很高的柜顶上了。妈妈笑着逗她说:“我闺女学会过日子啦,好东西知道留着了!”小贞低头没有说话,因为她的眼里,已经噙着泪了。
弟弟一个劲地问爸爸:“姐姐有了新衣服,我的过年礼物呢?”爸爸一掀开箱子,弟弟惊呆了,那里面是好大的一台电视机!银色的外壳,灰色的屏幕,还能抽出两根亮亮的天线。弟弟兴奋地跑过来,用双臂抱了一下,发现抱不过来。他一个劲地问小贞:“比对门山东家的大不?”小贞笑着拿眼睛白了他一下,脸上的骄傲劲已经回答他了。
到了晚上,屋子里挤满了人,来看大成子家的大电视,“以前只见过十二寸的呢,这个可真大!”“不用急,过不了一年,你家也能添一台大电视!”“是啊,现在的政策这么好,我得加油干哪!”这个电视,让大家有了信心,有了榜样,都说要像大成子那样干。
弟弟开始还兴奋地跑来跑去,可是跑着跑着,他就不见了,躺在炕的一角睡着了。夜深了,大家还盯着电视,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屏幕,画面里,春风正吹,花就要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