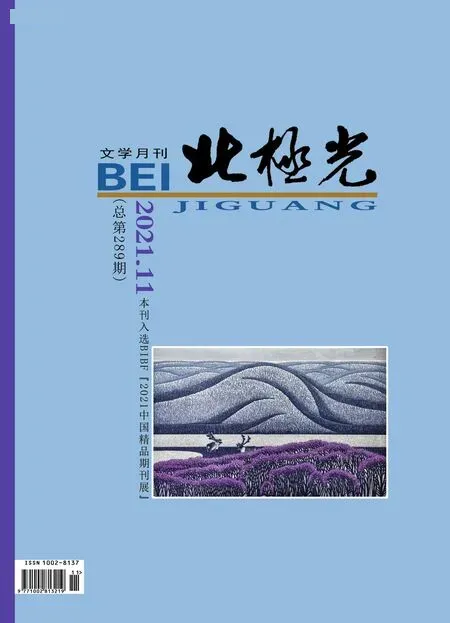乡情忆事(组章)
□陈西峰
故乡的老榆树
我老家有许多树,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老榆树。
榆树不挑地方,村边地头,房前屋后,甚至微碱地的壕沟边都长着榆树。我喜欢打麦场边的老榆树,有三棵树一字排开,连树干的弯曲弧度差不多都相同。早春时节,榆树还没有发芽,我们五六个小伙伴玩爬树比赛,或骑或坐在树干上,看远处刚返青的麦苗,看地里耕作的农人。天热的时候,巨大的树荫可以遮挡酷暑,我们在树下玩“顶针儿”游戏。
当然,我对老榆树的感情还与吃有关。春天榆钱儿长出来了,白中带黄,黄里泛绿,一串一串挂在树上,像一串一串的铜钱。从树上折下来几枝,把榆钱儿放在嘴里,一嚼儿,感觉微微的甜。有时榆钱儿长在高处的树梢上,人够不着,需要用钩子拽下来。母亲把我们采回的榆钱捋下来,在盆里洗干净,用笊篱捞出来,掺上棒子面,放上一点盐,在大锅里打烀饼。烀饼在大锅里一面成了嘎巴,一面是软软的榆钱儿棒子面,就着细细的淋上香油的咸菜丝,或者蘸上在蒜罐子中砸的烂蒜泥,或者抹上豆瓣酱就大葱,味道咸甜香脆,嘴里充满了别样的感觉,让人吃了欲罢不能。
榆钱儿没有了,叶子长出来,它的叶片很硬,叶面凹凸不平,鸟儿喜欢在树上栖息。我们悄悄地溜过去,站在树底下,拉开弹弓,用晒干的泥弹打鸟。偶尔打下来一只,会到水坑边抠出泥来做成泥团儿,把拔掉毛掏净内脏的鸟儿包在里边,放在柴火灶膛里烤,一顿饭做熟了,泥团也烧成了硬泥块,鸟就烤熟了,把泥掰下来,鸟的肉香香嫩嫩的,蘸上酱油,细细地嚼,慢慢儿地咽,味道鲜美难以描述。现在想来,真是十分罪过,但当年却是孩子们难得一尝的美味。
老榆树不知道长了多少年,人们好像也不爱惜它。有时怕马牛跑了,就把缰绳拴在树身上。榆树皮疙疙瘩瘩,沟沟壑壑,甚至像鱼鳞一样,一片一片房瓦式叠在一起,深灰色调中满是沧桑,但榆树皮却为人们提供了美食原料。把老树皮剥下来,用石磨磨成面,掺上细棒子面,就可以做饸饹擀面条了。榆树皮磨出的面很有粘性,发出一种淡淡的苦味,用它擀面条,拌上小葱鸡蛋卤,远比窝头饼子好吃得多。老榆树有顽强的生命力,人们用刀砍它,把皮剥下来了,他仍然不死,第二年又坚韧地活下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闹饥荒的岁月里,榆树不知救了老家多少人的命!
大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有一种虫子铺天盖地寄生在老榆树上,有人叫它金兰虫,据说是美国进口木材带来的,用各种农药都不管用,村里的榆树渐渐地稀少了。
场边的三棵老榆树也死了,但还在为人们奉献着。陈维恒大叔领着几个木匠把老榆树锯下来,用它作房檩,打家具。榆木属于硬杂木一类,用它做的家具,花纹像水曲柳一样,但是比水曲柳更硬,虽比不上黄花梨、紫檀木之类的“红木”名贵,但却非常坚实耐用。不怕磕碰,不怕开裂,也不怕热水烫,且价格低廉亲民,是农家人的所爱。
现在回到老家,很难见到老榆树了,但我常常怀念起它。因为老榆树倾其所有、无怨无悔地奉献着,像极了我每次返城时都捧着红枣、山芋、棒子面来送行的亲人们,像极了在老家坚守土地、默默耕种的乡亲们!
老家的除夕夜
人们常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老家在大运河的东部,与河西几个县的年俗就有些许差别,除夕夜的过法甚至是吃饺子的时段都有很大不同。
四五十年前,我们那里大多数人家过年是要上供的。老家的房子大多是“一明两暗”,中间为堂屋,两侧为卧室。堂屋北墙正中挂着红纸黑字“天地君亲师”的中堂,供桌旁边供奉着祖先匣子,上面供着祖先的牌位,上溯五代,供桌上摆放着贡品。馒头都点着红点,放在碗里边。馒头旁边还放着蛋糕、点心,以及苹果、香蕉、梨等水果,还有红烧的整条鲤鱼和一只完整的扒鸡。中间一炷粗粗的香点着了,冒着青色的烟柱,两侧又有两只燃得细细的香,整个堂屋烟雾缭绕,气氛庄严肃穆。上供的主角是家庭的男主人,他指挥着人们摆放贡品,这是家中地位的象征。堂屋的地上撒着麦秸,再铺上麻袋,人们磕头的时候不会弄脏衣服。
我们老家过年不仅是“生人”团聚,还要将已逝的先人“请”回家来,称作“请神”。年三十的下午,男主人要到祖坟地去,烧纸不多,点着了,就算请着祖先回家过年了。除夕过后一大早,人们还要以本族为单位给祖先上坟,在坟地里放鞭炮,这是一年当中放得鞭炮最多的地方,等于把昨天领回家的魂灵又安放到坟里面去,让祖先魂有所归。
我们老家大年三十包的饺子当晚是不吃的,要赶新年最早的时刻才下锅。即将到十二点时,父亲抱来了柴火,把水烧开,开始煮饺子。听到新年的钟声一响,哥哥按照父亲的指示,立刻跑到院子里,点燃早已备好的挂在晾衣绳上一挂长长的红色鞭炮,引信燃尽,噼里啪啦一阵爆响,迸碎的红纸散了一院子。
饺子煮熟了,要先放到供桌上,五个碗,五双筷子,每个碗中五个饺子,请逝去的先人们先吃,这个仪式就叫“上供”。此时,父亲会点着烧纸,祈祷祖先保佑全家平安,他虔诚地磕下头去,我们也都随着跪地磕头。讲究的人家每个屋子里也要供上一碗,有车的还要放到车上一碗,都是祈求平安之意。给诸神供过之后,人们才准备吃饺子。按照辈分的大小,大家都坐在炕上,嫂子把煮熟的饺子放在桌子上,桌子上还放着腊八蒜和酱油醋。家里岁数最大、辈分最高的老人家先吃。八九十岁的老人,半夜里本不想吃东西,但此时也要坚持吃一点。第二天早晨,人们给他拜年,第一句话总是问:“过年吃饺子了吗?吃了多少啊?”老人大声地回答:“吃啦!吃啦!吃了一大碗呢!”这就预示着老人身体健康。老人动了筷子,家中其他人才开始吃。孩子也要吃,因为这是长岁的饺子,必须得吃,而且吃掉的个数还要是自己虚岁的数字,代表又长大了一岁。
我们老家过年是要亮灯守岁的,大多数人整宿不睡。吃过饺子,才是守夜的开始,人们不再干任何家务活,或者打扑克或者玩纸牌。大年三十大门是不关的,各个屋的灯一夜都亮着,连厕所里都要点着油灯。不玩牌的人则吃花生、嗑瓜子,家庭条件好的,还会买些水果糖块。人们说着话,嗑着瓜子儿,不再干任何家务。我老家规矩中讲大年三十不干活,过年扔在地上的糖纸和干果皮都不能扫掉,因为那都是家里的“财”,不能随便扫出去的。没有踩踏痕迹的干果皮,蓬松地躺在地上,厚厚一层,也显得慵懒又悠闲,双脚踩上去发出清脆的啪啪声,便为这除夕夜增添了别样的背景音乐。此外,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一洗衣服、扫地等家务活也是不需要做的,这样对于忙碌了一年的女人们也是个解脱,可以在轻松和期盼中等着新年的来临。
我老家拜年可不只是说说“拜年的话”,必须实打实地跪地磕头。天还没有亮,四五点钟,人们便换上新衣裳开始拜年了。先给自家父母拜年,再接受辈分小或岁数小的人给自己拜年。这时候老人们是会给压岁钱的,当时给一毛两毛钱都会让孩子们欢天喜地,甚至是几分的钢镚都会珍藏在新衣服的兜里叮叮当当响着四处跑着炫耀。家里拜完年,全家的男人们会外出给村子里辈分大、岁数大的人拜年。每到一家,先在堂屋里给祖先磕头,然后再给岁数大的人磕头,整个村子几乎人人磕头。初一早饭后,本家的女人们才成群结队去拜年,而未出嫁的闺女是不需要拜年的。
老家的除夕,年年岁岁如此,已成了固定的模式,但是人们还是盼望着,虔诚热切地期待着。炕头上坐着亲亲热热的一家人,团圆幸福便如红彤彤的窗花与对联贴在每一家的窗户与大门上;大街小巷走着喜气洋洋拜年的人,欢乐祝福便如一串串的鞭炮声,这边落下那边升起。在小小村落中弥漫着的,是子子孙孙绵延不绝的平安、幸福、憧憬与希望。
赶年集
我小时候盼过年,除了有新衣服与好吃的以外,赶年集也是我非常盼望的一件事。记得大约在八九岁的时候,我随父亲去中旺赶过一次大集,从那以后,我就盼望过年。
腊月二十六赶“中旺”大集,是我们那里的习俗。中旺是天津与河北交界处的小镇,离我们村有十二华里,平时五天一个集,四面八方的人们汇聚于此,有买有卖,甚是热闹。腊月二十六是阴历年前最后一个集日,人们要采购年货置办各种物品,于是这里就成为乡下人全年最隆重的一个“集会”,尤其是要买过年的鞭炮,平日里几乎没有卖的。
记得那年腊月二十六,天儿特别好,暖暖的太阳照在身上,父亲骑着大铁驴自行车驮着我去赶集。我骑坐在后座上,母亲给我找了一个棉垫子,父亲用绳子绑好,坐上去非常舒服。母亲又给我找出一双新棉鞋穿上,赶集的热切渴望令人激动,虽是寒冬我却一点也不觉冷。
中旺大集以供销社为中心,分布在几条街上。平日里只要两条街就够了,但是今天还没进村,就发现人已堵满了街。父亲嘱咐我说:“今个儿人忒多了,跟紧了啊,千万别乱跑哇!”
集上人们可着道涌,几条街上全都是人,卖东西的在道路两边,东西在他们面前摆着,只有中间形成了人流。主干道上卖农具或者盖帘、浅子等生活用具,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只是顺着人流向前走。经过卖水萝卜的摊子,只见卖水萝卜的人在那里口吐白沫,高声嚷嚷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大夫开药方,掉在地上能摔八瓣儿,我的萝卜脆甜香,来呀,来尝一口我赛梨不辣的水萝卜!保准你想吃一筐!真甜呐!来呀,快来买呀!”水萝卜在筐子里,盖着麦秸,只有一个在外边,颜色翠绿,下面是白色的。卖萝卜的吆喝完了,用小刀剌了一小块儿:“尝尝,尝尝!来尝尝啊,不甜不要钱呐!”我不馋水萝卜吃,家中菜窖中有,我只是羡慕卖水萝卜的人竟然把萝卜吆喝得如此精彩。
我们到了另一条街上,找到卖肉的,有羊肉,也有猪肉,整条街上人头攒动,问的多买的少。到了卖猪肉的摊子前,整扇猪肉搭在板子上。卖肉的满脸横肉,挺凶的样子。他用手拍了拍白白的猪皮,啪啪地响,他也扯着嗓子高声嚷着:“现宰的!现宰的!快来买吧,过了今儿大集就得明年再吃肉了!”父亲问了问价格,听说是四毛钱一斤,踌躇了一下说:“嗯,那就给来五斤吧,多给点肥的行不?”卖肉的朗声笑着:“好嘞!”,然后麻利地拽过猪肉,照着肋扇那里划了一刀,肉成了一条,扔在秤盘子里,提起秤杆一称说:“五斤一两,算五斤吧!过年啦,大家都图个高兴!”父亲让他拿了一根麻绳,把肉拴起来,用手提着,高兴地说:“今天好啊,买了这么多肥肉,回家可以炼油了!”我知道,人们是用猪的肥肉炼出油来炒菜用,不像现在大家都嫌弃肥肉。那时候人们买肉,如果给的肥肉多,是比较开心甚至是值得炫耀的一件得意事。
接着父亲领我去买鞭炮。赶集的人把卖鞭炮的地方称为“鞭市”,“鞭市”在村边的轧麦场里,到了“鞭市”才知道什么是人山人海,这里才是年集的中心,也是年集与平时大集的不同之处。过年了,买鞭炮的人特别多,卖鞭炮的人更多。年前他们如果卖不出去,就要砸在手里一年,因此他们想尽千方百计要把鞭炮卖出去。轧麦场的四周摆满了他们的摊位。鞭炮就在地上放着,一个摊儿连着一摊儿。红色的小鞭盘成了一个大圆盘,“二踢脚”一捆一捆放着,“雷子”一个一个地放在纸盒子里。摊主互相比着放,以此来吸引买主。你放一挂小鞭儿,他放一挂大鞭儿。有人放了二踢脚,“嘣”的一声飞上了天,随后“啪!”的一声巨响,鞭纸被打碎,彩色的碎片随风飘落,人们一片叫好,买鞭的人便蜂拥而至。
父亲买了几挂小鞭,还有几包二踢脚,让摊主找了一个箱子,把买的肉放在底下,把鞭炮放在箱子里,父亲搬着箱子正要走。突然,不远处传来“轰!嘣啪!噼噼啪啪……”的声音,那是鞭炮集中炸响的声音,有人嚷:“炸市啦”!人群随即向四周跑散开去,人们一边跑却还一边回头。天上落下一些打碎的纸屑,地上冒着缕缕青烟,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气味。所谓“炸市”,就是鞭炮摊子着火了,鞭炮互相引燃,爆炸声响成一片。小鞭噼噼啪啪,二踢脚在天上脆响,二雷子炸得土屑乱飞,人们四散而逃,只见一个汉子在那里抖着双手,脖子上青筋暴露,满脸涨红,瞪大了眼睛盯着暴响声连成一片的鞭炮。父亲慨叹了一声:“唉,这个卖鞭的忒苦了,一年白闹了,赔大发了!”至今我还记得父亲的慨叹和卖鞭人涨得黑红的脸庞。
年集上卖吃食的人很多,路过时味道都那么馋人。我虽然眼馋,但我知道家里的家底儿,总是快步走过,绝不向父亲张嘴。在一个炸糕的摊子前,父亲停下来。油在锅里翻滚着,主人把面擀开,放上红豆馅儿,用手团一下,放到锅里,一会儿面团就翻滚起来,白白的小饼就变成黄黄的“小胖墩”,令人垂涎欲滴。摊主用长筷子夹出来,炸糕往下滴着油,放在铁篦子上晾着。父亲问价格,摊主回答“一毛钱一个。”父亲说:“来两个”!这可大大出乎我的意外。父亲付了钱,摊主取了两个炸糕放到一小片草纸上说:“趁热吃啊,趁热吃好吃!”父亲把炸糕递给我,我赶紧用手捧着,炸糕热热的。父亲说:“赶紧吃吧!”我右手捏住一个,有一点烫手。在家里我吃过母亲的炸油饼,也尝过母亲买来做素馅用的油条,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炸糕,我用嘴咬了一小口,脆脆的外皮里边却是粘粘软软的,瞅了一下,金黄的外皮里边却又白白的,中间的豆沙枣泥是深红的,再咬一口馅儿,太香太甜了,真是好吃,忍不住几口就吃完了。我把另一个捧举给父亲,父亲不吃。我坚持让父亲吃,父亲接过去,咬了一小口后,便递给我,说:“行了,你快吃吧!”我这才依依不舍地、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吃去了。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赶集,以至于五十多年过去了,还常常想起,尤其是在每年进腊月的时候。
老家的中秋月
我小时候最盼望的节日,除了过年就是八月十五了。
中秋节前后,是华北地区最好的季节。暑湿之气消尽,气候温凉适中。地里的庄稼开始收获了,丰收的喜悦挂在人们的脸上。白天忙得脚不沾地,到了中秋夜,农家也会过节,但他们不会吟诗作画,也很少把酒言欢,多是边干活边赏月,甚至趁着月光多干些活,劳动始终是农民生活的主旋律。
吃过晚饭,全家人在院子里一边干活一边等月亮。墙角篱笆上爬满丝瓜与扁豆,几根带棱的丝瓜从金色的花朵与肥大的叶子中间垂落下来,紫色的扁豆角与花骨朵一嘟噜一嘟噜地悬挂在高处。白天从地里掰下来的棒子轴,横七竖八地散落在院子里。黄昏时才从地里刨回的花生,新鲜饱满的壳上带着些湿润的土粒,静静地懒懒地躺在地上。这个季节很少下雨,人们放心地把收来的庄稼堆在院子里,等着明天的太阳。
月亮从东方升起来了,圆圆的,黄中带着红头,空气中充满了清凉。人们开始坐在板凳上剥棒子袍,黄白的棒子轴被月光笼罩着,像镀了一层金。一阵凉爽的微风过去,新剥出来的棒子的清香,混合着丝瓜扁豆微微的苦香,以及花生所带的泥土芬芳,便若有若无地弥散在农家的院子里。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已经十岁了,我盼着八月十五,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盼两样东西,鸭梨和月饼。我们那里出产天津鸭梨,头大尾小,青中透黄,皮薄汁多,口感脆甜,吃了润肺生津。虽说是本地特产,但如果不是节日,会过日子的人家也舍不得买来吃。我们家父母哥哥嫂子侄子还有三个姐姐,每个人能分到两三个梨。中秋夜吃梨,老家人非常有讲究,肯定不能用刀切,要洗干净用嘴啃,尤其不能两个人分吃一个梨,那寓意是“分离”,很不吉利的,只能一个人吃一整个梨,这对于平常很少吃到水果的我来说,再好不过了,可以过足了瘾。
我最渴望的还是八月十五能吃到月饼。至今我还记得那时的月饼是五仁的,紫红色,掰开来里边有甜甜的瓜子仁、核桃仁和花生仁,还有青红丝,尤其是绿色的半透明的果脯,是我们平常见不着的美味。我是全家最小的,也是父母最疼爱的,哥哥姐姐们只能分到一个,但父母总会偷偷多给我一个。
家人们一边干活,一边聊些家长里短。扯开棒子袍的“刺拉”声、撅下棒子袍的“咔嚓”声,与投到棒子堆上的“咔哒”声,伴着一家人轻轻的说笑声,在宁静的月光下,轻微但却清晰。
我慢慢啃着月饼,盯着月亮升起。抬头看看月亮,月光由最初的黄红色,变得越来越黄,越来越白,也越来越亮。父亲会指着月亮,告诉我月亮上有吴刚、有嫦娥、有月兔。月亮朦朦胧胧,我也看不清,只是低头啃着梨,再吃几口月饼,感觉那是一个安宁美好的夜晚。
月亮升到中天,院子里明晃晃一片光亮。蛐蛐的叫声低下去了,棒子袍也剥完了。父亲说:“天凉了,回屋睡觉吧”!那么自然,那么安详,那么平和。
老家的中秋月,虽无诗情画意,但照着我童年被父母疼爱的时光,照着与家人共同劳作的岁月,照着我们心中永不老去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