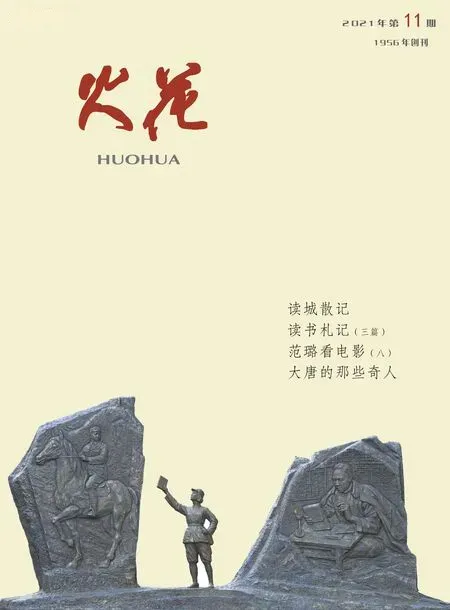读书札记(三篇)
张卫平
“暗夜深处的火光”
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他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伟大的诗人不仅呈现生命的斑斓多姿,更呈现他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生真谛的揭示。正如电影艺术大师塔可夫斯基在他的《雕刻时光》中所说,诗是一种对世界的感受,是一种看待现实的特殊方式,所以,诗是一种哲学,引领着人的一生。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能冲破直线逻辑思维的藩篱,再现生活的微妙与幽深、复杂与真谛。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能诗人是离上帝最近的人。诗人总是睁着一双探索的眼睛思考着生命不可知的未来。上帝的笑,更多的是对诗人探索未知的赞许。
阅读悦芳的诗感受最深的就是悦芳是一位让上帝不断在暗处发笑的诗人。诗人成为诗人有一种命定般的神秘力量。当一句诗击中诗人的时候,诗的种子便在她的心灵深处落地发芽。当悦芳被诗歌俘获的那一刻,她就知道诗已经成了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诗是她抒发情感、抵抗黑暗、瓦解孤独的唯一武器。诗也成了她感知世界、探索未知、思考生命的最好法门。悦芳的诗集呈现的正是她几十年走来的生命历程。诗人在早期的作品中除过咏叹时光易逝、生命短暂、孤独空虚、情爱难觅外,盘旋在诗人头脑中最多的意象是她的母亲。诗人早年丧父,是母亲柔弱的肩膀撑起了诗人少年的天空,母亲在艰难岁月中忙碌的身影成了她心底里对世界永恒的形象。当诗人长大成人后,过度消耗的母亲却永远地离她而去。怀念母亲,追忆母亲,感恩母亲就成了诗人在早期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旋律。“春天也长不出嘴唇,雨,是清明最忧伤的语言。把耳朵贴近墓碑,期待一场隔世的对话。飞舞的黑蝶,唤醒过往的岁月。”“风从对岸来,传来母亲的咳嗽声,我和月亮一起失眠。”“高原风冷漠地吹过,缤纷的梨花遍地抒情。炊烟越过村庄的笑声,只属于永不归来的岁月。”冰冷的忧伤成了悦芳早期诗歌的主色调。悦芳的成长就在于她不仅是一位多情多愁的诗人,而更在于她是一位对生命不断思考不断探索的诗人。这一时期她的诗语言干净、纯粹,思考直抵生命的本质,显示出了诗歌本就该有的力量和光芒。“是魔咒,有时又是诡计,是喧嚣的舞蹈,是长时间的寂静———它让你恐惧,又让你着迷。那虚掩的门,在等待被轻轻叩开,犹如贝克特在等待戈多。”“我是我自己的障碍,病着无法治愈的病,我活在我的无助里。我的一生,在石与花之间,清醒并沉默着。”“长久地凝视,从他人中发现我们自己。每一处黑的背后都是辗转反侧的深渊。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和深渊背后的眼睛。”“所有的镜子都是入口,在真实与荒诞之间悬挂着专横和虚无。它将所有的疑问毫不犹豫地回掷给我们,我们望着彼此,如同望着溺水的灵魂,偶尔,在一闪而过的光芒里,遇见永恒。”
这一时期悦芳的诗歌词汇里出现频率最多的词竟然是黑。如果说早期的诗歌中母亲是她难以忘却的痛,近期的诗歌里黑却成了她思考的底色。她是如此地迷恋黑,她在黑暗中思考,她睁着黑黑的眼睛在长长的黑中感受着黑的孤独、迷茫、失望。透过纷乱的现实,世界最本色的其实就是黑与白。但诗人似乎天然地就拒绝白,她信仰般地迷恋着黑,她用世界的一半来感受世界的另一半,她用黑来解读、阐释着她所感知的世界。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坐在写字台前抽了很长时间的烟,现实中的悦芳给我爽朗、简洁、明了的感觉,一点也看不出她与黑是如此地纠缠不休。“在宇宙的黑洞里种一朵透明的花。”“夜越黑,看得越清楚。神奇的光线背后,是更为神奇的黑。就像一幕真相,覆盖着另一种真相。”“暗夜行走的阳光,涉水而来,一只蝴蝶拯救了我。”“我在黑暗中闭上眼,仿佛给黑暗又关上一道门。”“裸露的肌肤是幻觉,有人在梦中说出真实。夜像一个密谋者,没有人需要为它哭泣或者命名。”“独坐黑暗中,梵高的星空在闪烁。忽又想起那个出售黑暗的人,他的名字叫铁乌鸦。黑夜比白天更栩栩如生,我不想说多余的话。”“黑,黑,黑。你在黑夜里看到了什么?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暗流涌动,你已坠落,如果没有学会用伤口飞翔,你坠入的不是深渊是地狱。而你臆想的暗夜,终将交给黎明。”“夜无休止地暗下来,细碎的牙齿深处,灵魂刮起了风。”“流动的黑,蝴蝶的翅膀、蜘蛛的纤足、豹子的花纹依稀可辨。这是属于光的陷阱。世界总比想象的要大、要哀伤。”“熄了灯,这间屋子就是整个世界。卸下面具,隐入巨大的黑暗,与过往时光中的人物对话周旋。有一种东西在悄悄逼近,像蒙克的油画《青春期》少女背后的黑影,安详平静又四伏杀机,只有走廊里的灯光依然灿烂。”这些带着黑色思考和光影的诗句在悦芳近期创作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她似乎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那把审视世界的单筒望远镜,如此的黑暗又是如此的光明,如此的简约又是如此的繁复,如此的朦胧又是如此的透彻,她只有在黑中似乎才真正明白了世界和人性的复杂含义。
诗人对黑的敏感可能更多来自她对生命最早的感知。苦难是诗人最好的催化剂。诗人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在孩子的眼里就是一座高高的山,就是孩子所有美好所有未来的天!现在天塌陷了,我们难以想象天塌陷后给孩子造成怎么样的打击,难以想象在孩子的生命中会有多长的黑和多冷的孤独。好在父亲去世后还有母亲,是母亲修补起她的天,尽管这个天不够完美,但好歹是个天,还有温暖,还有阳光,但二十多年后这个天也撒手而去了,诗人再次陷入慢慢的黑暗中。或许是在黑暗中呆得太长了,她对黑暗理解得是如此透彻和明了。“黑透了不就是光吗?”“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诗人在黑暗中渴盼的是黑暗尽头的那抹象征着未来、美好、温暖的光。正如她在诗中所吟唱:
其实我无意厘清人间的黑与白,
是冬天就应该沉睡,
生活的隐喻不需要谎言来遮蔽。
雪只是一种形式,
让秩序回归秩序,
让洁白成为洁白,
让我的身体走出这夜的黑。
“另外的生命”
我一直以为文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呈现人生或者生命的真相,揭示人生或者生命的真理,让我们的人生在无数的可能中活出最有意义的一种。就如著名作家福克纳先生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所说:人类是不朽的,这不是因为万物当中他拥有发言权,而是因为他有一个灵魂,一种同情心、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们有权力升华人类的心灵,使人类回忆起过去使他无比光荣的东西——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从而帮助人类生存下去。诗人的声音不应该仅仅成为人类历史的记录,更应该成为人类存在与胜利的支柱和栋梁。李月丽的诗集《我这样笨拙地活着》就是一部探索和感受生命真谛的诗作。
有人说诗人是离上帝最近的人。他们用自己多疑的眼睛不断打量着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企图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背后揭示出生活的真相。李月丽无疑是一个善于观察和思考的诗人,她从生活中发现生活。“以牙齿为主流的森林,虎狼高高在上。”“不再以为蠕动就是妥协,活着就得一边坚硬,一边柔软。”“去哪里都是多余的,你就是你的桃花源。当心静如水的时候,避世与隐民,安静与遗忘,就会从心里跑出来,立地成真。”“人类的互相不信任,什么时候感染了狗。”李月丽在发现生活真相的同时,思考和探求得更多的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一场花事,尽显人间枯荣。人间冷暖,一朵花足以佐证。”“该落的总会落下来,该来的白,总会如黑一样覆盖雪。”“把命交给一张白纸,让她白,让她飞,让她能去洁净地厘清一路的陷阱,黑的深度。”在李月丽的诗集中,黑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意象。其实世界就是黑白两色。正如她在诗中所说:“以一半黑一半白面世,是不是很正常。”如果黑色代表的是世界、人性阴暗的那一面的话,李月丽渴求的是纯洁、光明和那一尘不染的白。她在黑暗中思考,她也反复地打量着这个无处不在的黑。“向猫看齐,以一身白冲进黑暗,带着毁誉参半的身体,迈开猫步,走一场秀。”“黑暗在坦然中浮动,我伏在上面,跟琴声高低起伏,不知高有多高,更不知低能多低。”“黑白相咬,田地在一条线上相见,旷野放小万物,一株树、一间房、一个人,都如尘埃。”李月丽发现了黑,她也不断地和黑做着博弈。“闭上眼睛,黑暗涌来。关上心门,万事皆去。当习惯成为习惯,迷茫便不再迷茫。黑就黑吧,因为黑的就是黑的。若听陈果大教授所说,学习向黑暗妥协,那世界还有什么白?”“我的错觉来源于只相信光辉,那些黑暗的阴影与劣根,却深入骨头。”李月丽对黑暗的感悟与诗人悦芳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女诗人都在黑暗中禅悟生命的真谛。
诗人除过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外,她灵敏的触角感受的是人间的真情。她感悟生命的时候,感受最多的是孤独、黑白、尘埃、活着、彻底等等这些决绝的语词,给人一种冷硬的感觉。但诗人也是人,一样七情六欲,一样爱恨情仇。诗人的父亲去世有年,回忆父亲成了诗人的生活日常。她在写给父亲的一首诗中说,“无数次,您深夜的一声叹息,会在最静的时候突然响起,会让我突然看见您,成为我对您追忆的开始。直到今天,我接过您的长叹,长叹命运,长叹生活,长叹人生的起伏与不易。”她一次又一次地歌赞大地般慈祥的母亲,“母亲是用爱装满的河,当我们疼的时候,泪流向她,委屈给她,她会把疼收起,把甜给你。”诗人也是真性情,她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喝酒就大醉一场。女人爱哭,女诗人一样也会流眼泪,她在《我与哭》中直抒胸臆,“我会跑到无人的旷野,大张着口,我想把它放出来,让焦虑,让疼痛,让一些无奈的事情,滚出我的身体。”诗集中诗人用六七首诗叙述喝酒的酣畅淋漓,这也从另一方面看到诗人洒脱、豪放、直爽的性格。“被逼到墙角不能转身的人,都想到酒。”“嗨,再喝这最后一杯,让两抹酡红跃然夜空。把贼胆灌醉,抑或放大?”“有那么多怕吗?这辈子的风骨,就在这杯酒中沉浮。醒与不醒,都在春秋的眼睛中。”“今夜只是偶然,遇上酒,就是遇上火。”“有时候还真的该喝点酒,把憋屈的自己从酒里放出来。看看自己原来的样子,或静美,或张狂,或节制,或癫狂。”“不喝一场这样的酒,永远想象不出,酒是一把钥匙,能打开一把锁,能解放一个人。”诗人还有许多对故乡、亲人、朋友的真情表白,一样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李月丽的诗写得都非常短,这既是她的优点也是她的缺陷。优点是诗句虽短但意味隽永,她的诗受中国古典诗词影响颇深,三言五语,镜像已显,然后一转,别有况味。清代诗评家叶燮认为写诗要具备四个条件,就是胸襟、材料、匠心、文辞,有胸襟方有大境界大格局。李月丽在她的创作中已经显示出她的胸怀和气度,她的诗直抵生命的本真。但她的诗很短,有些似乎刚刚铺排便戛然而止,没有更深刻的阐述,给人一种蜻蜓点水的感觉。叶燮说,作诗还需要有好的文辞,月丽在写作中可能是凭着感觉来写,有感而发,一气呵成,但缺乏对语词的仔细打磨,有些诗句略显粗糙。
“在大地上铭刻”
在山西散文界,张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的散文最明艳的地方就是那种有硬度的语言,就像中国北方浩荡的风沙,粗粝、尖锐而又直击你的心灵。张玉生活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叫榆社的地方,太行山乱石穿空,浊漳河纵贯南北,是历史上胡汉杂处的重要之地。建立起后赵王朝的石勒就出生在这里。石勒是羯族中的一个豪杰,原是一个奴隶,在乱世中用刀剑砍杀出一个雄霸北部中国的大赵王朝。岁月悠悠,那个不可一世的大赵王国已经消失在榆社山头的蒿草里了,但那曾经的让人血脉贲张的羌笛之音却一直从南北朝流传至今。正如张玉在她的《我在榆社》里写的:“如果提到故乡,我头脑中首先出现的并不会是有关故土的种种,而是一些神秘飘渺的声音———大漠中孤单的驼铃、落日下凄婉的横笛以及月夜里一唱三叹的洞箫和城楼上横空出世的茄角——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一系列零散的画面——比如原野中奔驰的瘦马、江面上飘荡的扁舟、被雨雾打湿的单衫和客栈前暗红的灯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正是这种空寂、粗爽、简洁的生活养育了张玉散文语言中特有的风韵和气度。
最早读到张玉的散文是她的《北寨以北》。这是她早期写就的一部散文集,故乡、青春、时间和我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她目光所及的是她走也走不出去的故土,徘徊又徘徊,追寻又追寻,她在不断的叩问中企图找寻到祖先的高度和生命的深意。尽管文中充满了青春期的焦灼、反叛和不安,但文中的语言却显现出了一位优秀散文家所应当具备的那种灵性和张力。“现在这片废墟上生长着一望无际的玉米,每到夏天,玉米碧绿的叶子和油亮的红缨肆无忌惮地生长,似乎在供给废墟以生命。文化与历史在此缄默,只有我独自一人徘徊不已,感受着一份文化消亡时传递出的颓废而凄凉的美丽。我的伯父告诉我,曾经有一年,人们在城的遗址挖到一个骷髅,上面嵌有三个青铜箭簇,他认为这里曾有过激烈的战争,是一个古战场,或许是城门所在。伯父热切的目光消解了我一些不好的心境,但随之我陷入更深的空茫。我想,对这里泥土细节的关注,对这片已不复存在的城池的相信,是不是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北寨以北》)“我在恐惧和慌乱中闭上双眼咬紧牙关,于是我看到在漩涡之上还有一道碧色的桥梁。这是一道破碎的桥梁,它属于前世和来生,生与死的火焰在桥上猎猎燃烧,但我除了这里已无路可走,因为桥的彼端在宋代,那座草木葱茏的终南山。”(《似水流年》)“我不想弄得太真实,所以将时代和背景斗转星移。这其实是一个长篇的一小节,我太用力了。红衣半落,狼藉风雨,让宁碎多么狼狈。可是看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怎么样去想。宁碎的青春是错乱的青春,唯因错乱,才格外美丽跌宕。谁不曾在梦中醒来,看到无奈的枕中黄粱?”(《四季之巅》)。
张玉后来还写过一部散文集,名字叫《白羊在地》,我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如《白羊在地》《甲午笔记流光二十四拍》《青衣》《一尾名叫张玉的鱼》《蝴蝶梦中家万里》等等,与她的早期著作相比,已经褪去了青涩,语言剔除了不少杂质,对生命的探索和思考也显得深沉了许多。这部散文集是为晋军新方阵准备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列入其中,张玉倒是没有气馁,从她的北寨走出来,从她的榆社走出来,把眼量放到了更为宏大的三晋大地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行走,她用她的心把每一寸光阴细细地抚过,此后便有了这部洋洋洒洒的《表里山河经行处》。这部散文集收录了她近期创作的四十多篇作品,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展示了她对语言的天赋以及新达到的修辞高度。“多年以前我在北寨以北的土坯屋里睁着眼睛看着黑暗,想象着自己是一条硕大无朋的鱼,在荒无人烟的黄河故道溯游而上,四面激浪如箭矢击打我的鳞甲,我身下是粗粝的黄沙,河水卷着石块和浮木,我扭动身子避开它们,险滩一个接着一个,我乘着风云翔于浅底,游往龙门的方向。”(《吾王不返》)“不知何时,月亮出来了。它走得很慢,像我白天登山一样,步子沉滞。———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似乎闻到了月光的气味,一种辽远的、清而涩的植物和石块的气味。这是一种悲剧的味道。我一直以为月光之下游荡着很多悲伤的幽灵。感世伤逝的、寂寞独酌的、诀别的、相思的、孤独的——我看到月中有黑色的桂子,那也许是一千只伤心的眼睛,但是它们的泪水没法流出来。”(《千里婵娟》)“各地方言在秋天的色彩里浓重地流淌,阳光在尘埃中飞舞,像雪,像落叶,像某种意象,最终也化为河流。这些川流不息的事物,其实就是时间,我相信它是有知觉的,它在街道两侧驻足、审视,用带一点探究的眼光打量这浩大的意识流,她沉默地汇入流水一样的历史,最后流散在城墙、杨柳和古道之间,并成为它们的底色。”(《一个人的龟城》)
与前两部散文集相比,这部作品的视野更加宏阔,把审美的对象放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上来加以判断和思考,显现出不同凡响的格局和气度。王国维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开宗明义即阐明“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者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张玉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他徒步穿过狂风暴雨,她看到洪流吞噬五谷,席卷村庄,他站立于高山之巅,看到生灵涂炭的暮春三月。夜色如墨,骇浪如雪照彻天地,狂风灌满他的胸腔,芸芸众生在他脚下蠕动:那些牧人、那些农夫、那些浪子、那些过客、那些兄弟、那些情侣、那些老者、那些婴儿、那些逝者、那些活着的人,最终都在大水中挣扎———一条被鲜血滋润的、汤汤的大水。水流可载舟,亦可漂橹;水流可润物,亦可倾城。”(《吾王不返》)“我一直将石窟的艺术看成宗教审美的极致,它所涵盖的苦难、劳作、坚硬——都是神性的表达。昙曜雕刻的不是佛像,而是他所有的痛苦和悲悯、求索与追寻,是他和他的信仰存在的终极价值。昙曜已死,这些洞窟还没有凿完,鲜卑丢失在一千五百年前,流徙到这个小时代。释迦的白马趟过了云冈的落日,伎乐天是朝圣者的生门,大风深处,马蹄声碎,踏过典故的落花,你将半生的血刻在墙上。”(《一生低首拜云冈》)“走回客栈时,月亮躺在湫水中睡着了,而小镇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拉三弦的老人咿呀地唱着:九曲黄河十八弯,宁夏起身到潼关。万里风光谁第一,还数碛口金银山。百年前的碛口曾经商贸两旺:上千艘木船自北方的河套顺流而下,它们遮天蔽日的帆影在湫水上穿梭。从陕甘宁和内蒙运来的药材、皮毛、盐碱经此地转运至祁太平和晋阳,而东路的布匹、丝绸、茶叶和洋货则沿河北上。那时候口内的市场卖的东西大多叫碛口货,它们成就了一代晋商的汇通天下。我耳边仿佛响着数十年或数百年前人们搬运货物的声音和骡马的叫声,码头上是灯笼和火把,历史在黑暗中明亮起来。”(《一生的百渡在碛口》)
文学作品呈现的是生活或人性的真相,探索的是人或人类生命的真谛。《表里山河经行处》既是行走的散文,更是对历史、文化、生命的追索和思考。她是在行走,更是在寻找,既寻找历史,更是寻找那个灵魂深处的自己。这是一次灵与肉、物与禅、精神和山水的碰撞与交融。宋代禅宗青原行思大师在谈到禅修的三个境界时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张玉写的是山水,其实更多的是她自己。“我在这个夜晚,以及很多个这样的行走在表里山河的夜晚,都遵循着不变的规律,先是混沌的黑暗,然后是清冷的夜晚,之后是大寂寞的月亮,然后是我自己,最后我站在这空旷的光明孤独的峰巅,望着自己的灵魂。”“大风刮过来,月色暗下去,比我的头发还长的云脚一层一层漫上来。我不动,也不说话,对于一个孤独地行走在山河的女人,最美的遇见就是一夕成环的月亮。它这样圆,这样白,这样亮,这样遗世独立在山岗上。这时世界无言,大风过耳,众生沉睡,唯我独醒———我很清醒,从未有过的清醒,在珏山,多少泪水,多少红尘,一轮月,它是自己的情人。”(《千里婵娟》)“我似乎也成了崔莺莺,我抚琴看月,在枕席、竹荫、西厢的晚风中观摩自己的过去,年少轻狂的过去。属于爱情的一切已经过去,初恋不再,贞操不再,孤勇不再,而时间不离左右,我只能这样活着,活在对天真的痛惜,对生存的焦虑,对自由的绝望,对生命的无可奈何之中。只有这些建筑和遗迹,与时间同样永恒。它们陪着我,在心底最幽暗的角落,最柔软最不堪一击的地方,像戴着铜指套的手反复弹拨着那根琴弦。恍惚之间,我再次为贞元十六年那些刻骨铭心的夜晚泪流满面。”(《二十年来晓寺情》)“黑夜此起彼伏,月光不胜酒力。我咳嗽起来,有一个音符在我心里跳,但是我的嗓子哑了,我张了张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的回头路消失在灯光里。”(《牧童遥指杏花村》)“我年少的心事早已失落在十五年前的北寨以北,而人近中年的辽远情意,则步步惊心地穿行在此刻的风陵渡,这荒芜的浑浊的暗黄的不舍昼夜的水,这夹着水汽掺着砂砾没头没脑的风,而离我尚远的迟暮情怀,也突然在此地降临,借助阳光我看到一生的过往。”(《天涯思君不可忘》)
是版面的原因,还是资料的不足,有些篇章刚刚铺就,却急急收尾,似有言犹未尽之意,略感遗憾。但瑕不掩瑜,这仍不失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散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