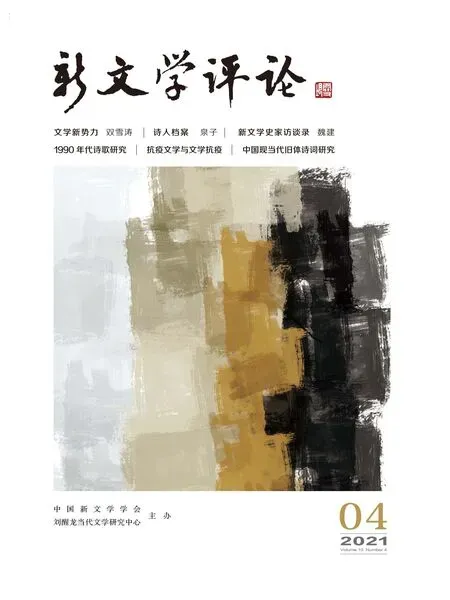以文字凿泉筑栈道通往诗意起伏的饱满
□ 张 悦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
从《空无的蜜》中将“青山的徒劳”作为首集之名,到以“青山从未如此饱满”为整部诗集命名,青山的形象在泉子先生诗歌景观中进一步得以凸显,愈加醒目。其形式上构成鲜明反差的两类诗作,在诗集中的排布也相应发生了一定变化。铺叙为主的长诗,在《空无的蜜》中集聚于第四辑“巨石”,而《青山从未如此饱满》这部诗集中,则是将铺叙为主的长诗与精短如偈子、俳句的短诗分散编排,更见起伏之势。两类诗作参差错落,展开泉子宏阔中包藏幽微的诗境,其全貌仿若一幅融合“白宾虹”疏淡清逸和“黑宾虹”黑密厚重的山水长卷,吸引流连赏读的目光。其立于诗思,回应空无,深蕴道和真理,自人世复苏的诗境山水,是对当下都市现实生存及精神家园山水式微的一种弥补。青山饱满、烟岚起伏的诗意胜境,令人驻足、沉浸,召唤着探访和凝思。
耿占春在《退藏于密》一书中讲道:“山,一个包罗万象的对象,一个像宇宙一样空无的对象—— 一座山——它最能挑战一个写作者的野心。”泉子诗中的青山,作为一种动静相宜的存在,相较于生命之有限触发的强烈情感动荡,显现出本质的静默,历时性维度同共时性维度相交织的“永无止境”(《消息》)。青山,以其无限静默,铭刻智园、林逋间的“诗词唱和”,“不曾忘却”千年以来甚或更古远的“风流人世”(《风流人世》),成为人类历史、文化乃至文明源流的见证者。青山,以其“缓缓地奔流”,映衬“一池的残荷、静静的湖水”所隐喻的因死别而充斥衰颓,却依旧恒常运转并未倾覆的人世(《我曾经不敢想象》)。青山“那仿若静止的奔腾”,似乎为诗人标注了“道与真理”尚且难即“更远的远方”(《远方》),就像诗的不可言说,就像本源的空无,终极的归宿。诗人笔下的青山,时而至刚至锋利,可用以“雕琢出/人世从未显现过的永恒”(《陈子昂》),时而至柔至清澈,可用来“洗心”,“获得大地至深处的澄澈、蔚蓝/与深情”(《洗心》)。青山掩映之下,不变中的多变,共存相倚的动静,变幻且兼济的刚柔,正是泉子对其趋向饱满的诗学、美学追求陌生化、张力化的表达。
“生生灭灭”被泉子视为“无穷无尽的天堑与断崖”,同时又是“通往道与真理的/无数的栈道或通衢”(《生生灭灭》),断裂中恰藏有前行的种种可能。诗思驱遣文字运动生成峻拔险峰,同样需凭借文字修筑的栈道涉险取路,而或隐或显、晦明交替的栈道所能抵达的景致,因读者的期待视野、接受体验甚至心性而异。泉子则坚守着以其颇具辨识度的文字,为读者凿崖架道的勤勉。《三十年后》一诗中,倒叙、插叙结合,将两个同学少年时的纯真情谊置于别后三十年间一方波折不断的人生经历之中,福祸相依、喜忧相伴,无常对有限的推搡间,一个偏远山村寒门子弟的命途多舛在细致、真实的笔触下展现。似乎当命运每次向“你”投射来光时,总会留下捉弄的阴影,甚至深渊般的阴暗,来自学业、职业、婚姻、双亲、子嗣各方面的打击,让“我”再次遇见的却是“并不沮丧”的“你”,“笑容始终挂在你的脸上”。而读者沿着诗人以文字铺设以诗行推进的情节拾级而上,行走在明暗交错的诱惑中,不乏迂回曲折,也难免惊心。唏嘘无常,感叹跌宕,心生怜悯,认同源于底层磨砺的坚忍,对跨越阶层的无奈感同身受,有感于情感纠葛的复杂、脆弱和难测,或是思考城市化进程对乡土家园的冲击,对亲情纽带的撕扯等。读者行至中途,领略到的已不是平视视角下的人世风光,而是诗的语言耸起的群峰层峦在云雾开合间起伏的多重可能与诗意。
《完美的形象》一诗中写道:“所有完美的形象一定是阴性的。”而《活着》《我们几乎同时听到了她的死讯》《他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豆腐西施》等长诗,则是以不同方式将女性“完美”的毁灭呈现给读者,流露出诗人对女性生存的关切和悲悯。无论是饱受重病、婚变折磨,致使“一条与痛苦感知相关的神经彻底断绝”而获得“一种几乎凝固的微笑”的女同事,屡遭“豆腐西施”一家欺凌并直接、间接引发了一系列家庭不幸,落下间歇性精神失常的“志才妈妈”,还是精明世故、口若悬河、颇具风情、自私强势的“豆腐西施”等形象,均于细节的真实中突显某种存在之悲。将家族性精神疾病埋下的祸根给家庭成员带来的苦痛和隐忧,集中在两代女性的不幸和彼此冲突,以及第三代女性身上潜藏的危机当中,或许亦是撕碎“完美”的有意为之。所谓“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离世,死讯竟是在“数月之后”的喜宴上传来,“一个悲伤者/那爆破般爽朗的笑声”究竟指向何种程度的悲戚,读者也许莫衷一是,而“她的美丽与风情万种”,愈加强化“完美”破碎的悲感。“诗的破坏力不是为了抵抗语言哑默的禁锢,而是从废墟堆中寻找一种可能的唤醒和重建”(朱涛《耳语的天空》)。此处,所谓“破坏力”并非语言本身制造的碎裂、毁灭,而是提炼于真实的悲剧,然而,同样不乏“唤醒和重建”的意义。一条条抵达存在之悲的栈道,汇合于凝视女性生存的观景台,同时,也成为凝望“人世之柔弱”,搜寻并呼唤“伟大的至善”的瞭望台。
在泉子看来,作为“完美的形象”化身的母亲,是“所有的芬芳与甘甜”“源源不绝”的赠予者,而与母亲分离之悲,又是人生必经的艰难一课(《哀歌》)。第五辑“哀歌”中,《睡佛》《去年这时》《悬崖般的一刻》《黄道吉日》《生命中最为低落的时辰》《我曾经不敢想象》《瞬间》等诗作,以及长达21节的压轴长诗《哀歌》,以更多朝不同方向蜿蜒曲折的栈道,通往与亡母对话,倾诉深挚哀痛与深切悼念的孤绝之顶。母亲睡佛般“安然”的姿态,未能缓和丧母之痛骤然降临的沉重打击,“一段多日来难得的轻松/而为喜悦注满的时辰”,蓦地显现出茫然无措的“悬崖般的一刻”。回忆中母亲总是笑容满面的,接受这慈祥笑容仅能停留于脑海的现实异常艰难,即便“从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穴中/艰难地爬了出来”,与母亲之间相隔的“由这思念得以赋形/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深渊”,始终难以逾越。《哀歌》中的诗节大多在“我”对母亲的诉说中展开,送别、安葬母亲的幕幕场景切换,浸透哀痛的真实细节催人泪下。遇猫、观荷的情景,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字里行间涌动的深情留恋,以及对母亲“依然和我在一起”的“坚信”成为这首诗感人至深的落脚点。久久凝视母亲亡故的阴云,“人世的局限与荒凉”再次注入诗人泉眼般的明眸,“人世至深处千古不易的绝望与深情”不堪悲哀凝集的重负,如雨而至。以二者明目、洗心,诗人从节哀顺变中感受到“一种悟道求真的力”,拥抱“因追随自然/而终于重获的/绵延不绝的人世”。
“人世”,是泉子诗歌中常见的高频词语,他认为“语言或者说诗在根本处是人,/或者说,人世有着怎样的美与善,/诗才能企及怎样的真与圆满”(《人世有着怎样的美与善》)。而这立足于人世的美与善,对“真与圆满”之诗的追求,伴随着“惶惑/与不得安宁”(《不得安宁》),甚至“终其一生的徒劳”(《银针》)。诗自“空无”“缓缓浮现的悄无声息,/而又永无止境”,有赖于凝视。诗人在对诗歌丛林的凝视中辨识自我,“是这片密密的丛林帮我找到了今日之泉子”(《经文》),将“诗的艰难”理解为“一个人毅然决然去成为自己时,/那一次次独自认领下的欢喜与绝望”(《诗的艰难》)。从对“那张古人与来者共有的面容”的凝视和辨识中邂逅知音(《游陈子昂读书台——兼赠胡亮》),遇见“那个不断醒来的自己”(《知音》);通过对“每一朵花,每一粒草,/每一颗露珠”,对“我们头顶的满天繁星”的诗意凝视,同故去的亲人相见(《妈妈离开我已整整半年》);通过对“光秃的树枝与嶙峋的山石”的深沉凝视,与“大地深处生生不息的力”重逢(《并非繁华落尽》)。
江南被泉子视作“孜孜于日常生活中的神性的温柔敦厚之地”(《温柔敦厚之地》),其环西湖而行的日课,则孜孜于对这种神性的发现。宝石山褶皱间的保俶塔、抱朴道院,西泠桥、孤山、白堤、断桥,凋零的荷花,飞上天空的野鸭,车窗前低低盘旋的大雁,新荷间穿梭游弋的鱼,公交车上的见闻,苏堤拱桥上的偶遇……诗人从“自然而然”之间提取人世“饱满而富足”的诗意(《没有》)。苏堤拱桥上苍老、孱弱的一对夫妇“急促的呼吸声/让我再一次看见了/拱桥那不易察觉的起伏”(《苏堤》),诗人敞开自我,感受到拱桥回视并回应生命、生息的起伏—— 一种神性的起伏。野鸭飞翔升空,“用翅膀搬运着远山”,以及“越来越远”的“人世”(《越来越远》),诗人或许是以视窗的后退,以疏离促成了对“人世”渐进的“所见”,并得以领悟野鸭飞翔的神性之美。
相较于“打捞起”“车水马龙的人世”(《一个车水马龙的人世》),获得“一览无余的人世”(《一览无余的城市》),诗人“更期待千年之后的读者”从诗行间“辨认出”“我”“繁华落尽的脸庞”(《一张繁华落尽的脸庞——赠王敏杰》)。希望自己能像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开初唐诗歌革新风气,在诗歌理论发展史上产生划时代意义的陈子昂,“因对风骨与兴寄的标举”,“雕琢出/人世从未显现过的永恒”(《陈子昂》)。畅想自己成为甚至超越王维、杜甫、李白、陈子昂,“从宇宙的子宫中,/再一次捧出”“整个盛唐”那般“伟大的人世”(《我还可能是谁》)。这陌生化的宏大的分娩,衬托出温厚江南傲立的诗坛巨人形象,及其催生一个时代的惊人伟力。这位不愿“辜负语言与万物深处的道或空无/透过如此纷繁的人世完成的,/对一位诗人的拣选与辨认”(《汉语的辨认》),为“汉语之未来”而忧心忡忡的诗人(《汉语之未来》),所选择的是“人迹罕至”的道路(《并非对无的执着》),“认领”的是被世代“弃绝”,饱经苦难成就圣贤、智者的道路(《命运》),坚持走“一条歧路”,“甚至是一条相反的道路”,直至“为这人世重新开掘出了/一条伟大的通衢”(《伟大的通衢》)。这样的写作之路,这“与曾经的知音不断地告别”,“而终于得以与最初的自己重逢的/道阻且长”(《道阻且长——致雷平阳》),在《烟云深处的道路》一诗中被隐喻为“一条烟云深处若隐若现的道路”,其间“仿佛不可逾越的天堑与山峰”之艰险,亦可凭着跋涉的脚步丈量,成为“回望中的山峦起伏”的盛景。
泉子将行走作为日课,让“心”一次次从“目光所及处”“汩汩而出”(《日课》),读者行走在其精短的诗歌之间,如从一眼清泉抵达另一眼清泉,经历一次又一次“洗心”之旅。借诗人对世界、宇宙,往昔、未来,永恒、绝境,诗、汉语,日常生活、伟大作品,道、真理、空无,张力、愤怒、死亡,阴与阳,爱与恨,美与善,温暖与慰藉,羁绊与束缚等等的明澈洞察,读者可照见围拢于自我周遭人世的饱满,诗意的无限可能。《秋天再往深处一点》中写道:“树叶再落下一些,/秋天再往深处一点,这里就不再有/一个你的藏身之地了。”“你”,可以是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可以是某种情绪、情感,可以是特定的审美体验,也可以是理念,及与之相关的哲思等。其诗意指向呈现出跨越具体与抽象,自我与他者,自然与文学、艺术边界的开放性。不同的读者,可自其中捧掬洗濯、唤醒己心的清澄。“在一场大雪过去很久之后,/只有沿湖亭台的屋瓦/依然是白色的”,诗人以这样的情境类比“第一次从经文中/品尝到甘醇的薄暮”(《在一场大雪过去很久之后》),而读者亦可从不同角度领略屋瓦留雪的隐喻和意境之美。无论源自文学熏陶、艺术渐染,还是道德教化、灵魂澡雪,任何能在心檐上久留莹白,进而内化,对修养、人格的持续净化,均配得上这“甘醇”回味。读者可持心灵容器,从中任取一盏清冽,自品甘甜。
泉子的雄心与抱负,坚守和孤绝,其所崇尚的“饱满的力”(《不是干枯》),“饱满的寂静”充蓄的张力(《张力》),所盛赞的“饱满的心”(《在岁末》),彼此连通成为庞大暗河。那藏于山岩、泉涌深处的激流,给读者以感召,亦将“真正的澄澈与通透”归还给“幽暗与寂静”(《真正的澄澈与通透》),归还给每位读者。奥克塔奥维·帕斯认为,“每一次阅读都产生一首不同的诗,没有一次阅读是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每次阅读,包括作者本人的阅读,都是文本的意外”,“文本只有通过这些变化才能实现自己”。(《弓与琴》)谙熟中国古典绘画艺术的泉子,善于节制笔墨,在诗境中营造类于写意山水的留白效果。其适时而止却又蕴含丰富生成性的精短诗句,向宏阔延展的诸多可能性,对一字一句发力的拿捏,显见凿泉者效法造化的智慧,深得写意山水造境的神韵。充分的想象空间,可令读者在反复品读中收获多种意外体验,具有酝酿于变化之中生成性的饱满,整体上显示出“此处无物胜有物”的启发意义与审美价值。
杜甫、屈原、陶渊明,之所以成为他们,在于“那颗为空无与人世之悲欢所穿凿的心”(《当我广为人知》)。读者可以从诗行间辨识出的泉子,怀有执着于汉语未来的忧心和壮志,“雕琢”永恒的追求和深情,“在对心灵的持续倾听与追随中”饮下“空无的蜜”(《空无的蜜》),用丰盈一颗圆融之心的诗思,咀嚼“人世之悲欢”。其诗歌中截然不同的两种典型风格,并峙而互补,共绘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画境。他以文字凿泉、筑栈道,将读者引入连绵青山起伏的诗意和饱满,引向救赎的无限可能,引向“汉声汉韵”回归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