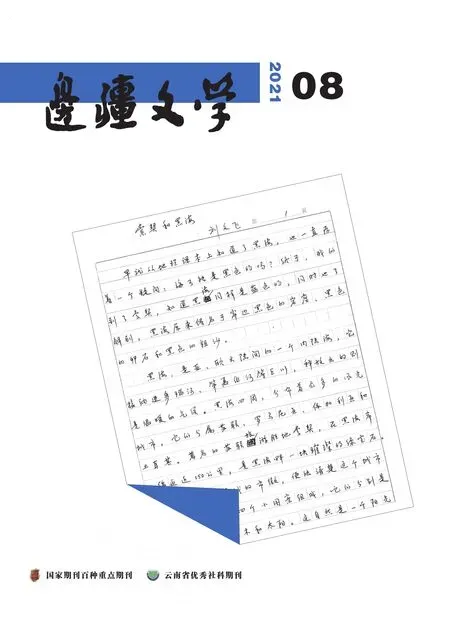缪祥涛的诗
缪祥涛
故乡
带一罐井水、一只碗
做一个背井离乡的人
夜晚,把一个喝井水长大的人
倒出来。一低头就看见碗里的月亮
直径,比老家的小十五厘米
茶歌
那是早晨,我和茶
倚在出租屋的茶案上,相依为命
像奔波者遇上流浪汉
静静地等待识别、注入、接纳
某一刻,茶会陷入短暂的迟疑
它不知道一把壶的胸怀,能不能
容下一片叶子风晒的遭遇
清明前,它离开母树
刚经历过揉晒、焙炒、挤压
在没有遇见容器之前,孤独在寂静中
沉默,隐忍
它偏爱炽热,将清冽冽的水煮沸
像煮沸我搓揉过的心灵
我迎面撞见,自身的枯萎、退让、无助
跟着沸腾一点点交出内心的苦涩
痉挛的叶脉里,藏着小小的春天
撞上拉姆拉措——致徒步人宁红瑛
水往低处流,你偏要向高处走
柔软不是宿命。在拉姆拉措神山的身体里
能够找到天空
——边远、荒芜、贫瘠,开始败露
——被俗世抛弃的云朵,有超出我们千尺的冷暖
——拉姆拉措湖的内心也是积雪。
你听见雪融化的声音,给了你
冰裂疼痛的知觉,也给你辽阔和胸襟。
——洁白覆盖灵魂时,有多于我们万米的陡峭
在拉姆拉措湖漂洗隔世的经卷,
朝圣者的足迹,也是慈悲的梵文
还要给你岁月的慷慨,给你勇气
让安宁转过身来,再走回去
沿着两倍长的蜿蜒,向泥土匍匐
在理塘
不是所有的水都喜欢急流
姊妹湖化身为天使的眼泪,为水草静默
水草为牛羊静默,牛羊为土地静默
磕长头的人们匍匐在大地之上
向蔚蓝俯首,称臣
风怎么吹都是顺从
不是所有的山都喜欢高高在上
在理塘,我把自己摁进水里,摁进
天空和浮云
格桑花开成一生中最美的自己
星辰在湖中饮水,准备着另一场春天
一片素不相识的流云
在扎嘎神山背面,倾听理塘寺的佛音
第一次离天这么近,借风的尺度
丈量白鹤的翅翼,夕阳一样辽阔
在理塘,圣洁的事物
先于人类学会了放弃语言
无字经
你见过无字经书吗?
我见过。逢年过节
她摆出两把空椅子,两副空碗筷
烧三炷香,三张钱纸
行三跪九叩之礼
拜请天地诸神驾临,就轻言细语念起来
她念到:菩萨保佑,丈夫
就往碗里夹一个荷包蛋
她念到:阿弥陀佛,儿子
就往碗里拈一只鸡腿
她念到那些冥冥中注定的人和事
总是用筷子敲一下碗口
多少年了!我一字不识的母亲
一直紧握一双木质的命
敲打着瓷质的木鱼
喜鹊之变奏
许多鸟鸣都有吉祥的玄音
喜鹊更胜一筹,音符里藏着卦象
叽为乾,喳为坤
闻声而至的游子对着旷野卜算
或客至,或书信。把家安在树的顶端
遥遥有期,大吉
繁花落尽,喜鹊并不知道
我们所称之为命运的声音
在一千公里之外飘零、仰望
从远处看,往近处飞
更适合一片落叶倾听
鸟窝,线团一样捂在谁的怀里
羽毛动了凡心,秃枝就有了温度
在高高的树顶,家
高悬于人间
在医院
“呼就是呼,吸就是吸,憋着气别动。”
——在医院,医嘱如同佛旨
需赤身裸体,完全暴露出真实的样子
医生如是说:“少抽烟,尼古丁和焦油,
是催命的鬼,取出太难。”
这让我感到毛孔粗大,紧张、沉默
第一次脱离汗水、泪水和血肉
与寄养在自己体内的贱骨头相遇。
医生如是说:“CT 室的射线比阳光更为有力
可以洞穿一个人的肉身,亦可佐证
灵魂犯下的罪恶。”
通透啊!在没有确诊之前我一直担心
带着太多生活的油腻混迹在健康的人群
孤独和恐惧,会不会发霉?
医生如是说:“在这尘世偷食恶果的人,
久了,还会生出狼心和狗肺。”
我忽然觉得,来到这人世
像是等一场原谅,或者救赎
披着烟熏火燎的袈裟
——掩凡胎,如裹尸
八月豆——致我亲爱的妻子
八月的藤蔓已经褪色。她的青春
还清晰可见。盘错于人世纷乱的枝丛
要让我遇见:真叶露心,抽蔓,旋蔓,开花结荚
风里来,雨里去,缠绵也曾被捆绑
但是不怕,柔软的命更具坚韧的品格
在高高的枝头,找寻热烈的出口
以她应有的和想要的方式
——孕育,垂爱,牵挂。
风吹过的时候,摇动着另一种惊心的可能
那是一个人满怀恭敬的心事
她欲撕裂自己,挤干毕生的水分
她腹中的籽粒就要分娩
当年,妻子就是这样剖开自己
抱出体内的豆子
先生:L 大爹
在老家乡下,先生的职业
就是扎堆亡灵:装殓,堂祭,超度,诵经
一辈子焚香,击罄,叩拜,净身
食别人家的斋饭,供别人家的神灵
L 大爹是佼佼者,更善于供奉心中的菩萨
七老八十,依然坚持为成了家的儿女们
积阴功,化福德。坚持在死人面前
替活人求福佑,诉衷肠,敲自己的木鱼
说到伤心处,就在阴魂面前,替活人叫苦
流泪。说不下去,就咳两声
咳是他转换悲痛的方法。那一瞬
仿佛跪在灵棚里的孝眷都是他的儿女
而他心知肚明,他们一心想要
活成在世的菩萨。他们并不愿意给生活下跪
是的,生死和垂暮离儿女太过遥远
当年我走的时候,他的咳嗽声比磬还沉
回来时,已置身堂屋供桌上的相框里
他身边有尊菩萨,烛灯,香炉和天地诸神
多年来,只有大妈端着清水
擦洗他玻璃的肉身
这个唯一懂他的女人,秉承了信仰
闲着没事就孤独的伏于供案
——诵读,发呆,对话,打盹
她睡着的时候,仿佛也已不在人世
那一刻,她也成了供桌上的摆设
在诸神面前,和他一起蒙受着灰尘
孤独小院
你住进去,灰色的面容
她不会拒绝你
——久违的老人。在枯萎的季节
牵挂:远行的蓬勃
我喜欢这种渴望的状态
守望的衰老性和植物的盛开性,形成怀抱
——那些父亲种下的花草
会和母亲抱着取暖
海棠、芍药、牡丹、茶花、杜鹃和迎春花
包围了热闹——他们是约好的
而这仅仅是
一个渐次老去的看花人对于盛开的误判
事实上,我们只是在花间取乐
搜寻奔波的旧翅膀
火葬
我愿意接受火的审判
一看见坟头草,我就担心
那些埋不掉的罪恶会重新发芽
我柔软的一生,未必
配得上一块石碑的硬度
烧了吧!一副没有贡献的躯壳
怎好占用国家土地
连同尘世这张二皮脸化成灰
撒掉,正好符合我的一生
只是不要撒在水里,在人海
我已漂泊得太久。撒到山中去
做草木的骨骼,一个五行木旺的人
生来,就欠人间一片森林
月如霜
中秋又占领了人间。黑白分明起来
我送走过的亲人,在月亮内部
起伏
第一个是父亲。二十二年前(冬月)
夜半风雪定,堆成他的晚期。
月色在他瞳孔里散开,他颤叨着:
“雪白,月亮白,白蛋白……白,
白,注射多了,人就没用了。”
四年前是大哥。9.18,月光
撞上耻辱的日子,体温在我怀里一寸寸
冷却,来不及呢出半句话的热量。
我第一次替他说出遗言:
“脸色苍白,唾沫黏白,海洛因……死白,
白,吸多了,人就报废了。”
孩子们围着我的母亲,要月饼
要天上白嫩嫩的圆圈。他们并不知道
饼一样的奶奶早已中了白色的圈套
一生面对着太多无法填写的空白
手里捧着心一样的饼,饼一样的月
掰不开的苦难,是她穷尽一生
对月光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