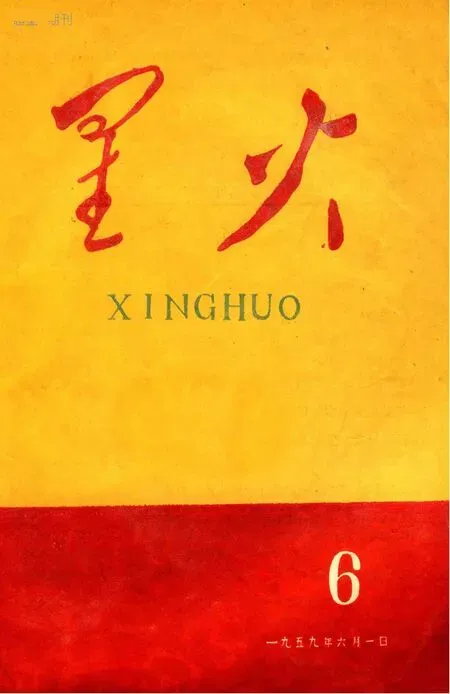在郴州遇见他们
丁小炜
我在傍晚时分抵达郴州,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从长沙过湘江、蒸水,一路南来。高铁时代,城市与城市的距离仿若一盏茶的工夫。
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穿郴州城而过,两岸傍河而建的房子,在璀璨灯火照耀下,颇有湘西凤凰古城吊脚楼的味道,而那楼宇翘檐又呈现徽州马头墙风格,好一派江南风光。秋夜清凉,月色朦胧,两岸酒肆林立,三三两两的食客信步登楼,湘菜的浓郁气息氤氲弥漫,尚未举杯已有几分醉意。
河曰郴江河,夜幕下的河岸线十分舒缓,河边蹲坐三五个钓者,带夜光的浮漂在水中晃动。只见刚刚甩钩入河,闪着荧光的浮漂就动了起来,继而猛地一沉。钓鱼的人不慌不忙,扬竿与上钩的鱼儿周旋,不一会儿,一条半斤重的刁子鱼就握在了手里。鱼身闪耀着银光,远远看去,那白色的扇形背鳍还在使劲伸展,即使当个看客也能感受到鱼儿的鲜活和钓鱼人的畅快。
郴州友人盛情,点了不少当地美食,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边品尝盘中美味,边欣赏河边夜钓,不觉酒兴大增,习习凉风里竟有些飘飘然了。
恍惚之间,眼前的景致俨然成了唐朝的郴州,几位唐时故人正向我走来……
一
迎面来的这位,应该是柳河东柳宗元。
记得中学的语文课里,就有柳先生的《童区寄传》:
童区寄者,郴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因取刃杀之。
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虚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
虚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还之乡。
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皆曰:“是儿少秦武阳二岁,而讨杀二豪,岂可近耶?”
用今天的话说,郴州儿童区寄使出了一记漂亮的“反杀”。他在山里正一边放牧一边打柴,两个强盗把他绑架了,捆到集市上去卖,但区寄凭着勇敢机智,手刃二盗,让十里八乡刮目相看。
友人初到郴州工作不久,我问此地民风何如,他哈哈一笑说,民风纯朴,却也义气彪悍。看来古风犹存。
柳宗元创作的这篇传记文学,寥寥数行,就刻画出一个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现在回想少时背读古文情景,脑际中对于区寄形象的勾勒渐渐复苏。
说起来,此时的柳宗元正逢人生不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王叔文集团倡导的“永贞革新”失败,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元和元年(806年)赐死,王叔文“朋友圈”里的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等八人,先后贬为边远八州司马。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专门对王叔文“永贞革新”的兴起与覆灭作了较大篇幅阐述。王叔文是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改革家,执掌政权后,积极改革不少弊政,诸如: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等冗官42人,节省财政支出;停盐铁使月进钱,盐铁使自玄宗时开始设置,是主管国家财务的机关,德宗规定盐铁使每月要送钱给皇帝,这是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事,叔文当政后,即禁止官吏私人进奉,下令停止盐铁使每月进奉金钱;释放后宫宫女300人及教坊女妓600人,不但减少了宫中怨女,也诏告了皇帝不重声色的态度;京兆尹李实乃朝廷宗室,但贪污虐民、残害百姓,又自恃受宠于德宗,对那些正直的官员进行谗言加害,王叔文将李实贬为通州长史……
总之,王叔文掌权后推行仁政,做了很多大快人心的好事。然其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推行新政本身,而是推行新政的行事方式。他的有些措施,唐宪宗继位后也是极力推进的,比如削弱藩镇、整饬吏治、加强财政等,还一度出现了所谓的“元和中兴”,但王叔文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广交私友,培植亲信,触动了皇室、宦官、藩镇、重臣的利益,冲击了唐代中央集权体系的政治根基,其圈子被整饬拆分、稀释瓦解亦是必然。
柳宗元作为王叔文圈子里的铁杆粉丝,肯定首当其冲遭贬。永贞元年九月,他先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在赴任途中再加贬永州司马,他在永州一直生活到元和十年(815年)。接着回京,但不久又被贬到柳州。岁月蹉跎,湖湘大地聊为所依。他毕竟是个文人,看到此方百姓疾苦,联想到自己的贬谪生涯,亲朋离散,精神苦痛,这篇《童区寄传》,表面是为穷孩子立传,实质是为底层人民呐喊。
邵州、永州、柳州、郴州,唐时故郡今犹在。未在郴州任过职的柳宗元先生,一定应惺惺相惜的朋友所邀,来此福地喝过几回闷酒,不然千年之后的我怎会在这里与先生神遇?
二
翌日晨,朋友延请我们至郴州一僻静小巷吃当地有名的“杀猪粉”,据说乃选用当日宰杀的新鲜猪肉烹煮而成,果然味极鲜美。
从小店鼓腹而出,但见路边有一棵几人才能合抱的大树,亭亭如盖,冠与楼齐,树前立有一石,上书“文星古樟”。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因上表诉天旱人饥和宫市之弊,请减免灾民赋税而获罪,被贬作连州阳山(今广东清远)县令。公元805年,韩愈被赦北归,在郴州待命长达三个月,好在有刺史李伯康的热情款待,期间他在郴州手植此樟,人们传说韩文公乃文曲星下凡,故将这棵树誉为“文星古樟”。
这一年正赶上“永贞革新”失败,韩愈在郴州滞留而迟迟得不到朝廷新的任命就不足为奇了。首都乱成了一锅粥,长安到郴州又没有高铁,人们又没有手机,送信的人不走个三五月才怪,谁在乎他这个遭贬的区区县令?
晨雾缥缈间,我仿佛看到千年古樟下站着一位清癯的老人,手拄木杖,粗布长衫,须发尽白,这不正是韩文公么?
据说,为帮韩愈解闷,李刺史特邀请他去郴州北湖参观当地的叉鱼活动。韩愈是北方人,看见如此新奇有趣的南方水上活动,不由得诗兴大发,写下了诗作《叉鱼招张功曹》:
叉鱼春岸阔,此兴在中宵。
大炬然如昼,长船缚似桥。
深窥沙可数,静搒水无摇。
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
中鳞怜锦碎,当目讶珠销。
迷火逃翻近,惊人去暂遥。
竞多心转细,得隽语时嚣。
潭罄知存寡,舷平觉获饶。
交头疑凑饵,骈首类同条。
濡沫情虽密,登门事已辽。
盈车欺故事,饲犬验今朝。
血浪凝犹沸,腥风远更飘。
盖江烟幂幂,拂棹影寥寥。
獭去愁无食,龙移惧见烧。
如棠名既误,钓渭日徒消。
文客惊先赋,篙工喜尽谣。
脍成思我友,观乐忆吾僚。
自可捐忧累,何须强问鸮。
这首诗写出了郴州人叉鱼之盛况。时值中宵,火光如昼,北湖水涨浪阔,叉鱼人手疾如梭,鱼在火光与水波间跳动,叉鱼人赛兴顿起,往来鱼儿与水影间,一旦叉得大鱼便嚎叫不止。这种情景,也许能让退之先生暂时忘却官场的得失,不再执意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吧。心是一个人的翅膀,今人尝言,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其实很多时候,限制人心的,不是周遭的环境,也不是他人的言行,而是一个人自身,能不能看开,能不能忘却,能不能放下。如果自我囚禁于灰暗的记忆,即便给你整个天空,也找不到自由的感觉。韩愈字退之,退一步就开阔了。因此,此时他虽行在贬谪之途,然面对此情此景,也不禁发出“自可捐忧累,何须强问鸮”的感慨来。
其实,韩愈一生不在诗名官名,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大名的,是他倡导的古文运动。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其时韩愈和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在“复古”的口号下,开展了一场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命,其功绩不亚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他们崇尚先秦和汉朝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的散文,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而对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大加挞伐,批评那些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华而不实,不适于用。然,中唐古文运动,虽在当时文坛取得胜利,但骈文并未匿迹,晚唐以后仍继续流行,特别是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
元和十四年,由于一件小事引来的祸端,韩愈再被贬潮州。他反对唐宪宗大肆兴建寺庙,仗着自己在唐朝文坛的地位,就给皇帝上了一封奏表,不想激怒了宪宗,一纸调令就让他再次南行,这时候他已是花甲之年。韩愈骑马从郴州的一个小山岭经过,此时好友李伯康已逝,韩愈追忆旧人,伤心不已,心神恍惚,竟至从马上滑下山坡。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时常想,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恰如一部中国贬官史。若没有那些迁客骚人,哪有《离骚》《琵琶行》《枫桥夜泊》《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岳阳楼记》《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闪耀千古的名篇?若没有那些宦海沉浮,哪有屈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范仲淹这些文学大家横空出世?
他们往往在波诡云谲的政坛上命运多舛,成为献祭的羔羊,而不是高悬的神龛。他们正直耿介,清高傲岸,不屑谗佞,不肯与混浊世俗同流合污,其结果自然逃不出被贬和遭逐。还有,他们往往任侠使性,偏执顽固,意气用事,再加之多愁善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仕途当然变得坎坷崎岖,深不可测。正如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三
吃罢“杀猪粉”,拜过千年古樟,好友安排我们取道临武、宜章,前往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一游。车上高速,一路南驰,畅通的出行让我又想起唐朝那些贬谪迁客,他们山一程水一程,不知要在这条官道上行走多久。
由于郴州在唐时的区位和交通的特殊性,此地成了朝廷贬谪地,或被贬官员的必经之地。然这些失意人在被贬郴州之后开始转运得福,因此郴州也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贬官福留”之地。他们有的路过郴州直抒感慨,有的凭栏长亭惆怅送客,有的不胜唏嘘、你唱我和,有的瘦马老仆、策杖而行,那些渐行渐远的身影,为这块土地留下了诗篇和传说。
本是一次没有既定目的的旅行,却让千年之后的我在此感悟一番昔日贬官的愁绪,车窗外的山道上,我似乎看到另外一位唐朝大咖与我们同行……他叫刘禹锡。
盛唐诗星璀璨,中唐也诗人辈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张籍、刘禹锡、孟郊、贾岛,这些人个顶个诗坛圣手,但这些牛人里边最刺头儿、最口无遮拦、最不怕事的,就是刘禹锡。他出生的时候,据说是母亲梦见禹王,所以取名禹锡。果然他二十二岁就中进士,三十二岁任监察御史,人生就像中了大彩票,踩上了五彩祥云。但是,后来他从云端一路翻着跟斗跌了下去……
刘禹锡与柳宗元、韩愈一样,和郴州也有很多渊源。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武陵)司马。“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元和十年,朝廷召禹锡自武陵还,但他放浪习性不改,又写了一首《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触怒了圣上,再次被贬为播州(今遵义)刺史,看来他是真的消受不起长安的十二时辰。诏书下达后,御史中丞裴度怜惜刘禹锡,向皇上求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好友柳宗元也上书皇帝,希望能以自己的柳州刺史一职和刘禹锡交换,以便刘禹锡奉养老母。最终,唐宪宗以“不欲伤其亲”为由,改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在南岭山脉九嶷山与骑田岭之间,两千余年的秦汉古道从临武穿境而过,它是湘南古邑临武连接粤北古邑连州的必经之途。刘禹锡骑着一匹老马,正在这条路上向连州踽踽独行……
在连州期间,禹锡与被贬的杨侍郎成为好友,写下了《和杨侍郎初至郴州纪事书情题郡斋八韵》《和郴州杨侍郎玩郡斋紫薇花十四韵》《和南海马大夫闻杨侍郎出守郴州因有寄上之作》等诗作,看来他与郴州这个被贬的杨侍郎也不是一般的交情。刘禹锡在广东连州五年,改善当地民生,百姓爱戴有加。还研究医学,常与柳宗元通信,讨论文学、医学,他发明了《治霍乱盐汤方》《治脚气方》《治疔疮方》三个药方,抄给柳宗元做实验,果然有奇效。研究医药学的同时,他的思想也逐渐变得唯物主义,不信魑魅魍魉,在那个时代,这种思想已经十分超前了。
刘禹锡屡处逆境而不沮丧,频遇挫折而不萎靡,他坚信只有回不去的过往,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正如他在那首《秋词》诗里写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谁说最好的季节已经过去?这才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节。
此行郴州,无意间寻访了三位唐朝文学家的足迹,与他们神交,乃人生快事幸事也。
说起来,柳宗元、韩愈、刘禹锡三人曾同时供职于御史台,亦是文友诗友酒友,韩愈和刘禹锡是唇枪舌剑的辩友,刘禹锡和柳宗元是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柳宗元和韩愈是志同道合的文坛搭档,他们简直就是中唐的“铁三角”,没承想这三人都在贬谪的烟波江上与郴州结缘。
元和十四年,一生波折的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享年四十七岁,刘禹锡用尽毕生心血整理了柳宗元的遗作,自己出钱刊印出版。韩愈怀着沉痛的心情为柳宗元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赞誉柳宗元在柳州为官期间的诸多功绩,并邀请著名书法家沈传师书丹。柳宗元去世五年后,韩愈也因病去世。刘禹锡写了一篇《祭韩吏部文》,其中回忆了当年跟韩愈以及柳宗元的友情,大意是说:韩愈擅长写文章,我擅长议论,我们两人一见面就争论不休,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柳宗元就出来打圆场,这样的时光真令人怀念啊。
梦回唐朝,恍觉这世间,存在一种友情,那便叫作柳宗元、韩愈和刘禹锡。
——郴州慈善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