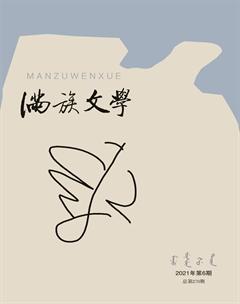缓慢的老屋(组诗)
石也
绿皮火车
车头差一点儿就碰到了
还没出现的时间。而车尾
几乎拽住了正在逝去的光阴
在座位上,像伸出拇指试刀锋
我碰了时间,但从没与分秒重逢
扑来的一切像个手捧容器的造访者
我的双手空空,在它止不住的赐予中
汽笛携着风急促奔跑
途经的土地与铁轨双向无觉
在涂成绿色的盔甲里
所有人都如此安全
太准时,像童贞泯灭童贞,暮年失去暮年
准点进站,离开的背影只呈现此时
车轮经过的地方一朵花正在吐蕊
花落发生在风吹来的途中
陶罐里的水
盈满,倒空,反反复复
印在上面的指纹碰触了什么?
不知身外的世界,水里的倒影
跟真物一样在消逝,像流动
要怎样守护才能留在原处
也许还有机会渗漏,罐壁上的水痕
隐现着河流遥远的身世
什么也没泯灭,江湖就如此安静
里面的黑暗囚于一隅,像暮色一样无限
不再像江河那樣流经大地
一路辉映蓝天白云,辉映星空
这不是清洗,纯净源自万念无存
一滴晨露或者一片汪洋,从始到终
什么也没失去,什么也没得到
黑塑料袋:另一种飞
它是无故的,这谁都知道
想必一只死去的鸟儿
把翅膀借给了它
万物作证:它没有丝毫动机
但它确实在飞,在无所依靠之处
找到了无处不在的依靠
飞过树林,飞过河水
不仰望也不鸟瞰,它拒绝认知
途经一切又忽视一切
薄如蝉翼而不透明
哗哗作响却沉默无声
被撕裂,像一头黑色的水母
任何移动之物都不能与它同行
唯有飞过之后
才知道它去了哪里
缘 由
谁知道,被风吹起的尘土
是在什么时候落下的,怎么落在了那里
父亲在田垄上耕作
天空泊着那样的一朵云
山在那儿,什么给了它形状
蓝了千年万年,天还是那个颜色
像父亲那样,不管是什么
只要出现,就是缺席
缓慢的老屋
盖着盖着,就出现了一座房子
那样的屋脊和那样的墙
那样的门和窗,那样的炕和锅灶
第一缕炊烟升起来时
房子就变成了家
后来,牛和鸡鸭都记住了这儿
再后来,土墙出现了裂缝儿
有了烟火的熏痕
多年以后,房子慢慢成了老屋
它似乎一直在那儿
跟旁边的一棵梨树一样,没有原因
灯
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父亲在暗中伸手
“咔哒”一声,十五瓦的灯泡冒出了光
吃完晚饭不久
父亲在北炕头躺下
伸手一拽,灯灭了
后来,父亲死了
一盏比平时用的大三十瓦的灯泡
挑在大门口,亮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