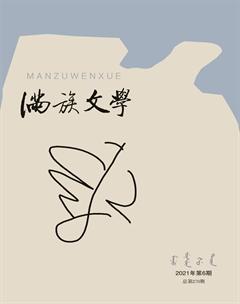洛阳桥上的黄昏(组诗)
怀金
南太行的乌鸦
一大早,它们就叫着,嘎嘎地叫。
在高空中盘旋,划出一个个大圈,一会儿
突然折返,似乎是回马一枪。
叫声更响了,柿树林的上方,有一只
已经飞过了对面的山脊。
柿子还在树枝上打灯笼,
风,它不开口,担心一张嘴,
柿子就会泥巴一样掉下来,
南太行,我不能
用巍峨来形容它,更不能学那只大白鹅
惊叫一声。它们都绷紧了一根弦。
在云台薄壁
有一个纠缠的护法僧,面对清晨
把巨石推下山谷。
我听到“啪”的一声。
只有雪能照亮它,只有雪才能
使它的叫声更黑。而最后的一盏灯,
干瘪着
似乎是南太行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根吸管拉住了它。
老鸹一粒粒搬运着石子。我在诗歌中
正一粒粒地清除出去。
诺弗勒堡
花砖地板,暖色的墙。
木质沙发,小圆桌,花瓶。
她用钢琴弹了一首曲子,然后
坐在暖气片旁,略带沙哑的嗓音
开始说:写作的恐惧。
你有权利去写
一只苍蝇之死。那是她走进储藏室
看到在玻璃上飞,而后死。
“我没法忘记苍蝇
可怕的挣扎。”她语气平缓
仿佛仍在写作,到处
都是文字,甚至整座房子
都在写。
疯狂缠绕着她,疯狂
也是写作,写作就在她的皱纹里。
抽烟。酗酒。爱和被爱。
孤独越来越深。窗台上
一溜花瓶中干枯的花,
她不会扔。就算是死了
也不扔。
院子里,整整齐齐地
摆放着桌椅。此时是空的
她在等周末,那个传奇。无人
探寻她的书桌,无人
可以拿走一根稻草。自然
还有另一个更深的
古堡。没有人
用两种声音写作,我确信
她用绝望創造了第三种。
黑发卡,拢着一头
灰白的短发。这个小老太婆
老得像是一小堆灰烬。不用吹
她还会放出火来。我只能
轻轻呼出三个字:
杜拉斯。
洛阳桥上的黄昏
从两车道到双向六车道,甚至
更早的浮桥,步行
骑马、驾车,你的影子都在。甚至
你赤足蹚过洛水,或从桥上跃下,
你的诗集跃下。有一刻,苇丛中的
苦恶鸟叫着你的名字。
它是欢快的。它的腹中
怀着一个黄昏,那是被一根大铁锚
拖住的旧宫殿。深扎于水中的柱础,
在吃他密集的光、绣线,和空中
翻卷的饕餮纹。一枝脱去了籽粒的
莲蓬,含有最大的有限性,它看到
孔子入周,也看到他不见的
黍离、麦秀。而一颗
玲珑心,正被夫子以剑刻下。
土地无心,土地可以被删减、省略。
一只鹭鸟
仍不飞,不驾车,它走水路
逐日。它的酸性体质,痛于风,更痛于
磁悬浮的黄昏。这是一个
被反复强调的年月,公驴企鹅
找到了家的相似物:请允许我
在楼顶静坐一分钟。晾晒的
床单、被罩、还有衣服,该收了。
它们花花绿绿的,伸展在
干净的风中。突然就看见
晒裤衩的小阮,他弹琵琶的样子,
与猪喝酒的样子,赤身裸体的样子,
我就深感羞愧。现在
你看不见的麦子
开始灌浆。祝融号火星车,刚刚踏上
乌托邦平原——你确认,你看见的
古代,才刚刚开始形成。
纸 船
纸船在水面漂,这是你折叠的,并
一直乘坐的船。一些细微的波纹
就会使它晃动。鸟试着
放下它的脚,鱼也可以跃上来
躺平一会儿,有水草挽留的话
就秉烛夜谈。更多的时候它往上漂,到
起点处,但总也不能够。它来来回回地漂,
给运河添加点帆影。
船上有口粮,泽草所生,种之芒种。
大海来临之前,它不会沉,只会没有,
只会无。
船上手写的文字、残句,一把尺子正称量它们:
快速的颤栗和有芒的慢。
为了放逐,它守着自己的空。
为了沉没,它不断加重岸边那块青石板
古老的体温。
和一棵杨柳谈论它的嗓音与沽酒术
——和杜牧《张好好诗》
它们在阳光下清洗,枝条纷披
一根一根地洗。这一根是戒律,
那一根是鸟,
远处,是被垂钓的歌姬。而歌声
有时候是杨,有时
是柳。肯定有一只长长的胳膊
在沉默的语义中打捞
一根针的人间谍影。
如今我们用二维码,扫描
洛水中的两只残月,那被童年
擦伤的,必和卵石交换了定位法。
除了再见,还有什么是绿色的?
一丝浪花被缝入腰间。文字有命,
腰间有记忆。
涂污的长句下,一碗烈酒
坠地,当垆的还在当垆,她和诗歌
达成了平衡术:折柳的
顺便折弯了月亮的合金。当然
没有谁是职业的,
更有什么是狭窄的?比如猫
在话语剩下的部分,一杯淡酒
缜密的角落:如此。好吧。似乎是
一切活着的遗照,坐在
完美的幽暗中。
注:史载,杜牧早期随江西观察史沈传师转至宣州幕府,其时沈传师之弟沈述师(李贺临终托稿之人)也来到了宣州,并纳幕中歌妓张好好为妾,几年以后张好好为沈述师所弃,流落至洛阳,以贾酒为生,杜牧在洛阳重新相遇,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张好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