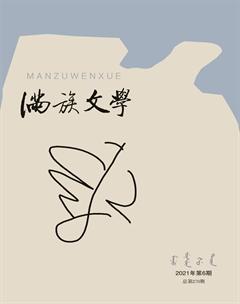鸟的隐语
1
寂静的午后,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树叶上,地上留下斑驳的树影,风在树林里四处游弋,把树叶吹得哗哗作响。在故乡后山这片熟悉的树林,我看见一条树蛇在一棵杉树上快速盘旋,蛇仿佛一个善于折叠术的表演者,很快就钻进了树半腰的一个洞穴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恐惧所带来的颤栗流遍全身,树洞里传来揪心的呼救声,绝望与无助交织在一起。这是我熟悉的一只啄木鸟的巢穴,每次跟随母亲上山干农活,我总会看到它勤恳地在树干上啄食的身影。正当我感到头皮发紧、不知所措时,雌啄木鸟拍打着翅膀在半空中盘旋了一圈后,降落在树洞口。啄木鸟多才多艺,不仅是经验丰富的木匠,更是技艺精湛的体操运动员,以九十度垂直角度站立在树干上的啄木鸟正欲进洞,却迅速捕捉到了危險的气息,雏鸟在洞穴里发出阵阵悲鸣。啄木鸟细长而锋利的嘴巴迅速啄在蛇身上。遭到袭击的树蛇从洞穴里窜了出来。啄木鸟救子心切,它加快着啄的频率,试图把眼前这条庞然大物赶走。蛇迅速展开了反击,它原本盘成一团的身体忽然迅速伸展开来,一下子扑到啄木鸟身上,迅速把啄木鸟缠住。啄木鸟不停地啄着,青绿的蛇把它缠得更紧了。一场生死博弈在我眼前展开。此时,村里卖豆腐的老王恰好路过,捡起地上一根细长的树枝,一下戳中了蛇的七寸。被击中要害的蛇很快从树上掉了下来,转眼消失在青草丛中。
洞穴里的三只幼鸟幸免于难。黄昏时分,夜幕缓缓降临,我从山顶上下来,看见这只灰黑色的啄木鸟仍然站立在洞口,守护着她的儿女们。
翌日清晨,我跟随母亲步入山间,看见险些遭遇家庭劫难的雌啄木鸟正在另一棵树上啄洞,准备把家安到一个更加安全的洞穴。啄木鸟频繁地把细长而锋利的嘴巴刺入树的表皮,发出笃笃笃的响声,声音回荡在山林间,空旷而悠远,我走到山顶依旧隐约能听到啄木鸟发出的声音。
临近午后,从山顶下来,行至半山腰,我看见村里人老派手中抓着一条白花蛇。蛇背部的一个个细小的伤痕提醒了我。恍然间我才想起这是昨日侵入啄木鸟洞穴的那条蛇。这条白花蛇无疑将成为老派盘中的一道美食。老派是手艺精湛的猎人,也是厨艺高手,他经常在山间转悠,捕捉到的猎物有的自己吃,有的则卖给山下马路边的那个小餐馆。次日中午,路过老派家门口时,我看见他在院子里娴熟地把蛇皮剥掉,切成一截截蛇肉。看见我,他热情地邀请我中午来家里吃蛇肉。我委婉地拒绝了。野兔、野鸡、野猪以及游走在山间的蛇大都成为村里人的盘中餐,成为山下饭馆里烹饪的绝好食材。
同为树林的一份子,它们与啄木鸟命运迥异。人作为食物链顶端的高级动物,喜欢用自己的道德准则和利益尺寸来衡量动物。啄木鸟因善于捕捉藏匿于树木中的害虫,是森林的保护者而被人类尊称为森林医生,享受着被保护的待遇。作为森林卫士,村里人很少捕捉啄木鸟,即使调皮的孩子捕捉到了,也会在大人的谆谆教诲下放生。村里人看见啄木鸟面露微笑,敬而远之,仿佛见到了神灵一般。蛇却因丑陋的外形,让人避而远之。
2
啄木鸟的觅食本领独一无二,千万年来的进化造就了它独特的身体构造。细长而坚硬的喙、尖端携带细钩的舌头、具有极强防震荡功能的头盖骨、带钩的足趾以及坚硬的尾巴,给啄木鸟稳稳地站立在树干上寻觅敲击昆虫提供了最强大的后盾。在时间长久的打磨下,上帝赋予了它一套觅食的绝好装备。
晨曦时分,晨露从青翠的草株叶片上滑落,山林间响起婉转清脆的鸟鸣声。这看似静谧的场面,却无时无刻不暗藏着杀机。晨起的啄木鸟仿佛从军的花木兰,坚硬的盔甲在朝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细长而坚硬的嘴巴仿若锋利无比的矛,此刻它已走出闺房,准备奔赴战场。笃笃笃,这独特的敲门声一旦响起,树内的昆虫如临大敌,脸色恐慌。啄木鸟敲响了隐匿在树内的昆虫的丧钟,这是“外科医生”的特权。
在老家,我们把天牛称呼为水牛。水牛是年幼时我们酷爱捉的昆虫,调皮的我们蹑手蹑脚地一步步靠近树干,迅疾地伸出右手,钳状的手指瞬间捉住了栖息在树枝上的水牛,水牛发出嘎吱嘎吱的呼救声,急欲逃脱。天牛不是牛,却气大如牛,它嘴角边的两个钳子,锋利如剪刀,啃食树木时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仿佛人握着锯子锯木头,天牛因此而被戏称为锯木郎。它长长的触角勾起我很多童年的回忆,让我想起年幼时父亲买回来的那台黑白电视机,没有安装闭路电线时,就依靠电视机左右两边的两根天线来收电视频道。年幼时爱看《西游记》,每集不落,《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头上也带着两根天线,神采奕奕。天牛身上两根比自身身体还长的触角,不仅能感知障碍物的大小和形状,提供嗅觉、触觉和味觉的功能,还是彼此之间交流沟通传递信息的法宝。
年幼时我经常把一根细长的白线绑在被捉到的天牛腿上,牵着它在地上走,或者双手往半空中一扔,看它在天空中飞舞,仿佛放风筝一般。天牛在半空中发出嗡嗡的呼救声。天牛越飞越高,带给我游戏的兴奋和喜悦。那时的我尚不知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里却蕴含着残酷的生存法则。年长后,在异乡的城市森林里觅食,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地捆绑着我,让我深陷在迷茫的深渊里。
天牛用锋利的牙齿在粗糙的树干上撕开一道裂缝,把排下的卵注入树中。幼虫在树的表皮生活一段时间后慢慢侵入树的木质部生存。隐匿在树干内的天牛幼虫弥漫着先天的犯罪色彩,它仿佛是频频作案的逃犯,把自己隐匿得越来越深。
啄木鸟像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掏出听诊器,紧贴在树干上。树发出均匀的呼吸声,这是健康的暗语。啄木鸟没有失望,它拍打短小的翅膀,又锲而不舍地跳到另外一棵树干上,很快轰隆的响声伴随着阵阵杂音传递到它的耳里。啄木鸟惯用声东击西的策略,在它不停地敲击下,有的敌人主动缴械投降,有的却依然顽固不化。啄木鸟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加快了啄木的频率,最终破门而入,伸出细长的舌头,舌上锋利的细钩仿佛镣铐一般,铐住了敌人的双手。天牛束手就擒。
当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心里不知为何疑窦丛生,我写的就是最真实的啄木鸟吗?啄木鸟一生的功过早已盖棺定论,人类早已在它身上贴上益鸟的标签,无从反驳。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安排,所谓啄木鸟是森林医生,只不过是人类一厢情愿的道德绑架,那不过只是出于生存本能的觅食。
多年前的夏天,干旱时节,大地一片荒芜,我看见一只鹰在半空中长久地盘旋着,几分钟后像是忽然看见什么,径直俯冲下来,转瞬又迅疾飞起。鹰嘴里叼着一只虫子。鹰落地的刹那,散落在干枯草丛里觅食的几只鸟受到惊吓,像是老鼠见到猫一般,迅疾飞起,朝密集的树林里飞去。干旱的大地上,鹰的加入,增加了其他鸟觅食的难度和危险系数。迅疾飞起的鸟惊魂未定地栖落在树枝上,看一只啄木鸟从容地在树上娴熟地啄食着,笃笃笃的响声响彻了寂静的山林。死里逃生的鸟儿窘迫地看着正在忙碌的啄木鸟,饥饿和落入虎口的风险加剧着它们内心的恐慌,它们惊慌地鸣叫着,从这棵树流浪到那棵树,没有一棵树真正属于它们。它们隐匿在枝繁叶茂的树枝上,透过树叶的缝隙东张西望,时刻警惕着四周的风吹草动。
烈日下,大地裂开一道道缝隙,风裹挟着热气从远处袭来,地里的稻谷哗哗作响,仿若发出阵阵呼救声。虫子随着木屑掉落在地,啄木鸟没有独吞食物,它把捕捉到的猎物分一部分给正在给它站岗的山雀。轻盈调皮的山雀显然是啄木鸟忠实的岗哨,它一边吃一边叽叽喳喳地鸣叫着,这是它们之间互通的暗语。不远处,一只雀鹰在半空中久久地盘旋着,它迅疾而下的那一刻,山雀突然鸦雀无声。突然中断的沉默敲响了死亡的警钟,啄木鸟瞬时隐藏到了树干背后。山雀的及时提醒让啄木鸟从死亡的阴影中逃脱出来。扑空的雀鹰垂头丧气地在树枝上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又一跃而起,飞到了半空中。
在雀鹰眼中,啄木鸟始终是被捕捉和猎杀的对象。在鸟界,没有道德的束缚,只有赤裸裸的本能和欲望。人作为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在欲望的器皿上安装了一个阀门。
啄木鸟啄木的场景总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盛夏时节,屋外凉风荡漾,萤火虫在半空中飞舞,父亲光着膀子在闷热的屋子里做着木工活,锋利的刨在木头表面游走着,发出吱吱吱的响声。父亲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木匠,他靠自己的好手艺和勤劳养活我们一家子。村里人刨土取食,父亲刨木取食。或许是这种原因,我对在树木上耗尽一生的啄木鸟心生好感,倍感亲近。
3
啄木鸟白天啄木取食,晚上栖息在树洞里。它的一生都与树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啄木鸟是留鸟,短小的翅膀注定它们不能远行,只能一辈子住在森林里。就像我的祖辈父辈,他们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土地,未曾踏出村庄半步。鸟有留鸟和候鸟之分,人未尝不是如此。在城乡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养家糊口,我像钟摆一样在异乡与故乡之间来回颠簸着,只留下年迈的双亲钉子一样固守在乡村的老屋里。2007年大学毕业至今,我已在外流浪了十多年,浑身弥漫着漂泊的气息。许多个夜晚,在逼仄狭小的出租房里,我渴望像啄木鸟一般,长久地呆在故乡的那片树林里,侍奉年迈的双亲。
与啄木鸟独来独往或者成对出門的性格不一样,有一种织布鸟,它们喜欢过群居生活,它们会在一棵树上筑造十几个鸟窝。相比于织布鸟的热闹,我更喜欢啄木鸟式的孤独。人生最终还是要独自面对浓浓的黑夜,回归黑暗,与黑暗融为一体。
房子是人安身立命之所在。燕子住的是土坯房,啄木鸟住的是小木屋,它们自食其力,问心无愧。人在大地上行走,夜幕降临时,躺在木板床上酣然入睡。有的人身居逼仄狭小的出租屋,一上床就能酣然入睡,有的人居住在偌大的别墅里,却患上了失眠症,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作揖、跪拜,有的人靠白天骨头的弯曲却始终换取不来晚上短暂的安宁,跌入精神的深渊里。年近五旬的舅舅在建筑工地上担沙、挑砖,沉沉的重物压弯了他的背颈,当夜幕潮水般降临,空荡简陋的宿舍里,昏黄的灯光下,小型电风扇高速旋转着,他躺在简易的木板床上,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千百年来,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方式,磨穿了躯体的骨肉,却擦亮了精神的骨骼。
不是每个人都会为早日拥有自己梦想的房子而埋头努力,也不是每只鸟都会为拥有自己的窝而不断在树林里穿梭。人很容易陷入不劳而获的陷阱里。
不会建房的大杜鹃会趁着大苇莺外出觅食的间隙,跳入大苇莺的巢穴里,惟妙惟肖地模仿雀鹰的叫声。在外觅食的大苇莺隐约听到雀鹰的鸣叫,吓破了胆,不敢回巢。大杜鹃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给它争取了充裕的时间,足以让它从容地把蛋产在别人的窝里。
大杜鹃下的蛋与大苇莺下的蛋在颜色和纹路上极其相似,觅食归来的大苇莺没有看出任何破绽。大苇莺辛苦地孵蛋,几天后,小杜鹃破壳而出。恶带着某种遗传,刚产下的小杜鹃模仿着大苇莺雏鸟的叫声,来赢取大苇莺妈妈的喂养。僧多粥少,小杜鹃趁大苇莺妈妈外出觅食的机会,干脆把鸟窝里未孵出的蛋挤出窝,从而换取大苇莺单独的喂养。恶一旦未被惩治,就会肆意生长,变成灭顶之灾。
大苇莺患有先天的脸盲症,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被养大的杜鹃飞入密集的丛林里,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有回头。这是血淋淋的鸠占鹊巢的故事,人未尝不是如此,一旦丧失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就很容易成为罪恶的帮凶。
大姨结婚五年也没有生养出小孩,无奈之下,领养了一个三岁的女孩,女儿养到十八岁,考取了师范学校,亲生母亲找上门来,把孩子要了回去。几经争吵,表姐还是回到了亲生母亲家里。半年后,大姨和表姐在医院偶然相遇时,大姨兴奋地看着她,表姐却低着头,面无表情地看了大姨一眼,匆匆上楼去了,形同陌路。大姨每次跟我母亲讲起这一幕,眼角总是泛着泪水。人性的复杂在这里呈现得淋漓尽致。
与大杜鹃不同,啄木鸟是非辨别能力很强。啄木鸟用情专一,恪守一夫一妻的生存法则。孵蛋的重任并没单独落在雌鸟身上,体贴的雄啄木鸟不停地给妻子换班,夫妻俩轮流孵蛋,在窃窃私语中憧憬着自己孩子的降生。雏鸟尚睁不开眼,只能通过不断啼哭来呼唤母亲觅食。一个月后,雏鸟羽翼渐丰,它探头探脑地走出温暖的巢穴,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屋外陌生的世界。看似平静美丽的树林,危机四伏。它拍打双翅,略显稚嫩地在半空中滑翔着,很快它就落在一棵树干上,学着母亲的模样啄木取食。
啄木鸟有标准而统一的飞行姿态,它们每次翅膀拍打三次,紧接着是一次短暂的滑翔,如此循环往复。一个多月后,掌握了娴熟飞行本领和生存技能的小啄木鸟展翅高飞,飞向了更加广阔的森林,离开了养育它的父母,在父母的不断回望里,消失在树林尽头。在啄木鸟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家族谱系的契约精神和动人的情感。
4
橡子是啄木鸟过冬必备的食物。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啄木鸟——橡树啄木鸟,这是一种勤劳又团结的鸟,它们过着家族式的群居生活。还没有繁殖任务的橡树啄木鸟每天都在为搜集橡子和其他食物而奔波着。寒冬来临前,橡树啄木鸟在一棵树上啄出一个个小洞,洞的大小恰好可以容纳一颗橡子。一棵树在橡树啄木鸟的啄击下,变得面目全非,伤痕累累,树干上布满密集的弹孔,仿佛被机枪扫射过。我仔细端详这棵伤痕累累的树,才发现这是一棵枯树。我对橡树啄木鸟的误解顿时消失。它们只选择枯树储存过冬的橡子。橡树啄木鸟是聪明的,它不是把所有事物储存在一个洞穴里,而是采取分散保存食物的策略,以防止盗贼一次性把食物窃走。
祖父看着电视上一棵被橡树啄木鸟啄空过的树,树干上布满密集的小孔,每个孔的间距均匀,他一下子陷入沉默之中。这一幕一下子刺痛了他,他的面色忽然变得通红。这让他想起他从军上前线的日子。祖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他们隐蔽在丛林后,机枪扫射在树木上所留下的密集弹孔,让他们此生难以忘记。祖父细细端详着这一幕,时光仿佛倒流,又回到了遥远的时光里,那些年轻而又鲜活的面孔不断显现。历史这棵树是一面鲜活的镜子,对历史的不断回望,不是揭伤疤,而是为了更好地铭记与反省。
今天,当我重回故乡,故乡已变得陌生。禾水河干枯,河床裸露,石头在烈日的照耀下闪烁着一层白光。山上的土地长满齐腰深的杂草,年幼时那片密集的树林早已不见踪影,几棵树木零星地散落在山间,啄木鸟已无处可寻。
人类的命运与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从一只啄木鸟身上能看到一棵树的影子。啄木鸟给了一棵树健康活下去的尊严。人贪婪的欲望却一步步把啄木鸟逼到绝境。
我从一只啄木鸟的命运里窥见人的命运。
【责任编辑】王雪茜
周齐林,籍贯江西,80后,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有作品百余万字散见于《作品》《山花》《清明》《青年文学》《北京文学》《散文海外版》《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火》《散文选刊》等。曾获华语民间散文第一大奖,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第四届、五届广东省散文奖,第六届东莞荷花文学奖,首届全国产业工业文学大奖新人奖,第三届全国产业工人文学大奖散文奖。著有小说集《像鸟儿一样飞翔》,散文集《被淘空的村庄》《少年与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