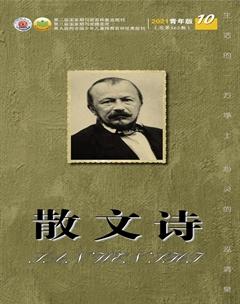随笔二篇
巴荒



永恒的链条——母与子
残破的壁画中流露出古拙的历史气息,远去的生命和文化,如呼吸般从壁面喷出,令我亢奋不已。岁月的风蚀和雨濯,使那些历史的图式形成特殊的斑驳和流淌的形式,可以一层层剥开的涂层,演绎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命;因此,颜料的流淌形式,国画式的点苔,石青石绿效果的运用,以及国画的积墨效果,水彩晕染方式,没骨画手法等等,皆可拿来为我所用;而宗教图式的构成,则更能强化我对属灵状态的表达。我企图将形而上的宗教与人文关怀和形而下的生命状态统一起来。
以宗教感的庄重来呈现生命的状态,强调的是生命的精神要素,在人性的关照中,把和谐与冲突、对立与统一的共存性展示出来。在这里,陌生与熟悉,温馨与冷漠,宁静与焦虑,接纳与拒绝,对抗与融合,排斥和相互给予,或是对生命表象的质疑,都各自演绎着生命进程中的种种真实性,这是我自身生命感悟中的不同层面和不同的表述话语……
《恒》与《圣灵与生灵》这一批我近年的创作,即是艺术的实践,也是生命体验中不由分说的自然流露。我从2007年开始做这个题材,所有的形象都来自于生活,彝族和藏族因我的出生地之缘故,是我最熟悉的少数民族,我的画多出于此。最初我是用纯油画做的,感觉传统的油画技法温温的,不痛不痒,在墙上挂了,或是在库房里扣着存放了三四年,一次偶然地和朋友交流关于综合材料的制作并意外地得到些指点,突然决定用色粉、胶等综合颜料与油画材料混合处理,形成了这个主题风格化手法的变奏。总之,这还只是刚刚启程的一种艺術试验,远不是成熟的技术终结。用什么材料,实在不是重要的事,达到视觉表达的审美效果也只是一种面对自己和观众的诱惑,只有流淌在画面的气息和隐含在造型和色彩斑点的精神和情感(或情绪与状态)才是艺术表达的价值核心。而核心的核心则是在一切精神价值体系中的独创元素。这里也有着我的朦胧期盼:坚持艺术的永恒性母体,表达艺术个体反抗艺术市场化后的平庸化倾向,探索人类灵魂被拯救的当代艺术途径,或许,这只能仅仅是个人化的微弱呼唤……
母爱与和谐的追求是永恒的,叛逆与反抗也是永恒的,人类借此坎坷地前进……
过去的时光
据我父亲讲,我出生在夜里零点。父亲把我的出生地指给我看:锦江边,四川大学红瓦村一幢僻静的小楼。他亲手为我接生,但他并不是一个医生。对这一切,母亲总是微笑不语。没有人能告诉我,我的出生是属于14日的夜,还是属于15日的凌晨?抑或是15日夜的尽头……一个模棱两可的时间,是在一道分界线、一个临界点上诞生的许许多多脆弱的生命之一。
不知道那种与生俱来的模糊和神秘感,是不是借此隐伏在生命之中,使我在追求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价值之时,情不自禁地探索和表现与此相关的一切——
我的童年与河流、泥土、草木以及鸟虫相伴。
50年代初的川大校园绿树成阴,锦江从川大的校门也从我家的后门经过,河的下游两岸都是农田,我家就住在城市和乡村的交界线上。锦河在洪水季节常常是泥浆浑浊的,但我喜欢守望这条家乡的河流。遇有机会,我就挣脱大人的手溜到河边一条泥泞的小路,跟着河流走,或等候河的下游走出三四个裸背赤足的汉子——他们神情木然,身体倾斜,拖着长长的泥绳;我跟着他们在岸边行走,直到他们和身后的船消失在九眼桥……后来,从母亲那里才知道,他们是纤夫。
我家从锦江河南岸搬到北岸,又从北岸搬回南岸,人工栽培的灌木丛围绕我的家园。受我母亲的影响,我的童年时代处于种植、饲养和采集标本的巨大的热情中。一有空,我就在家门外的菜园子里挖土、浇水种菜或嫁接果木;看着种子埋进土里,再冒出绿芽来,感到无比新奇和快乐。有一年,我把菜园子种成了蓖麻林,把无法在家中喂养的蓖麻蚕统统移到蓖麻叶上放生,那天夜里下了一场雨,第二天,所有的蚕都死了,我伤心地哭了一场……
父亲告诉我:“针孔可以成像。”这消息使我欣喜若狂,我整天拿着一个扎了针孔的纸盒子对着窗户,看纸盒里的“成像”。针孔换成了放大镜,却制造不出快门,相机还是没有做成。我找来一个木盒子、一堆马粪纸,收集父亲的老花眼镜镜片和母亲的显微镜镜头,用9分钱一把的铅笔刀为工具,折腾了好些天,做出一只望远镜和一台放大机来。望远镜可清楚地看到院墙上土钵中的仙人球刺,放大机能将底片上指头尖大小的面积放大,实验的成功让我兴奋了好久。我恳求父亲给我买一台照相机,但那时家中姊妹多,经济条件不许可,这愿望终没能实现。日后我也没有专门从事摄影,但20年后,我依然喜欢在暗室里折腾,想来却与儿时相关。
初中毕业,我成了失学的“病残知青”。像童年一样,我守在家园附近,但昔日的菜园子已被路人踏为平地。
父亲希望我在他的身边读他的“大学”:物理学,但我最终还是迷上了绘画。1977年恢复高考,给了我上大学的首次机会,阴差阳错,我放弃了四川美术学院到北京就学,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设计专业的4年本科毕业之后,我留校任教。迷恋绘画并充满了创造欲望的我,因涉事太浅,长久地不知道该怎么努力。后来,我去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做美编,中国美术报做执行编辑……
命运像在捉弄我。我的油画《流》在大学二年级时(1980)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的铜奖,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它;以后又以连环画、油画、版画和丙烯画等参加过全国美展和市美展。但在大学期间,我创作得最多的却是诗歌。我从不知道它们可以发表,但是,一些人看了说喜欢,就拿走了。它们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了下落。出于工作的职责与需要,我做过电视剧的美术设计,参加过学院的教学和演出的配合工作;我画插图,搞封面装帧和海报广告设计;写美术评论、报道和采访……但我心目中最高的艺术追求仍然是油画。西藏归来,我发表了一些油画和诗歌,但发表得最多的却又是摄影。如此便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之疑,惹得一些好心的同行师辈和朋友的惊诧与善言相劝。
对油画,我曾以为除此之外别无出路。而我越是追求于此,它就越是显示出它的高度和难度,不论是作为一种职业,还是作为一种文化与艺术的追求。油画便像是久孕的奇胎在我生命的底层膨胀。它形成得早而容易,却成熟得晚,不到成熟,它好像就不能诞生。
人讲顺从天意。我终相信,凭着对生命与艺术的虔诚和苦心,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并且对我生命过程中不可抗拒的种种劳动的方式,我都一视同仁地认真以待。摄影是我获取外部世界种种形象和材料的一种方法,暗室里的工作是一种乐趣,我爱油画则为人生,在绘画表现所不及的领域里,我觉得文字对我充满了魅力。
而我从小就体弱,病魔就像咬上了我,让我在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环境中品尝各种疾病之苦。也许因为体弱,我才特别渴望到自然中去展示自己的力量;也许因为我不具备强壮的体格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这种展示,我才在艺术里发现了更含蓄而永恒的力量。
第一次独自远行是1985年去云南写生,我到了瑞丽的弄岛。我的主要收获是相信了自己独立的力量,它为两年后我独自去西藏奠定了基础。西藏成全了我生命力量的最大张扬,也破坏了我最为纯净的生命幻觉;多次往返高原、不辞辛劳的工作,也让我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数年之后,我才从一种新的形式中艰难地找回自己的力量,于是有了《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