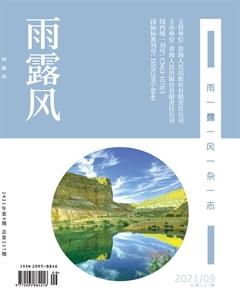《双鸟渡》的非自然叙事研究
摘要:爱尔兰作家弗兰·奥布莱恩(Flann O'Brien)的《双鸟渡》中体现出了非自然叙事的特点,整本小说框架奇特,叙述者不断在“我”的现实生活和虚构小说中穿梭,在故事和结构上形成了“陌生化”的效果。在叙事学经典的故事(Fabula)和话语(Syuzhet)双层模式中体现出《双鸟渡》叙事上的非自然性。
关键词:非自然叙事;元小说;不可能世界
一、“非自然叙事”的概念论述
“非自然叙事”(Unnatural Narrative)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已经存在于希腊罗马时期的虚构叙事中[1]396,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而引发一些理论家集中地探讨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非自然叙事”一般是指与“自然叙事”相对的概念,莫尼卡·弗鲁德尼克在《建构“自然”叙事学》中将“自然叙事”定义为自然的口头叙事,在此基础上,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扬·阿尔贝(Jan Alber)、亨里·斯科夫·尼尔森(Henrik Skov Nielsen)、斯坦芬·伊韦尔森(Stefan Iversen)等理论家集中探讨非自然叙事这一现象,使“非自然叙事学”(Unnatural Narratology)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一大分支。
非自然叙事学中不同的理论家对“非自然叙事”这一概念界定的角度不尽相同。理查森的理论基础主要建立在文本的虚构叙述,他认为“非自然叙事是违背了传统的自然叙事、非虚构叙事和那些企图模仿非虚构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2]111理查森在“摹仿说”的基础上区分了“非摹仿”(nonmimetic)和“反摹仿”(antimimetic),后者比起前者,在叙事形式和叙事再现上都有违反常规的特点,并将“非自然叙事”等同于“反摹仿”。阿尔贝认为非自然叙事体现的是“身体上、逻辑上和人类不可能的场景和事件(不管读者是否对这些场景和事件感到陌生)。”[3]436他借助认知参数来衡量非自然叙事,将“不可能”等同于“非自然叙事”。阿尔贝的理论扩大了非自然叙事的范围,尼尔森认为“所有非自然的叙事都是虚构的,但只有一些虛构的叙事才是非自然的。”[4]72他将非自然叙事归为虚构叙事的子集,比起一种边界分明的文类,更偏向于一种修辞手段,这种手段需要读者用非自然叙事策略来解读。伊韦尔森将非自然叙事理论扩展到小说文本以外的方面,比如广告,并提出了“永久性陌生化”[5]459的观点,即非自然叙事作为一种修辞,让内容保持着不可翻译的新鲜感。笔者认为,非自然叙事并非一种严格的文类,其边界应当是透明的,即指明一种不同于常规摹仿叙事的方法,接受者的主观认知也影响着这一概念的边界。虽然模糊的边界对精确的定义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更有利于对文本不同角度的分析和理解。
通过对上述几个理论家主要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非自然叙事学是一个充满分歧,没有清晰界定的学科。非自然叙事学同时也是一门充满挑战的学科,它既有突破传统的一面,也有继往开来的一面。总之非自然叙事学是一门动态的学科,不同的声音让其充满活力,迈向欣欣向荣,向更多更新颖的角度拓展。
二、《双鸟渡》的内容与研究现状
《双鸟渡》是爱尔兰作家弗兰·奥布莱恩在1939年出版的小说。《双鸟渡》主要的内容是爱尔兰大学生“我”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德尔莫特·特雷利斯(以下简称为特雷利斯)也是一位作家,他想写一部揭露罪恶的小说,但是小说中被“借”来的角色们对他的安排十分不满,于是角色们在特雷利斯沉睡的时候试图反抗这种局面,最后这些角色通过说服特雷利斯在小说中出生的“儿子”——奥立克·特雷利斯(以下简称为奥立克)来惩罚作家特雷利斯,特雷利斯在他“儿子”的笔下被送去法院接受审判并受尽了皮肉之苦。眼看这些角色的复仇就要成功,但是在红天鹅旅馆中,特雷利斯的女仆在收拾被风吹散的小说时,随手将这些纸页塞进了壁炉中生火,而这些纸页正是书中这些角色的活动场所,随着壁炉中燃烧的火焰,复仇计划戛然而止。这部小说除了上述情节外,还包含了“我”的自传《追忆人生路》、“我”在写作时摘录的一些笔记和关于爱尔兰神话传说的部分习作,这几部分看似不相关的内容被奥布莱恩打碎并分散在小说的各个部分。这种“片段节选”式的呈现方式为这部作品带来了迷宫一样的叙事结构,小说中的人物不断进行“跨层”,多层的故事在作者的“搅乱”下,形成了《双鸟渡》情节与话语层面的“陌生化”。
《双鸟渡》自1939年出版后,直到2019年才出版了中译本。在国内的研究仅有陈永丽的《〈双鸟戏水〉的后现代主义手法研究》的硕士论文,陈永丽从元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戏仿和不确定性四个层面探究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笔者认为《双鸟渡》中存在大量的“非自然叙事”,即突破了传统非虚构小说的“摹仿”框架。本文采用叙事学中经典的“故事”和“话语”双层模式,从故事层面的非自然叙事和话语层面的非自然叙事进行文本分析,并考察作者的用意。
三、话语层面的非自然叙事
(一)谜面交织的话语
俄国形式主义最早提出了“法布拉-休热特”双层叙事理论。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法布拉是故事素材的集合,休热特是作家对素材的重新排列;托马舍夫斯基认为法布拉是按照自然时间因果顺序排列的事件,而休热特是对时间顺序的重新排列。之后的叙事学理论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整个叙述学体系,建筑在这个双层模式上面,无法回避。”[6]120因为这两个术语发展出了非常多的翻译方式,为了避免混淆,本文采用“故事”对应“法布拉”(Fabula),用“话语”来对应“休热特”(Syuzhet)。
“话语”是指作家对素材的重新排列。尚必武指出,在自然叙事中,话语为了建构故事,通过改变素材顺序的方法而达到一定的效果,在非自然叙事“话语自身却成了被传达的内容……在非自然叙事中,话语颠覆或消解了故事。话语颠覆故事的手段就是一系列反常的叙述行为。”[7]100奥布莱恩的《双鸟渡》文本内容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大学生“我”的自传《追忆人生路》;“我”创作的小说:包括一小部分摘录、爱尔兰神话传说相关的习作和以德尔莫特·特雷利斯为主角的小说;特雷利斯创作的小说;特雷利斯的“儿子”奥立克创作的小说。奥布莱恩将这些内容打散并拼接在一起,小说的情节随着作者的思维而跳动,这样的叙事手段打破了整个故事的连贯性,还给读者留下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关于“双鸟渡”题目的内涵、爱尔兰神话中的人物再现的意味等等,奥布莱恩只是在不停地向读者抛出谜面,读者没有寻觅到谜底的时候新的一轮谜面再度展开,每一件事情构成的谜面交织起来构成了叙事的迷宫。正如特雷利斯笔下的角色沙纳汉说:“不过比起答案,我更喜欢问题本身。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问题为学术探讨提供了无限契机。”[8]311而在小说中,“问题”为小说的结构提供了无限契机。在小说的开端,“我”提出小说要有三个开头,并用麦克菲里、弗里奇斯和芬恩三个人物开了三个头;在“我”的练笔中,“我”模仿了古爱尔兰神话的叙事口吻讲述芬恩的故事;又通过芬恩之口,引出了疯国王斯威尼的故事,并用大量的诗句和华丽的词语展现出来;在斯威尼的故事中,又插叙了诗人威姆·凯西,并通过凯西的诗歌将“我”在现实生活中喝的波特普啤滑稽地插入到特雷利斯的小说中;在善灵寻找恶灵并集结来自不同故事的角色前往红天鹅旅馆的故事中,善灵与恶灵关于奇数、真理和袋鼠的争论不断地穿插在故事中,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出结论,而是像一张网一样无限地延展开来;而在小说中的“问题”是:为什么小说的角色能够反过来审判书写他们的作者?属于不同层次的故事中的人物,他们为什么会相遇?来自不同故事、被“借”来的各色人物,他们在《双鸟渡》中起到什么作用?他们的身份有什么隐喻?但是奥布莱恩并不向读者展示这些谜面的谜底,而是不断地编织谜面,甚至到了故事的尾声,读者也很难在文本中寻找到答案。
《双鸟渡》中多样的叙事风格、互相交叠的片段,前后矛盾的情节以及陌生化的叙事手法在话语层面产生的功能颠覆了故事本身所展示的内容。奥布莱恩片段式的叙事和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将一个个的“问题”摆出,读者跟着作者天马行空般的思维在问题构成的谜面之间穿梭,“作者带着我们在其中穿梭,而穿梭的过程本身即是目的。”[8]411在特雷利斯的小说中,他笔下的角色们反叛并审讯他的过程,其精彩程度胜过他小说中本来的内容,对话语的处理正是作者向我们展示的关键;同时,奥布莱恩在处理道德上的二元问题时也并没有“答案”显露,如特雷利斯笔下试图营造的“恶”与角色们试图回归本真的“善”之间的冲突、彬彬有礼身形庞大的恶灵和窘态尽显有身无形的善灵的对立等等,他们的出现并没有为故事下一个定论,而是在含糊不清中展现了其中的矛盾。奥布莱恩的小说在话语层面的胜利掩盖了故事本身所要展现出的内容,使得故事的完整性和自然性都受到了挑战。
(二)元叙事与小说的糅合
“元小说”(Meta-fiction)通常指“小说自己谈论自己”。[6]299威廉·加斯(William H. Gass)在《小说和生活图案》中将其定义为“把小说形式当作素材”的小说。王丽亚认为元小说试图在叙事结构上建立“自我指涉”(Self-reflexivity):“不仅强调故事及其叙述行為的虚构性,而且通过模糊叙述者与故事、读者之界限,使读者拒绝认同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性和权威性。”[9]35元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手段,赵毅衡认为“它的‘非现实不是在内容上,而是在形式上,它在叙述方式上破坏了小说产生‘现实感的主要条件。”[6]300在《双鸟渡》中,叙述者“我”的传记里,不断夹杂着“我”撰写小说、思考小说的过程,奥布莱恩在这里将小说和撰写小说的过程一并展现,小说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在虚构性和非虚构性之间划清了界限。“我”在撰写传记和小说的同时,会将一些笔记和摘录一同置入文本中,其中这些看似不影响小说情节的片段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写作。“我”在与朋友们进行了关于文学的讨论后,单独记录下一段“阐释的性质”:
“一部小说的作者若是不择手段的,小说就有可能是暴虐专横的。面对疑问,我们可以说一部令人满意的小说应当让读者一看便知是编造出来的,读者愿意相信多少,可由自己控制。若是强迫笔下角色彻头彻尾都好、都坏,或是从头到尾总受穷、总享福,那是不民主的……角色应当可以在书与书之间相互串换。现存的文学作品应整个儿被视为一座灵薄狱,有洞见的作家从中按需挑选角色,现成的傀儡里挑不出合适的,再去创造也不迟……只需对过往作品旁征博引,读者便能即刻了解每个角色的特点,不必再劳神解说。”[8]37
在这一段论述中已经能够得到后文有关“我”的小说的情节暗示,特雷利斯因为要创作一部主题为“恶”的小说,就让角色们扮演恶棍、恶灵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与反抗,因为很多被特雷利斯“借”来的角色本不是恶人,也不愿意作恶;来自不同故事或神话传说的弗里斯奇、沙纳汉和芬恩等人汇集在同一部小说中反抗特雷利斯,他们都十分清楚自己是小说中的人物,还要在表面上迎合掌管他们的作家特雷利斯。奥布莱恩在这里将“我”的传记和小说穿插在一起,将小说的创作过程、创作思路展露出来,即元小说的“自我指涉”便显露出来。这样元小说颠覆了传统非虚构小说的摹仿框架,创造出违背小说自然化的叙事。如在特雷利斯的“儿子”奥立克出生时,“我”突然中断了关于他出生情形的描写,并插叙描写这一部分遇到的难题和思辨的过程:
“关于结构上或者说论证上遇到的难题:如何艺术地处理并描写特雷利斯先生私生子的出生过程,这项任务无论是从技术角度、结构角度还是艺术角度上看,我都感觉困难重重……宣告自己无能为力,是在我决定删除一段十一页纸长的内容之后。这段内容浅谈孩子如何出世以及孩子与憔悴的母亲如何悲伤地谈论他的父亲——只要是读过的人,都认为实在乏善可陈。”[8]269
“我”在这里删除了小说中感到棘手的部分,并向读者解释原因,这一行为的突然出现让本来“乏善可陈”的情节变得引人注目。“我”在这里将自己对这部分情节的构想和与朋友们的讨论都展现了出来,即使这一部分已经被省略,但是可以从插叙部分的讨论看出“我”在撰写小说时的细致考虑:人物的外形、情节连贯等等因素,最终“我”决定避免耸人听闻之嫌在此处不多加描写。
在奥立克惩罚“父亲”特雷利斯的过程中,他主要通过写小说的方式来复仇。奥立克在写作期间,除了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下之外,还不断地融入其他角色们的意见。奥布莱恩在这一部分还将围观创作的其他角色的意见和讨论展示出来,正是因为角色们有不同的意见,奥立克为惩罚父亲的小说写了三个开头,并听取不同的建议不断地修改小说。在《双鸟渡》中,小说主体和作家创造构想小说的过程这两部分内容交替穿插,放置在同一文本中,作者打破了自然叙事的连贯性,将属于不同叙事层次的片段糅合,并将小说的虚构性通过自我指涉、自我意识展示出来。小说还交叉使用了不同的叙事媒介,如新闻稿、诗歌、手稿和传记等形式混杂在一起,在话语层面建构了非自然的叙事结构。
四、故事层面的非自然叙事
(一)不可能世界
“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最早由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提出,最初是用来回答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神学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不矛盾且合乎逻辑的事物都可以组成可能世界。[10]13-15随后可能世界理论作为一个哲学研究问题被哲学家们讨论,其成为理解探索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相互区别的一个工具。在叙事学中,可能世界理论最早由卢波米尔·道勒齐尔(Lubomiír Dolezêl)引入,他认为文学所建立的世界并非是对真实世界的摹仿,而是建构了一个有独立存在的可能世界;玛丽-劳尔·瑞恩(Marie-Laure Ryan)融入了技术与符号等相关理论,是可能世界叙事学理论的集大成者;[11]可能世界理论在认知叙事学方面有较深的影响,如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从认知叙事学的角度提出了“故事世界”(Storyworld):“对叙事的理解需要根据文本线索和它们所带来的推论来重建故事世界。”[12]对故事世界的理解需要借助作者的语言文字和读者的认知框架,再建构一个合乎“可能世界”的世界。
与可能世界相对应,阿尔贝提出了“不可能世界”,涵盖了可能世界之外的不合常规、不合逻辑的事件。阿尔贝的理论的依据是可能世界理论与逻辑规则的联系,让可能世界无法呈现出不符合逻辑规则的世界。在《非自然叙事:小说和戏剧中的不可能世界》一书中阿尔贝详细阐述了非自然叙事的“不可能世界”,他认为非自然叙事是指“表示身体上、逻辑上和人类不可能的场景和事件”,[3]436这一概念正与不可能世界相联系,阿尔贝将非自然叙事等同于小说中不可能世界的构建。《双鸟渡》正是建构了一个结构多变、人物众多、故事荒诞的不可能世界,本节从事件、时间、空间和人物四个维度来探究《双鸟渡》在故事层面的非自然性。
(二)不可能事件
不可能世界在有科学和逻辑的真实世界中无法实现,但是在想象的文学世界中可以存在。特雷利斯在创作他的小说时不仅会借用其他小说中的角色,还会自己“生产”出角色来,弗里斯奇便是特雷利斯打破了自然繁殖规律诞生的人物。“旅馆业主德尔莫特·特雷利斯先生顺利产出一位名叫弗里斯奇的男人。据称,这位新生儿状态相当好,个头五尺八,身材魁梧。”[8]66这位新生儿不仅拥有成年男性的体格,而且在文化知识方面也不逊色;特雷利斯还让自己的夫人诞生了一名只活了六天的中年西班牙人;他自此还发展出一套“自体繁殖理论”,他实现了无须受精受孕的人类繁殖,打破了“降生必是人之初”这一惯常的观念;他还认为人可以繁育出适龄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类,比如弗里斯奇,这样可以减少人类因为抚育孩子而出现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文明时代,将孩童抚养成人是乏味且不合时宜的。”[8]67不仅是弗里斯奇,特雷利斯强暴笔下的角色而出生的“儿子”——奥立克也是如此。虽然作者“我”删去了对他出生过程的描写,但是奥立克在诞生后直接映入读者眼帘的形象是“一个矮壮的青年男子”,脸上的粉刺“每个都有六便士那么大”,他还继承了父亲嗜睡的习惯。特雷利斯对于传统自然繁殖观念的颠覆打破了一般的认知框架和逻辑规律,在不可能世界中建立了自己的繁殖理论,并在小说中实行。
(三)叙事分层与叙事跨层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知,《双鸟渡》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虽然在结构上这些故事被碎片化地混合在一起,但是每一个故事都应归属一个清晰的叙述层次。赵毅衡为叙事分层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上一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下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或叙述框架。”[6]264也就是说,处在高层次的叙述者为处在低层次的叙述者创造了故事框架,而叙事行为是在被叙述的事件发生之后才能进行的,所以叙事层次越高,时间就越靠后。奥立克作为特雷利斯在其小说中“诞生”的儿子,应该与特雷利斯分属于两个叙述层次,特雷利斯属于高叙事层次,他创作的小说为奥立克的故事创造了框架。但是,在特雷利斯笔下的角色们对他表达不满时,处在低叙事层次的奥立克通过写小说来干扰处在高叙事层次的“父亲”,他将自己的父亲写进法院并接受法官和书中其他角色的审判,这时,奥立克笔下的小说与其父亲的叙事层次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也就是说,对特雷利斯的惩罚是现在进行时而不是过去时。在奥立克笔下对“父亲”的审判中,法官召集来了书中所有的角色来作证词,不仅有特雷利斯在此本小说中的角色,还有和特雷利斯处于同一个叙事层次的作家特雷西,甚至还有特雷利斯另一部小说《禁闭之禁地》中会说话的奶牛以及“我”笔下的习作主角芬恩和从芬恩的讲述中提到的疯国王斯威尼也参与到这场审判中,在这里就引出了“叙事跨层”的概念,即突破叙事分层之“隔”而连接处在不同时空的文本。由于叙事层次越高,时间就越靠后,所以高层次跨越到低层次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如果低层次跨越到高层次,那么会出现时间悖论。《双鸟渡》打破了现实世界的自然线性时间观,奥立克的复仇计划以及角色们与作家特雷利斯共住红天鹅旅馆等现象,正是体现了小说中的时空交错引起的时间与空间的不可能与非自然现象。
《双鸟渡》中存在着许多时空交错的跨层的现象,如在已故小说家特雷西的小说中,角色沙纳汉、鼻涕虫威拉得和小矮子安德鲁斯三人接受作者特雷西委派的任务到林森德去放牛,这时另一个和特雷西处在同一叙述层次的作家亨德森在写一部关于牛贩子运牛的书,他派遣小说中的角色莱德·基尔赛盗取了特雷西小说中三人组的牛,两部出自不同作家的小说中的人物在此产生了冲突,在准备交战时,鼻涕虫还叫来特雷西另一部小说里的印第安人来帮忙。分属于不同层次、不同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在此汇聚,阿尔贝提出的“本体越界”(Ontological Metalepsis)在小说中形成了打破摹仿框架的跨层叙事;特雷利斯将自己笔下的角色们都安排到红天鹅旅馆中入住,以便更好地监视他们,而笔下的角色们都十分清楚自己是虚构小说中的人物,他们用安眠药让特雷利斯长久地沉睡,以便自由活动和寻找时机反抗特雷利斯,这违背了自然的空间观,属于“逻辑上的不可能”。处在小说内部的人物可以与作者同住在一个空间内,并从低层次跨越到高层次中干预小说情节的发展;这一系列时空交错的现象向读者展示出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能世界,体现了小说反摹仿的特点。
(四)不可能角色
角色是叙事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元素,阿尔贝认为在非自然叙事作品中,非自然角色涵盖了许多不合常理的存在,他考察并概括了五种主要非自然角色:人类和动物混合体、死去的角色、类机器的人类和类人的机器、变形的人物和同一人物的多种版本。《双鸟渡》里特雷利斯的小说中有一对对立的角色——善靈和恶灵,恶灵是弗古斯·麦克菲利梅,他有着庞大的身躯和三条尾巴,他在特雷利斯笔下被带上了“恶”的属性;而善灵,是一个有身无形的存在,他经常藏到恶灵的口袋里,所有第一次听到他说话的角色都会大吃一惊,因为没有人能看见他,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善灵本是为了引导特雷利斯的儿子奥立克出生的,但是因打牌输了又放不下脸面而只好把引导权交给恶灵。与善灵的不守信用相对,恶灵反而彬彬有礼,处处显示着绅士的一面。非人的非自然角色在小说中背负起架构荒诞主题的功能,也引起了关于善与恶二者的思考。从芬恩的讲述中进入故事的疯国王斯威尼,他因为亵渎圣物而被诅咒变为飞鸟,他有着飞行能力和人类的思维,属于人与动物形象的混合,他栖在树枝上吟诵着一首首诗歌;他还能够一口气跳跃过五个郡,漫无目的在空中游荡,他虽然疯癫,但是仍有自己的自由,他可以“远离人类虚妄的嘈杂”[8]138。但是他在恶灵一行人前往红天鹅旅馆途中从树上跌落下来,浑身是伤,虚弱不堪,他吟唱的诗歌越来越接近世俗话语,他的伤也没办法让他重返天空。人与鸟类结合的非自然角色斯威尼,正是失去了“飞行能力”而跌入了人类的嘈杂世界,也正是自由难觅、世俗难脱的写照。
五、结论
奥布莱恩的《双鸟渡》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小说,其中不仅有作者别出心裁的叙事手法,还有爱尔兰神话传说穿插其中。综上文分析,《双鸟渡》有着非自然叙事的特征。首先在话语层面,谜面交织的叙事迷宫正是奥布莱恩想要向读者展示的重心之一,自我指涉的元小说正是小说直指虚构打破摹仿的叙事手法;其次在故事层面,阿尔贝的“不可能世界”在《双鸟渡》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其中包含了故事情节、故事时间、故事空间和故事角色的非自然。这部20世纪出版的小说在故事和话语层面都别开生面地有所创新,非自然的叙事手法也正是奥布莱恩突破传统的尝试。
作者简介:王晓宇(1996—),女,甘肃白银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叙事学。
参考文献:
〔1〕尚必武,布莱恩·理查森.非自然叙事学及当代叙事诗学:布莱恩·理查森教授访谈录(英文)[J].文艺理论研究,2012,32(05):110-114.
〔2〕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3〕尚必武.非自然叙事学[J].外国文学,2015(02):95-111;159.
〔4〕[爱]弗兰·奥布莱恩.双鸟渡[M].韩慕照,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
〔5〕王丽亚.“元小说”与“元叙述”之差异及其对阐释的影响[J].外国文学评论,2008(02):35-44.
〔6〕李维,扬·阿尔贝非自然叙事理论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7.
〔7〕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的理论模型[J].国外文学,2010,30(01):3-10.
〔8〕陈永丽.《双鸟戏水》的后现代主义手法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7.
〔9〕李敏锐.萨尔曼·拉什迪小说中的非自然叙事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7.
〔10〕尚必武.什么是叙事的“不可能性”?——扬·阿尔贝的非自然叙事学论略[J].当代外国文学,2017,38(01): 131-139.
〔11〕尚必武,不可能的故事世界,反常的叙述行为——非自然叙事学论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01):8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