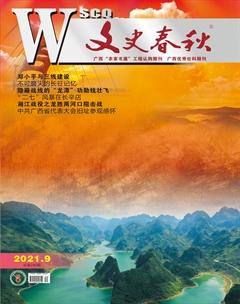刘鼎与埃德加·斯诺的交往
郑凡
了解中共党史的人大概都听过刘鼎这个名字,他原名阚思俊,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就入党的老革命家。他早年在德国留学期间,经由朱德介绍入党,后由德国转去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1930年秘密回国,加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之后,刘鼎还曾担任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之间沟通的“信使”,在西安事变前后做了大量细致而卓著的工作。刘鼎这个名字,就是他去西安后开始用的。
在东北军工作期间,刘鼎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相识,并与其结下很深的渊源,甚至《红星照耀中国》(中文名《西行漫记》)一书的面世,也与刘鼎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
刘鼎与斯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6年的3月下旬,当时刘鼎刚从九江敌营逃脱出来,潜回上海后,一时无法找到组织,便蛰伏在同情中国革命同时也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中,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刘鼎后又在上海的宋庆龄家中躲了几天。
刘鼎的经历和学识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当她得知张学良在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希望中共能派人到西安与他接触时,便毫不犹豫地将刘鼎介绍给了当时的中间人董健吾。
刘鼎在与董健吾见面会谈之后,反复思考,认为这是一个在国难当头之际向手握重兵的张学良陈述政见、宣传抗日的机会,于是义不容辞地接下这份工作,毅然踏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
临行之前,宋庆龄希望刘鼎此行能带上两位外国友人一起前往,在西安尋找机会把他们送到陕北苏区。其中一位外国友人便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他是当时英国《每日先驱报》的驻华记者;另一位是新西兰医生海德姆(即马海德)。作为活跃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他们都希望能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
由于刘鼎与斯诺他们彼此都不曾见过面,便通过董健吾与他们约定车次与时间,在火车上见面。顺利见面后,经过3天辗转的车程,一行人终于到达西安。刘鼎安排斯诺与马海德在当时西安最高级的宾馆西京招待所住下,便前往位于玄风桥金家巷一号的张学良公馆,拜访张学良。
刘鼎与张学良见面后,交谈得很愉快,同时还得知一个令他十分欣喜的好消息:不久前张学良已经两次去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会谈过,并且约定了与周恩来的肤施(今延安)会谈。刘鼎急于找到组织,便向张学良坦诚自己也想随他一起去洛川的愿望,张学良一口答应,并表示当天就可以与他同去洛川,随后前往陕北。刘鼎没有想到事情竟然这样顺利,仓促之下,加之又是秘密行动,他来不及向还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斯诺和马海德两位友人道别,也没能给他们之后的行程做任何安排,就连忙与张学良一起坐上了飞往洛川的飞机。
斯诺与马海德并不知道刘鼎到西安后的情况,他们在宾馆等了好几天,没有接到什么消息,钱差不多花完了,也无法联系到去陕北的途径,只好原路返回上海。但斯诺他们不知道的是,刘鼎在肤施会谈后,跟随周恩来到瓦窑堡,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过程中,就已经将一位外国记者与一位外国医生与他一同到西安,并想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这些情况一一做了说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斯诺回到上海后,对此次没能如愿进入陕北苏区很不甘心,他再次拜访宋庆龄,留下了一份有11个问题的预采访清单,包括诸如红色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平等条约的方针政策,对日本、英国、美国和苏联的政策以及能否与他们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等问题。
这份采访清单于1936年5月中旬传到了陕北苏区,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专门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了此事,对斯诺的问题做了认真的答复准备。在中共中央看来,虽然当时国民党有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但如果有外国记者可以把共产党的活动与主张如实地在国外媒体上发表,那么国民党长久以来对共产党的一切污蔑与造谣自然会不攻而破。1936年5月底,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代表冯雪峰将斯诺想要进入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写信报告给中共中央,并请中央派人对他们的行程给以妥善安排。
二
1936年6月12日,斯诺第二次到达西安,接待他的依然是刘鼎。此时,刘鼎的公开身份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实际上是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全面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是斯诺此次陕北之行的“护航员”。
刘鼎与斯诺两位老相识再次见面,自然是十分高兴。刘鼎安排斯诺住进西京招待所后,为妥善保险起见,他找到张学良商量,能否用私人飞机将斯诺送到延安,但张学良认为用飞机送外国人过去实在太过显眼,建议用卡车。刘鼎转而找到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与他商定用六十七军来往于西安与延安之间的军用卡车送斯诺前往苏区,出发在即又因为连日大雨交通中断,在西安延宕了数十日后方才成行。
斯诺利用在西安的这段时间,在刘鼎的安排下游览了大雁塔、碑林、开元寺等名胜古迹,采访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军政要人,收获颇丰。7月初,刘鼎接中共中央的通知前往安塞开会,在会上将斯诺等人的行动安排报告给中共中央,中央据此安排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到苏区的前沿白家坪,以做好前期的迎接工作。
7月13日,历经波折的斯诺终于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并参加了为他举行的欢迎晚会。斯诺抓紧时间对毛泽东等人进行采访,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搜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按照计划安排,接下来的8月下旬,斯诺去了在豫旺堡的彭德怀指挥部,然后去陕甘革命根据地西部前线采访。斯诺原本计划用1个月的时间完成他在前线的采访工作,但没有想到去了之后,想要采访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一直到了9月底,才带着大包的资料和红军战士送给他的许多纪念品,从前线返回保安。
斯诺在前线采访期间,他的夫人海伦也来到西安,海伦找到刘鼎,希望通过他的协助将自己也送到陕北。刘鼎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中共中央后,得知斯诺还未从前线返回,并不在保安,考虑到当时情况复杂,海伦去保安可能会迟滞斯诺从陕北返回的行程,加之交通也十分紧张,刘鼎便劝海伦先返回北平,并安排了她与张学良的会面。张学良在与海伦的会面中明确地表达了他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意见,海伦回去后将这次的谈话发表在美国报纸上,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
斯诺回到保安后,毛泽东花了几天时间与他彻夜长谈,斯诺得到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被毛泽东身上革命者的气魄与天才的政治军事智慧所折服。随着战事转急,毛泽东几次致电刘鼎,希望安排斯诺尽快离开苏区,刘鼎接到电文后,催请张学良派车赴洛川将斯诺接回。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为了安全,他在红军控制的地域一路步行到甘泉西北的下寺湾,然后由刘鼎安排的人接应到洛川东北军驻地,一起乘坐卡车返回西安。
斯诺在陕北苏区待了100多天,采访内容写满了14个笔记本,收获了丰富的一手访问资料,第一次拍摄到中共苏区真实而珍贵的照片。为了防止这些资料在路上被宪兵搜查出来,斯诺把它们都放在一个手提袋里,然后将手提袋放在车厢后的一个麻袋里,与其他麻袋以及一些破损枪械混在一起。本以为如此安排万无一失,没想到军车路过咸阳时,将所有的麻袋和待修枪支都卸在了当地一个军火库里。斯诺到西安下车后才发现装着手提袋的麻袋不见了,当下急得不得了,等候在一旁负责接应的刘鼎得知这一意外变故,赶忙一边安慰斯诺,一边要求司机带着他原路返回军火库寻找。司机见天色已晚又加上长途疲累,本想推脱到第二天再说,刘鼎知道事关重大,果断要求立刻返回,无论如何要将斯诺的包找回来。
三
关于这一段资料遗失的波折,斯诺在后来的日记里写道:“我一夜合不上眼,担心那手提袋被国民党宪兵发现并没收了,第二天黎明时分,我的朋友带着原封不动的手提袋踉踉跄跄地走进来了……”他所写的这个朋友,正是不遗余力帮他把手提袋找回来的刘鼎。而刘鼎之所以是“踉踉跄跄”走进来,除了他毫不停歇的一路奔波之外,还因为他们刚一进城,就遇到突发事件——蒋介石突然飞至西安视察,通往西安的公路都换由蒋介石的卫队站岗,一切交通陷入停顿,西安也关闭各处城门,开始戒严,如果稍微晚一点,他们的卡车就没法通过重兵把守的机场公路了,斯诺的资料还能不能安全带回西安也是个未知数,这一路的情况危急程度可想而知。
一年后,以这次采访为底稿成书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一个月内就重印了5次,很快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共产党和红军再也不是国民黨宣传的妖魔化的“土匪”,而是一群有血有肉、有远大理想、有救国使命的战士,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那张照片更震撼无数人,国民党口中的“匪首”竟然是这样一个神采奕奕的青年人,在延安那破旧的窑洞前,他坦然深邃的眼神中根本看不到任何的窘迫,反而是笃定了未来的胜利必定属于他们。《红星照耀中国》像一盏明亮的灯,指引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出路的年轻人走向光的来源——陕北。
刘鼎在送斯诺离开西安时,一再地叮嘱他:“你可以写其他的人,但一定不要写我。”对于刘鼎来说,保证斯诺安全地进出陕北苏区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他必须要完成好。斯诺知道刘鼎工作的隐秘性,答应了他,在书中只字未提刘鼎的名字。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段历史才慢慢浮出水面,1970年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时,还向相熟的人打听刘鼎的情况,但遗憾的是两人没能见到面。
斯诺整个陕北之行,都与刘鼎有直接的联系:斯诺前往陕北苏区时,刘鼎负责为他疏通往返路线、保驾护航;斯诺离开陕北时差点将自己采访的手稿与资料丢失,刘鼎竭尽全力帮他找回。这部在国民党高压封锁下真实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真实情况,被译为20多种文字,轰动世界的不朽名著,在时局纷乱、前路晦暗之时,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如果不是刘鼎在深夜里找回这份“无价之宝”,这本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也许无法为广大读者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