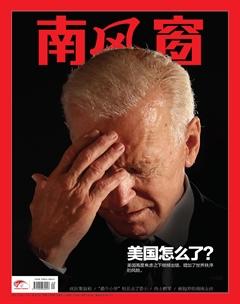谢英俊,六十七岁的“三岁小孩”
姜雯

2021年8月28日,中国台北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牌楼前,“大眾葬文化行动祭”活动正式开启了为期10天的长跑,其间包含各种讲座、行动艺术、展览、表演等。
“大众葬”源于1931年蒋渭水医师因染疫(伤寒)而亡,他的支持者们藉由他的去世而举办了一场陈情抗议活动“大众葬”。在蒋渭水去世90周年后的8月,台湾仍笼罩在新冠疫情之下,这次的“大众葬”就是为了“让往生者生产力量,让无力者说话”。
而这次所有的活动,都举办在一个造型独特的巨型黑色帐篷之下— “大众帐”。这顶帐篷长72米、宽24米、高5米,是由谢英俊带领的“第三建筑工作室”的二十几个实习生,用了一个晚上搭建而成。
当天因为难以预料的强风和过于光滑的地面,而致使搭建帐篷时遇到一些挑战,后来他们增加了一倍的配重,让这顶巨型帐篷顺利完工。黑色的遮光网在风中摇曳,它不仅为前来参加活动的人遮阳,更是为了“庇护在疫情中冤死的亡魂”,谢英俊说。
谢英俊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建筑设计师,1954年出生于台中县和平乡,1977年从淡江大学建筑系毕业,尔后从事建筑业多年,其中包括“新竹科学园区”厂房的建造。
台湾在1999年发生“921大地震”之际,谢英俊受朋友之邀前往南投日月潭邵族部落进行灾后重建,也于此开启了让当地人“自己盖自己的房子”的“协力造屋”理念,他开发出的“轻钢架型式”自由、简单、成本低,当地民众还能因地制宜,用当地的材料打造符合需求且环保的家园。
2004年谢英俊认识了大陆“三农”学者温铁军,开始在大陆的农村推广他的建筑理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谢英俊更是进入四川偏乡协助灾后重建;2009年台湾发生“八八水灾”,谢英俊帮忙800多户住民重建。
多年来,他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农村,中国的河北、河南、四川、西藏等地,还有尼泊尔、加纳、芬兰等国。若不是此次疫情将他“困”在台湾,南风窗特约记者大概也很难有机会采访到这位六十七岁的“三岁小孩”。
自己的房子自己盖
我见到谢英俊的时候,他戴着一顶圆帽,白色的头发在脖子后面扎成一个短马尾,穿着简单的T恤,指挥着年轻的学生们固定被大风吹得摇曳的固定杆。烈日之下,脸上的皮肤被晒成了发亮的古铜色。一夜没睡,却还精神抖擞的模样。
我向他约访,“现在就可以啊”,他像个身经百炼的老将军。
“这么随性的吗?”我显得有些讶异。
“对啊,很随性啊。”他笑起来。“过两天就要回去日月潭,不在台北了。”我说我可以去日月潭找他,他说“随时都可以”。
9月1日一早,我接到了谢英俊打来的电话,他说要回去日月潭的工作室,参加实习生的“结业报告”。说走就走,我匆匆忙忙收拾了行李,跟随他一路开车南下,3小时的路程,谢英俊说,不讲话的话开车很容易打瞌睡。
爱开玩笑、对大陆的历史和地理比我还熟稔—我与谢英俊聊天时常常有种“答不出考题”的感觉。而我们要去的他位于日月潭的“第三建筑工作室”,正是位于“921大地震”所重建的邵族部落内。
“第三”其实有着多重意涵。一个是“第三世界”,正如中国曾经自认是第三世界国家;二是来自南美洲的“第三电影”概念,有别于欧洲强调个人虚无价值体系跟好莱坞体系的电影;三是“跟传统和现代两边都不搭”,如今人们既抛弃传统、又离现代性很远。
“我讲的现代性,是欧洲特殊时空之下产生的一个文化价值体系,跟我们现在所讲的现代性是不同的价值体系。那是一种很纯粹的现代性,我们现在还够不到。”
这就要回归到谢英俊的“协力造屋”理念,他认为,如今我们盖房子的权利被剥夺了,但盖房子本身就是一种人权。而“协力造屋”,就是把盖房子的权利还给住民,让人们可以“自己盖自己的房子”。
“协力造屋”,就是把盖房子的权利还给住民,让人们可以“自己盖自己的房子”。
“921地震后,我协助参与重建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前原住民部落或农村,房子都是自己盖,那现在为什么没办法自己盖呢?而且遭遇地震后,大部分工作都停了,都在那边等人家帮他盖房子,但你要付钱啊,又没钱。我就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他们本来会盖房子的,用传统的方式盖房子没问题的,但是他用新的方式就不会了。所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是我们整个工业体系、建筑体系,甚至各个领域,一种让人失能的状态。所以我们能不能把自盖房子那种状态找回来?”
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用最简单的技术,让“盖房子”这件事变得“常民化”,一般人都能动手参与。
谢英俊开发的“轻钢系统”有别于一般盖房子所用的钢筋混凝土,他把技术简化到“老人小孩只要会拧螺栓”就能盖的状态,盖房子的过程中也不需要“焊接”,轻钢架本身是镀锌的,这样就能做到非常好的防锈功能。别以为“架子”不牢固,在里面灌浆后结构非常坚固,比钢筋混凝土的房子更能起到抗震的效果。
技术只是外在的,重要的是当地住民“自己盖自己房子”的过程。就像我们即将到达的日月潭邵族部落,整个部落40多户人家,就是“921地震”后邵族原住民自己盖起来的。屋子内部是轻钢架,外部则用竹片、木头等搭构。虽为“重建”,但房子不会像是单一无趣的流水线作业,房屋保留了邵族人的传统、文化和特色,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岁月流淌过后静谧又活泼的生活气。
黄昏下,车窗外流过日月潭透亮的水,我们驶入山上的邵族部落,车一进去,住民们都向谢英俊挥手打着招呼。对于蜗居于城市水泥森林的我来说,已经好久未见这般的“亲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