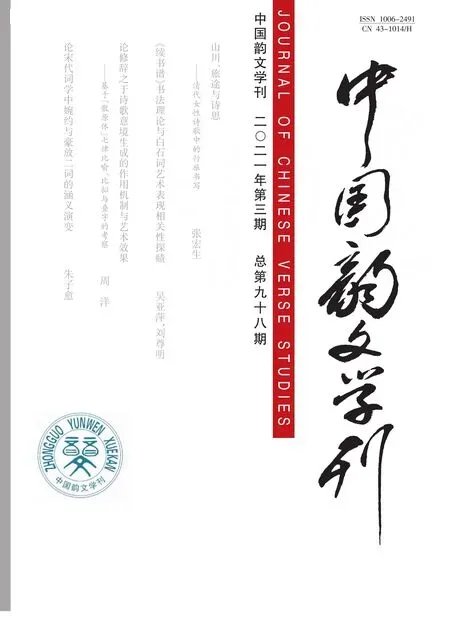口头上的诗歌小集
——元白吟诵小集与伎唱小集的形成与流传
沐向琴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说:“夫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斯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文学,唐诗宋词元曲,皆所谓一代之音乐文学也。”唐诗作为唐代文学之代表,与音乐的关系密切,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云:“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咏以永其言,吟以伸其郁,叹以抒其伤,唱则吐于喉吻,弄则被诸丝管。此皆以其声为名者也。”唐人的诗歌在当时可以被吟诵、被歌唱,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吟诵的主体可以是任何人,歌唱的主体则主要是懂得音律的乐人。朱光潜先生曾对诗歌歌唱与吟诵这两种方式加以区别:“文人诗虽不可歌,却仍须可诵。歌与诵所不同的就在歌依音乐(曲调)的节奏音调,不必依语言的节奏音调;诵则偏重语言的节奏音调,使语言的节奏音调之中仍含有若干形式化的音乐的节奏音调。”元稹和白居易在交游过程中经常吟诵对方诗歌,他们与乐人也多有来往,诗歌被传唱的情况很多,为元白吟诵诗歌小集与伎唱诗歌小集的形成与流传创造了条件。
一 吟诵诗歌小集
吟诵作为诗歌鉴赏活动,深受诗人喜爱,频繁出现在元白的诗句中,如白居易《江上吟元八绝句》云:“大江深处月明时,一夜吟君小律诗。”《吟元郎中白须诗兼饮雪水茶因题壁上》云:“吟咏霜毛句,闲尝雪水茶。”元稹《和乐天感鹤》云:“吟君《感鹤操》,不觉心惕然。”《酬乐天书怀见寄》云:“况我江上立,吟君怀我诗。”元白吟诵他人或自己诗歌的情形还有很多。吟诵诗歌既是文学鉴赏活动,也是诗人之间交流情感的重要方式,元白经常吟诵对方诗歌以寄托思念之情。

从“把君诗卷灯前读”“吟君数十篇”等诗句,可以看到两人吟诵对方诗歌的细节。白居易所吟的元稹诗歌,不是一篇两篇,而是以“诗卷”“数十篇”的状态出现的,说明这些可能是元稹诗歌小集的最初形态。这些诗卷的形成过程可能有两种情况。(1)元稹的诗歌本就是以编辑好的状态寄给白居易,编纂者自然是诗人自己。因为两人相距太远,书信往来所费时间太长,干脆将多首诗歌编纂成小集再寄赠给对方,纵向拓展文学交流的广度。元和五年(810),元稹被贬江陵,白居易仍在长安,这也是元白第一次长时间分离,白居易在此期间酬和元稹的诗歌中提到两地的距离是“荆州又非远,驿路半月程”。从长安到江陵,即使走驿路也要半月之久,也就是说,书信及诗歌传递到彼此手中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故自元稹被贬江陵之后,元白多以诗歌小集的形式寄赠唱和,大大促进两人唱和诗的创作与传递。(2)自元稹被贬江陵,后又被贬通州,白居易也被贬江州,元白只能通过书信往来互通有无、维系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收到对方寄来的书信及诗歌越来越多。为了方便随时欣赏和吟诵,白居易将元稹寄来的诗歌进行编纂,这就有了元稹诗歌小集的呈现。在第二种情况下,元稹诗卷的编纂者是白居易。不管是元稹自编诗卷寄给白居易,还是白居易编纂元稹所寄诗歌,元白唱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人诗歌小集的编纂。
上文推测白居易吟诵的元稹诗歌小集可能源于其代编而成,其实白居易确有为方便吟诵而编纂元稹诗歌小集的文学活动。元和十二年(817),元白各在贬地通州和江州。元稹在游览阆州开元寺时,题写白居易诗歌于寺壁以寄思念之情,并寄诗《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白居易在收到元诗后,作《答微之》酬和。且为了进一步答谢元稹题诗寺壁之举,白居易自编自勘元稹绝句小集,并制作成屏风置于座侧,方便随时吟咏鉴赏,其《题诗屏风绝句》诗及诗序详细记录了这次编集活动。白居易从元稹所寄数百篇诗歌中挑选出100首,因屏风尺寸所限,以短小的绝句为佳。选定诗篇后,又亲自抄写于屏风之上,经过仔细校勘,最终完成小集的编定与题写。从元稹前后寄诗给白居易多达数百首这一点来看,他们每次寄和的诗歌绝不止一篇两篇。白居易制作元稹诗歌小集屏风除了如诗人所说睹物思人、吟咏自解之外,还有传播元稹诗歌的目的,甚至有借此文人轶事扩大他们自身声名之故,如诗序末云:“前辈做事多出偶然,则安知此屏不为好事者所传,异日作九江一故事尔?”白居易吟诵元稹诗歌小集的情况还可见其《偶吟》诗云:“元氏诗三帙,陈家酒一瓶。醉来狂发咏,邻女映篱听。”这首诗写的是白居易醉后吟咏元稹诗歌小集的场景,诗中的“三帙”即三卷,明显是元稹的诗歌小集。
元稹也曾吟诵白居易诗歌小集。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作《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诗,寄赠给了包括元稹在内的多位友人,元稹以《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酬和,其诗序云:
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予司马通州,二十九日与乐天于鄠东蒲池村别,各赋一绝。到通州后,予又寄一篇,寻而乐天贶予八首。予时疟病将死,一见外不复记忆。十三年,予以赦当迁,简省书籍,得是八篇。吟叹方极,适崔果州使至,为予致乐天去年十二月二日书。书中寄予百韵至两韵凡二十四章,属李景信校书自忠州访予,连床递饮之间,悲咤使酒,不三两日,尽和去年已来三十二章皆毕,李生视草而去。四月十三日,予手写为上、下卷,仍依次重用本韵,亦不知何时得见乐天,因人或寄去。
元稹当时因身患疟疾从通州去往兴元疗疾,无暇酬和白诗。在疾病好转后整理书籍时,看到白居易前几年寄来的八首诗歌小集,情不自禁吟咏起来。适逢李景信自忠州来访,带来白居易去年书信及多首诗歌。好友久别重逢,更有白居易新寄赠诗,“连床递饮”之间,定少不了诗歌吟咏。元稹甚至大发诗兴,一次酬和白居易诗歌32首,并将其编纂成诗集。这也是元白唱和诗集编纂的开端。
除了吟诵对方的诗歌小集外,元稹与白居易也曾吟诵自己的诗歌小集。长庆四年(824),元稹在为白居易编纂别集《白氏长庆集》时,回忆两人在长安游玩的往事,作《为乐天自勘诗集因思顷年城南醉归马上递唱艳曲十余里不绝长庆初俱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夜后偶吟数十篇两掖诸公洎翰林学士三十余人惊起就听逮至卒吏莫不众观群公直至侍从行礼之时不复聚寐予与乐天吟哦竟亦不绝因书于乐天卷后越中冬夜风雨不觉将晓诸门互启关锁即事成篇》云:“春野醉吟十里程,斋宫潜咏万人惊。今宵不寐到明读,风雨晓闻关锁声。”诗题中“递唱艳曲十余里不绝”“偶吟数十篇”写的正是元白吟诵各自诗歌小集的多种场景。长庆初年,元白各从贬地回京并身居要职,久别重逢的喜悦和仕途上的意气风发,俱体现在春游城南和夜宿斋宫时的吟咏不绝。白居易《与元九书》亦记载此事:“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觉声者二十里余,樊、李在傍,无所措口。”元白在长达20多里路程中,各自吟诵绝句诗歌小集,而樊宗师和李绅等友人在旁却无从开口,可见元白对诗歌吟诵的熟悉与热衷。
元白诗歌小集的吟咏不仅存在于诗人之间,甚至上达宫廷禁内。白居易《元公墓志铭》云:“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元和末长庆初,元稹因唐穆宗索求诗歌而编集进献,因受献者身份高贵,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效果显著,进献诗集中的数百篇诗歌得到宫中人的吟咏传唱,甚至远传海外诸国。
诗歌小集的吟诵作为文学鉴赏活动,有时具有群体性特征。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序》云:“及足下到江陵,寄在路所为诗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为,章有旨,迨于宫律体裁,皆得作者风。发缄开卷,且喜且怪。仆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唯与杓直拒非及樊宗师辈三四人,时一吟读,心甚贵重。”在收到远贬江陵的元稹所寄17首诗歌小集之后,白居易与其他共同好友一起吟读,担忧的心情必然有所缓解。白居易还曾邀请元宗简共同吟咏元稹诗歌,其《雨中携元九诗访元八侍御》云:“微之诗卷忆同开,假日多应不入台。好句无人堪共咏,冲泥蹋水就君来。”诗人共吟友人诗歌,是集诗歌鉴赏、文学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活动,还能加深诗人之间的友谊。当有友人逝去时,诗人想到的是共同吟咏的人又少了一位。大和七年(833),白居易作诗《哭崔常侍晦叔》云:“丘园共谁卜?山水共谁寻?风月共谁赏?诗篇共谁吟?花开共谁看?酒熟共谁斟?”悼念去世的崔玄亮,为无人共同吟咏而叹息。
二 伎唱诗歌小集
吟诵诗歌小集产生于诗人之间的交游活动,伎唱诗歌小集则产生于诗人与乐人交往过程中或乐人传唱过程中,乐人对文人诗歌的传唱起关键作用。
元白诗歌在当时流传于市井坊间,连乐人也争相传唱,乐人传唱他们诗歌的记载有很多。白居易《竹枝词四首》其四云:“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又《闻歌者唱微之诗》云:“新诗绝笔声名歇,旧卷生尘箧笥深。时向歌中闻一句,未容倾耳已伤心。”白居易经常能听到乐人歌唱元稹诗歌。元稹《酬乐天江楼夜吟稹诗因成三十韵》云:“妓乐当筵唱,儿童满巷传。”元稹也听到歌妓在筵席上歌唱白居易诗歌。唐宣宗《吊白居易》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与元稹的诗歌有乐人歌唱,也有儿童传唱,乃至街巷处处可闻。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琵琶行》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并流传的。《琵琶行》之“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句中的“翻”与音乐密切相关,说明《琵琶行》是可以演唱的诗歌。王建《霓裳辞十首》其四云:“旋翻新谱声初足,除却梨园未教人。”白居易《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亦云:“琵琶师在九重城,忽得书来喜且惊。一纸展开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可见“翻”具有演奏乐器的意思,可翻的诗歌自然是可配乐歌唱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记载歌妓以能诵《长恨歌》为自己增价的故事:“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任半塘认为这里的“诵”未必没有歌唱的含义:“此妓之诵,仅背诵而已欤?抑且有韵节之诵?”此处的歌妓之诵定然有别于文人之诵,更接近乐人的唱。《旧唐书·元稹传》亦载宫妃诵元稹诗歌云:“(唐)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这里的“诵”显然指的就是歌唱的意思。吴相洲在《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之关系研究》一书中经过详细考证,认为歌妓之“诵”《长恨歌》就是演唱的意思,故《长恨歌》是经入乐歌唱的诗歌。
乐人在传唱元白诗歌时,以单篇诗歌形式存在的现象颇多,如白居易《长恨歌》《秦中吟》《琵琶行》等;也有以小集形式传唱的现象,如元稹的《长庆宫辞》。《旧唐书·元稹传》云:“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然元稹《长庆宫辞》今已不存。至于元白伎唱诗歌小集的形成,或是由诗人自编的适合入乐歌唱的诗歌小集,或是乐人或他人编纂的专门用于歌唱的小集,抑或是在传唱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诗歌小集。如白居易《醉吟先生传》云:“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箧。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白居易不仅教导家中乐妓跳《霓裳羽衣舞》,还教授他们歌唱《杨柳枝》新作,而“新词十数章”显然是白居易所作并自编的诗歌小集,从中亦可推知家妓对白居易诗歌的歌唱不止于此。无论元白歌唱小集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具备的特点均是能入乐歌唱并得到乐人传唱。
元稹与白居易的诗歌能够得到乐人广泛传唱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元白本身就精通音律,具备歌唱能力、演奏能力、舞蹈鉴赏及指导能力等。元白时常参加宴会,听乐人奏乐、演唱。元稹《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云:“君弹乌夜啼,我传乐府解古题。”白居易《听弹古渌水》云:“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元白甚至经常自己弹琴、吟唱。白居易《梦得相过援琴命酒因弹秋思偶咏所怀兼寄继之待价二相府》云:“我正风前弄《秋思》,君应天上听《云韶》。”《答微之咏怀见寄》云:“聚散穷通何足道?醉来一曲《放歌行》。”白居易在诗中自言会弹奏《秋思》,能唱《放歌行》,其弹奏及歌唱能力应远不止于此。元稹《元和五年予官不了罚俸西归三月六日至陕府与吴十一兄端公崔二十二院长思怆曩游因投五十韵》云:“那知我年少,深解酒中事。能唱犯声歌,偏精变筹义。含词待残拍,促舞递繁吹。”元稹说自己能唱犯声歌,同样具备较高的音乐素养。
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曾对歌妓唱诗的情形进行了详细描写,其诗序云:“《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白居易还教导家中歌妓演唱《伊州》曲,其《伊州》诗云:“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小玉是白居易的家妓之一,《伊州》则是曲调名。《新唐书·礼乐志》载:“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诗人还与歌妓共同排练演绎乐曲。白居易凭借优秀的音乐技能,依照舞谱指导乐人排练《霓裳羽衣舞》,其《霓裳羽衣歌》诗云:“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霓裳羽衣歌》是白居易酬和元稹之作,而元稹原唱已佚。玲珑,即余杭歌妓高玲珑。谢好、沈平,居易称此二妓“皆当时歌酒之侣”。据白诗,白居易刺史杭州时,曾教导她们排练演绎《霓裳羽衣舞》。后来,会跳《霓裳羽衣舞》的舞者乐人皆离散,也无人知道此种曲舞。元稹录谱于诗,作《霓裳羽衣谱》寄赠白居易。从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对《霓裳羽衣舞》演出场景的细致描绘,依稀可见集唐代歌舞之大成的舞曲风貌。
其二,元白深知并重视歌咏的力量。元白主张将诗歌播于音乐的诗学思想,如重视乐府诗歌创作、要求恢复初唐的乐府采诗制度、对以入乐为目的的乐府诗歌的创作要求是“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等。他们还常常在诗歌中流露出希望自己或他人的诗歌得到传唱的愿望,如元稹《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云:“怜君诗似涌,赠我笔如飞。会遣诸伶唱,篇篇入禁闱。”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云:“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事实也如此,元白入乐传唱的诗歌不在少数。元白曾为宫廷乐府作诗,将自己的诗歌入乐亦是可能的。元和二年(807),白居易作《太平乐词二首》,题下有诗人自注云:“已下七首在翰林时奉敕撰进。”其他五首为《小曲新词二首》《闺怨词三首》。元白既精通音律,在诗歌创作中又特别注重“体肆”,故其诗歌更易于入乐传唱,进而得到乐人歌唱。
其三,元白与歌妓、乐人交往密切,乐人熟悉并有机会传唱他们的诗歌。据柏红秀《白居易与乐人交往考》《元稹与乐人交往考》两文考证,与白居易交往密切的乐人可考者至少有45人,其中宫廷乐人8人,府县乐人22人,家乐13人,青楼乐人2人。与元稹交往过的乐人确证的有21人,其中宫廷乐人2人,营妓12人,家乐5人,市井乐人2人。其中,官妓高玲珑与元白俱有过交往。据王谠《唐语林》卷二载:
白居易长庆二年,以中书舍人为杭州刺史,替严员外休复。休复有时名,居易喜为之代。时吴兴守钱徽、吴郡守李穰,皆文学士,悉生平旧友,日以诗酒寄兴。官妓高玲珑、谢好好巧于应对,善歌舞。
阮阅《诗话总龟》卷四十二“乐府门”亦载:
商玲珑,余杭之歌者。白公守郡日与歌曰:“罢胡琴,掩瑶瑟,玲珑再拜当歌出。莫为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前鸣,白日催人酉后没。腰间红绶系未稳,照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元微之在越州闻之,厚币来邀,乐天即时遣去,到越州住月余,使尽歌所唱之曲,即赏之。后遣之归,作诗送行兼寄乐天曰:“休邀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却向江边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时。”
商玲珑即高玲珑,是余杭歌妓,曾在白居易的指导下学习《霓裳羽衣舞》,可见其歌舞技艺俱佳,在元白诗歌传唱和流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参加的筵席常有高玲珑的身影。元稹时为越州刺史,以重金从白居易处邀请高玲珑到越州,“尽歌所唱之曲”,其中就有元稹自己的诗歌。元稹在送别高玲珑时作诗赠别,其《重赠》诗题下有诗人自注云:“乐人高玲珑能歌,歌予数十诗。”“数十诗”是元稹的诗歌,可能属于元稹在市井坊间流传的适宜歌唱的诗歌小集,为乐人所熟悉。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唐绝句定为歌曲”条云:“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并举多例说明唐代文人诗歌被时人选为入乐歌唱的情况并不少见。任半塘《唐声诗》亦认为唐人以诗为乐府歌辞并用于歌唱的情况较为普遍,专取名篇名句入歌也是常俗。以元白及其诗歌在当时的声名和流行程度来看,被乐人歌唱的诗歌应不在少数,如白居易称元诗“暗被歌姬乞,潜闻思妇传”,白诗亦“随分笙歌聊自乐,等闲篇咏被人知”。
三 吟诵小集与伎唱小集的流传
唐代中前期,文集传播仍以手抄摹写为主。曹之《中国出版通史》认为,唐初期已发明雕版印刷技术,主要印刷对象为印纸、佛经,不包括诗集、文集等文学作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亦说道:“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虽然在唐玄宗时期就已开始,但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只零散印一些日历、医书,以及佛道等书,印儒家的经书是在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刻九经印版’开始的,这一工程至后周广顺三年(953)才得以完成。唐朝读书人念书,就只有靠手抄。”在唐代雕版印刷尚未流行的手抄时代,单篇作品的流传最为广泛,而小集因体量小、体裁集中等特点,比正集更易传播。再者,相较于手抄模式,口头上的传播更加迅速、广泛。元稹与白居易的诗歌作品在当时得到较大规模和大范围的传播,主要依靠的是吟诵和伎唱等口头流传方式,特别是当他们的诗歌以十数篇甚至数十篇的小集形式流传时。白居易《题裴晋公女几山刻石诗后》序云:“裴侍中晋公出讨淮西时,过女几山下,刻石题诗……夫嗟叹不足则咏歌之,故居易作诗二百言,继题公之篇末,欲使采诗者、修史者、后之往来观者知公之功德本末前后也。”道出白居易题诗石壁的目的在于传播裴度讨伐淮西藩镇的功德,采用的方式则是题写诗歌以备他人吟咏,并希望得到采诗者的注意和传唱。晚唐诗人杜牧曾借李戡之口批评元白诗歌说:“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这番话虽为批评元白诗歌之语,却从另一角度肯定了元白诗歌在口头上的成功传播,也说明元白诗歌在当时的确流传广泛。
元白诗歌出现在他人口中时,吟诵与演唱的方式并存。从《白氏长庆集序》《与元九书》等文可知,他们的诗歌受众自上而下遍及各阶层,所谓“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以及“王公、妾妇、牛童、马走”皆能吟咏传诵,反映了口头传播的范围之广。元白诗又因乐人、宫妃等歌唱受皇帝赞赏,如孟棨《本事诗》“事感第二”条记载白居易以杨柳托意赞美伎人樊素和小蛮的诗歌经宫中乐人传唱被唐宣宗赏识,《旧唐书·元稹传》载妃嫔以元稹诗为乐曲歌唱受唐穆宗称善,可见歌唱对诗歌传播的影响力。元白诗歌借吟诵与伎唱口头方式广泛流传的同时,他们的诗名也得到极大播扬,“元白”并称的佳话正源于其诗歌传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