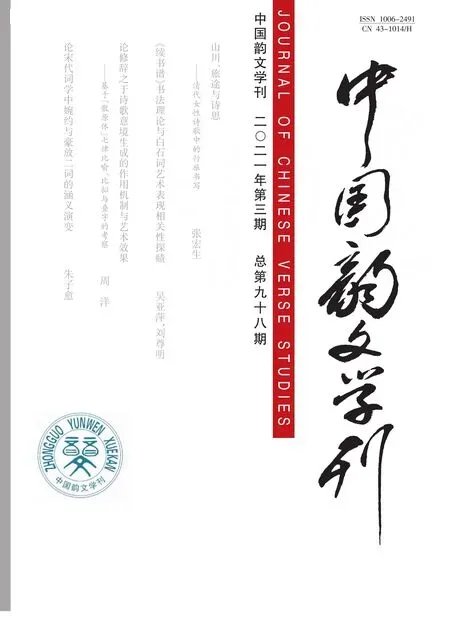山川、旅途与诗思
——清代女性诗歌中的行旅书写
张宏生
(香港浸会大学 中文系,香港 999077)
一 生活空间和创作空间
若是按照传统的观念和公开的闺训,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空间很受限制。但是,实际生活和理论教条之间,往往有着一定的距离。这一距离当然不是从明清才开始出现的。至少在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就有逐渐开阔的趋势。铁爱花在《随亲宦游:一种宋代女性行旅活动的制度与实践考察》一文中,探讨了宋代对于女性随亲宦游在制度上发生的变化,同时指出,“从生活实践层面来看,在宋代,女性随亲宦游的行旅活动十分常见”,主要类别则有随父亲、随夫、随子三种。高彦颐在其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认为,明清之际的江南闺阁女子虽然在名义上遵从着“三从四德”等观念,但她们对自己的生活空间有所经营,并没有完全被幽禁于家庭之中,而是有着陪同父亲、丈夫甚至是儿子赴任或出游的机会,因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和男性共同的社交圈,从而进入公众领域。事实上,从宋到清,这一趋势一直在延续。明清女性生活空间的扩大,使得她们能够开阔胸襟,增长见闻,也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相应的,在她们相关的文学书写中,风土景物、民情物态、历史畅想、故乡情怀、亲情友情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从而构成一个较之以往更为鲜活的文学世界。
生活空间与创作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时期,人们常常探讨女子的诗歌创作怎样才能做出成就。如果说,顾若璞曾通过其孙媳钱凤纶的经历有这样的总结,“性固不可不强,学亦不可少”,表现出天分之不可全恃,严辰则更具体地从三个方面指出,闺秀若想“生以诗名,没以诗传”,必须是“天授诗学”“人结诗缘”“地历诗境”,也就是说,既要有天分,又要有机遇,同时还要开阔境界,而这个开阔境界,即所谓“地历”,也就是刘勰所提出的“江山之助”。这一点,在清代不断被批评家所强调。
潘汝炯谈女儿潘素心的创作时曾这样说:“论诗者以为,所经城郭、江山、风俗,皆有益于其诗。”那些讨论潘素心诗歌的人提出有三个要素(即“城郭、江山、风俗”)提升了其创作成就,而这都是和潘素心自幼即随潘汝炯宦游分不开的。对于这一层意思,冒俊在《重刊自然好学斋诗钞后序》中说:“论诗于闺阁中,才綦难矣。无良师益友之取资,无名山大川之涉历,见闻所限,才气易孱……”骆绮兰《听秋轩闺中同人集诗序》也说:“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瀹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这两位批评家,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却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都提出了“见闻”对女性创作的重要性,而这个“见闻”,既包括师友之间的讲论,也包括山川的陶冶。所以,袁克家为其姊袁镜蓉《月蕖轩诗草》作序,谈到姊姊的创作成就,就有这样的总结:“归会稽吴梅梁少司空,随任宦游,一至楚,再至蜀。道经数万里,奔走二十年。凡名山大川,以及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人情喜怒哀乐之变态,无不蕴于中而发于诗。”严辰为其妹严永华的集子作序时,谈到其妹的成就,也这样说:“大凡女子,闲置深闺,老死牖下,不知乾端坤倪是何景象。即终身把卷吟哦,只如候虫之鸣,不知有穴外事。若吾妹生长滇黔,随父兄宦辙所至,于滇之三地,黔之上下游,跋涉几遍。搜奇抉险,悉发于诗。……迨于归后,随轺四出,东则曾经沧海,北则亲睹皇居,西则远及炎荒,南则溯洄天堑。出处廿四年,往还数万里。到处双旌揽胜,双管留题,以巾帼而获江山之助。”“巾帼而获江山之助”和包兰瑛所说的“山川雄壮助诗情”是一个道理,这就把刘勰的话,赋予了符合后世情境的转换,是从一个特定层面对女性诗歌创作的思考,也是把女性的诗歌创作活动与士大夫的传统联系到了一起。
不妨看看骆绮兰的《四十感怀》:
人生百年间,世事若朝露。
修短尽在天,穷通总随遇。
况受女子身,尺寸谨跬步。
苦乐由他人,己复何所与。
我今已四十,元发欲化素。
自念髫龄时,偏解爱词赋。
上窥秦汉文,下读唐宋句。
穷年徒矻矻,颇似一韦布。
远游虽莫遂,吴越适几度。
泛月西子湖,探梅邓尉路。
情随山水遥,疾中烟霞痼。
这首诗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她特别道出了自己酷爱读书的特点;第二,她特别指出自己受女性身份的约束,无法酣畅地到处漫游的遗憾。这两个方面,正好是古代读书人对自己的期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骆绮兰是镇江人,她表示自己虽然无法远游,但能够几度往还于吴越之间,也是人生的快意之处。在这样的山川行旅之中,她的感情得到熏陶和延展,她对山水的喜好,就像唐代的田游岩一样。“烟霞痼”,出自《旧唐书》对田游岩的记载:“游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谓曰:‘先生养道山中,比得佳否?’游岩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圣代,幸得逍遥。’”骆绮兰的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清代不少女诗人对于行旅的心态。而骆氏的这种描述,在归懋仪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印证。归氏出嫁后,曾随夫宦游,席炜称赞她“陶冶山川归大雅”,康恺总结其创作:“闺中欲怪诗情远,随宦年来游览多。”都认为和山川陶冶分不开。她的创作和一般闺阁之作有明显区别,很大程度上是多年随宦、到处游览的缘故。
二 行旅之险与人生之难
行旅途中,固然有着快乐的时日,如章婉仪的《月夜扬帆过峡江舟次联句》记载了他们夫妇和女儿、女婿之间在峡江行船的经验和感受,一门联吟,堪称韵事。但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何况,正如刘若愚所总结的:“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是悲叹流浪和怀乡。对于西洋读者,这可能显得太伤感,但是请不要忘记中国的广大,从前交通的困难,在主要城市中高度文明的生活和远乡僻壤的恶劣环境之间的尖锐对照,以及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的重要性与其对祖先的家根深蒂固的爱。进而,由于是个农耕的民族且住惯陆地,中国人大体上是缺少流浪癖的。”而且,以从宦而言,既然为宦之地并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则宦游的道路也无法自己选择。因此,途中就不一定都是岁月静好,一帆风顺。这时,诗人们往往能够深刻感受到大自然的另一个方面,从而在作品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如席佩兰《上太行》:“闻说人间险,人人畏太行。千寻穷鸟道,九曲入羊肠。况以深闺质,偏冲十月霜。登高非孝子,轻易别家乡。”鸟道有千寻之高,山路弯曲蜿蜒,行走不便,所以一般人都畏惧行走太行,更不要说深闺之质,本就不耐江湖风波。于是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中,对于道途的困苦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仿佛是和这首诗相呼应,陈蕴莲《兰山放歌》写道:“长空苍苍野茫茫,两旁乱石如牛羊。车声辚辚石上过,电掣雷轰半空堕。时防脱辐愁须臾,局促已仆辕下驹。马瘏仆痡色沮丧,百步九折向空上。忽然一跃如飞梭,转瞬已下千丈坡。又如忽挟王良策,人马去天不盈尺。又如亚夫将军降自天,仰视千仞心茫然。此时未免心如捣,此际咸愁不自保。平生辛苦我深尝,此险真如上太行。”兰山是蒙山的分支,《临沂县志》:“兰山,城南八十里,旧兰山县所由名也。六峰耸峙,极北一峰东面有石甚白,望之如半月。”若从实际情况看,兰山并不高,海拔只有130多米,可能也不一定有那么险,大约诗人是将从天津一路行来所经历的艰难,浓缩在这里了,所以自注也说:“过此出山。”也就是对过往山行的一个总结。诗写得生动传神,跳荡飞扬,颇有几分苏轼的风格。末句与太行作比,则正应了席佩兰那句“人人畏太行”。
行旅所开阔的视野,不仅有认识山川,也有认识民情。尤其是对于闺秀来说,毕竟她们中的很多人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对于下层生活所知较少,因此,有些所见所闻不免引起很大的心灵震撼,而这种震撼,往往也会加深她们对旅途艰难的理解。如陈蕴莲《长清道中》:
驱车适千里,陂陀少平陆。
倏如鸢堕溪,又若猱升木。
仰观接青冥,俯视骇心目。
去地已千尺,路转几百曲。
怪树生龙鳞,空岩转羊角。
无令尘污人,其奈风翻扑。
黄沙集成岭,乱石叠作屋。
居民半瘤瘿,村姬更粗俗。
无由辨颈腮,阔领裁衣服。
言语尽侏俪,形骸间硗秃。
不知彼苍意,赋此一何酷。
行行长清道,辄作数日恶。
茅店薄暮投,留客少饣亶粥。
堆盘具葱薤,裹饭进藜藿。
云此岁欠收,山家少旨蓄。
却之勿复进,所至因休沐。
在山泉水清,渴饮意已足。
明发新泰郊,好与清景逐。
长清在济南西,南接泰安,地处泰山隆起边缘。这首诗主要写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景观,二是山民长相,三是当地饮食。对于一个江阴闺秀来说,自小生活在江南,嫁给武进左晨后,仍然基本上是居住在江南,如今穿行在山东的山里,感受就太不一样。山路的崎岖暂且不提,她碰到的山民,多是脖颈粗大,可能是由于缺碘而导致的甲状腺疾病,看起来颈子和脸一样粗,所以衣服也都是阔领。这真是惊心动魄的观察,让她不禁发出“不知彼苍意,赋此一何酷”的慨叹。饮食也无法习惯,饭菜当然是粗劣,印象更深的恐怕还是堆在盘子里的大葱,娇小姐当然吃不下去。这些,虽然可能只是行旅中的一些花絮,却也让她们更进一步体会到人生之苦。
当然,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的,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本就息息相关,所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看到如此山川,如此风土,如此人物,当然也会勾起诗人对自己生活的联想。如钱孟钿《江上阻风作》:
我生周甲子,鬓已积霜霰。
随夫宦天涯,秦越楚蜀遍。
陆登大散关,去天尺五半。
屈曲九折坂,巉岩接云栈。
下轰水积石,上绝南去雁。
舟行下三峡,水急回流旋。
岸狭仅容刀,壁立矗霄汉。
朝朝渡九滩,滩石利如剑。
八月渡钱塘,江流浩迷漫。
潮来鳖子亹,缕缕白一线。
俄而涌雪山,砰訇飞匹练。
撼天天根摇,振地地轴断。
声如千钲鸣,势若万马战。
拏舟弄潮儿,跃浪忽隐现。
归船三日卧,心悸目犹眩。
今岁过九江,阻风彭泽县。
四野茫无人,孤舟泊荒岸。
但闻吼江涛,浪卷雪花乱。
长年有戒心,婢仆色俱变。
我无刘宠钱,又乏胡威绢。
数拳郁陵石,聊与沉香伴。
衣裘敝已久,暴客何所羡。
坦怀竟就枕,朝暾色已绚。
轻帆祈南风,乘流五两便。
钱孟钿的丈夫崔龙见,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恩科进士,授陕西南郑县知县,调富平县。历官杭州府同知、湖北荆州府知府、四川顺庆府知府。官至湖北荆宜施道。钱孟钿显然常常随夫赴任,因此以诗歌的形式,记载了在自己六十年的生命中,“随夫宦天涯,秦越楚蜀遍”的历程。大散关位于陕西宝鸡市南郊,自古是川陕咽喉。诗先写在陕西的陆路之行,然后重点写在长江沿三峡而下,或在钱塘遇潮,或在九江阻风。对行旅的这些记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突出其险。照理说,旅途之中,不可能只有险途,没有坦途,只有危急,没有从容,但作者笔下的景物有着集中的指向,显然有着刻意的选择。或者,她是用这样的方式,暗示其丈夫行走宦途的艰难。这也让我们想起了姜夔著名的《昔游诗》。姜夔以大篇联章的方式,所记述的场景多是奇险者,以此表达行走江湖之苦,并暗示国家社会的危局。钱孟钿的作品在气象上当然无法和姜夔的相比,但其思路却可以互相参照。
三 山川跋涉与历史情境
虽然女子的阅读在中国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但以诗歌的形式来展示历史感,则是到了清代才更为突出。发源于魏晋南北朝,并在唐代如胡曾等人手里得到极大发展的咏史诗,也为清代女诗人所喜爱。如陈蕴莲对晋代的历史很感兴趣,她把自己的这种兴趣浓缩在《论晋史》的数首诗中。更突出的是汪端。汪端深于史学,曾作《读史杂咏》十二首,咏秦汉之事;作《读晋书杂咏》四十首,咏两晋之事。她不以成败论英雄,有《张吴纪事诗》二十五首,咏张士诚集团之事,又仿《张吴纪事诗》例,成《元遗臣诗》十二首,展示了以诗论史的才华。
这种对历史的关注,不可能在其行旅诗中没有体现。纪昀称,迈仁先生“生长京华,足迹所及者近,未能涉历名山大川以开拓其胸次,而俯仰千古之思,周览四海之志,笔墨间往往遇之”。指出即使阅历不够丰富,仍然可以通过书本进入广阔的诗歌世界。进一步看,对于女诗人而言,如果说,历史感的增强使得她们通过书本开阔了心灵空间的话,则在行旅之中,将经行之地与历史记载加以印证,不仅能够增强现地的感受,而且也能增强对历史的认识。徐德音在为林以宁《墨庄集》作序时曾这样说:“或弥节脂车,眺中原之苍茫;或悲笳朔雁,揽边塞之荒凉。登眺名山,则情同康乐;咏怀古迹,则调比少陵。”所谓“咏怀古迹,则调比少陵”,指的是杜甫离开夔州之后,沿江而下,前往湖北江陵时,由于足迹相近,写了五首诗,分咏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等的事迹。这种做法,对女诗人也是示范。林的诗歌成就或许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这却是对当时创作的一种真实描述。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人物或事件,大致可以视为文学创作的母题,得到后世作家的歌咏,上述杜甫所咏五题就是如此。这样的创作,使得行旅更加具有了历史的厚度。徐德清南下途中,经过邳州和淮阴,写有《次邳州》和《韩侯钓台》二诗,在分别回顾张良和韩信的故事后,称赞前者“千载如君诚大勇,从今制胜济刚柔”,感慨后者“始知禄位能昏智,不记当年受胯时”。曾懿婚后随丈夫袁学昌宦游福建,从成都经重庆,一路沿江而下,经过奉节,游览了一些景点,如武侯庙、八阵图等,所写的一些诗,如《由夔府溯流而下山峡险峻古迹甚多诗以纪之》之二:“八阵雄图余垒蟠,卧龙遗庙枕狂澜。断云压雨过鱼复,一舸洄旋飞过滩。” 自注:“八阵图在府南,垒石为之,武侯庙即在八阵图台下。”这些都是对中国历史进程起到重大作用的地方,经行于此,则似乎历史也活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说,行旅和怀古就往往能够结合在一起。如包兰瑛《江行望燕子矶》:“秣陵城下买轻航,鼓枻中流感慨长。江上猘儿经百战,矶头燕子自千霜。翩翩远势疑飞动,滚滚归心接混茫。可惜便风不能泊,开窗无语对斜阳。”诗人经过南京燕子矶,想到当年东吴在此的一番事业,心中充满感慨。《三国志·孙策传》“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句下南朝宋裴松之注:“吴历曰:‘曹公闻策平定江南,意甚难之,常呼猘儿难与争锋也。’”燕子矶矗立长江畔,沾满历史风霜,看尽人间沧桑。虽然只是江行,匆匆一瞥,以往的阅读体验不可能不浮现出来,所以就会“感慨长”。而到了燕子矶,也就算到了南京。明代至成祖时,虽然迁都北京,但南京作为留都,政治地位还是很高,到了清代,仍然有其特别的重要性。因此,在这里纵览历朝,回首兴亡,不免发思古之幽情。又如徐灿《广陵怀古》:“六朝烟草总茫茫,占得风流独不亡。夜永笙歌沉月观,春深花鸟吊雷塘。清淮一水长通洛,垂柳千条尚姓杨。莫向迷楼悲泯灭,李花零乱落霓裳。”诗中将六朝和隋朝联系在一起,重点描述了隋炀帝奢靡的生活,不过徒然供后人凭吊而已。当然,大运河仍在,河边的千条垂柳,留下了隋炀帝的痕迹。最后二句非常巧妙:迷楼是隋炀帝所构建,他曾经非常得意地说:“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现在迷楼固然已经泯灭,但起兵灭隋的唐朝呢?唐朝的皇帝姓李,此写李花,一语双关。李花为何凋零?那是因为唐玄宗时期由盛而衰。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贵妃善跳霓裳羽衣舞,乃以此代指当年的繁华。可是现在李花零乱落于霓裳之间,当然象征着大唐的繁华已去。所以,隋朝固然是因奢靡而亡,唐朝又何尝不是?作为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明朝灭亡的诗人,她的这一书写也是意味深长的。
行旅中,固然可以感受帝王将相,朝代兴衰,但由于女诗人的文人属性,她们往往也会对文人的命运特别感兴趣。著名诗人汪端是杭州人,她的诗中对和杭州有关的历代著名文人多有表现,如《苏公祠》《龙井谒秦少游祠》《水磨头吊姜白石》《南湖吊张功甫》《铁冶岭寻杨廉夫读书处》《西马塍访句曲外史张伯雨故居》《南屏山调太白山人孙太初》《宝康巷访朱淑真故居》等。离开杭州后,来到苏州,她写了《石湖别墅吊范致能》;来到绍兴,她写了《寄题陆放翁快阁》;来到无锡,她写了《梁溪谒倪元镇祠》;来到丹阳,她写了《过丹阳丁卯桥吊许浑》;来到扬州,她写了《竹西亭吊杜樊川》。对于范成大,她赞美其“清游记得邀词客,檀板银筝谱暗香”,写姜夔在范成大石湖做客,创作出《暗香》《疏影》的一段佳话。姜夔由于得范成大的知遇,所以才能不仅在生活上有所依靠,而且文学上也能取得更大成就,汪端显然对此非常称赏。对于陆游,她特别指出“世人漫讽南园记,久以闲心狎白鸥”。这二句所说是陆游为韩侂胄撰《南园记》事。据《宋史·杨万里传》,韩侂胄权势方炽,“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所谓“他人”,即指陆游。《宋史·陆游传》:“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看来当时有所讽刺的人确实不少,以至于也有人为之辩诬。如罗大经 《鹤林玉露》云:“《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谀辞。”周密《齐东野语》云:“昔陆务观作《南园记》于平原极盛之时,当时勉之以仰畏退休。”韩侂胄请陆游撰记的时候,陆游已经退休而居住于绍兴,正如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所说:“游老病谢事,居山阴泽中,公以手书来曰:子为我作《南园记》。”这也就是说,在汪端看来,不仅《南园记》中并无谀辞,而且陆游已经退隐山林,不问世事,更不可能以此记而想获取什么。汪端娴于史事,她抉出这一段故事,说出了对陆游的理解,也是一种文人与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还应该提及的是,行旅之中,也会经过与历史上的著名女性相关的地方,这方面比较多的作品是写西施、昭君、二乔等。如陶安生《过小乔墓作短歌以吊之》:
姊从君,妹从臣,英雄儿女俱绝伦。曲同顾,醪同注,豪气柔情两相慕。玉帐留连历几春,阿瞒铜雀愿徙殷。风流已盖三分国,玉树琼花尽后尘。可惜奇缘天也忌,周郎竟继孙郎逝。佳儿虽缔两家姻,后死尚违同穴誓。惟欣香冢近城隈,公瑾相望土一堆。想见月明荒野夜,英灵犹得共徘徊。
记载中的小乔墓不止一处,但此诗前的一首是《望冶父山》,冶父山在安徽庐江县,因此诗中所言之墓应是在庐江者。小乔是周瑜的夫人,周瑜病逝后,葬于庐江东门,小乔住守庐江,抚养遗孤,十三年后病卒,享年四十七岁,葬于县城西郊。诗中描写了大乔与孙策的遇合,英雄儿女,豪气柔情,两心相悦,令人羡慕。当然,关于赤壁之战前,曹操号称要建铜雀台,欲得二乔以享乐,不符合历史,因为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而铜雀台之建造则是在建安十五年(210)。陶安生所写,是从《三国演义》而来。小说中写曹操占领荆州之后,随即挥师东下,进攻东吴,声势浩大。而当时东吴国内或战或降,两派意见分歧,甚至吴主孙权也举棋不定,踌躇万端。刘备方当然是希望东吴对曹军开战的,于是小说记载了诸葛亮劝说周瑜的一个情节,告诉周曹操发兵的动机:“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诗中讽刺曹操愿望落空,正是为了强调周瑜的神勇,为此,甚至推许其“风流已盖三分国”,将杜甫《八阵图》中对诸葛亮的描写移了过来,可见诗人对这一对伉俪的仰慕。诗的后面遗憾二人死未同穴,虽然如此,城东、城西,遥遥相望,英灵能够常常相与徘徊,仍然令人感到欣慰。
这一类的作品一方面写出了二人政治上的功业,另一方面,更为强调的是他们心灵的相知,其中当然带有女诗人们的深深感喟。
四 山川之美与诗思之妙
创作的激情来自新鲜事物的激发,走出家门的行旅,使得生活发生了重要改变,正能够提供这种刺激,从而引起内心的强烈反应。像归懋仪就明确指出,江上的行旅,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在《江行》四首之二中,她写道:“江流激奔腾,山势助雄壮。横青夹两岸,涌翠叠千嶂。合沓势如引,巉岩力不让。引领缅来奇,回首失往状。平生好奇心,兹焉一舒畅。”写行船江上,山和水之间的互动。由于是在江南,所以特别点出“横青”和“涌翠”,一个“横”字,写出江狭树茂;一个“涌”字,写出江流曲折。而水流之急,水石相激的力量之大,也都非常形象生动。诗人明言自己平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所以看到神奇的大自然,才能心神俱醉。
有了好奇心,往往也就有着发现的惊喜,如席佩兰《晓行观日出》:
晓行乱山中,昏黑路难辨。
默坐车垂帘,但觉霜刮面。
冰上滑马蹄,胆怯心惊战。
前骇绝壑奔,后虑危崖断。
合眼不敢开,开亦无所见。
俄顷云雾中,红光绽一线。
初如蜀锦张,渐如吴绡剪。
倏如巨灵擘,复如女娲炼。
绮殿结乍成,蜃楼高又变。
五色若五味,调和成一片。
如剑光益韬,如宝精转敛。
精光所聚处,金镜从中见。
破空若有声,飞出还疑电。
火轮绛宫转,金柱天庭贯。
阴气豁然开,万象咸昭焕。
有了后面所看到的奇丽景色,前面经历的那些昏黑之际行走于山路之中的艰难,好像都是值得的。席佩兰用她的笔,描述了一幅生动的日出图:先是看到云雾之中,一线红光隐隐出现,就像铺开蜀锦,剪出吴绡,色彩烂漫。忽然之间,宛如巨灵劈开华山,又似女娲炼出彩石,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光芒映照中,云层中结成绮殿,幻出蜃楼,而又调和五色,精光凝聚,好像金镜挂在天上。这一轮红日跳出云层,呈现动态,破空若有声,同时速度之快,竟如闪电一般,将一个火轮,一道金柱,贯穿天庭。于是,一扫阴霾,万象光明。诗写得痛快淋漓,描写日出的过程,非常精彩,而笔下又有章法,末句一结,将前面对晓行山道的种种艰难和忧惧一扫而空,作为铺垫,张弛有致,非常老辣。
尽管这些女诗人中不少是被生活被动地推到以往不曾想见的山水之中的,但当真置身其间,她们也会被深深打动,从而用诗笔加以描写。其中不少作品刻画出了所见之奇,如袁镜蓉《登七盘关》:“绣岭重峦叠万千,羊肠曲径走盘旋。风来壑底犹飞雪,人到山巅望若仙。殿角铃声悲落日,马头云气阻征鞭。回看绝壁临无地,但听潺湲响碧泉。”七盘关在七盘岭上,位于川陕交界咽喉处,号称西秦第一关,古时是四川连接秦岭以北的东北、华北、中原以及西北的唯一道路枢纽。袁的丈夫在四川做官,她也间关相随。这首诗描述了七盘关的重峦叠嶂,羊肠小道,特别写了从壑底卷上来的风,以及山头似乎要阻滞策马行进的云。而且回看来时的绝壁,好像下临无地,只能听到潺湲的泉声。这首诗可以和《山行》对读:“高风瑟瑟动前旌,万叠冈峦不易行。盘马回峰愁鸟道,掀车乱石走雷声。眼穿落日孤城远,身入层云一羽轻。自笑此生常作客,年年随宦苦长征。”这个“掀车乱石走雷声”,可以和岑参的“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相媲美,而“眼穿落日孤城远”,更形象地见出山行之人“望山跑死马”的特定感受。“身入层云一羽轻”则是将人到高处,对于尘世沧桑的感悟写出,在那个特定的高度,回看下方,真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渺小,不值得一提,这就有了庄子《逍遥游》中的感觉。正是这样“年年随宦”的经历,为她的诗歌注入了这样独特的内容。历代歌咏七盘山的诗很多,如沈佺期有《夜宿七盘岭》,杜甫有《五盘》,岑参有《早上五盘岭》。袁镜蓉继承了诗坛的传统,而对其间的奇险更为关注。袁镜蓉的丈夫吴杰道光二年(1822)秋曾“典试陕甘正考官”,不久,又出任四川学政,袁氏“以是冬挈眷之四川学署”;道光十年(1830)春,吴杰又“调四川川北道”,袁氏“奉先舅归里而旋之蜀”她以羸弱之躯,艰难地在这条道路上行走,感受自是不同。
有时候,所谓奇,也包括僻。王德宜是松江人,嫁给巡抚汪新之子,曾和丈夫一起随侍公公远赴贵州,“凡山川所经历,古迹所凭吊,以及花鸟虫鱼,俱发为有韵之言”。王德宜在贵州所写的诗,最著名的是《黔中吟》七律十首,其中写了自己从江南来到贵州的种种心情,并对当地独特的风土民情作了细致的描写。如“寻螺天漏山堆墨,绕郭岚迷雾隐花”(第一首);“苗女扫妆垂辫发,黔山积铁哆唅砑”(第二首);“云根人语畲初斫,铜鼓龙鸣雨又来”(第四首);“象教苗传持贝叶,羊皮人只辨鹦车”(第六首);“僰人资食桄榔面,吏驿风传芍药羹”(第七首);“居民当暑无纟希服,犵狫肩舆尽卉裳”(第八首)。这些,不仅见出她的好奇之思,而且将贵州的特定人情物理,做了一定程度的表现。曾懿来到福建,也被当地风情所吸引,其《闽南竹枝诗八首》之三:“窄袖织腰黑练裙,香花堆鬓髻如云。压肩鲜果沿街卖,贸易归来日已曛。”之八:“盘龙宝髻簇流苏,红袖买春携玉壶。怪道冰肌甘耐冷,严冬犹自赤双趺。”或写身穿白色裙子,“袖窄弯时不碍肘”,并满头插花,挑着水果当街叫卖的女子,或写打扮得非常漂亮,“盘龙宝髻簇流苏”,却又赤着脚的女子。前者以见福建女子之操劳,“闽中凡耕田、挑负贸易者,半是妇人”;后者以见福建女子之妩媚以及气候与他处不同,“闽中女子妩媚者多,然虽至严冬不袜亦不觉其寒,奇矣”。当然,所谓僻,也还包括在行旅途中看到的罕见之物。如蒋蕙幼年时,其父亲在大子州、吉木萨一带做官,她随之宦游,“耳闻所见,诡异殊常”,如雪山、火山、哈密瓜、土鼠、雪蛆等。她把这些记录下来,也是行旅之中的重要收获。
既然这些经行之地如此打动了她们,她们除了被所见所闻深深吸引,还要努力寻找最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对这些引起她们灵感的事物加以描写。在这方面,她们继承了中国山水诗的传统,往往既有大谢的繁富,又有小谢的清丽。从创作实践看,如果是写五言律诗,也有不少是从唐诗中姚贾一路以及后来受其影响的永嘉四灵一派来,中二联多作景语,特别追求字句的推敲。如曹贞秀《舟过南阳阻水》和《舟行即事》:
积水浑无地,波流接大荒。
阴风掀白浪,落日度危樯。
树杪烟痕断,山腰雾气长。
暮天空阔处,征雁独南翔。
系缆寒潮落,开帆巨浪惊。
江声翻远树,海气撼孤城。
山涌波心出,灯悬塔顶明。
东流空日夜,阅尽古今情。
造语清新而又富有表现力。如“落日度危樯”“树杪烟痕断”,都写得生动形象。至于“江声翻远树,海气撼孤城”二句,则显然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来,虽然气势上稍逊,也能写出壮阔的景色。
这些,说明生活空间扩大之后,不仅引起了感情的激荡,也引起了艺术的激荡。当她们努力选择最为恰切的语言去对所见所感加以描写时,作诗本身也就被赋予了另外的意义。
五 流亡之痛与家国之思
女诗人的创作得“江山之助”,固然可以开阔视野,扩大空间,但是,有时候,她们所直接面对的就是“江山”。尤其是在战乱频仍,或者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在外行旅,更加能够感受社会的氛围,因而使得作品也带有更为厚重的历史感,创作境界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给当时人的诗歌创作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不少女性被抛到时代的洪流中,虽然随波浮沉,却也有自己的坚持。和李清照词名相埒的徐灿,嫁陈之遴为继室,夫妻琴瑟和谐,多有唱和,有盛名于时。不过,他们生在乱世,陈之遴的仕途多有起伏,先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受父亲的牵连,被判以“永不录用”。明亡后,陈之遴很快就降清,虽然一度颇受重用,官至弘文院大学士,但仕途险恶,也迭经挫折。据《清实录》:“壬辰。吏部等衙门会议,陈之遴、陈维新、吴维华、胡名远、王回子等,贿结犯监吴良辅。鞫讯得实。各拟立决。得上旨曰:陈之遴受朕擢用深恩,屡有罪愆,叠经贷宥。前犯罪应置重典,特从宽,以原官徙住盛京。后不忍终弃,召还旗下。乃不思痛改前过,以图报效。又行贿赂,交结犯监,大干法纪,深负朕恩。本当依拟正法,姑免死,着革职,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盛京,家产籍没。”也就是说,陈之遴于顺治十三年(1656)和顺治十五年(1658),两次 “流徙盛京”。徐灿作为妻子,也一并“流徙”。
徐灿有着较强的家国意识,对于丈夫陈之遴的降清,心中不以为然,但作为女子,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也无法选择,于是,心中有很多苦闷。这些苦闷,连同山河破碎的悲愤,都在其行旅诗中有所体现。如《舟行有感三首》:
几曲芙蓉浦,凌风恐易过。
流连情不浅,指顾恨偏多。
雁外孤樯落,霞边众岫罗。
不须歌玉树,秋袂久滂沱。

呜咽邗沟水,汀回晚系舟。
江都无绮业,建业有迷楼。
月皎鸿秋吊,花红鹿昼游。
芜墟腥未歇,杵血满寒流。
这是在大运河中行船,经过扬州所写。虽然带有怀古的性质,但一则说“不须歌玉树,秋袂久滂沱”,再则说“芜墟腥未歇,杵血满寒流”,不仅是对王朝兴废再三致意,而且有着深沉的现实之感,是对明清易代的深深感喟。
文学史上往往把徐灿和李清照相提并论,但二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李清照的时代尚可以避居江南,而徐灿则面临着彻底的亡国,因此,在她的作品中,也就不时展现出一种茫茫无所归的感觉,如《登楼》:“高阁哀弦咽晚风,断云收尽碧天空。河山举目何曾异,岁月催人自不同。几日羽书来蓟北,千群浴铁下江东。余生尚想岩栖隐,兵气休侵旧桂丛。”《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徐灿用这个典故,正是为了说明今昔之别:当时偏安江左,尚有恢复中原的希望,现在已经是“千群浴铁下江东”,国土完全被占,如此,则即使想寻找一片宁静的地方,恪守内心的坚持,也是不可能的了。这首诗,可以和其《唐多令·感怀》一词对读:“玉笛送清秋,红蕉露未收。晚香残、莫倚高楼。寒月羁人都是客,偏伴我,住幽州。 小院入边愁,金戈满旧游。问五湖、那有扁舟?梦里江声和泪咽,何不向,故园流。”都是表示无地可避的悲哀。
如果说,江南之行还是更多体现了带有传统意义的伤感的话,则两次随丈夫被贬辽阳,就更有着特别的况味。徐灿有《秋感八首》写自己在辽阳的生活。对于一个出生于姑苏的江南女子,边塞之行无疑令她印象深刻,更何况丈夫还是戴罪之身。“弦上曾闻出塞歌,征轮谁意此生过。”(其一)开宗明义,说出了生活的落差。这个落差,表现在风景物候上,就有“霜侵帘影催寒早,风递笳声入梦多”(其一),就有“风来四野宵偏厉,天入三秋昼易阴”(其二)。于是,在这样的情形中,更加思念“家山明月”(其一),而且,“瑶琴犹自理南音”(其二)。这个“南音”是什么呢?就是以往生涯中几个令她难忘的地方。一是北京,住在西山,“朝回弄笔题秋叶,妆罢开帘见晓峰”(其三);二是南京,徜徉在秦淮河畔,“朱雀桁开延夜月,乌衣巷冷积秋烟”(其五);三是苏州,这是她的家乡,“几曲横塘水乱流,幽栖曾傍百花洲。采莲月下初回棹,插菊霜前独倚楼”(其六);四是杭州,这里也是他们夫妇曾经居住之处,地理是“天堑潆回环两越,风流娴雅接三吴”,而他们在西湖,则有“宛转行雕轮,摇曳度兰舫。随波穷胜游,隔烟发清唱”的回忆。清初被贬东北的流人,对于“游”往往都有非常的敏感。徐灿北游至此,心念所系,都是南游情事,将两种游对写,立意很深,也是其民族观念的一个侧面的表现。
清代中叶以后,外患频仍,最早面对的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虽然距普通百姓没有那么近,但也能在日常生活中打上烙印。陈蕴莲嫁武进左晨,“中岁随夫婿官津门”,在天津,正逢鸦片战争之役,集中多有记载。陈蕴莲向有大志,在《题程夫人从军图》中,她这样说:“男儿生世间,功业封王侯。女儿处闺阁,有志不得酬。读书空是破万卷,焉能簪笔登瀛洲。胸怀韬略复何用,焉能帷幄参军谋。”对于社会对女性所做的限制深致不满,但这并不妨碍她关心家国之事。鸦片战争爆发时,虽然身在天津,相距遥远,但她一直密切关注。如定海之战,终于以失败告终,她写有《闻定海复陷》一诗,紧接着又有《闻宁波警》《闻京口警》等作品。似乎是为了证实她的忧患意识,鸦片战争的烽火也从南方烧到北方,触及她的生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不久大沽失陷。5月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在这种情况下,陈蕴莲从天津避往保阳(即保定),这客游中的客游,使得她别有感触,写有《旅夜抒怀》三绝句(题注:“津门示警,避居保阳”),分别题为《看剑》、《缝衣》和《夜寒》,如下:
漂泊谁怜泪暗弹,出何草草返何难。
夜深胆怯挑灯坐,但把吴钩子细看。
天涯萍梗欲何依,归梦都因久客稀。
玉质自知勤护惜,将眠缝裹旧时衣。
美人原不隔云端,咫尺谁知一面难。
旧日明珠今草芥,有谁怜惜此时寒。
第一首继承了她一贯的豪情,虽然生逢乱世,漂泊流离,身为女性,无从作为,但仍然壮心不泯,有所期待。第二首和第三首写客居生活的艰辛,以具体的细节,点出战争对普通人的影响。
如果说,从涉及的疆域看,鸦片战争从规模上,还只限于一些局部地区的话,则稍后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席卷大半个中国,历时十四年,深刻影响了许多民众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妇女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死于战乱者(不少是自杀而死)已是不少,更多的人则到处逃难,流离失所。杭州郑兰孙嫁同乡徐鸿谟,随其至扬州赴任,正遭遇战事,俞樾的《郑孺人传》对其这一段经历有所描写:“咸丰三年,贼陷江宁,顺流而下,将薄扬州。时徐君奉檄乞援于淮,孺人曰:‘事急矣,吾姑高年,不宜久居危城。’而又惧中途遇抄掠,乃尽弃其囊箧,惟奉纯皇帝赐文穆诗卷,及其家乘与先代遗像,从孙太孺人,挈子女以出,奔如皋。……”太平军曾三次攻陷扬州,分别是咸丰三年(1853)、咸丰六年(1856)和咸丰八年(1858),郑兰孙也至少有过三次逃往如皋的经历。她的集子里不少作品都要通过这个背景来看。如《癸丑二月,扬城告警,予仓皇奉姑慈出避,感而赋此》二首之一:“金钗钿盒尽抛残,遁迹幽居魄也寒。疾病每求医药苦,辛劳欲乞米盐难。囚容蓬首形成鬼,夜黑朝饥梦怎安。任尔霜风欺瘦骨,寸心一点自怀丹。”写这趟避兵之行,不仅米盐困难,而且缺医少药;不仅形容憔悴,而且心理紧张。在《予避兵困苦,惟觅野菜煮食,闺友杨夫人怜之,裹粮相馈,作此以谢》中,她更集中笔力,写出了由于生活窘迫,缺少粮食,幸得闺友相助,以及相关的心理活动:“耻云面北学偷生,视死如归未足惊。夙习诗书知大义,誓全白璧保清名。吞毡敢仿孤臣志,啮草还深伏枥情。难得兰盟闺阁友,裹粮相馈出真诚。”这首诗并没有具体描述由于缺粮而带来的艰困,而是以志节自励,以古代的贤士为榜样,写出了漂流在外的一种情愫。
漂流在外,最深切的感觉就是没有了家的感觉。从历来女性书写来看,她们对社会变动的反映,往往都是和自己生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很少直接写。如吴茞《秋窗夜课风雨鸣檐,百端交集凄然成咏》:“竟夕吟未已,翛然对短檠。无家成濩落,有梦未分明。秋老江湖色,风高鼙鼓声。残篇空自检,幽恨总难平。”她在江湖之中,听着满耳的鼙鼓声,深切地感到“无家成濩落”。袁绶《赴晋就养,迂道至沪上省母,示六弟》四首之四:“国破家何在,途长就养难。干戈犹未戢,行旅几时安。亲老尤愁别,家贫却耐寒。还期复位省,仝奉板舆欢。”而“无家”,有时真的就意味着家人的生离死别。孙佩兰是浙江钱塘人,嫁胡陛言。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杭州,她们全家逃难而出,半路与太平军遭遇。胡陛言被执,不屈而死。孙佩兰随父避难,先至定海,复至宁波。在宁波时,她写了一些作品,展示了家庭的悲剧。丈夫殉难,自是深切怀念,其他如婆家与母家,也常在念中。如《端午寓甬感赋四绝》之三:“白首姑嫜住异乡(余随家严避难至甬,余姑与小姑仍住杭州),生离话别更凄凉。几回盼切平安字,恨不能飞各一方。”又《寓甬接杭信,知孙文伯舅公家殉难,余姑暨小姑依随一处,不免连类及之,寸肠欲断,泪咏二绝》之一:“惊传舅氏陷门墙,难忍凄凉欲断肠。想必蜘蛛连一网,最怜白发更张望。”就写了困在杭州的婆婆和小姑,生死不明;而舅公一家则已经殉难。这是非常深切的国破家亡之感。更不用说,离开家园的漂流,本身就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如吴茞《癸亥五月山中寇窜,将避难之海门,感赋四律》之二:“天涯歧路怅何之,家国零丁又一时。敢说拔身离虎口,居然逐客到蛾眉。转蓬未许垂杨系,流水终愁上峡迟。安得栖身似同谷,悲歌细和少陵诗。”虽然脱离虎口,仍是天涯歧路,身世如转蓬,不知飞向何处,因此深羡杜甫在经过动荡的生活后,终于能够在同谷暂时栖身,过着宁静的生活。
到了清代末年,和民族革命、社会改良结合在一起,女性诗人的行旅诗又有了新的内容。她们中的少数人能够跨出国门,感受天下的风云激荡,因此增强了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秋瑾。
在秋瑾的生命历程中,赴日本留学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旅途中,在异乡时,她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在诗里面。如《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首诗写于1904年夏,当时赴日留学,在黄海上航行,或有往返之事。诗人就像“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宗悫一样,豪情满怀,虽然孤身一人,但求真理于异域,带回故国的,将如同滚滚春雷。因为国家已经灾难深重,内忧外患,纷至沓来,面对这种情形,心中的块垒,浊酒难销,痛感神州大地,缺少人才。于是希望用自己之所学,带领志士,力挽狂澜,唤醒民众,进行革命,重整乾坤。大约有志之士,面对大江大海,壮其波涛汹涌,感其一去难回,往往别有情愫。在此之前,沈善宝曾写有《满江红·渡扬子江》。如果说,沈善宝在渡扬子江时,想到南宋的巾帼英雄梁红玉大战金兵的故事,感慨自己身为女子,不能一展抱负,因而怨恨苍天的话,秋瑾则感到女子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自信满满,充满豪情胜概。这是时代之别,当然也带有个性之别。
从徐灿到秋瑾,这些女诗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踏上旅途,她们的情感都经历了巨大的激荡,在家国的背景中,其行旅生活更有内涵,更有着时代的印痕。
六 心灵空间与想象神游
在清代,虽然女子的社会空间大大开阔,但这只是相对的,既然主要生活在内闱,她们中的大多数不一定具备主客观条件,因此仍然有一定的限制,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尝试开拓生活空间的期待,尽管这种空间往往是心灵上的。高彦颐总结明清妇女出游的几种形式,除了“从宦游”“赏心游”“谋生游”,还有通过文字进行的“卧游”。所谓“卧游”,有不同的指向,大致上也可以叫神游。
神游就是在想象中加以游历。这方面最常见的是题画,如张纶英《题山水画帧》:
幽居结岩岫,萧萧山木秋。
中有绝代人,濯发清泉流。
览兹动遐思,岁月忽我遒。
安得牵烟萝,诛茅尘外游。
怆然念身世,漂泊同浮鸥。
作者虽然说的是山水,实际上焦点集中在那个“绝代人”。既然是“濯发”清泉,则自然使人想起“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的渔父,观览之时,忽动遐思,无限寄意林泉,期待能够“牵烟萝”,“诛茅”而作“尘外游”。所谓“烟萝”,又使人想起《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立意高远。末句写面对这样一幅画面,更加感慨身世,如同浮泛的沙鸥。这样的憧憬,似乎更像是传统士大夫心理的体现。
神游体现出的是想象力,游仙也是其中的一种。一般来说,女子的生活比较现实具体,她们的创作写日常生活的比较多,但是,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学养,培养出来的人也有不同。此所以李清照的《渔家傲》作为一首游仙词受到学界特别的关注。清代女诗人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探索,如钱孟钿写有《小游仙》六首,对天宫的情形有所想象。第二首:“玉女投壶万籁清,风涛迭奏步虚声。月中亦有婵娟子,碧海亏盈夜夜情。”想象月亮的盈亏,不仅使得下面的世人有“月有阴晴圆缺”的感慨,善感的嫦娥,也会因此而有感慨。第五首:“长风吹梦落烟寰,花发扶桑色易殷。试上蓬山重回首,鲸波如带月如环。”诗人想象来到传说中的仙山蓬山,回首人寰,看到鲸鱼在海中的姿态,月亮绕行如环。所以,不仅是天上和地下的关系,而是有了三维空间:天上、地下、神山。
对于身份的有意识或潜意识的感受,是女子游仙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如江淑则《梦游仙》:
昨夜梦游仙,仙人远在蓬莱巅。海风茫茫波渺渺,身骑白鹤升青天。空中却见众仙子,佩玉锵锵彩云里。一时见我笑而起,酌以琼浆味如醴。使我胸次无氛埃,愿从执役登瑶台。瑶台红日从天来,四海光明万象开。清辉遥映三珠树,翡翠巢高鸾凤度。弹璈击磬移我情,忘却红尘无限事。仙人赠我驻颜丹,壶中日月殊尘寰。我亦相顾笑,就约栖云山。喜极仰天望,失足踏波浪。惊起三更露正长,拥衾抚枕生惆怅。

明清女子之游固然较之以往已经大大增多,但也还有不少人,或者自己不具备行旅的条件,无法出游;或者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无法尽情地游,因此,她们的心灵期待,往往也从别人的经历中体现出来,展现出另一种神游。如归懋仪《题玉桥五兄宛陵游草》:
青莲才绝世,鸿轩渺九州。
独爱青山色,言上谢公楼。
后来谁继踵,白云长悠悠。
余兄负奇气,雅嗜林泉幽。
……
迢递至宛陵,宛陵胜无俦。
溪水清且澈,百尺浮清鲦。
濯缨人不见,惟见双白鸥。
溪上敬亭山,山亭回复修。
落日樵响绝,飞鸟鸣相求。
名贤觞咏地,双垂南北楼。
南楼快已登,黄花当酒筹。
将毋仙人魄,云霄相劝酬。
是何登高期,适与九日谋。
北楼虽未至,胜概眼中收。
高吟江练句,如共元晖游。
云霞与水石,一一成清讴。
至今萧斋梦,犹绕宛陵洲。
我来泛琴水,虞山苍霭稠。
示我诗一帙,细字明银钩。
犹疑敬亭云,飘然落翠裯。
渔歌如可接,猿啸无时休。
梧桐橘柚句,邈焉媲前修。
宣城是一个诗的城市,前有谢朓等,后有李白等,都在这里留下了千古传诵的佳作。这首诗一开始就说,李白酷爱谢朓之诗,曾经登上谢公楼,写下了千古华章。“后来谁继踵,白云长悠悠”,江山有待,其玉桥五兄将继此诗坛盛事。于是泛舟清溪,登上敬亭山,造访名贤觞咏之地。特别写南北二楼。登上南楼,痛饮菊花酒;北楼虽然没有上去,但楼前盛概,一览无余,吟诵谢朓“澄江静如练”的名句,千古相接,心神俱醉,以至于“至今萧斋梦,犹绕宛陵洲”。玉桥的宛陵之情不仅其本人回味不已,诗人自己也是心驰神往。归懋仪本也是有着山水胜情的人,“我来泛琴水,虞山苍霭稠”。作为常熟人,她泛琴水,登虞山,显然未能有惬于心,吟诵五兄的诗,“犹疑敬亭云,飘然落翠裯”,显然极大地满足了她的山水之情,让她也跟着神游一番。她最终的评价是:“梧桐橘柚句,邈焉媲前修。” 梧桐橘柚,出自李白《秋登宣城谢朓北楼》:“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玉桥的诗是否能够媲美李白,姑且不论,但归懋仪从其诗中得到了极大的享受,却是毫无疑义的。
七 总结
到了清代,女性的生活空间不断扩大,闺阁女子以各种方式踏出闺门,给她们的诗歌创作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尤以表达行旅的作品最为突出。
行旅开阔了诗人们的眼界,无论是壮美还是秀美的风光,都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表现对象,但是,由于不少作家的行旅多是随宦,基本上并无选择道路的余地,因此,旅途中的艰难往往给她们的创作打下更深的烙印,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收获了奇僻的感受。至于战乱中或社会动荡中的流亡,则更作为独特的一笔,使得她们的行旅带有时代的印痕。
行旅,不仅是身体的行为,也是心灵的行为。尽管清代女性的生活空间确实有所扩大,但社会规范仍然对她们有所限制,因此,借助题画、游仙和梦境等神游的方式去释放情绪,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