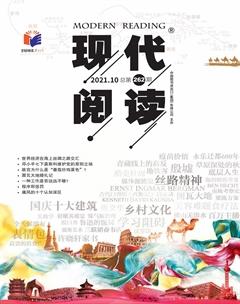永乐迁都600年,重塑近世中国政治格局
1421年2月1日,即明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永乐皇帝朱棣在奉天殿举行了盛大的朝贺仪式。自此而始,北京为京师,不称行在。然而,从“两京体制”到还都南京,再到定都北京,整个迁都过程历时近四十年才尘埃落定,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十七日,刚刚即位的宣德帝朱瞻基,决定派遣长弟郑王朱瞻埈去南京孝陵谒祭。行在礼部呈上的“郑王诣南京谒陵合行事宜”中,明确规定元旦、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皇太后圣节、中宫千秋节时要在本府拜呈表笺。同时限定南京各衙门的官员,只能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拜谒郑王。几乎将一年中各节日的事宜全部规划在内。由此看来,宣德帝并非是派郑王代替即位伊始的自己进行谒祭,而是起初就计划令郑王长期停留在南京。
半年前的三月,洪熙帝朱高炽接受臣下还都南京的提案,当初身为皇太子的宣德帝被派往南京留守谒祭孝陵。某种意义上讲,郑王谒陵可以视为此事的沿袭,可见当时先帝还都南京的决定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约束力。
随从郑王的官员,为丰城侯李贤和行在兵部尚书李庆。此前,随从皇太子即现在宣德帝的同样是此二人。当然,皇太子和亲王有着巨大差别,只因当时长男尚未出生,无法册立皇太子,选择长弟郑王前往南京应属妥当的安排。
但是,八月二十一日启程前往南京的郑王,在动身仅仅45天之后的十月四日,便接到召还北京的命令。宣德帝令随行官员中的一人,即行在兵部尚书李庆留在南京管辖兵部。比照设想郑王长期停留在南京的“合行事宜”,这一紧急决定难免给人留下唐突的印象。
宣德帝敕谕李庆留南京,理由是:“南京国家之根本,所系甚重,朕夙夜在念。必有心腹大臣居之。卿可留彼,专理兵部之事。”敕谕中如此叙述,标志着本应由皇族留守的都城南京降格为由大臣居守,地位明显降低。
朱元璋在金陵(南京)建立政权,在历代王朝中首次将国都设置于此以统治全国。后经靖难之役,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洪熙帝决定还都南京,初创期的明王朝就像钟摆一样,南北摇摆不定。有人称这种动摇为“第二次南北朝”。即10世纪以来,由于塞外各民族的崛起和统治的需要,所形成的南北分裂时代的遗制。南北分裂的形势,自唐王朝灭亡后历经三个半世纪,才由所谓的“征服王朝”元朝实现了统一。即便在元朝统治的90年间,仍然留有可以称为“南北朝的延长”这一分裂的实质。朱元璋政权定都南京,以北方为中心配置诸王并赋予军权,洪武初期,将开封设定为“北京”,在临濠(后称凤阳)建设“中都”,也正是因为分裂的实质仍然存续。
永乐帝决然迁都北京,是从汉族立场出发,谋求再次实现南北统一的举措。其结果,与经济重心向东南移动相反,在分裂时代实现扩张的中华世界的中心不得不北迁。永乐帝选择的是比分裂以前更加向北的移动,直接继承了蒙古皇帝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的“大都”。扩张后的中华世界不限于农耕社会,还包含了游牧社会,那么选择处于两种社会交界线上的北京作为首都就成为必然结果。然而,这种尝试的阻力非常巨大。从永乐元年(1403)創建两京体制起,到永乐十九年(1421)断然实行迁都,直至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定都北京,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岁月。在北京的地位尚未稳固之际,宣德帝将郑王召回北京,废止皇族留守南京的制度,标志着永乐初年以来的两京体制,特别是为皇帝巡幸北京和皇太子监国南京的南北分裂的遗制画上了句号。政治的权力与象征,由南北两个焦点构成的椭圆形,重新归结为只有一个焦点的圆形。至此,明王朝进入守成期。
由于永乐十九年紫禁城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烧毁的严重事态,臣下们提出了对迁都的批判。令人意外的是,大多数上奏是指摘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导致漕运的艰难,并没出现拒绝迁都的意见。经过争论和摇摆,朝野形成了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相互补充的分离,中国近世社会的框架就此完成。
(摘自外文出版社《明代迁都北京研究:近世中国的首都迁移》 作者:[日]新宫学 译者:贾临宇 董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