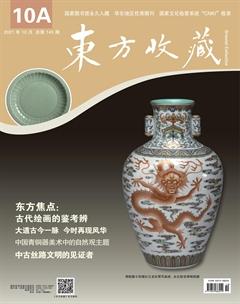仇英粗笔水墨画的研究与鉴定
毛代炜 陶李



仇英(约1498—约1552),字实父,号十洲,原籍江苏太仓。史载其“所出微,尝执事丹青”,说明他出身不高,可能当过画工。目前,仇英存世的绘画作品以设色工笔绘画为主,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玉洞仙源图》轴(图1)、天津博物馆所藏《桃源仙境图》轴(图2)等都是其代表作品,而纸本水墨绘画则较为少见。仇英的水墨绘画有两种面目,其一为南宋院体风格的粗笔水墨绘画,其二为兼工带写的设色细笔绘画。现存的粗笔绘画作品有两幅最具有代表性,分别是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下眠琴图》和藏于荣宝斋的《松溪高士图》。对这两幅绘画进行对比鉴定,可以进一步拓宽对仇英艺术风格的认识。
一、院体绘画的传承
“行家”与“利家”之说起源于宋代,赵孟頫则将其引入绘画领域。此后,水墨画逐渐成为了文人墨客表达心境和抒发情感的主要艺术形式。董其昌继承这一理论,在《画禅室随笔》中提出了“南北宗论”,并将仇英归类为北宗画家,而北宗画家中的李唐和马远是“院体画”的代表人物。李唐曾先后任职于宋徽宗和宋高宗的画院,其人物画特点是以细笔画面部、粗笔描衣纹(图3)。而马远作为李唐的学生,则继承了李唐发明的大斧劈皴法,史载其“岩壑用焦墨,作树石、枝叶、夹笔石皆方硬,以大斧劈带水墨皴,甚古”(图4)。从构图的角度来看,南宋时期的院体画家一改北宋范宽式的全景构图和高山巨树为画面中心的布景方法,采用“边角式”的构图方式,图像中的山石树木自边角伸出部分,呈“三角形构图”;从绘画技法上看,主要表現为山石多用大、小斧劈皴来表现山石嶙峋质感,粗笔浓墨画轮廓;树木则用焦墨表现树皮粗粝,枝干线条遒劲,转折尖锐;人物衣纹多用钉头鼠尾描和折芦描,起落笔之处方折突出,表现质感粗糙和褶皱堆叠。这种绘画不仅在视觉上极具表现力,而且十分考验画家的写生和造型能力。
元代初年,由于赵孟頫“复古论”的巨大影响,南宋院体画一度式微,直至明代“浙派”的崛起,院体绘画才重新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中。戴进是“浙派”的创始人,其绘画风格“纯以宋院本为法,精工毫素,魄力甚伟”(图5),董其昌亦赞“国朝画史以戴文进为大家”。吴伟师从戴进,继承了戴进的院体画风格并成为“江夏派”的代表,他的绘画笔力雄健、笔墨粗犷、造型精确(图6)。二人都曾任职于皇家画院,对明代宫廷绘画产生巨大影响,吕纪、林良等人的绘画作品都带有鲜明的院体绘画特征。
而在随后崛起的吴门画派中,“行利皆擅”的画家当属唐寅(图7)和仇英。据记载,唐寅“画法受之东村”,而仇英也“少师东村周君臣”。周臣,字舜卿,号东村,姑苏人。史载其“法宋人,峦头崚嶒多似李唐笔,其学马、夏者当与国初戴静庵并駈(驱),亦院体中之高手也。”观其绘画面目为院体风格,人物衣纹和山石树木的线条也以折芦描、钉头鼠尾描和乱柴描为主(图8)。董其昌虽贬低“北宗”,但是对仇英评价甚高,认为自李昭道之后“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就连文徵明亦“不能不逊仇氏”。
二、两幅绘画的鉴定与研究
1.《柳下眠琴图》(图9)
此图原为虚斋旧藏,庞元济曾记载于《虚斋名画录》 中,尺寸大小基本与记载中一致。画面中主要人物为一文士和其仆从,布景为山石和粗柳。文士头戴葛巾,斜倚古琴,卧于土坡上,面前展开一手卷。坡右侧有一僮仆负囊左视文士。画面右侧中部有作者楷书本款“仇英实父制”,款下有“仇英实父”白文印、“桃花﨩(岛)里人家”白文印各一枚。
本幅作品虽为仇英少见的粗笔绘画,但画面各方面特征与仇英的工笔绘画作品特征有相似之处。画中人物身体比例比较准确、造型自然,轮廓线条下笔迅速有力,体现出画家扎实的写生功力;衣纹以淡墨的镢头钉描和钉头鼠尾描为主,间有粗笔短线段,表现衣料的质地较粗,体现了文士的清贫。尤其是人物的面部刻画精细,人物区别度很高。主人身份的文士国字方脸,额宽面阔,双目有神,鬓须长垂,口鼻端正,与上海博物馆藏另一幅仇英的细笔设色绘画《右军书扇图》的人物面部相似(图10)。而僮仆的面部则瘦削突出,筋骨毕现,表情愁苦,穿粗布麻衣,腰系草绳,脚穿草鞋,与主人的形象呈现出鲜明对比。
作为背景的树石未现全貌,只从侧面和边角出现,呈现稳定的三角形构图,是典型的院体绘画的边角山水构图。远山以淡墨染出,近处山石则用粗笔画出轮廓,淡墨染底,上覆浓墨,侧面多以小斧劈皴为主。柳树以粗笔浓墨画出树干,又用浓墨破淡墨画出树皮,尤其是皴法的行笔方向与树干轮廓成斜向相交,给人以树干虬曲向上生长的视觉效果;柳树枝杈不勾轮廓,直接用淡墨画出,粗笔雄健,细笔轻盈,从枯笔可见行笔迅速;柳叶则以细笔写成,成团有序分布,密而不乱,取势各异,仿佛随风飘动。
仇英文化水平不高,落款多只做穷款。仇英的落款一般有三个特征:其一为仇英没有专门的书法用笔,落款多用绘画用笔,因此字迹的笔画粗细与书法家写的字不同;其二为“英”字中的“丿”不是一笔写成,而是分成两笔,所以“丨”与“丿”之间断开导致相接处突出;其三为“實”字中的“母”两边不出头,写成“田”字。此图中的落款均符合这三个特征,因此可以认定是仇英的亲笔款(图11)。
总结以上特征可以看出,本幅《柳下眠琴图》虽是纸本水墨绘画,但是仍符合仇英作品的各项特征。鉴于其皴法和墨法都已经向文人画靠拢,且书法水平高于早期工笔画的落款水平,因此可断定这幅作品是仇英中年之后的成熟作品,与唐寅的某些作品风格趋同,也可能是受到文徵明粗笔绘画的影响。
2.《松溪高士图》(图12)
此幅《松溪高士图》中一文士左依凭几,盘腿而坐,右手自然抬起,一童仆蹲坐右侧收拾包裹。画面背景为远山、巨石,一松树枝杈自右侧伸出,末端挂有藤蔓。画面右下方有作者落款“仇英实父戏墨”,并有白文印两枚“仇生实父”“桃花隝(岛)里人家”。
图中文士方面大耳,头裹发巾,神态平静祥和;四肢比例协调,向左斜依凭几。人物衣纹多方折,墨色较浅,行笔迅速,线条短促有力,类似于用毛笔进行速写,属于减笔描中的钉头鼠尾描和镢头钉描,表现衣纹的褶皱感。童仆在旁整理书简,面带愁容;衣纹用墨较重,线条描法与文士相似。这两人与《柳下眠琴图》中两人的线条描法、面部神态和身体姿态几乎相同,因此断定应为同一人所作(图13)。
背景中的松树和巨石的一部分从画的边角进入画中,与《柳下眠琴图》相同,呈三角形构图。松树用笔粗犷,轮廓线条遒劲刚硬,行笔迅速,枝干转折之棱角分明,树皮用淡墨涂皴,间杂浓墨;近景石块石则粗笔勾画轮廓,小斧劈皴表现侧面,墨色浓淡对比明显。点苔下笔有力,多为长点或方点,用墨较重。
本幅作品的落款为少见的“戏墨”,应为仇英仿效文人画的游戏之作。落款的风格与仇英本人的题款风格相符合,而且“仇英实父”和“桃花﨩(岛)里人家”两方印章相同。书法特征与另一幅《募驴图》相比较可以看出,“仇”字笔画粗细分布一致,“英”字“艹”回笔路径相同,“丨”与“丿”相接处突出,“實”字中间为“田”,而“父”字捺画一致。“戲”字与《募驴图》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细笔绘画《蕉荫结夏图》中的“戏”几乎相同(图14)。从书法风格和印章的磨损程度来看,《松溪高士图》的创作时间应更晚一些,应是仇英本款无疑。
三、相关作品的研究与鉴定
南朝宗炳提出绘画要“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其后谢赫提出了“绘画六法”,其中有“应物象形”一法,系统准确地指出造型是绘画的基本要素之一,元代汤垕也指出“人物于画,最为难工”。但古代社会文人士大夫掌握话语权,进而主导了绘画风格的走向。与职业画家相比,文人的文化水平较高,将诗书画印相结合,完善了中国绘画的形式,却缺乏必要的写生造型技巧。所以在文人画中,“气韵生动”被拔高,尤以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影响甚广,而“应物象形”则受到轻视,尤其是董其昌认为 “北宗”绘画“非吾辈所当学”。如倪瓒和黄公望,其作品只有以树石为主题的水墨山水画;沈周所画人物用笔极简,属于几乎没有面目的点景人物(图15);文徵明的山水画清雅秀丽,但其画中多有人物比例失衡、器物造型失真的现象(图16);“四王”以山水画著称,只有以曾鲸为代表的“波臣派”人物画和以恽寿平家族为代表的没骨花卉能做到形神俱备。这对中国古代绘画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传统美术中的写真造型艺术从此一蹶不振。
在全能型艺术家赵孟頫之后,能做到形神兼备的文人画家屈指可数。但这无意间也造就了“行利合流”的现象,诸多职业画家创作了一大批既有生动的写实技巧,又融“气韵”于画中的作品,代表人物有元代的王渊、边鲁、陈林和张中,明代的代表人物则是戴进和仇英。在对此类画家的作品进行鉴定之时要点如下:
1. 其作品风格承接南宋院体画风格。南宋的院体绘画较之北宋院体画虽布局有变,但仍以北宋的写实绘画为基础。而以仇英为代表的职业画家,多出身于画工,其职业要求即是以“应物象形”为首要条件。画家能够运用精确的写生技法描绘人物的面部、花卉和禽鸟,用流畅的速写技能描绘人物的服饰、树木和巨石。描法以钉头鼠尾描、镢头钉描和折芦描为主,皴法以大、小斧劈皴为主。
2.作品风格文雅,格调高古。仇英并非一般的画匠,其曾长期临摹古代绘画,并与文人墨客多有交往,因此其作品既造型准确又不失古典文雅之气。民间仿造者无此条件,因此作伪的质量较低,目前所见多为工笔重彩的“苏州片”仿品,如国内公私收藏机构所藏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不下十数件,且均自认为真迹,一時间难以厘清。
3. 落款具有个人特色,作伪者无法模仿。职业画家一般书法水平不高,因此在画面上的落款多以篆隶作穷款,以描代写,内容为字号、年款、创作时间和地点等。仇英早年多用画笔描摹篆书款或隶书款,不能称之为书法。但这两幅水墨作品以楷书落款,书法水平较之早年有所提高,可能是因为常年书写,熟能生巧,且仍以绘画用笔书写落款。此种书写习惯独具特色,可致擅画者难仿字,擅书者难摹画,也算是一种独家防伪的方式。
4. 此类作品和仇英的工笔画相比,用笔更强调书写性,提按变化更丰富,中锋侧锋并用,干湿浓淡变化自然,“墨分五色”的理念得到了较充分的呈现,从而使作品中的传统笔墨的韵味和魅力得到了更自由的张扬。显然这也是深受赵孟頫“书画同源”理论的影响,因此仇英这类风格的作品十分珍贵。
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风潮席卷欧洲。虽然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西方油画也开始通过宗教绘画的形式传入我国,但是传统的审美观念根深蒂固,导致中国的艺术界轻视西方美术的造型艺术,认为其只是徒具外形的“工匠画”。而当时西方的传教士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绘画的不足之处:“中国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貌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像。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与生人亡异也。”直到清末康有为等人出国游历之后,亲见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巨作,认识到了西方美术的科学之处,才开始下决心走上振兴传统美术之路。而通过对仇英作品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正确地认识传统美术自身的可塑性和拓展性。
以仇英为代表的传统职业画家能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准确地融自身的绘画技能与主流审美观于一炉,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美术的旺盛生命力的表现。面对西方的科学美术,既不宜夜郎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若能通过科学的鉴定方法,还原仇英这位艺术巨匠的完整面目,当足以为美术史增补新的材料,也可以让更多人全面地了解仇英,了解传统的中国美术,振奋民族自信,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