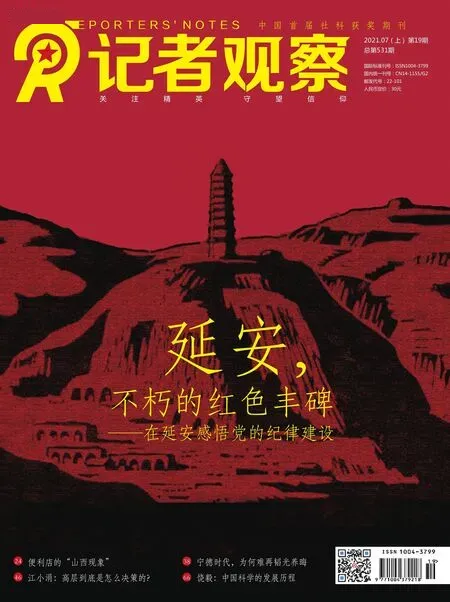人类瘟疫斗争史:科学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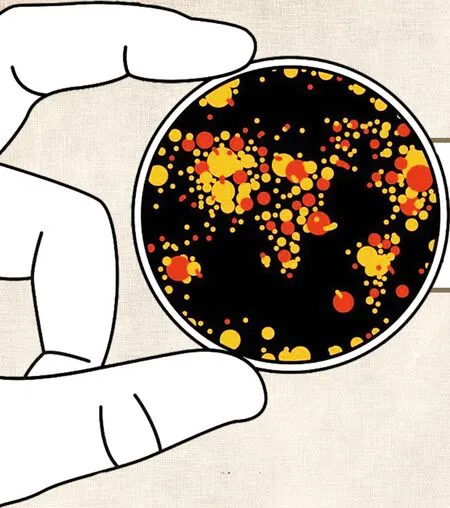
2020年冬春是一个值得人类铭记的时刻,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它给我们带来的伤痛将永远成为我们反思与重建的印记。当疫情袭卷而来,城市就像座荒岛。在人人自危的底色之上,潜伏着恐慌与顽强。无数人意识到,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人类是多么渺小。
千百年来,放眼全球,瘟疫是最大的人类杀手,没有之一。确实,纵观人类文明史,瘟疫带来的恐慌与灾难几乎贯穿始终,无论是古希腊的“雅典鼠疫”、古代中国的“建安大疫”,还是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这些瘟疫无一不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由瘟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比战争、饥荒还多。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血和泪的瘟疫抗争史。
人间炼狱
多灾多难的时候往往尽显人间百态。翻开历史,有过记载的严重瘟疫,席卷过的地方几乎都成了人间炼狱。
公元前430年,一场大瘟疫暴发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城邦,这是历史上首次有明确纪年的瘟疫。几乎在顷刻之间,从海边到内陆,从城镇到乡村,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死亡的气息蔓延在雅典的每一个角落,一度被视为骄傲的雅典社会治理体系趋于崩溃。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无限悲痛地记录了当时的惨剧:“有些病人裸着身体在街上游荡,寻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于此病,吃了躺得到处都是人尸的乌鸦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这场瘟疫持续了三年时间,带走了一半雅典人,死亡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连执政官伯里克利都在这场瘟疫中病死,整个城邦元气大伤,萎靡不振。甚至在后来与斯巴达的战争中也连连失利,最终输掉了这场决定雅典命运的战争。

黑死病油画《死神的胜利》 彼得·勃鲁盖尔

黑死病相关油画
纵观中国历史,瘟疫也几度肆虐,史书上每隔几页就写着“大疫”二字。而发生在中国东汉末年的大瘟疫,死伤更为惨重。古语有言:“大战之后有大疫。”三国征战不休,但战争带来的伤亡远远小于瘟疫,“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07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建安大瘟疫”。著名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早逝,其余五人全部死于这场瘟疫。当时,曹丕和曹植均记载了此事,曹丕痛悼:“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植更写过一篇《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统计是1607万多户,人口是5006万。到三国末年,魏蜀吴合计户数只余149万多户,人口仅余560万。
瘟疫从来不止一种,席卷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最恐怖瘟疫当属黑死病,即腺鼠疫,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目前最严重的瘟疫。黑死病蔓延最疯狂的年代是14世纪。1346年,蒙古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咖法,当时久攻不下,蒙古军队又有人患了鼠疫。于是他们用抛石机将一具具鼠疫尸体抛进城内和河道里。短短几年,这些依托老鼠而蔓延的传染病,通过跳蚤作为宿主,在大街小巷里迅速传开。欧洲国家全部沦陷,没有一个例外,社会秩序崩塌。祸不单行的是,当时欧洲宗教认为猫和女巫一样,都是邪恶化身,便屠杀了所有城市的猫。没有了天敌的老鼠,繁衍速度更快。薄伽丘在《十日谈》里描述:“有人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地在自己家中咽气,直到尸体发出了腐烂臭味,才被邻居们发现。”中了鼠疫者,基本三天暴毙,没有什么治疗手段。欧洲为此损失2500万人。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随之而来的还有天花、伤寒、霍乱和“西班牙大流感”等等一系列传染性疾病的大流行。但从古代到中世纪,再从中世纪到近现代,人类之所以能在瘟疫的肆虐下持续繁衍、生生不息,依赖的除了生育能力还有不屈的信念及强大的科技。
救世良药
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可以说是一部社会治理的进化史。从束手无策到井然有序,“隔离、疫苗和口罩”是抗击疫情的三大功臣。
雅典瘟疫被一位名叫希波克拉底的古希腊医生所终结,经过多次的试验和总结,他发现那些造成瘟疫的病毒怕火,于是雅典人在公共场所燃烧带有各种植物香料的火堆,这些燃烧的火堆驱除掉了空气中的病毒,瘟疫终于得到了控制。建安大疫中,张仲景写下了《伤寒论杂病论》,创造性地确立了对瘟疫的辩证施治原则。而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也随着人们免疫的建立、卫生习惯的改善和严厉的隔离制度的实施得以结束。以仅限的医学与科学水平对抗瘟疫,这是前人能够做出的最大努力。
黑死病来临时,“隔离”成为欧洲各国开始采取的措施。根据当时各国颁布的命令,当一个城市出现瘟疫时,首先要采取的措施就是隔离,甚至封城,城市以街道为基本单位,安排专人负责。在隔离五六天后,开始对每所房子进行清理和消毒。这期间诞生在意大利的“医学隔离”一词,意指通过隔离有效断绝病源输入,被后世视为防疫典范。在公共卫生史上,也有“伤寒玛丽”这一经典隔离案例。玛丽携带有伤寒杆菌,相继传染了52人,其中7人死亡。因此她被武力隔离在纽约附近的北兄弟岛上的一个传染病房。1938年,玛丽去世。在玛丽69岁的生命中,有27年是在被隔离。
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还是一部医学进步史。过去数千年来,人们对抗瘟疫,治疗疾病,用的是望闻问切,用的是经验相传,用的是不断试错,每种药物研发、每个疾病被解决的背后,都意味着海量的试错成本。经历了古代放血、灌肠、水银熏蒸、“种人痘”的愚昧,近代消毒、麻醉技术的探索和现代的基因研究,无数生物学家和医生摸索着黑暗前行,前赴后继。


AI算法检测疑似病例

健康码防疫
在人类与天花的抗争过程中,治疗手段从中国古代的“人痘”疗法到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明的“牛痘”疗法,现代医学最为重要的免疫学概念横空出世,这一概念直接催生了疫苗。终结一战的“西班牙大流感”结束8年后,青霉素问世,因流感引发的肺炎不再无药可医。在对抗霍乱的过程中,约翰·雪诺开启的流行病学成为日后预防医学的基础,而从疫情中诞生的公共卫生理念和由此引发的公共卫生运动推动着欧洲乃至世界公卫现代化的步伐,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大自然是最具创意的“药学家”,它造就的金鸡纳霜、青蒿素,为人类对抗疟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疟原虫也在不断产生抗药性。百年来,人们一次次寻找新的抗疟药,又随着疟原虫抗药性的进化,重新寻找新的抗疟元素,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青蒿素提取成功。随后,耐青蒿素疟疾开始出现,人类又开始思考如何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直到现在,斗争仍在持续。

“西班牙大流感”

“伤寒玛丽”
其实,除了不断探寻研究疫苗和药物,人类还曾经寻找其他防疫手段,口罩就是最著名的发明。从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的肺鼠疫到“西班牙大流感”,在伍连德的推动下,从中国到世界,口罩逐渐与疫情防治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战友”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
历史向前
每一次大瘟疫的流行,往往伴随着人类发展的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往往比枪炮、战争还要剧烈和深刻。15世纪末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全球化探索,天花、疟疾、霍乱等瘟疫也以船为媒,从北美到非洲,迅速在全世界扩展。在这些“战疫”中,不仅仅有关于毁灭、死亡和绝望的故事,更有关于科学和探索的珍贵记忆。瘟疫向后,历史向前。历史总有相似场景,但绝非简单的重复。每一代人都在挑战着所处文明时代的能力极限,尽可能让社会资源的配置跑赢病毒的扩散。是科技让这种抗争变得更有意义。
当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时。颁发健康证、建立隔离区、记录死亡人数、组织慈善活动、丧葬事宜和城市治安……西方在这场对抗瘟疫的过程中,孕育出有独立自治能力的公民社会雏形。在700年后的今天,欧洲中世纪的健康证被发端于中国杭州余杭区的二维码取代,隔离也早已不是简单的画地为牢。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社会按下暂停键的同时,也倒逼着人类用更高效技术手段和社会组织方式,去抵御瘟疫这个千年宿敌的侵袭。在任何时代,战胜瘟疫都没有捷径,但在新时代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数字化治理则是迄今为止疫情能给人们的最大启示。
当中国大面积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时,阿里巴巴推出的健康码,是整个疫情期间实用性最强、覆盖最广、传播速度最快的数字化工具。一个二维码解决了中国1/3城市、数亿人健康信息申报的问题,这背后的数字化能量和治理效率令人震惊。而健康码只是“数字安全城墙”中的九牛一毛。免费服务全国27省份的达摩院智能疫情机器人、新冠肺炎CT影像识别准确率达96%的AI诊断技术、可以对疫情高危人群的预警和追踪的AI“防疫师”……数字化治理带来的创新创造,在疫情期间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健康码”。
面对疫情,隔离只是最基本的防护手段,疫苗才是关键。各大国纷纷展开疫苗研发,而贫穷弱小的国家只能在大国博弈间嗷嗷待哺。截止2020年7月20日,全球当前有大约250种候选新冠病毒疫苗在研发中,其中至少有17种疫苗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走在前列,甚至已经转向了当下最前沿的生物计算领域,往破解人体蛋白质折叠秘密、解开人体疾病的机制等方向探索。而这背后较量的除了大国实力,更是新一轮的科技竞赛。
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写道:“是技术将我们与我们拥有了5万年甚至更久的那种生活方式分开了。技术无可比拟地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它创造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存在方式。”毫无疑问,瘟疫灾难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科学的经验和技术,或许可以让我们找到与世界相处的更好方式。
人类和瘟疫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从用火烧死病毒到疫苗的批量生产,从对人体的一无所知到“玩转”基因,只有经历愚昧才会相信科技。我们普通人身处在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所享受到的所有医疗水平的进步,背后都是前人在疾病防治上的无数改进和变革。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往前探索,永不停歇。这正是科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