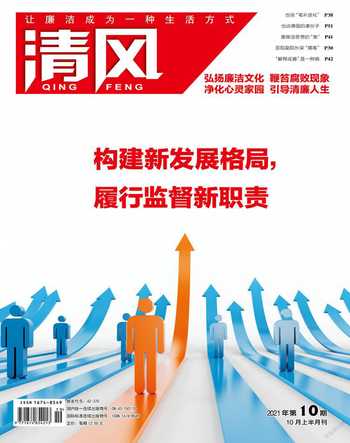毛泽东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贡献
彭金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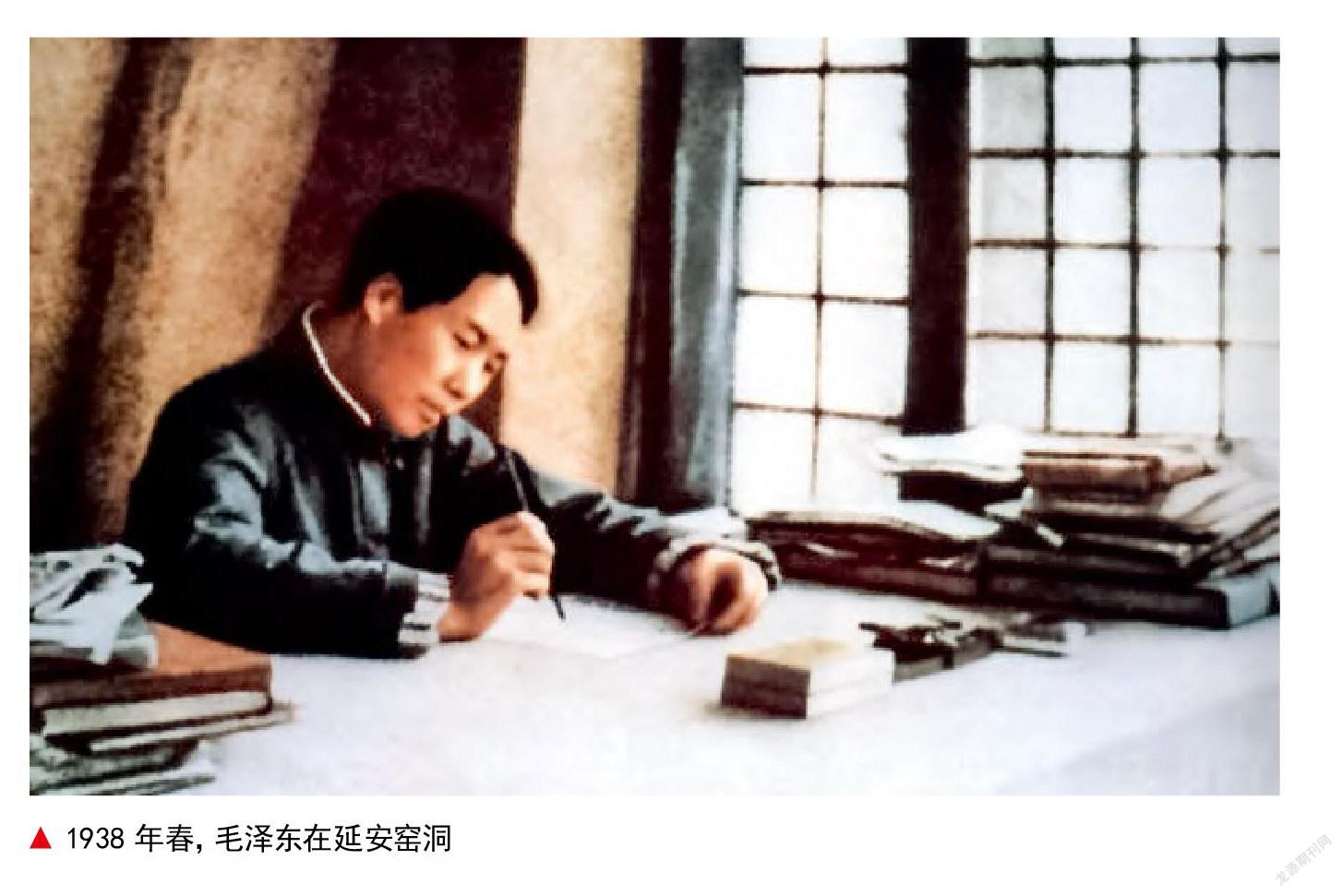
当前,全党上下都在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并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一贯重视研究党的历史,重视用党史上的经验教训教育党员干部群众。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多,比如奠定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理论基础,收集整理了党的早期历史文献资料,发起并领导了第一次党史学习教育,对党史做了一系列极富价值的论述等等,对我们当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奠定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理论基础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一系列著述、讲话和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对党史学习教育指导性很强的理论和观点,奠定了党史学习教育的理论基础。
一是撰写“两论”,客观上奠定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哲学基础。“两论”即《实践论》与《矛盾论》,是毛泽东于1937年7月和8月间先后撰写的两篇哲学论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之作”。毛泽东对党内普遍存在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的学风十分痛心,他写作“两论”的最初目的是揭露并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用生动活泼而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原理,揭露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在哲学根源上的错误,对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系统提出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内容、方法和目标要求。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了学习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即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哪一步,不是个别细节,但重点是路线和政策。此外,还要研究与党的历史相关联的古今中外各种“历史遗产”,包括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史,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历史等等。关于学习研究的方法,毛泽东强调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他列举了古今中外法、综合分析法、辩证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还原历史法。毛泽东还提出了延安时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概括起来讲,就是要使全党对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明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同時要加强党外宣传,使全国民众认识到党在中国革命的中坚地位;就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三是强调了教育形式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多个场合谈到了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的问题,提出了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结合,文艺要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为政治服务;不仅仅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是宣传家,一切工作干部都是宣传家;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观点。党史学习教育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受众是全体党员干部,他们文化程度、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不一,毛泽东强调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分类施教,教育形式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不应该是形式生硬、内容空洞的党八股。
亲自主持党史文献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
毛泽东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编辑整理,并为此做过许多工作。红军初建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就文献资料搜集工作向前委秘书处和其他红军部队签发指示文件。1930年12月28日,正当第一次反“围剿”紧张时刻,毛泽东与朱德签发军令,命令连、营、团把所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一律集中到师部,防止散失。在红军长征途中,每打下一个县城,他就亲自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去搜寻有关图书文献资料。1949年9月上海刚解放不久,原先隐蔽在上海负责地下党中央文库工作的陈来生,将自己保存的104包计15000余件珍贵的党史文献资料上交党中央,毛泽东当即亲自批示电文嘉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与周恩来又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将存放在苏联的原共产国际保存的一批重要的中共党史文献资料运回北京保存研究。最能反映毛泽东重视党史文献资料工作的几个历史片段,是延安时期他亲自主持编辑3本“党书”;建国后又亲自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版4卷本《毛泽东选集》。
3本“党书”为3部党的文献资料集,即《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编辑“党书”起因是为党的七大准备会议材料,这个过程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3年。原本分头负责收集工作的人很多,导致这项工作推进缓慢。于是毛泽东决定直接负责此事。在不断进行的资料收集过程中,毛泽东就着手进行编辑整理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六大以来》汇集了各类文章519篇,280余万字,实际上有汇集本与选集本两种。《六大以来》编辑出版以后,大家兴趣倍增,纷纷要求像《六大以来》一样编辑一本六大以前的文献资料集,供研究党史使用。于是,毛泽东在1942年年初开始编辑《六大以前》。考虑到两本书篇幅浩大,通读不易,毛泽东于1943年从中挑选出最能代表各个时期党内路线斗争的文献,编成《两条路线》。当时,在延安及各根据地的高级干部几乎人手一套《两条路线》,充分反映了党内第一次党史学习教育的盛况。《六大以来》等3本“党书”是批判“左”倾错误路线的有力论据,毛泽东后来说:“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
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已经出现5个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但还没有一部由中央组织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供党员干部学习使用。新中国成立后,此事显得更加迫切。此外,苏联也希望中共中央尽快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其实,1948年夏天在西北坡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酝酿这项工作了,但因公务实在繁忙,一拖再拖。1951年3月,毛泽东与3位秘书在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又称“小白楼”)内集中修改审定《毛泽东选集》前3卷,为期两个月。这项工作从头至尾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于1951年10月,第一次发行量达106.6万册,成为举国欢庆的一件大事。不久,第2卷与第3卷也先后于次年4月及1953年4月出版,但并没有接着出第4卷,这是时机还不成熟的考虑,也反映了毛泽东惯有的审慎做派。直到1960年年初,毛泽东才开始决定编辑出版第4卷。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完成出版,至此,建国后第1版《毛泽东选集》1~4卷全部出齐。《毛泽东选集》充分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发展、成熟到进一步发展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经典著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毛泽东选集》中绝大部分文章都是说史论理、史论结合,是学习研究党史的经典教材。
对党史做过许多有价值的论述
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述党的历史,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做过论述,对重要人物做过客观评价,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进行过系统归纳总结。这些论述高屋建瓴、实事求是、一针见血,既是历史本身,又是我们史海探宝的重要工具。
毛泽东非常看重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革命和历史进程的影响,经常在各种场合提及和回顧。包括重要历史运动和历史现象、重要会议、重大战争与战役等。他在论述重要历史运动和历史现象时,看重阐述思想文化意义,比如,他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反对封建文化的文化革命;他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他在论述重要会议时,看重会议对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作用。比如,他认为遵义会议是我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的开始;认为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赢得了大好局面,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在论述重要战争战役的时候,他看重论述其战略意义,他讴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他系统论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胜利必将属于中国,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而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认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是人民的胜利;认为抗美援朝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赢得了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等等。这些论述都是建立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十分精辟。
毛泽东对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做过评价,客观公正。一是为对革命先行者和元勋的推崇缅怀。他曾两次在纪念孙中山的会议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孙中山是一个谦虚的人,全心全意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追忆李大钊是他“真正的老师”。二是对革命战友和部下的赞赏与鞭策。他评价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是“人民的光荣”;评价周恩来有“吐握之劳”;称赞邓小平“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认为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称赞习仲勋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等等。三是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深刻批判,包括陈独秀、王明、博古、张国焘等,主要是集中在“左”、右倾错误路线方面。在批判的同时,他也指出不要一切都否定。如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这些评价客观公正,是我们学习研究党史的重要线索,又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可供借鉴的方法。
(作者单位系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